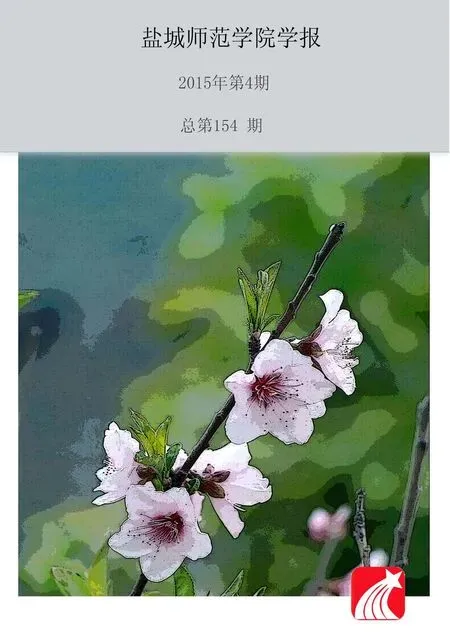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
张兴龙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
张兴龙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梳理了长三角城市群概念生成的理论源头与时代沿革,界定了戈特曼世界级大都市带语境下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具体内涵,厘清了明清以苏州为中心的“八府一州”城市群积淀的物质文化资源,阐述了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类型及构成特点。指出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陷入的困境,揭示了物质文化资源“不设防”的表层困境背后,隐藏着“伪设防”导致的“二次伤害”与“开发性破坏”导致的“第二种濒危”的深层困境。
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八府一州”;“开发性破坏”
对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研究,首先需要从学理上解决两个逻辑命题:一是如何界定长三角城市群概念,或者说,长三角城市群究竟包括哪些城市;二是当代语境下的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阐释的可能性何在。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界定及物质文化资源阐释的可能性
首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长三角城市群概念被国内学界广泛运用,但是,这个城市群究竟指代哪些城市,仍然显得过于宽泛和粗放。按照维柯《新科学》一书的观点,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的本质,不妨从概念生成的理论源头与时代沿革上追溯。
一方面,从概念生成的理论源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概念是西方“大都市带”、“都市群”理论与国内“长三角”、“长三角经济圈”嫁接、延伸与再创造的产物。1976年,戈特曼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一文,首次提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是世界上六大都市带之一[1]。戈特曼提出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长三角”、“长三角经济圈”,在地理区位、主要城市上存在着明显的重叠或交叉关系,特别是“都市带”的概念与国家提出的建设长三角“大都市圈”、“世界级城市群”规划理念一致,由此被国内普遍当作长三角城市群概念的理论源头。
另一方面,从概念内涵的历史沿革上看,国内学界提出的长三角城市群,经历了从区域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圈,向大都市带意义上的“世界级城市群”的转变,其指代的具体城市随着国家行政规划、经济政策的推进而不断变化。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当时的经济圈城市主要指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五个城市。1993年,上海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的战略构想,沿用20多年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正式变为城市群概念,城市群除了包括长三角经济圈的五个城市,还有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等共14个城市。随着1996年地级市泰州的设置,以及2003年台州市进入长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又发展到16个[2]。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该文件首次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26市,提出把长三角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3]。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长三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依据《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世界级城市群”[4]。
那么,长三角城市群究竟指代哪些城市呢?从国家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似乎就是苏、浙、沪全境内的26市。但是,这种想法实际上混淆了“长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密集城市群”与“大都市带”等概念之间的差异。按照戈特曼对大都市带的界定,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本质上属于世界级大都市带,而大都市带的形成至少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城市群内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且通常在都市带内保持着高频繁的通勤;二是城市群内有大量的乡村非农人口;三是城市群内的人口集中和密集主要表现为经济机遇和巨大财富的聚集,而并非仅仅是人口居住的密度。另外,大都市带内的城市经济主要依靠智慧来发展,有别于传统城市产业[5]。从这些特征看,苏、浙、沪全境内26个城市在流动人口的通勤频率、乡村非农业人口的规模比例、人口密集程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均不具备大都市带的特征。因此,长三角城市群指苏、沪、浙全境内26个城市的说法,只是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密集的一种泛称,与戈特曼世界级大都市带语境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有着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长三角城市群在30多年内从最初的五个“增容”到26个,覆盖的地理空间从长江下游的以上海为中心、太湖流域为主体的“小长三角”,逐渐扩展到苏、沪、浙全境的“泛长三角”,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包括“内核区”、“辐射区”和“泛化区”的特殊结构:一是以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五个“点状”城市为“元结构”的三角状区域,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内核区”,长三角城市群此后的历次“增容”,都是以此为起点再对外扩张。二是以16个城市“连点成线”搭建出来的“条状”沿线密集的城市带,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的“辐射区”。这个区域与苏南、浙北这一传统的长江三角洲的地理区位基本吻合。三是以26个城市“从线到面”共建的庞大城市群落,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泛化区”。本区域内的苏北和浙南的城市,与真正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相距甚远,属于传统长三角地区向外溢出的部分。
综上所述,以16个城市组建的“辐射区”是长三角城市群最稳定的区域,属于戈特曼世界级大都市带意义上的城市群。一方面,当代语境下的长三角城市群概念的出现,正好始于16个城市从“毫无瓜葛”到“抱团组队”的特殊历史区间上。另一方面,较之“内核区”城市之间联系紧密但数量过少,“泛化区”城市数量较多但联系疏松、差异较大,“辐射区”城市群数量多、联系紧,区域文化精神的同构性、相通性明显,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特别是主要城市之间流动人口的通勤频率、乡村非农业人口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方式,也更接近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特征。因而“以16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框架一直保持稳定,并受到普遍的认可”[6]。
其次,就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研究的可行性而言,如果对16个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进行追溯和还原,那么就会发现“它的核心仍是明清时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6]。在地理位置上,当代语境下的长三角城市群与明清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几乎重叠。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7]
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地区经济最发达、形态最成熟、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市群,应天(今南京)、杭州、苏州等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构成了城市群的一级城市;松江、嘉兴、湖州、常州、镇江等以经济繁荣著称的城市,是城市群的二级城市;在一、二级城市周边地区密布的盛泽、栖塘、硖石等无数市镇、草市,成为联系都市与乡村经济网络纽带的三级城市。虽然“八府一州”城市群并非铁板一块,同一等级城市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但是,就大都市、大城市、市镇绵延连缀起来的都市群落整体状况而言,它们在经济结构、空间格局、商业市场、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等方面,仍显示着与当时非城市形态区域迥异的特点,又与今天长三角都市化进程极其相似,“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都十分接近”[8]。
由此可知,当代语境下的长三角城市群与明清历史上“八府一州”城市群有着血脉纽带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八府一州”就是长三角城市群在古代中国的成熟形态,长三角城市群则是古代中国城市群在当代获得新的生命形态,其胚胎早在明清“八府一州”的发展中就已开始孕育[9]。太湖流域经济区、城市群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拥有极为丰厚的城市文化资源,而对长三角城市群文化资源的梳理及其物质文化资源的阐释,也应以此作为对象。这既为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阐释提供了可能,也使得这种阐释显得十分必要。
二、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类型与构成特点
文化资源是以“文化”为生产对象、以创意为主要工具、以创造经济产值为最终目标的生产资料,在文化产业链中,它综合了保护、开发与再创造多种手段。城市文化资源则是文化资源的城市形态,从资源分布的空间形态上看,城市文化资源存在于城市空间,有别于乡村文化资源;从资源所处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上看,按照斯宾格勒的城市是人类文明高级形态的观点,城市文化资源属于人类文化资源的更高逻辑环节。城市物质文化资源是城市文化资源的基础与代表,对它与城市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及自身的构成,可以借助西方城市学家芒福德的城市理论加以阐释。
芒福德认为,城市在本质上具有“容器”和“磁石”的双重功能,从其起源时代开始就是一种“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的“特殊的构造”[10]33,芒福德的城市理论,为我们研究城市文化资源的类型、特点及物质文化资源的构成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方面,城市是以地理空间为直观形态的物质“容器”,其内部既容纳了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地方物产,也包括了经过人们长期经营建设而形成的园林、街道、民居、寺庙等人工建筑设施,它们属于典型的物质文化资源,是城市存在的物质现实基础和空间结构,是人们形象化认识城市的逻辑前提。提到城市,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城市独具特色的地质、地貌特征以及个性化的地标建筑。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进程中,物质文化资源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转换而褪色、消减,甚至消亡,因而对这部分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更具紧迫性。
另一方面,城市的特殊构造还在于并非是物质实体的机械堆积,而是以特有的制度文明将物质与非物质资源有机组合起来的文化形态,具体包括了城市物质环境所负载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学艺术、娱乐节日、民俗活动等内蕴,它们是城市存在的非物质性人文基础和历史结构,是为建筑物灌注生气理念的“城市的灵魂”。与城市物质文化资源相对应,它们通常被表述为城市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转化而褪色、消减,可以“超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11],是物质文化资源具有磁石一样吸引力的隐性力量和“内在蕴涵”。
从类型上看,形式多样、向度多元的城市物质文化资源体系,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城市自然景观、地方物产、生态环境为代表;一是以建筑设施为代表。前者基本上属于大自然馈赠给城市的天然的物质文化资源,是城市资源开发的基础,相当于城市物质文化资源中的“第一自然”。后者则更多地被打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烙印,属于人工创造的城市文化资源,相当于城市物质文化资源的“第二自然”。
从构成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常常被表述为物产富饶的江南水乡,这里水网密布多如蛛丝,烟雨连绵恍如梦境,物产富足不可胜数。数千年的文学诗赋一直对这片温润的土地情有独钟。与之相应的城市建筑、园林景观,通常被标识为粉墙黛瓦、庭院通幽、枕河古镇的“小桥流水人家”。但是,这样的“宏大话语”对长三角城市群自然景观、建筑设施等物质文化资源的概括,并没有彻底厘清古代“八府一州”经济区的本体结构,由此往往导致对物质文化资源特征的概括流于模糊粗疏,不利于真正贴近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本质特征,无法区分它与其他江南城市物质文化资源之间的差异。在强调城市文化个性化、特色化的今天,我们对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进行“微观叙事”,特别是对打上“人的本质力量”烙印的“第二自然”文化资源细微辨析,有助于更清晰地审视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本土性特质,便于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开发城市文化。
具体来说,长三角城市群的物质文化资源既与本区域独特的气候、地理、水文等“天性”相关,更与当地民族的“人性”有关。
一方面,明清“八府一州”城市群与同时代的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物质文化资源具有规模宏大、形态成熟、积累雄厚的特点。
首先,从城市群整体规模上看,清人刘献廷记载了当时国家财富、人口分布状况,“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即封建帝国东、南、西、北方向分别有苏州、佛山、汉口、北京等四个聚集点。从当下城市群的视角看,这四大城市是明、清时代中国四个城市群落的中心,而当时的“四聚”也正是今天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武汉四个城市群(圈)的首位或中心城市。特别是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除了苏州,“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明代全国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位于该地区的就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鸦片战争前夕,这一地区大中小城镇密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均居全国之冠,从芜湖沿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共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这一数量同比占当时全国的一半[12]。这表明“八府一州”城市群在规模形态、城市密度上,较之其他城市群更突出。
其次,从城市群中心城市上看,同样是以工商繁盛著称的城市,以苏州为中心的“八府一州”城市群显示出比其他“三聚”财富积累更雄厚的特点。明代中期后,人称“天下财货莫不盛于苏州”(郑若曾,《康熙吴县志》卷二六:兵防)。康熙时人沈寓称赞苏州,“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沈寓,《清经世文编》卷二三:治苏)。在繁华程度上,苏州与京城并列。如果排除京城政治中心的特权优势,单凭商业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苏州显然更胜一筹。
再次,从城市群内部小城镇财富积累上看,仅南浔一镇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据刘大均《吴兴农村经济》记载,“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13]这表明当时的长三角城市群在富商巨贾、财富积累上较之其他地区更突出,物质文化资源的丰厚是其他城市群无法相比的。
另一方面,明清“八府一州”城市群与同为长江以南的其他城市群相比,因为特别深厚的人文浸润而给物质文化资源灌注更浓厚的诗书儒雅气息,并直接积累了富有诗书氛围的、数量庞大的物质文化资源。当时的“八府一州”科举之盛、考中进士人数均冠绝于全国。以考中进士人数的省份论,明代浙江全国第一,江苏第二,清代江苏第一,杭州次之。以考中进士的州府论,在全国考中进士最多的九个府中,明代八府一州占据三席,清代则占据五席。以进士人数在全国的排名论,在明代,苏州第三,常州第五,嘉兴第九;在清代,杭州第一,苏州第二,常州第三,嘉兴第四,湖州第五[14]250。以“八府一州”在江苏、浙江内部占据比例论,明代的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77%,清代的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包办了江苏省状元总数(113名)的86%[14]246-247。另外,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发明家,也大半出于这一地区[15]。科举教育的兴盛对物质文化资源的直接影响,不仅直接推动了这一地区书院、藏书楼、名人故居等文化教育建筑设施资源的数量繁多、规模宏大,而且,给他们居住的城市、古镇、街道、宅院烙上了深刻的文化气息,使得这里物质文化资源比其他相同的建筑设施多了一份诗书氛围。因此,不仅北方的京师、西部的汉口,在人文积淀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城市物质文化资源总是缺少一些诗书氛围,即使与自然条件同等优越的巴蜀、荆楚、岭南等长江以南地区相比,它还是要“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这正是千百年来,它会“成为中国民族魂牵梦绕的一个对象”[16]的重要原因。
一切文化皆是人化。无论是繁华大都、深宅通幽,还是小桥古镇、杏花人家,都是长三角城市群古代形态投注了江南民族智慧的物质文化资源,人文积淀为城市物质文化资源灌注了财富之外的诗书氤氲,成为它与其他城市物质文化资源构成的重要区别。
三、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面临的困境
丰厚的城市物质文化资源,既是明清“八府一州”城市群创造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今天长三角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必需的资源。但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正在陷入困境。
从表层上看,困境主要在于许多城市对物质文化资源的“不设防”。具体表现为,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正在遭遇城市化进程及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与粗暴践踏,文化资源的恶性损耗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土地和水永远是一个城市物质文化资源最基础的要素。明清以来,这里以拥有温润富饶的土地、清秀俊美的河湖资源而骄傲。然而,一方面,当下长三角城市群正面临着建筑一天天增高而土地一寸寸下沉、经济年年增长而损失年年加重的尴尬。调查表明,城市在升高,地面在下沉,已成为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亟待解决的新难题,其中,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地面沉降的重灾区。几十年来,长三角地区因为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3 150亿元。其中,上海最为严重,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3 328.28亿元。如果按照目前的沉降速度,到2050年,海平面将会上升40--70厘米,长三角很可能桑田变为沧海[17]。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的水资源破坏已到了危及城市居民生存的程度。长江和太湖是长三角城市群绝大多数城市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源头,但是,城市发展的“粗放式”经营和不合理规划,经济发展的冲动和短视行为,城市和企业污水往往不加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都在严重威胁着城市水源。据统计,长江沿岸约有40多万家化工企业,在长江下游尤其明显,仅南京到上海,长江沿岸就有8个大型临港化工区[18]。另外,黄金水道危险品运输量加大,仅南通长江水域每天就有约30万吨的过境危险货物,对上海、苏州、南京等沿江城市水源造成直接威胁[19]。2007年,一向被认为长三角一颗明珠的太湖,爆发蓝藻灾害,周边城市臭气熏天,无锡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告急,导致市民涌入超市哄抢、疯购矿泉水。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沪、苏、锡、常、杭、嘉、湖等城市水源均依赖太湖,但这些城市企业污水的直接排放,拉高了城市的经济产值,却把城市赖以生存的水源“最终蜕变成了一颗千疮百孔、被严重污染的黑‘心’”[20]。这场危机带给长三角城市群的已不仅是经济损失,还在于彻底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对太湖的美好意象:“无锡蓝藻以其刺眼的色泽、现代性的腥臭气、古典审美主体无法接受的形式感与心理体验,向当代人展示了一个真实而沉重的审美对象世界。”[21]
从深层次看,困境还在于许多城市的“假保护”、“伪设防”对物质文化资源造成的“二次伤害”,即开发过程中的“破坏性保护”与“开发性破坏”。
“破坏性保护”主要指当前长三角城市在物质文化资源保护过程中,存在着不合理、不规范、不科学的保护措施,造成物质文化资源恶性损耗后的“二次伤害”。物质文化资源需要多种保护措施来“设防”,但是,设防必须以合理、规范与科学为标准,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是“假保护”、“伪设防”,不仅无法起到保护物质文化资源的作用,还会造成“二次伤害”。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许多物质文化资源不被列入保护对象,往往处于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消亡”,一旦地方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更频繁,破坏的程度就更严重,消亡的速度也更快,从而演变为“沸水煮青蛙”的“突然死亡”。长三角许多具有江南传统文化特色的古镇建筑的保护就面临这个问题。2006年,乌镇、西塘、周庄和甪直,组合为“江南水乡古镇”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些古镇建筑因为保护而避免成为一片瓦砾,摇身一变升级为著名旅游胜地、世界文化遗产。但是,经过大拆大建与宏伟规划后的古镇、古街、古宅,已经难以找到“原汁原味”的江南味道。随着游客的蜂拥而至,“真实、完整的风貌逐渐缩小变少,各种“再现”、“重建”成为最多最大的部分”,被保护的古镇村落从建筑的风格到色调,都惊人的相似,“甚至你在中国的许多古镇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建筑”[22]。因此,“假保护”、“伪设防”本质上是对已遭到破坏的物质文化资源的更严重的“二次伤害”。
“开发性破坏”主要指当前长三角城市物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因为过度的商业开发与没有上限的利益期望,导致开发对象成为“第二种濒危”的严重状况。对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意味着保持传统江南城市文化的原汁原味不流失,但是,这并不等于将之视为标本存放于博物馆的展台上,文化资源的保护需要通过开发挖掘其内在价值,为城市生活、经济发展发挥必要的作用,于是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复杂难题就出现了。许多城市在没有上限的利益期望驱动下,不惜采取“过度”和“造假”的手段,因为“‘过度’和‘造假’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带来名与利的双赢。与可以看到的消失相比,这种信号或者叫倾向,更加危险,也更加缺乏应对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第二种濒危’”[22]。
芒福德认为,如果城市所实现的生活不是它自身的一种褒奖,那么为城市的发展形成而付出的全部牺牲就将毫无代价[10]119。同样,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而言,如果各种保护和开发不是对资源自身的一种褒奖,而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驱动,那么,城市付出的牺牲也就毫无意义。因此,对长三角城市群物质文化资源进行抢救性挖掘、保护与开发,是正在建设“世界级都市群”的长三角城市群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世界级都市群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当下,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竞争,演变为城市群竞争的世界性趋势,挖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世界级都市群普遍的成功经验。我国长三角城市群与其他世界级都市群的经济差距,远没有文化软实力差距更为明显,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长三角城市群文化资源,特别是城市物质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GOTTMANN. Megalopolis System around The World[J]. Ekistics, 1976, 243: 109-113.
[2] 刘琦.进入“长三角城镇群规划”意味着什么?[N/OL].芜湖日报,2006-04-10.[2009-04-27].http://www.wuhunews.cn/folder1150/folder76/2009/04/2009-04-27965.html.
[3] 徐益平.26城市“引擎”轰鸣 “大长三角号”强力启程[N/OL].东方早报,2008-11-12. http://www.dfdaily.com/html/42/2008/11/12/433755.shtml.
[4] 贾玥.国务院正式批准长三角规划:将建世界级城市群[EB/OL].[2010-05-24].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1680674.html.
[5] GOTTMANN.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30-46.
[6] 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J].江苏社会科学,2009(5):228-233.
[7]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9-449.
[8] 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J].学术月刊,2005(8):113-117.
[9] 刘士林,刘新静.江南文化资源的类型及其阐释[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5):37-44.
[10]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延,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1] 武廷海.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J].华中建筑,2000(3):122-123.
[12]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走过十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十周年纪事[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序言.
[13] 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南浔镇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392.
[14]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227-250.
[15]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J].清史研究,2004(1):1-14.
[16]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09.
[17] 杨迪.中国超50个城市发生地面沉降 尚无统一监测网[EB/OL].[2011-11-16].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1-16/3465178.shtml.
[18] 长江流域废水排放量不断刷新 黄金水道岌岌可危[N].经济参考报,2011-11-09.
[19] 赖臻,朱旭东.中国城市水资源调查[N].中国日报,2012-02-14.
[20] 吕明合.太湖蓝藻:斩不断、理还乱[N].南方周末,2011-07-11.
[21] 刘士林.无锡蓝藻事件凸显江南诗性文化的现代性问题[J].探索与争鸣,2008(1):68-71.
[22] 齐欣,杨雪梅.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唱独角戏 警惕“第二种濒危”[N].人民日报,2012-06-15.
〔责任编辑:陈济平〕
G127
A
1003-6873(2015)04-0022-06
2015-05-12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扬州文化资源研究”(14ZWB00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明清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江南小说’的新变”(2015SJB659);江苏省大学生村官研究所资助项目“大学生村官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JSCG1510)。
张兴龙(1972-- ),男,江苏连云港人,淮海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城市科学等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4.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