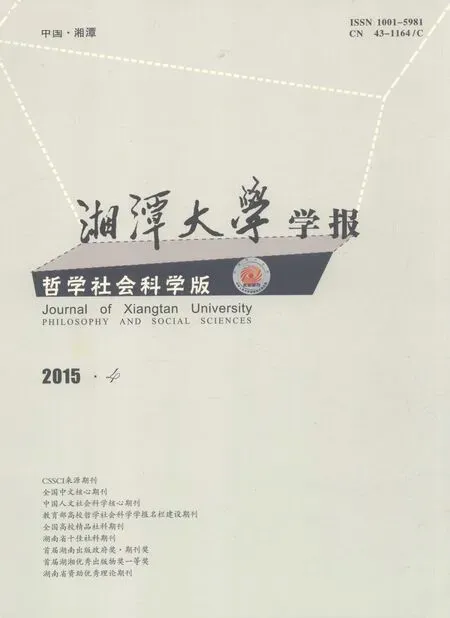职务犯罪死刑控制与刑罚严厉化之立法协调*
邱帅萍,龚铮宏
(1.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2.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湖南湘潭411000)
职务犯罪死刑控制与刑罚严厉化之立法协调*
邱帅萍1,龚铮宏2
(1.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2.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湖南湘潭411000)
摘要:在职务犯罪领域,如何协调限制、减少死刑与严惩职务犯罪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不论是根据立法沿革还是根据现实需求,增加死刑罪名都缺乏必要性与合理性。贪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应废止贪污罪的死刑。但基于受贿罪所固有的社会危害性,并兼顾当前的反腐情势,有必要保留受贿罪的死刑。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刑罚结构均应做不同程度的调整。
关键词:职务犯罪;死刑控制;刑罚严厉化;贪污罪;受贿罪
职务犯罪一般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1]P58。职务犯罪的死刑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讨论、审议过程中,职务犯罪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就成为了热议话题,《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也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了修改。“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法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且最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限制和减少死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决策领导层、法律人和普通大众的普遍共识”[2]153,《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出台就基本反映了这一共识。201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然而,对于职务犯罪,尤其是贪腐犯罪,中共中央却“毫不手软”,十八大报告严正表达了严惩职务犯罪、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腐败问题甚至被提升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可见,限制、减少死刑与严惩职务犯罪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张力,如何从立法上加以协调调整,已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一、严惩职务犯罪无须新增死刑罪名
死刑的限制和减少非意味着不能在整体削减死刑的情况下增加死刑罪名;另一方面,仍有不少人呼吁增加包括贪腐犯罪在内的部分死刑罪名①参见“激辩死刑罪名存废”,http://news.163.com/14/1107/11/AAEO2SQM00014AEE.html,2015年2月27日访问;“我国拟取消强迫卖淫罪等9种适用死刑罪死刑是不是震慑犯罪的最有力方式?”,http://bbs1.people.com.cn/post/1/0/1/142916819_2.html,2015年2月27日访问。;目前中共中央的反腐决心也十分坚决。因此,职务犯罪领域是否应该增加死刑罪名,值得探讨。
(一)从立法沿革上看,缺乏新增死刑罪名的必要性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死刑罪名数量一直在变化,呈抛物线的发展趋势:从建国初期的十余种死刑罪名,到现行刑法颁行前的71种死刑罪名,死刑罪名数量一路攀升,而现行刑法的颁行使得死刑罪名减至68个,《刑法修正案(八)》将死刑罪名降低至55个,《刑法修正案(九)》又拟再减少9个死刑罪名,将其减至46个。在近70年的刑事立法实践中,尽管颁行了多部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等,尽管死刑罪名不断变化,然而,职务犯罪领域的死刑罪名及其数量却异常稳定。自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中规定了贪污受贿行为的死刑以来,除了1979年《刑法》颁行之后至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颁行之前的这段时间,受贿罪没有设置死刑外,职务犯罪领域始终针对且仅针对贪污罪和受贿罪保持死刑设置。
死刑罪名数量的发展变化表明,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在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死刑的司法实践。在此情况下,即便死刑罪名曾一度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增加了50多个,国家立法也一直没有对职务犯罪领域内的死刑罪名作出重大调整,没有新增死刑罪名,这也反映出保留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足以符合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中对于刑罚严厉性和最高刑设置所提出的要求,无须另行增加死刑罪名。况且,当今我国死刑罪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刑罚的结构日益合理,刑事法网的日益严密,死刑对于整体上打击预防犯罪的必要性程度越来越低,增加职务犯罪领域的死刑罪名便更属不必要。
(二)从现实情况看,缺乏增加死刑罪名的合理性
据统计,我国刑法中,职务犯罪所涵盖的罪名共有50个。其中,除了贪污罪和受贿罪配置有死刑外,仅有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配置了无期徒刑,其他犯罪的最高刑均为有期徒刑。从刑事立法的体系性和协调性角度看,较为稳健的刑罚力度的加重应当是逐格升级,而非跳格升级,加之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最长刑期一般仅为十五年,因此,如若增加职务犯罪的死刑罪名,应该先考虑增加挪用公款罪或者行贿罪的死刑配置。
挪用公款罪属于典型的挪用型贪利犯罪,社会危害性尚不及同属于职务犯罪的贪污罪这一典型的侵占型贪利犯罪,因为“挪用的实质在于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违背所有人的意愿而暂时地控制他人财物”[3]660,而侵占是对财物的永久性控制和支配。在贪污罪的死刑配置饱受争议的今天,很难设想为挪用公款罪配置死刑的可行性。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似乎也没有学者主张为挪用公款罪配置死刑。基于司法实践的要求而为挪用公款罪配置死刑,更加缺乏可行性。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挪用公款案的罪犯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学者甚至在其统计的130份挪用公款案的刑事判例中未发现1例无期徒刑的判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判决比例仅为4.7%[4]6。这不但说明挪用公款罪不应被配置死刑,连其能否配置无期徒刑也应受到质疑。
尽管近些年来国家查处贿赂犯罪的力度明显加强,但预防贿赂犯罪的效果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有些学者将原因部分归结为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均存在的“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认为应当加重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5],甚至像受贿罪一样对行贿罪增设死刑[6]。该观点值得商榷,这主要是因为: (1)行贿者往往在犯罪中处于从属或者弱势的地位,行贿者往往觊觎或者受制于受贿者的职权或者因职权而形成的便利条件,没有受贿者的同意或者主导,犯罪无法完成; (2)行贿罪与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在内容上虽无本质差异,但存在间接与直接的不同,行贿罪是透过受贿罪而间接侵犯法益。由此,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受贿罪,如果行贿罪与受贿罪同等处罚、配置死刑,势必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从世界范围来看,废除死刑或者停止死刑执行的国家和地区已从1948年的14个发展至当今的158个,削减、废除死刑是世界性趋势[7]111。在此背景下,增加死刑罪名应当慎之又慎。而前述分析又表明,我国职务犯罪领域增加死刑罪名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以增加死刑罪名来严惩职务(贪腐)犯罪实属不当。
二、严惩职务犯罪无须保留贪污罪死刑
在职务犯罪领域削减死刑意味着应当尽可能地废止相应的死刑罪名。许多学者在研究职务犯罪的死刑存废问题时,都将贪污罪与受贿罪合并论述。然而,贪污犯罪与受贿犯罪之间在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宜逐一讨论其死刑存废问题。
(一)贪污罪死刑保留论者的主要观点
学界有不少学者反对现阶段着手废止贪污罪的死刑,其主要理由有: (1)贪污罪并非简单的经济犯罪,其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属于独立的犯罪类型,不能简单地因为贪污罪属于贪利型犯罪、没有剥夺人的生命就认为其应当废除死刑[2]154; (2)在我国刑法目前还没有对非暴力犯罪全面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对于严重的贪腐犯罪,也就没有单独取消死刑的理由[8]58; (3)死刑是最为严厉的刑罚,能够最有力地威慑犯罪,保留死刑能够彰显国家对于惩治贪腐犯罪的决心[9]59; (4)贪腐犯罪能够威胁社会公众的生命、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并且容易导致社会道德沦丧。[10]10
(二)反驳与回应
现阶段是否着手废止贪污罪死刑,这一问题与贪污罪的犯罪类型以及其他非暴力犯罪是否全面取消并无密切的关联。不可否认,与盗窃、诈骗等单纯的财产型犯罪不同,贪污犯罪不但侵犯了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进而使得其社会危害性超出了盗窃犯罪、诈骗犯罪等。但是,“举轻明重”的原理在此无法适用,刑法虽然为盗窃罪和诈骗罪配置了无期徒刑,却未配置死刑,贪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较高也仅仅意味着贪污罪的最高刑罚配置不能低于无期徒刑,而非意味着应当将之升格为死刑。当前我国刑法仍有许多非暴力犯罪没有废止死刑,但这并非意味着贪污罪应当保留死刑。如果贪污罪应当在非暴力犯罪中最后被废止,那么,就必须证明贪污犯罪是所有非暴力犯罪中社会危害性最严重的犯罪,然而,似乎没有任何证据或者有力的观点能够表明这一点。
死刑虽是最严厉的刑罚,但这并不足以构成保留贪污罪死刑的主要理由之一。刑罚的严厉性只是保持其对犯罪威慑力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刑罚的及时性与不可避免性对于打击和预防犯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存在明显的死刑罪名过多、刑罚结构过于严厉的问题。过于追求死刑的严厉性上的威慑效果只会让刑罚改革避重就轻。即便当前国家反腐任务十分艰巨,反腐决心十分坚定,亦无须通过死刑来“杀鸡儆猴”。在特定时期,国家总会基于社会情势制定打击特定犯罪的政策或者计划,如之前开展的几次“严打”以及不定时发动的打击“两抢一盗”行动。对于严打,学界和实务界已经深刻反思过于追求刑罚严厉性所产生的弊端,“严打”刑事政策也已被“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取代。对于长期以来不定期进行的打击“两抢一盗”行动,除了抢劫罪属于能够危及人们生命的暴力犯罪而配置有死刑外,抢夺罪和盗窃罪都未配置死刑,盗窃罪更是经历了由配置死刑到废止死刑的变化。因此,威慑犯罪、严惩贪污并非要依赖死刑。
基于社会大众生命、政府合法性基础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的考虑而揭示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而论证保留贪污罪死刑的合理性,该种方式欠妥当。所有的犯罪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危及社会道德的稳定性,因为犯罪的本质除了社会危害性之外,还包含有应受谴责性。而论及危害社会道德的程度,贪污犯罪作为一种法定犯(或曰行政犯),其尚不及诈骗罪、强奸罪、聚众淫乱罪之类的自然犯(或曰刑事犯)。就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言,包含贪污罪在内的所有职务犯罪都能够产生此危害。惩治贪污并非意味着一定要判处贪污犯死刑,当前更重要的措施在于确保贪污行为能够及时查处,严密刑事法网。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即便是比贪污犯罪更为轻微的职务犯罪,即便对其配置死刑,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依然会受到巨大威胁。认为贪腐犯罪会危及社会公众生命安全的论者,其论证理由是:“国家公职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减少了本应投入社会建设或用于救济的财政资金,赋予不具有合格资质的企业生产、建筑、交易的许可,允许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不合格的人员行使公共权力,这些都将成为产生社会危害甚至灾难的定时炸弹”[10]8。实质上,该观点除了减少社会财政资金这一点能够适用于贪污罪之外,其他理由均主要适用于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关联并不紧密。
贪污罪死刑废除论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废除贪污罪死刑的理由,这些理由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①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将贪污罪和受贿罪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其死刑存废问题,因此废除贪污罪死刑的理由也基本适用于废除受贿罪,这些理由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保留受贿罪的死刑”中予以述评。。笔者需要提出的是,贪污罪配置死刑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9]14,这才是废除贪污罪死刑的主要理由。无论是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还是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贪污犯罪行为人都未达到罪该至死的程度。从主观恶性上看,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主要在于侵犯国家财物所有权,具有贪利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之于盗窃并未严重多少。虽然贪污行为在客观上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或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但这更多是受行为人贪利动机的驱使,是为了方便侵吞国家财物而为之,而非行为人主要目的。从人身危险性上看,一旦行为人被剥夺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且在具有再犯可能性的前提下被剥夺再次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其犯贪污罪的人身危险性便无从谈起或者无法转化为对社会的现实威胁。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说,行为人一般仅针对国家财物,其侵吞行为一般不会衍生出其他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主要在于侵犯国家财产所有权和国家的廉政制度。就侵犯国家财产所有权而言,其行为与普通的盗窃罪无异,而且在国家经济实力日益雄厚、民众经济状况差异巨大的当今,很难说侵吞国家财物的社会危害性在整体上一定高于盗窃公私财物的危害性。就侵犯国家的廉政制度而言,固然其危害严重,但是廉政制度的建设更多在于制度保障、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国家的廉政制度断不会因为出现一些相当严重的贪腐犯罪而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即便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贪腐犯罪,只要无期徒刑等刑罚执行到位,也能够达到较好的刑罚效果,毕竟,行为人所真正在意和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非破坏职务的廉洁性。
因此,无须基于廉政制度建设的考虑而将贪污罪的刑罚配置为死刑。
三、严惩职务犯罪须保留受贿罪死刑
受贿罪的构造与贪污罪的不同,应当废止贪污罪的死刑,并非意味着也应当废止受贿罪的死刑。
(一)受贿罪死刑废止论者的主要观点
学界关于现阶段是否应当废止受贿罪死刑的争议,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归纳:一是是否应该着手废除全部犯罪的死刑;二是单就受贿罪而言,是否应该着手废止其死刑。受贿罪死刑废除论者所提出的观点不在少数,但归结起来主要有: (1)受贿行为不具备暴力性; (2)经过刑罚的改造与惩处,行为人一般不再具备再犯的能力,也不会产生再犯的心理;[11]14(3)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保留受贿罪死刑不利于展开惩治此类犯罪的国际司法合作,不利于国家履行相关的国际公约;[2]154(4)对受贿罪适用死刑,是对罪犯人权的剥夺,有违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从现代国家死刑废止的趋势看,人道性无疑是当代全球各国死刑废止最为重要的内在根据[12]74。
(二)反驳与回应
受贿行为不具备暴力性并不意味着受贿罪死刑就应当废除,死刑与犯罪行为的暴力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从罪质上说,暴力性犯罪与死刑并不等同,因为暴力性犯罪不一定导致人的死亡,而死刑意味着剥夺行为人的生命;从结果上说,很多导致人死亡的犯罪、可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并不一定是暴力性犯罪,导致人死亡的犯罪也不一定是可判处死刑的犯罪。例如,生产、销售假药罪所对应的行为可能导致多人的死亡,但并非暴力性犯罪,刑法却规定了死刑,过失致人死亡罪所对应的行为导致人死亡,但最高刑仅为7年有期徒刑。
受贿犯罪的行为人经过刑罚的改造与惩处之后,虽然他有可能不具备再犯能力,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一般不会产生再犯的心理,而且根据当今以一般预防为主流、报应占有重要位置的刑罚目的体系格局,剥夺再犯能力这种特殊威慑几乎被公认为不是衡量刑罚力度的最重要尺度,因此也不足以成为否定受贿罪死刑的重要论据。
保留受贿罪死刑是否会在现实中制约相关犯罪的惩治,对此应当辩证地对待。对于不会判处死刑的受贿犯罪人,我国可参照与西班牙签订的引渡协议,承诺不判处或者执行死刑,以解决制度上的障碍[13]180。对很有可能或者应当判处死刑的受贿犯罪人应如何处置,这在更高层面上属于一种外交政策或者策略的选择,就如同外交大使等外国人的犯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样。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个国家有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我国不能仅仅基于国外存在受贿罪免除死刑的立法而盲目地跟随。至于是否应当履行国际公约,由于我国已签署的国际公约并未明确针对受贿罪等犯罪而要求成员国废除其死刑,因此,对此本文暂不予评价。
死刑之所以饱受争议,与其是否具有人道性、是否侵犯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权,并非一个自明或者固定的概念,它的内涵需要不断地深入探求且不停地在变化发展,而且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其的理解并不相同。例如,在死刑问题上,美国作为一个以保障人权为社会根本的国家,依然有近2/3的州没有废除死刑,废除死刑之路遥遥无期[14]9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认为,死刑不是酷刑且符合美国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并为民众所认可[15]121。在国家层面上,鉴于人权这一概念所承载的价值,几乎不会有国家会认为自己国家存在死刑刑罚就会侵犯人权或者意味着无视人权;在民众层面上,就我国而言,“由于延续几千年的死刑历史遗迹因果报应文化的浸染,同时也由于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社会环境的影响,死刑在我国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16]142。因此,很难说死刑在我国不具有人道性、侵犯了人权。
基于受贿犯罪所固有的社会危害性,基于当前的社会情势,保留受贿罪的死刑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受贿犯罪行为虽然是基于贪利而实施收受、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是,该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非一般的贪利型犯罪或者财产型犯罪(同时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除外)所能比拟。后者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犯罪数额上——贪污罪还包括国家的廉政制度(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犯罪数额以及相关的国家制度仅能反映受贿罪的一部分社会危害性[17]102,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受贿罪是交易型的贪利犯罪,受贿人往往会为了钱财而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在实践中,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后所实施的行为,往往会产生非常严重社会危害后果。例如,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其收受贿赂后,擅自降低审批药品的标准,纵容不法企业生产、销售假药,以致多人死亡或者遭受严重的身体伤害,其最终也因为受贿行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从近些年来我国所已经或者正在查处的职务犯罪领域的严重刑事案件来看,受贿犯罪而非贪污犯罪才是国家所打击的重点犯罪中的重点。经学者抽样统计的十年职务犯罪死刑适用现状表明,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大多是受贿罪而非贪污罪,其中被立即执行的贪污犯罪罪犯更是少之又少[18]58。近些年来在反腐过程中所查处的大案要案中,绝大多数罪犯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主要是基于其受贿行为,例如郑少东、陈同海、许宗衡、薄熙来、刘志军、文强、黄松有等;受到查处的大小“老虎”之所以被刑事立案侦查或者提起公诉,也主要是基于其行为涉嫌构成受贿罪,例如蒋洁敏、李春城、李东生、冀文林、万庆良、季建业和王永春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因涉嫌触犯贪污罪而被追诉。
由此可见,职务犯罪中,真正的最大的毒瘤是受贿犯罪,而非贪污犯罪,保留受贿罪的死刑反映了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符合目前严峻的反腐形势的需要。
四、严惩职务犯罪须调整现有死刑罪名的刑罚结构
立法上协调职务犯罪领域内死刑控制与刑罚严厉化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有关死刑罪名的增加与存废,还应当考虑如何优化现有死刑罪名的刑罚结构。
(一)贪污罪刑罚结构的调整
废除贪污罪死刑仅仅意味着死刑得到了控制,并非意味着严惩职务犯罪的目标得到了实现。易言之,如何在废止贪污罪死刑的同时,保持其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引人深思。
根据贪污数额和犯罪情节的不同,我国刑法基本按照从严至轻的顺序一共为贪污罪设置了7个量刑档次,分别是: (1)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4)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5)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6)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7)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方面,这些错综复杂的量刑档次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不小的困惑,量刑也极不统一,例如,贪污五万元可能面临的处罚上至无期徒刑并附加没收财产,下至五年有期徒刑;贪污十万元上至死刑并附加没收财产,下至十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根据第1、2位阶量刑档次,刑法为贪污罪设置了绝对法定刑,这反映出刑法过于重视打击贪污犯罪,不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此外,贪污罪的刑罚设置还存在附加刑单一的问题,贪污罪仅配置没收财产,且仅为某些位阶高的量刑档次配置了附加刑。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虽然保留了贪污罪的死刑,但是对贪污罪的刑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按照由轻至严的顺序设置了4个相互衔接的量刑档次,杜绝了绝对法定刑的存在,丰富了附加刑的配置。根据贪污数额和犯罪情节等,量刑设置具体可分为: (1)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2)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4)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总的来说,《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基本上实现了对贪污罪刑罚结构的优化,十分有利于严惩贪污犯罪以及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然而,前述表明无须为贪污罪配置死刑,因此有必要考虑第(4)位阶量刑档次的存废或者修改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废止贪污罪的死刑的同时修改第(4)位阶量刑档次的设置,那么该量刑档次就变成了“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绝对法定刑,显然不符合刑罚结构调整的要求。就废止该量刑档次的设置而言,由于其对应的罪状为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而第(3)位阶量刑档次的罪状为“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鉴于“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本身属于“特别严重情节”中的一种,且第(3)位阶量刑档次包含有无期徒刑的设置(同时也包含有没收财产刑的设置),因此,废止第(4)位阶量刑档次的设置较为妥当。
(二)受贿罪刑罚结构的调整
根据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于受贿罪,根据受贿数额和情节,比照贪污罪的规定处罚。因此,贪污罪刑罚结构存在的问题,大体等同于受贿罪刑罚结构存在的问题。然而,贪污罪与受贿罪无论是在犯罪性质、行为方式还是社会危害性上都存在差异,就当前惩治职务犯罪的形势而言,贪污罪属于可以废止死刑的罪名,而受贿罪的死刑应当保留,因此,对二者“以相同的刑种和刑度追究刑事责任,无论从静态规范比较还是从动态司法实践比较都不具有科学性”[17]102。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依然沿袭了“受贿罪比照贪污罪处罚的传统”,但是,在肯定该草案积极意义的同时,有必要反思如何更好地调整受贿罪的刑罚结构。如前所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基本上呈现出“宜简不宜繁”、量刑档次之间相互衔接、法定刑相对确定以及扩大附加刑的适用等特点。虽然贪污罪与受贿罪之间存在差异,但鉴于二者均为腐败型的职务犯罪,且二者在立法沿革上表现出许多共同之处,由此,可在贪污罪量刑设置的基础上略为修改,以优化受贿罪的刑罚结构,基本思路为: (1)参照贪污罪的草案规定,设置3个位阶的量刑档次; (2)受贿罪的每个档次法定刑均较贪污罪严厉; (3)保留受贿罪死刑,同时取消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此,不妨将受贿罪的量刑档次设置为: (1)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参考文献:
[1]郑勇,罗开卷.职务犯罪的立法比较与借鉴[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4(3).
[2]赵秉志.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J].法律科学,2014 (1).
[3]赵秉志.刑法分则要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4]刘健.实务中挪用公款罪的罪刑均衡——以实证研究为视角
[D].长春:吉林大学,2014.
[5]黄秋熊等.严厉打击行贿犯罪,遏制腐败现象蔓延[N].人民法院报,2014-08-28.
[6]“我国应加大惩治行贿罪的力度”[EB/OL],http://www.cqjcy.gov.cn/qfwy/infos/InfoDisplay.asp? NewsID =4624,2015-2-27.
[7]毛立新.联合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和立场[J].河北法学,2014 (4).
[8]张绍谦.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新思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4).
[9]马松建,蒋兆乾.贪污罪的刑罚配置新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10]毛昭晖,刘辉.贪污受贿罪死刑不应废除的法理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
[11]蔡淮涛.论受贿罪法定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3(6).
[12]于雪婷.受贿罪法定刑设置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
[13]郑士立.职务犯罪死刑制度之思辨[J].民主与法制,2014(4).[14]徐岱.美国死刑走向废除的障碍及启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6).
[15]于志刚、曹晶.美国的死刑保留政策与新死刑保留主义[J].政法论坛,2013(6).
[16]阴建峰,丁宁.宪政维度下中国死刑改革之思考[J].刑法论丛,2012(3).
[17]焦占营.贿赂犯罪法定刑评价模式之研究[J].法学评论,2010 (5).
[18]蔡梦玲.职务犯罪死刑适用研究——以近十年来部分案例的刑事判决为样本[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
责任编辑:饶娣清
The Legisla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Controlling Death Penalty and Severe Penalty in the Realm of Duty Crime
QIU Shuai-ping1,GONG Zheng-hong2*(1.Law School,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Hunan,411201; 2.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Yuhu District,Xiangtan,Hunan 411000,China)
Abstract:In the realm of duty crime,it’s necessary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coordinate the control of death penalty and severe penalty.From the views of legislative evolution and current demand,it’s of no necessity or rationality to add the crime of death.The social harmfulness of corruption crime is limited,for the reason of principle of compatibility of crime,its’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bolished.In consideration of bribery crime’s social harmfuln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its’death penalty should be reserved.The structure of criminal law about corruption and bribery should be adjusted in different degrees.
Keywords:duty crime; control of death penalty; severe penalty; crime of corruption; crime of bribery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12YBB092)以及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国家惩罚权配置问题研究”(14A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邱帅萍(1986-),男,湖南南县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龚铮宏(1971-),男,湖南湘乡人,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收稿日期:2015-01-12
中图分类号:DF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5) 04-0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