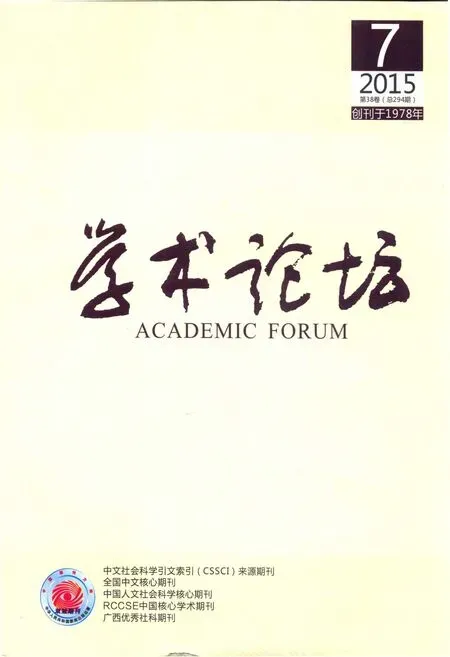历史视角下执政忧患意识的影响因素及质量提升研究——执政意识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黄义英,秦 馨
执政忧患意识是执政者基于对自身角色职责的认定而产生的一种忧虑意识。 习近平曾强调:“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1]执政忧患意识本质上是一种问题意识, 是对执政活动是否还存在问题、 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去应对问题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判断。 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忧患意识都是必要的。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缺乏忧患意识的执政者不能及时回应民意诉求, 不能保持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就会出现专横、麻木、冷漠、奢侈堕落、肆无忌惮等现象。 历史上, 统治者倡导或者标榜忧患意识的官样文章比比皆是,而实际的治理绩效却大不相同。 历史不但是已经发生了的政治, 而且也可能是正在发生的政治的合理解释和即将发生的政治的观念预演。在讨论执政忧患意识建设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得到诸多的启发。
一、影响执政忧患意识的主要因素
(一)执政者的综合素质
据《论语·子罕》记载,孔子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因为有这样的修养,所以孔子的人生充满了忧患意识,就如《论语·述而》所说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人的性格、认知水平和能力等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倘若性格上的缺陷和能力上的不足能够为后天的修养所弥补,仍然可以做到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问题,虚心接受建议。 而如果放弃了修养,这些缺陷和不足就会体现在行动上,并最终影响行动结果。
《吕氏春秋·骄恣》就说过:“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 ”隋炀帝虽然在执政后期充满了失败情绪,但在他前期执政生涯中,是表现出肆意妄为、不虞后患的心态的。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就记载了他的自负:“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因为自负,所以他明白告诉别人,“我性不喜人谏”。 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就会把大问题看成是小问题,把小问题看成是没问题。
还有就是太在乎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功业和形象,容不得半点怀疑和批评。 只要有人讲存在问题,就被认为是恶毒攻击。 忧患意识变成了自我欣赏。这一点,就连大半生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到了晚年也不能免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记载了唐太宗要人谈看法不过是找机会向别人展示自己如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更愿意听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一类的奉承话。
中国古代谏诤制度的长处在于真知灼见可以立即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并付诸实行,而不必经过多数人的票决和复杂的过程,其短处在于最高统治者面对多种政策倡议和行动方案时无法判断何者为正确的,何者为错误的,甚至是以对为错、以错为对。 当拥有决策权的人对问题缺少相应的体认时,就难免出现令先知先觉者乃至大多数人“长太息以掩涕兮”那样的尴尬。 如果最高统治者乐以忘忧,就能将大多数人的忧患意识置于无用武之地。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七就记载了在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宦官仇士良致仕时教他的党徒“固权宠之术”:“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 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
(二)执政绩效
执政绩效是指执政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所呈现的实际业绩和效能。 正确的忧患意识如果转化为执政者的正确决策和谨慎行动,就会取得较好的治理绩效。 但忧患意识能否持续,却和执政者能否提出新的目标任务并达成共识密切相关。 如果治理目标相对单一,而且在短时期内容易实现,则在目标实现以后,执政者的忧患意识必然出现衰减的趋势。 以“安”或者政权巩固为目标的统治,在清除了竞争者,建立了强大的军队、警察、监狱,以及让老百姓有了温饱之后,也就等于有了“安”的感觉,整个执政意识也就都由“安”生发出来。 即使出现一些天灾、骚乱和边境冲突等,也一般相信凭借政权的力量能够加以控制,使忧患意识持续的主观需求不再那么迫切了。 执政者没有把每做一件事都上升到政权安危的层面来考虑。 这就是魏征在《贞观政要·刑法》中所说的“隋氏以富强而丧败”的问题。 在魏征看来,“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富强之后,没有人相信一件事处置不当就会导致危亡,“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 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
良好的执政绩效也容易使执政者形成思维惯性, 不能或者不愿意看到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严重性。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就记载了隋朝晚期天下大乱时,隋炀帝却“恶闻贼盗”,对于虞世基所说的“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务以介怀”一类粉饰太平的话“良以为然”,而以据实奏报的人为“妄言”。
如果忧患意识并未导致预期的治理效果,执政者就会产生失败感。 如《汉书·哀帝纪》就叙述了汉哀帝接受改元、易号建议:“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也记载了隋炀帝在公元618 年充满了失败情绪,照镜子的时候对萧后说:“好头颅,谁当斫之! ”并认为“苦乐贵贱,更迭为之”,不应该伤悲。
(三)政治体制和运作方式
政治并不仅仅是在人们早已设定好的制度框架内运行。革命是最典型的在制度框架外运行的政治,而执政也不意味着能完全按照已有的制度框架来思考和处置一切问题。人们在判断一种政治的民主或者专制属性的时候,常常把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混同起来。实际上,两者的关系是复杂的。政治体制的专制或民主与政治运作的专制或民主之间未必是绝对对应的,政治体制可以是专制的,但政治运作却可以有一些民主气息。 同样,政治体制可以是民主的,但也不能排除政治运作中的不民主。
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宣称要把自己的政治体制搞成民主的,但在思想理论上,却一直坚持政治运作不能搞专制独裁。 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否导致专制的政治运作,关键在于人。 忧患意识的产生,既和政治体制有关,也和政治运作有关。 这里面也分不同的情形。 一种情形是政治体制在不断地制造着社会矛盾,而政治运作却能够使相关的信息在各个层级的执政者之间得到有效传播,并最终形成忧患意识;一种情形是政治运作不断地造成社会问题和问题意识,而政治体制是支持问题意识的形成和传递的。 某一现实问题是否会引起相应的忧患意识,以及在何种层级和何种范围的执政者中引起忧患意识,要经过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的接受、分析、过滤或放大。
唐太宗的政治体制和隋炀帝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区别,贞观早年的政治体制和贞观晚年的政治体制更没有实质性不同,区分主要在于政治运作。 在不根本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及加强执政者自身素质的综合修养,保证政治运作的开明性,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试图获得他们理想中的忧患意识时经常采取的办法。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中,有可能激发执政者忧患意识的事件也不尽相同。在许多国家,日食不会引起执政者的忧患意识,而在中国古代,这就是很严重的政治事件。 一个美国的州长宣布自己要进军总统宝座,这恐怕也不会引起在任总统的不安,而在中国古代,一个诸侯向周王室问九鼎之轻重,就构成周天子莫大的隐患。
(四)社会矛盾的强度和烈度
不管是何种素质的执政者,也不管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如何,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的强度和烈度时,都会引起相应的忧患意识。 在风雨飘摇的王朝末期,上自皇帝大臣,下到一般的官员胥吏,还有众多的文人学士,心中都充满了忧患意识。 因为任何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也无法再对现实问题进行随意的解释和缩小其影响。 然而,这并不说明王朝政治正在经历一场能够起死回生的自我革命。因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忧患意识的质量越低。
人们并不仅仅追求有忧患意识这样的简单事实,而是希望有高质量的、能够有利于形成良好治理格局的忧患意识。 政治是一国之公事,权力是天下之公器,它所需要的忧患意识是和天下之兴亡、苦乐联系在一起的大公至正的忧患意识。 也就是说,忧患意识首先立心要公、要正、要纯,然后才能保证执政者的思维沿着正确的途径展开,其政策和行为才能符合执政规律的要求。 就如《吕氏春秋·贵公》中说到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忧患固然使人勤于政事,但倘若为一己之私而忧患,执政者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就会出现反常现象,政治就会偏离轨道。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强烈忧患可能导致政治活动的暴虐化。 他们不但自己拿不出好政策,而且也会拒绝他人提出的好建议。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记载了贾谊对秦亡教训的论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
二、提升执政忧患意识质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执政忧患意识质量的提升,就是使有一定质量的忧患意识成为可持续的。 它首先意味着忧患意识具有科学的内容,具有适当的强度,其次意味着忧患意识要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在人群中广泛存在,而且不断改变其形式以顺应时代的变化。 为此,必须清除不利于忧患意识形成和传递的各种障碍,同时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体制。
(一)构建合理的执政目标体系
执政目标是和执政者的阶级属性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受各种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儒家虽然悬设了“小康”、“大同”这样的高远理想,道家也悬设了“至德之世”这样的理想,但没有成为执政者意识关注的重点。 在古代中国,执政者最实际的目标就是维护自身的权力、地位和利益,用“安”字就能概括。没有外患,没有内忧,就是“安”。在这样的大目标下,“小康”、“大同”的内涵也变成比较容易做到的了。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就是“小康”;只要没有边境袭扰事件,就可能是“大同”。 而内忧重于外患,所以,只要感到别人都服从了自己的权力,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很难再有什么忧患意识。这就是魏征在《贞观政要·君道》中所说的:“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已经巩固的政权将来有可能被人推翻,但至少目前看不到丝毫迹象,所以,所谓的忧患意识虽然见于官样文章,但每个人的心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忧患。
而在一个更加合理的执政目标体系中,忧患意识并没有因为某个目标的暂时实现而消失。 这不是说目标制定得越高远越有利于保持忧患意识,而是说,某个目标实现之后,人们立即又为另外的目标而努力,不断有新的任务激励,就不易于懈怠。 然而,共同的理想只适于宣传,而未必能够与个人的生活发生真切的联系。 执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岗位体系,岗位体系具有天然的惰性,试图将一切问题都纳入既定的轨道处理。 糟糕的岗位体系能够把所有涌现出来的新问题都变成老问题,从而消解了人的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人的进取心和创新意识。 一个仅凭短时期内积累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就可以应付自如的岗位,相对于静止的执政目标是有意义的,但对于不断提升和丰富的执政目标体系来说是失败的设置。 所以,构建合理的执政目标体系,更关键的在于将共同的理想分解为具体的岗位职责,而且让同一岗位的要求对于每个工作者来说都是不断提高的。
(二)执政者要正确地认识、评价和宣传执政绩效
“晒政绩”符合人之常情。 普通人工作上取得了一点成绩,都迫不及待地向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宣传,执政者也是常人,社会大众应该允许执政者适当晒一晒成绩单。如果一个社会对执政者的艰辛没有体谅,对执政者的成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根本不允许他们表白,这实际上不利于监督和鞭策执政者, 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都是有害的。没有批评声音的政治注定要变质,而无谓的批评只会制造对立情绪。在充斥着“不论你做什么,也不论你怎么做,我都绝对不满意”情绪的社会,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强制与对抗。
“晒政绩”也符合政治逻辑,因为这是执政合法性的理由之一,有利于巩固执政基础。 “延续几个时代, 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2](P57)然而,这并不表明执政者“晒政绩”可以不受节制。 《淮南子·人间训》云:“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 ”也就是说,执政者主观上要认清做出成绩不过是履行了职责, 不应萌生邀誉之心。 执政者出于担心丢失选票,担心地位不保而宣传政绩,常常会主动把存在问题遮掩起来。 这倒不是说他们会宣称没有任何问题, 而是说他们会非常策略地提到这些问题。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服别人,结果只是催眠了自己。 这样做还会导致社会舆论要么跟着歌功颂德,要么大唱反调。 迫于尖锐批评的压力, 执政者会形成政权不稳的忧患意识;目睹问题如山,社会大众则形成“君上无道”的忧患意识。 两种忧患意识都很强烈,但对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又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执政者应该正确认识、评价和宣传执政绩效,使得执政者和社会大众的忧患意识能够形成合力, 把注意力聚焦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上,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三)建立信息自由流通和共享机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一个人因为某些问题而产生深深的忧患,但不等于其他人也有这样的忧患。 对于即将降临到身上的灾难,有的人先知先觉,有的人后知后觉,有的人甚至浑然不觉,听而不闻,这都是正常现象。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有的人的忧患纯粹出于个人得失考虑,患得患失,而修养程度高的人也就没有相同的感受。 有的人因忧患而奋进,有的人因忧患而颓废。 有的人的忧患体现了卓识远见,有的人的忧患意识可能是杞人忧天。 然而,人们虽然可以从理论上清楚地区分各种忧患意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易进行这样的区分。 如果在政治上事先设定标准,对各种忧患意识进行有益与有害的划分,并且只鼓励有益的忧患意识,而严厉禁止所谓的有害的忧患意识,那么人们就会按照权力大的人的趣味来思考,这比之于让错误的忧患意识流行,是更值得人们共同忧患的事情。
政治上另一种常见的妨碍忧患意识形成的弊病,是执政者对信息的封锁和分级传递,以及在不能封锁的时候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被封锁的信息肯定是执政者认定为有害的信息,只在一定级别的人员中传递的信息大多也属于这种情况。被加工过的信息,被认为是对执政者最少损害的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不能说执政者没有忧患意识,而是一言一行都浸透了忧患意识,但这种忧患意识越强烈,就越容易阻断后续的忧患意识。 因为它割断了执政者的忧患意识与社会大众的忧患意识之间的依存关系,使执政者的忧患意识失去了持续生长的肥沃土壤。 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依然能形成自己的忧患意识,这样,一个国家的忧患意识就出现没有交集的两种形态,而不能与社会一起脉动的官方忧患意识,若转化为政策和法律,是难以收到预期治理效果的。所以,“对沟通的有效管理如同处理危机本身一样重要”[3](P30),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共享,对于忧患意识的持续性和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政治需要有忧患意识,而且需要的是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忧患意识。 诚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中所言:“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政治的忧患意识,应该是对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忧患,而不是对个人得失的忧患。 毛泽东也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4](P1128)因此,对于执政忧患意识的研究,应该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执政者具有并保持忧患意识,即忧患意识的有无问题,解答的是“忧患意识是必要的”这个命题;二是如何使忧患意识在治理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即忧患意识的质量问题,解答的是“什么样的忧患意识是必要的”这个命题。我们党一直重视忧患意识等执政意识的建设,从历史的角度总结执政忧患意识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找出提升执政忧患意识质量的一般规律,可以为我们党执政意识建设的具体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6/30/c_126691978.htm,2014-06-30.
[2]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 迈克尔·里杰斯特.危机公关[M].陈向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