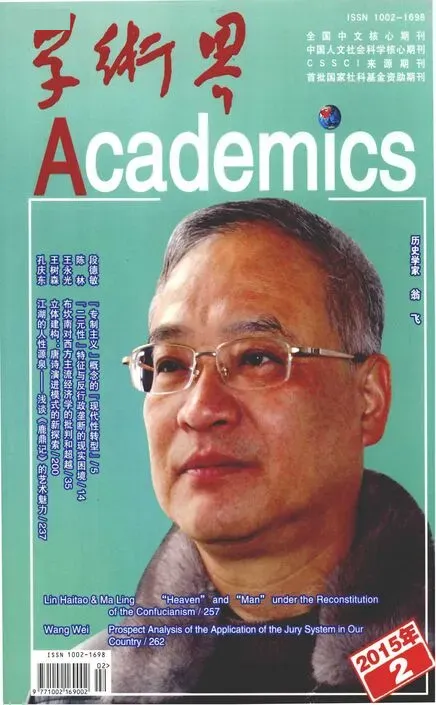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专制主义”概念的“现代性转型”〔*〕
○段德敏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近年来,对“专制主义”(despotism)这一政治、历史概念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代表作品有常保国《西方历史语境中的“东方专制主义”》、〔1〕王义保《专制主义的概念溯源》、〔2〕许苏民《“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3〕等等。但目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分析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之上,“专制主义”概念本身在西方思想源流中的转变、特别是它在近代的关键转型却甚少被论及。孟德斯鸠作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可以说大致继承了传统的对专制主义的理解,但他的政体分类学说中的“专制主义”概念已然超出“东方”的范畴,成为西方世界内部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虑的政体类型。而在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那里,这一概念则发生了更为彻底的“现代性转型”:一方面,他接受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的定义;但另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古典时代以来的专制主义概念在理解和批评现代政治方面正失去意义,现代社会自由政治生活的反面不能再用传统的专制主义来定义和描述。为此,托克维尔发明了“新专制主义”或“民主时代的专制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认为现代人应该警惕的政体形式。正是在这一概念发展的基础上,托克维尔提供了审视我们在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理论视角。
一、专制主义:从古典到近代
在我们今天的一般语境中,专制主义几乎总是与民主相对,而区分二者的关键也与统治者的人数有关。民主一般被认为是多数人的统治,而专制主义则指向一个人的统治,因此专制又与“独裁”含义相近。在这一点上,西方和东方的语境似乎并无太大不同。然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或政治理论中,这些术语则有其特定的渊源及特定的含义。例如,在西方古典时期,“专制”(despot)和“独裁”(dictator)二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含有贬义,而后者则不仅不含贬义,反而是正当政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如西塞罗即称罗马的“独裁官”为“至高无上的勇敢者。”〔4〕而根据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的论述,独裁官是古罗马共和国宪制范围内的制度安排,它通常是在紧急状态下(如对外战争时)设立的职位,该职位拥有最高权力,且无需为其任期(通常为六个月)内的行为负法律责任。〔5〕同样,“专制主义”这一术语也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具有其特定的意涵。
“专制主义”的概念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统治的种类与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无关,主人对奴隶的统治、父亲对子女的统治以及君主对其臣民的统治,三者虽然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人数上相似,但它们在种类上完全不一样。在讨论政体的分类时,亚氏所指的显然是城邦的统治形式。首先,按照城邦统治者的人数,可以划分为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其次,按每一种统治是否照顾到城邦整体的公共利益,每一种政体又可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的政体大致可以分为六类:在以全城邦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正宗政体中,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在只照顾统治者们利益的变态政体中,有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换而言之,僭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变态形式,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变态形式,平民政体是共和政体的变态形式。〔6〕
我们经常会将僭主政体(tyranny)和专制(despotism)相混淆,但即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也已经能够看到这二者明显的区别。僭主政体是城邦中一个人的统治,与君主政体不同的是,这种统治只以统治者一人的利益为依归,而不顾及城邦的公共利益。因此,它实际上是对君主政体的否定,或对君主政体统治形式的违背状态。僭主违背的是城邦的公共利益,因而含有强烈的贬义。无论是从合法的君主转化而来,还是通过夺取权力而来,僭主一律被视为“不合法”的统治形式。然而,亚里士多德关于“专制”的分析却存在于他对君主政体的具体分类之中;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专制政体可以算作“合法”的政体形式之一,这一点恐怕是我们今天的读者难以料到的。在亚氏那里,君主政体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拉根尼(斯巴达)政体,其斯巴达王实际上是军事首领;野蛮民族的君主政体;民选总裁(“艾修尼德”)式君主政体,即经过民意推举的君主;史诗(英雄)时代的王制,王位由父祖遗传于子孙;最后一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由一人代表整个氏族或城邦,全权统治全体人民的公务,接近于家务管理。〔7〕
在这一君主政体的分类中,唯有第二种属于“非希腊的”野蛮民族。亚里士多德称它类似于僭主政体,但又有所不同。二者主要的不同在于,这一“野蛮民族”的君主政体尽管主要以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但它“也出于成法,列王都是世袭的”。换而言之,与僭主政体不一样的是,这一政体并不是“不合法”的状态,而其臣民也自愿接受这一统治。如何会有这种区别?亚里士多德解释道,这是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8〕与此相应的是,作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形式,僭主的统治“出于篡夺”,通常是非常不稳定的,需要时刻“防备着本邦的人民”,因而经常要把自己寄托于外邦的雇佣兵。而“野蛮民族”的君主政体则在这方面顾虑较小,因为人们往往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君主的统治,尽管君主对待臣民如同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此对“野蛮民族”君主政体的描述正是后来西方政治学语言中“专制主义”这一概念的来源。而专制主义与僭主政体的区别也正在于前者是属于希腊以外民族的依成法的主人对奴隶的统治,而后者则是违背公共利益的非法状态。
这里“僭政”和“专制”二者在古典意义上的区分还可以从它们各自所含的贬义程度上看出。根据马里奥·突希提(Mario Turchetti)的考证,“专制者”(despot)一词本身在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语言中所含的贬义在程度上比“僭政”要小很多。如在西塞罗那里,与其接近的词是“dominus”,而该词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体系中只是主人的意思,并未直接表明这一主人是好还是坏。而“僭主”一词则不一样,起码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该词便一直包含强烈的贬义,象征着统治者对人民合法权利的侵犯。而自西塞罗以来,这种“侵犯”逐渐被看作是对自然法或人们的自然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专制”或“专制主义”则逐渐与亚洲民族联系在一起,这种统治形式类似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但人们却倾向于接受这种统治,正如罗马共和国中的公民在某一时刻自愿接受某个“专制者”的统治一样,唯一的不同只在于,前者开始包含强烈的贬义色彩。〔9〕
在近代西方,对“僭政”和“专制”作最清晰而明确区分的恐怕当属让·布丹,他在《共和六书》中说,“僭主式的王权政制是那种将自然法践踏在脚下、摧残人民的天然自由的政制。”〔10〕而专制王权则是来自于正义战争中一国对另一国的征服,其结果是被征服国的人民沦为征服国的奴隶,并任由后者处置,但这一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合法”的。反之,如果奴隶是由不正义战争中获得,则对他们的统治则不是专制,而是僭政。〔11〕布丹对僭政和专制作了法律意义上尽可能清晰的区分。但总体而言,正如突希提所说,专制主义长期以来存在于西方世界对东方君主政体的想象中。亚洲的民族似乎缺乏反抗的精神,而更趋于自愿接受主奴统治。因此,“专制主义”可以说位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的“边缘”,它代表着一种政制的可能性,但它典型地存在于东方。在西方世界,人们更多地面对的是合乎自然法的王制和违反自然法的僭主政体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似乎很少会出现在东方式的专制主义之中,而这也正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之所由来。〔12〕
二、孟德斯鸠与专制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基础:一是“古典”,即其专制主义的概念基本是古典式的;二是“东方”,即其范围仅限于西方人想象的东方。在这一方面,近代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立场颇为重要:他既大致继承了这一专制主义想象,又对其有关键的突破。如果说在孟德斯鸠之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家通常把专制主义当作政体分类的边缘形态的话,孟德斯鸠则非常明显地将其正式纳入政体的分类之中。其中原因与十八世纪欧洲王权的绝对化和甚嚣尘上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这一大背景不无关系,孟德斯鸠明确地将专制主义归为各类政体中最极端、最坏的一种,无疑有一种挑战时风的姿态。换而言之,孟德斯鸠试图用以往仅限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来衡量当时的西方政体,这在当时来说是颇具挑战性的。
孟德斯鸠对古典时代的政体分类学说作了大量修正,以适应当时已经开始现代化的政治生活。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将主要焦点放在了君主制和专制主义的区分之上,而这两种政体又都是在疆域广大的国家中的政体,其中的君主制与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君主政体已不可同日而语。亚氏的政体分类仅限于城邦范围内,而孟德斯鸠所面对的则是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各大王权国家。相应地,在古典时代的城邦中,如果说人们有充分理由期待各种政体之间发生转变的话,〔13〕那么在近代的欧洲,君主制向平民统治政体——即民主制——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国家基本都是以贵族等级体系为基础的极为稳固的君主政体。因此,孟德斯鸠的新的政体分类方法也显得顺理成章。在他那里,君主政体的反面是专制主义,僭政似乎并无存在的必要,因为这一时期的人们并不生活在可以轻易召集公共集会的城邦当中。当路易十四称自己为太阳王、宣称“朕即国家”时,他是僭主还是专制者?事实上已经很难区分,因为他既成为国家的“主人”,又颇得人们的承认。孟德斯鸠认为更清晰的政体分类应该将专制主义作为坏政体的理想型。君主国广大的疆域和森严的等级使得人们可以轻易服从一个专制统治者,尽管“僭政”(Tyranny)一词仍然还存在于欧洲政治语言之中,起码在孟德斯鸠那里,君主制最重要的对立面已经变成以往只存在于东方的专制主义。
孟德斯鸠将政体的要素分为性质和原则两类,政体的性质是指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14〕按性质分,“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15〕为了与欧洲的君主政体区分开来,孟德斯鸠强调专制主义中“无法律又无规章”的状态,但在他所列举的专制主义国家的例子中,无论是在当时的土耳其,还是其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中的波斯,国王对臣民的统治始终都存在一定的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与欧洲君主制下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不一样。换而言之,孟德斯鸠强调欧洲君主制国家中“法律”实际上处于统治地位,即便君主也需要遵守法律,这是它与专制主义相区别的关键之处;专制主义国家中的君主则在法律之上,无需遵守任何法律。是不是接受法律的统治成为孟德斯鸠区分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一个标准,但这显然不是全部。这里的法律只是制度意义上的规则,而人们心中的法度才是孟德斯鸠要讨论的重点,即人们在心中是否接受统治者为合法,如果合法,它又是哪种“合法”?这里就需要引出孟德斯鸠对政体原则的论述。
著名政治理论家茱迪斯·史珂拉(Judith Shklar)认为对政体“原则”(principle)的分析是孟德斯鸠政体学说的重点,原则对政体来说相当于灵魂之于人。〔16〕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起来的人类的感情”,〔17〕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意识形态是在社会之外为社会提供指导性原则的思想体系,而政体的原则直接指向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以城邦为背景的民主共和国和贵族政体中,政体的原则分别是美德(virtue)和节制(moderation),分别指的是公民对其祖国的爱和贵族团体在统治时对自己行为有意的限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honor),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fear)。荣誉在君主政体中与地位、品级联系在一起,人们要求优遇和高名显爵,这一方面强化了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一个君主和臣民都需要服从的“法则”,即荣誉的法则。孟德斯鸠说,暴君不知道什么是荣誉,“只有在有固定政制、有一定法律的国家,方才谈得上荣誉。”〔18〕因此,荣誉主要指向臣民在君主面前的独立性,〔19〕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权力受它的动力的限制。……荣誉像一个皇帝,统治着君主,又统治着人民。”〔20〕对专制政体而言,“品德是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因为荣誉意味着在君主权力之外还存在其他的相对独立的权力,它会形成对专制统治者的直接的挑战,继而会引起动荡和冲突。因此,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国家的君主为维持稳定,必须使人们心中充满畏惧。“当君主有一瞬间没有举起他的手臂的时候,当他对那些居首要地位的人们不能要消灭就立即消灭的时候,那一切便都完了。”〔21〕
尽管孟德斯鸠与布丹及其他思想家在描述“专制主义”的细节上有许多不同,显然他们都将专制主义看作持续性的主人对奴隶的统治状态。在孟德斯鸠那里,欧洲君主国中的君主与其臣民之间虽有上下等级关系,但臣民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臣民和君主都需服从共同的法则,这在《论法的精神》所描述的英格兰政制中体现尤甚。而专制国家中的君主则几乎“拥有”臣民的人身,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主奴关系相差无几。这也是为什么在“专制政体的教育”一节中,孟德斯鸠说,“君主国家的教育所努力的是提高人们的心志,而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了。”〔22〕在这种主奴关系中,主人可以为所欲为,也就是说他不受任何制度意义上的限制,但主人往往在奴隶心中具有某种合法性,甚至神圣性;另一方面,奴隶往往“承认”主人对他的统治合法,这也正是为什么主奴关系以至专制主义政体经常能长久维系的原因所在。
在《论法的精神》中,专制主义的主要例子是当时的土耳其,而在《波斯人信札》中,专制主义则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得以展现,小说的主人公——波斯贵族乌兹别克与后宫中的夫人及仆人之间关系即可被理解为孟德斯鸠对东方式专制主义的想象,乌兹别克对其后宫的占有和其夫人们心中时刻存在的恐惧感是相辅相成的。乌兹别克需要以恐惧保持其后宫对其绝对的忠诚,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以暴力手段镇压任何不忠行为,但他最希望看到的则是他们的主动效忠,而其夫人们也确曾竞相争取主人对她们的宠爱。〔23〕正如葛罗拉莫·伊目布鲁哥里亚(Girolamo Imbruglia)所说,任何专制主义当中都会存在一定的“共识”(consensus),只不过这种共识是主奴之间的共识而已。〔24〕孟德斯鸠所警惕的正是,在欧洲进步的浪潮中,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堕入这种“共识”之中,自愿接受专制主义。
三、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
需要指出的是,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学说带有明显的贵族特征,其君主制和专制主义之间的区分也是以此为背景。英格兰的君主政体被他赞誉为唯一“以自由为直接目的”的政制,其中的权力的制衡机制也是其三权分立学说的典型。孟德斯鸠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权力的互相制衡,英格兰人民才得以获得“自由”,即一种“心境平安的状态”,不用担心一只抬起来的手会随时向他们挥来。〔25〕但这三个权力的设置——无论是君主还是上、下议院——无一例外都是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孟德斯鸠对此也非常清楚,他所描述的自由不是在身份上人人平等的自由,而是等级社会中权力的受限制和法治的确立。正是因为这一点,安娜琳·德·德恩(Annelien de Dijn)将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称为“贵族自由主义”。〔26〕相应地,在孟德斯鸠那里,专制主义也保留着这一“贵族”的色彩,它主要指一种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与其相对的不是以普通公民参与政治为基础的现代民主,而是权力受到制约的君主制。这一点在托克维尔那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言,孟德斯鸠的自由观是以身份不平等为社会背景,而托克维尔一方面继承了孟德斯鸠的自由观,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身份的普遍平等已是既成事实且不可逆转。〔27〕因此,在托克维尔那里,专制主义有了新的含义。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担心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专制的暴君,而是权力高度集中、统治细致入微的政府。在现代社会,由于身份上的人人平等,即便是最有野心的政治家也需要将政治权力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之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开头即指出,在现代社会,“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28〕但人民主权的至上性并不代表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会自动受到制约,更不能保证政治生活的自由和开放。恰恰相反,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的身份平等和人民主权为另一种形式的奴役作了准备,这种新的奴役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不同,但其对自由的否定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界通常对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颇为重视,但事实上纵观托克维尔主要著作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才是其分析的重点。然而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多数的暴政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的孤独的个人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因而在多数的判断面前往往无能为力。〔29〕身份的普遍平等一方面使个人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另一方面却又使其无所依凭,成为“原子式的”个人。这种个人表面上独立,但在社会关系中却软弱不堪,很容易被“多数”或“集体”这样的存在所左右。事实上,同样的个人也会轻易地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屈服。在托克维尔看来,个人无法承认其他具体的个人比自己更为优越,但却会轻易地服从于非个人化的、社会性的权力。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正是因为这种代表关系,它才获得任何传统的王权都无法获得的权力。传统欧洲的王权代表的是上帝的意志,但上帝的意志的解释权却主要在教会手里,因而王权很难充分绝对化。但正如托克维尔研究专家卢西安·若姆(Lucien Jaume)所说,在现代社会,人民的意志在政治领域取代了上帝,〔30〕国家权力因此也很容易变得至高无上、不受限制。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专制主义的分析正是以此为基础。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现代国家权力并不像传统的专制主义那样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依归。相反,它往往以为人民谋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直接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国家权力一般也不会以残暴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相反,其统治形式往往温和而有耐心。然而,在权力的绝对性方面,它并不输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因此也很难说人们有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托克维尔说,这种压迫“与至今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压迫均不相同,……我曾试图用一个词精确地表达我对这种压迫所形成的完整观念,但是徒劳而未成功。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词汇,都不适用。”〔31〕托克维尔称这种专制主义为“新专制主义”(new despotism)或“民主时代的专制主义”(democratic despotism),他这样描述这种专制主义的特点: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32〕
因此,在托克维尔这里,这种新专制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父权”,而且是父权中最坏的一种,即“把人永远看成孩子”的父权。传统的专制权力并不会以经济的发展、国家生产总值的提高为直接目的,但现代国家权力往往以此为主要诉求。然而,新专制主义之下的国家却将其统治下的人民看作不能参与政治事务的孩子,父母可以为孩子谋取利益,但不能让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管理。显而易见,这种新专制主义在国家权力的绝对性之外,另一核心特征即是公共政治生活的不存在。在贵族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是贵族阶层,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另一方面也正在于除君主以外其他贵族也会有效地参与政治。但在现代社会,身份的平等并不能保证人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热情。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是双向的:一方面,国家权力并不希望人们的政治参与,甚至会积极地防止人们过问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人们往往也倾向于将政治生活看作负担,而更愿意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追求物质利益、享受私人生活。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批判即人们过分沉溺于物质享受,贵族社会中的追求伟大和崇高的精神则很难找到。平庸的性情和过度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使得现代人很容易匍匐在专制的国家权力脚下,将影响和决定人们命运的政治权力交给国家,失去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
托克维尔对新专制主义的这种分析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重要特性。当然,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尚难看到下一个世纪的极权主义灾难,“新专制主义”的概念与极权主义也绝不相同,但他对人民主权基础上的绝对国家权力和公共政治生活之消失二者相结合的描述,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极权主义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贝马斯在回顾极权主义出现前的政治社会时说,当时的国家“一切为了民众,然而一切都不通过民众”〔33〕。这一总结与托克维尔的判断不谋而合。保罗·拉和(Paul A.Rahe)将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新专制主义描述为一种“软专制主义”(soft despotism),并认为这种软专制主义将永远是现代社会的阴影。如何防止这种专制主义?拉和引用托克维尔说道,“人们朴素而崇高的、为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社群的利益负起责任的欲望”是对付软专制主义唯一的堡垒。〔34〕
四、结 语
正如当代政治哲学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所说,政体区分的意义和受重视的程度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来呈逐渐消减的趋势,绝对的国家权力成为安全和秩序的保证,而不是对它们的威胁。〔35〕如果说孟德斯鸠还直接使用亚里士多德式的政体分类方法的话,托克维尔恐怕是十八世纪以来少有的仍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一传统影响的思想家。政体分类的意义不在于分类和识别本身,而在于对不同的政治生活之可能性的想象,它使我们能够在现有的政治生活之外,用另一种类型的政治生活反思和批判现有的政治生活。专制主义则是这种政体分类中的特殊一类,它在西方古典时代以来的很长时期中代表着东方的特殊的政治生活,但在孟德斯鸠那里,它以新的面目正式成为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之一,成为与自由政体直接相对立的政体。而托克维尔笔下的专制主义则增加了人民主权和身份平等的内容,专制主义描述的不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把人永远看成孩子”的父权。从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现代性转向,现代社会的自由的反面不再是传统的专制统治,而是新的专制主义。
注释:
〔1〕常保国:《西方历史语境中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王义保:《专制主义的概念溯源》,《学术论坛》2008年第6期。
〔3〕许苏民:《“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4〕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3页。
〔5〕Andrew 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9-111.
〔6〕〔7〕〔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译书馆,1997 年,第132-134、158-161、159页。
〔9〕Mario Turchetti,“‘Despotism’and‘Tyranny’:Unmasking a Tenacious Confus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Vol.7(2),2008,pp.159-181.
〔10〕〔11〕Jean Bodin,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trans.,M.J.Tooley,Basil Blackwell,1955,pp.61,57.
〔12〕关于东方式的专制主义的讨论,还可参见 Franco Venturi,“Oriental Despot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24(1),1963,pp.133-142.
〔13〕易宁:《论波利比乌的“政体循环”说》,《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
〔14〕〔15〕〔17〕〔18〕〔20〕〔21〕〔22〕〔2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9、8、19、20、28、26、33、155页。
〔16〕Judith N.Shklar,Montesquieu,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75.
〔19〕因此,如将法文原文honeur翻译为“荣宠”远不如平实地翻译为“荣誉”来得准确,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23〕Montesquieu,Persian letters,trans.,John Davidson,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1891,pp.41-48.
〔24〕Girolamo Imbruglia,“Two Principles of Despotism:Diderot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de la Boëtie,”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Vol.34,2008,pp.490-499.
〔26〕Annelien de Dijn,“Aristocratic Liberalism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The Historical Journal,2005,Vol.48,No.3:pp.661-681.
〔27〕Raymond Aron,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Vol.1),trans.Richard Howard & Helen Weaver,Garden City,New York:Anchor Books,1968,p.244.
〔28〕〔29〕〔31〕〔3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64、287-290、869、869页。
〔30〕Lucien Jaume,“The Avatars of Religion in Tocqueville,”in Creating God:Sovereignty and Religion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ed.by Miguel Vatter(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1),p.280.
〔3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34〕Paul A.Rahe,Soft Despotism,Democratic Drift:Montesquieu,Rousseau & the Modern Prospect,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279.
〔35〕Pierre Manent,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trans.,Rebecca Balinsk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1.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Rationale for Banking Regulation〔*〕
- Approaches to Legalize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lish Teaching Model in China〔*〕
-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Language”——the Regional Linguistic System:Developing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 On the Systematic Dynamic Teaching Experiment of College English〔*〕
- The Explanation of the Vernacular Words in the Dunhuang Li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