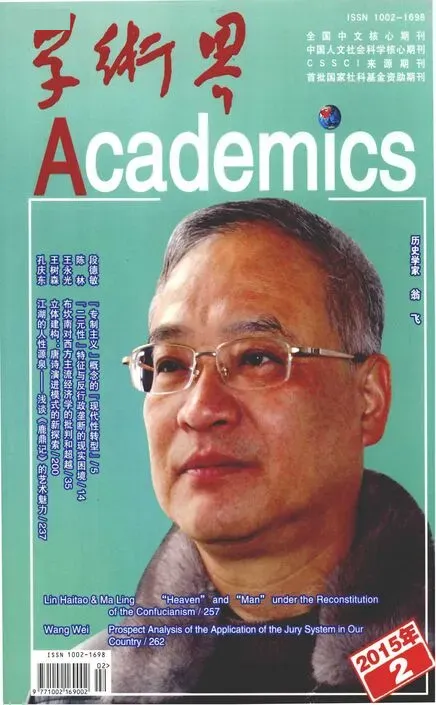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二元性”特征与反行政垄断的现实困境〔*〕
○ 陈 林
(1.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一、引 言
反行政垄断是当前反垄断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经济宪法”〔1〕,《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以整个第五章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可见反行政垄断是我国经济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至有学者〔2〕认为:反行政垄断是整部《反垄断法》的重中之重,没有反行政垄断的条款,反垄断法就会变成“无牙老虎”。
然而《反垄断法》于2008年生效至今,反行政垄断工作开展得甚为缓慢,行政垄断案件数量寥寥无几,甚至找不到原告胜诉的案例。较典型的案例是,北京兆信公司等四家防伪标识企业于《反垄断法》生效当天〔3〕起诉国家质检总局。但司法机关并没有援引《反垄断法》的法律条文,而是沿用行政法条文驳回原告的起诉。在一宗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却依据行政法进行判决,而非已然生效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不难看出,反行政垄断的推进举步维艰。
既然国家“坚决反对”〔4〕行政垄断,为何却会在反行政垄断的实际推进中遇到困境?本文认为,反行政垄断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垄断的两个“二元性”特征。其一是,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既有统一性,也有对立性,即行政垄断的市场经济“二元性”;其二是,行政垄断同时受行政法和《反垄断法》规制,这些法律之间的矛盾既有统一性,也有对立性,即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二元性”。在王俊豪和王建明〔5〕提出的垄断性行业的垄断“二元性”基础上,本文将上述两个特征归纳为行政垄断的“二元性”。
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对立统一性,厘清《反垄断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与行政垄断权力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监督机制,分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对立统一性,从而揭示反行政垄断工作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制建设与垄断性行业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二、行政垄断的市场经济“二元性”
由于垄断具有“二元性”,破除行政垄断就必须根据垄断性行业的垄断“二元性”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的分类规制手段。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使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6〕。而竞争和交易正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特征,如《易经》解释汉字“市”的说辞“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行政垄断通过限制竞争,阻碍资源遵从市场规律的流动,从而干扰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性。但由于渐进转轨的国情约束和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容许行政垄断长期存在,二者还存在统一性。
沿此思路,本文将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之间对立性和统一性并存的现象,称之为行政垄断的市场经济“二元性”。行政垄断的这种“二元性”将长期影响反垄断法制建设,同时对垄断性行业的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行政垄断市场经济的“二元性”往往更多地表现在理论层面,时刻影响着政府、企业和个人对行政垄断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对反行政垄断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
1.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
行政垄断限制了竞争,它似乎走到市场竞争的对立面。没有竞争,市场再也不能把资源配置到最高效率的企业和最需要这种产品的消费者手上,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自然受到损害;没有竞争,市场也不能促使企业采用最有效的生产技术,并保持最低的成本和价格水平。
行政垄断确实损害了市场的竞争活力,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合法的行政垄断〔7〕却是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因为,我国的市场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可以保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行政垄断自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行不悖。
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不止于此。从历史经验来看,激进转轨国家在改革之初就通过立法、司法彻底消灭行政垄断,反行政垄断是国有经济改革的孪生儿;渐进转轨则不然,它允许行政垄断的长期存在。根据陈林和朱卫平〔8〕的经济史研究,我国的行政垄断制度演化与国有经济发展史基本同步,行政垄断在建国之初便与国有经济共生共存。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制度也并没有随国有经济改革和私营经济发展而消失,反而日渐成熟。转轨时期的行政垄断制度是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不变,与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相辅相成。这是今后我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与垄断性行业改革中的主要路径依赖。
总之,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长期共存,二者之间的矛盾存在统一性。
2.行政垄断与市场竞争的对立性
一面是限制竞争,一面是社会合意,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损害市场竞争活力的行政垄断却有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如此独特的逻辑底下,社会到底该如何看待行政垄断规制下的市场竞争?本文对此的基本判断是,行政垄断下的市场并非市场的常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容许行政垄断的存在,其理由如下。
行政垄断离不开行政权力,它是一种基于行政权力的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在亚当·斯密刚发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年代几乎不存在。当时的人们一直认为市场运行得那么完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与交易使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达到高度统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一些人们当时难以理解,更无法解决的市场问题的出现,社会对市场的赞美与信仰一下子变为抱怨与害怕。人们奔走相告: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经过多年研究的确发现:不完全信息、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客观存在且难以克服的经济现象既是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市场似乎不再完美。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支持政府干预市场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思潮不断涌现,政府干预正式步入历史和经济学史的大舞台。
关于“市场失灵”的定义和衡量标准,西方经济学已达成基本共识。厉以宁〔9〕认为,对于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不能起作用或不能起有效作用的情况即市场失灵。一些经济学教科书对市场失灵作出更为明确(从数学上)的界定——对资源配置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价格P大于边际成本MC的市场〔10〕;损害经济效率的市场〔11〕;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12〕。从国内外常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本文不难归纳出市场失灵的确切定义——当一个市场实现不了完全竞争状态下的P=MC,该市场产生的社会总福利(消费者剩余加企业利润)必然小于完全竞争市场,市场的经济效率受到损害;完全竞争市场所能实现的社会总福利在已知的所有市场形态中最大,一旦偏离这样的最优状态,市场便失灵了。
完全竞争市场不仅需要完全信息和零外部性,它更需要很多企业参与竞争。完全竞争市场上必须有许多买者和卖者,以至于每个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企业数量无限多,价格P才会接近边际成本MC,社会总福利才得以最大化。然而,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发展与创新,它们往往未能等到足够多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就已经步入衰退期,完全竞争直至产业消亡还未能出现。完全竞争跟绝对垄断(一家企业、没有竞争)一样,都是市场极其罕见的极端情况,绝大多数市场都以某种程度的、但却不完全的竞争为特征。甚至可以说,完全竞争只是市场本身永远实现不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的市场一定是不完全竞争市场。
不完全竞争损害了社会总福利,不具有完全竞争市场所具备的全部社会合意性。但这种无效率是模糊且难以衡量的,也难以解决——政府干预不可能改善这种市场结果。对于市场竞争,社会关注的不应该是它能否把社会福利和总产量提升到极致,而是如何在市场“天生”失灵和竞争“天生”不完全的情况下,使社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有限家企业参与竞争并获取一定经济利润(P>MC)的不完全竞争是市场的常态。
或许会有人据此推断:既然有限家企业参与竞争的市场是合理的,那么以控制在位企业数量、限制市场竞争为目标的行政垄断自然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产业规制手段。本文对此不以为然。
诚然,市场做不到出现无限多竞争企业的完全竞争状态,但市场本身是“天生”地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存在超额经济利润(价格P大于在位企业的边际成本MC),市场上就必然会有趋利的企业家、投资者创办企业,进入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在位企业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市场价格不断降低,单个企业的经济利润日益减少。社会总福利从绝对垄断的最小值逐渐往完全竞争的最大值靠拢。自由进入或者说自由竞争,是市场“天生”具备的竞争活力——经济利润导致新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加剧反过来减少企业利润,趋利的市场进入行为成为经济利润的自动调节器和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催化剂。
一旦出现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干预,这条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就被外生变量打断。在行政垄断保护下,无论市场价格多高,不管在位企业攫取了多少经济利润,甚至只有一家国有企业专营专卖,潜在进入企业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唾手可得的大量利润擦肩而过。缺乏选择余地的消费者同时只能接受高价格。新企业不能加入市场,市场因而缺乏竞争活力。这一切并非因为那支“看不见的手”出现失灵,而应该归责于另一支“看得见的手”限制了市场竞争。
政府控制了在位企业数量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度,使竞争本来就不完全的市场更加缺乏竞争,市场竞争活力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这意味着:行政垄断只会加剧市场失灵,而非克服市场失灵。如果把企业可以自由进入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比作一个考试总不能拿到满分的学生,那么行政垄断下的市场则是一个被强迫交出一份60分甚至不及格答卷的学生。竞争市场尽管不能实现完全竞争这一“满分”的理想状态,但新企业不停地加入竞争行列,至使市场带来的社会总福利不断提升。竞争市场总是向着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全竞争状态)发展。行政垄断却杜绝了市场往如此“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使坏的更坏,使本来可以更好的好不了。既然不完全竞争是市场的常态,常态下的市场又“天生”失灵,这个社会怎么能够因为市场实现不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而反对它,怎么能够因为市场拿不出满分答卷而消灭它?更不幸的是,以行政垄断限制竞争只会使市场竞争更加不完全,行政垄断只会在后天进一步加剧市场失灵。
总之,行政垄断损害了市场的竞争活力,它与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的对立性。
3.行政垄断与社会公平的对立性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行政垄断却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产生了冲突,甚至直接损害了社会公平。
一个社会必须关注公平,但却不代表实施行政垄断就可以得到公平。反倒是市场经济本身有能力给人类社会带来公平。自古以来,人们在市场中自由地选择职业和社会分工,你情我愿地进行交易,在同一市场规则下参与公平竞争。市场从来不会强迫某人必须从事指定职业,更不会禁止人们生产某种产品。因为只要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足够价廉物美,就一定可以找得到属于自己的交易对象。市场本身永远不会限制竞争。市场竞争因而会给社会带来公平——每个人都在竞争市场中体现自我价值,在同一游戏(博弈)规则下平等地争取利益最大化。
为保护市场的竞争活力和公平竞争,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致力于消除经济性进入壁垒、限制兼并、分拆寡头企业。促进竞争、维护公平竞争是俗称“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所必须具备的本分职责。即使是转轨国家,其反行政垄断的力度也不容小视。如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仅在1994年就依据《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查处了22起行政垄断案件,其中就包括国家铁路管理局限制私营企业进入货物运输市场的行政垄断案件〔13〕。而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则依据《竞争法和限制商品市场的垄断活动法》,分别在1994年、1997年和1998年查处了881、1400、1737件行政垄断案件,大概占到全部垄断案件的四分之一左右〔14〕。
正因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与反垄断法的公平性,我国才会出台旨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法》。反观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它不可能创造公平,反而只会损害公平。过高的市场价格和额外的经济利润只造福少数受行政垄断权力保护的在位企业,伤害的却是全体消费者与没有特权的企业及其职工。根据吴敬琏提供的数据,2008年我国垄断性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关于行政垄断对社会公平的危害,主要研究包括学者刘小玄〔15〕、姜付秀和余晖〔16〕、张原〔17〕等,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总之,行政垄断损害了社会公平,与以公平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的对立性。
三、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二元性”
在现行法制体系中,行政垄断同时受一系列行政法(如《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及《行政复议法》等)与“经济宪法”《反垄断法》的规制。这两个法律体系的目标具有一致性——规范行政行为,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18〕。但实际上,两个法律体系在具体司法操作中,却出现了很多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反垄断法》的法律效力受到一系列行政法的干扰,导致其法律位阶低于行政法,是近年来行政垄断案件几近于无、反行政垄断工作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对于行政垄断,行政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矛盾同时存在统一性和对立性,本文将之归纳为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二元性”。
1.赋予行政垄断合法性的行政法体系
2004年前后,我国行政法体系随陆续出台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等而日渐成熟,行政权力的使用逐渐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尤其是在2004年7月,由全国人大制定的《行政许可法》正式生效。
对于行政垄断,这种冲击或者说变化尤为明显——行政垄断开始受到法律保护。《行政许可法》从法律的高度给行政垄断赋予合法性。该法第十二条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事项,行政机关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几乎在《行政许可法》生效的同一时间(2004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政策及其附件《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规定了我国哪些产业、项目属于“重大和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市场准入必须进行行政审批。2004年9月,国家发改委“依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了部门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制定了详细的行政审批制度。
公民或法人若要在《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指明实行核准制的产业投资项目或进入市场,就必须按《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规定,“向政府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地方发改委)依据部门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进行行政审批、核准或备案。而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同样必须严格遵守《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等法规,由投资主管部门进行审批。此外,《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还规定:“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专门规定的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按有关规定执行”,即所有法律法规都可以设置行政垄断。
在《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其附件《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和行政法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家发改委也相应地制定出部门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配套完善。
依据上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企业进入特定产业参与竞争进行行政审批,是各级“投资主管部门”合法实施行政垄断的行政权力。
2.行政法与《反垄断法》的矛盾冲突
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后,《反垄断法》本应成为监督和制衡行政垄断权力的一部关键性法律。但《反垄断法》第51条“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却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即《反垄断法》规定:在行政垄断案件中,其它法律和行政法规适用优先。如果单纯从行政垄断的角度上看,《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行政法与《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等行政法规都成为了《反垄断法》的“上位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似乎是我国法制体系中行政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效力位阶关系——《反垄断法》的法律效力低于行政法。
在中国反行政垄断第一案“北京四企业起诉国家质检总局”中,由于《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做出最终裁决”,因此法人或个人对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垄断行为提起诉讼前,应该先经过行政复议。北京兆信等四家企业对行政垄断行为的不服没有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因而没有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资格。
但问题是,北京兆信等四家企业是依据《反垄断法》提起的诉讼,有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应该不影响这起经济纠纷案件的法律程序。最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三个月行政诉讼期限,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申请,不予受理该案。本文尽管没有看到该案的卷宗以及司法机关的相关解释,但根据《反垄断法》第51条,司法机关援引《反垄断法》的“上位法”《行政诉讼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该判决的合法性是理所当然的。
在行政垄断权力与当前法制体系下,公民在特定产业中创设企业和企业(法人)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权利被严格限制,在“禁止投资产业”甚至被完全剥夺。被行政行为约束的公民(企业家)和法人代表(企业或其他组织)即为行政相对人,掌握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则是行政主体。如果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绝对适当,行政行为就必定合情合理更合法。对于这样的行政权力,那些即将进入“核准”程序的企业自然无需担心会否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些审批不过关的企业也没必要抱怨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但是,由于行政权力的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及强制性特点,决定了它是最容易违法或被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19〕。现实中的行政权力完全有可能被滥用或使用不当。
为此,“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才会用整个第五章专门规制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由此可见,我国并不否认行政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尤其是用于限制竞争并涉及到部门、地方及企业的经济利益的行政垄断权力。然而,行政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矛盾对立性,对反行政垄断的司法工作产生严重的影响,以致于行政垄断案件基本上无法立案。《反垄断法》的法律效力受到损害,其反行政垄断功能当然也被束之高阁。
总之,现行的行政法体系与“经济宪法”《反垄断法》存在很多立法冲突,反行政垄断自然举步维艰,困境重重。本文认为,由于行政法与《反垄断法》的对立性,行政垄断与法律制度产生了“二元性”特征,这将成为今后推进反行政垄断工作的根本性制约。
3.缓和相关行政法与《反垄断法》对立性的有效途径
无论是在经济学理论中,还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竞争是市场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反垄断法》第一条)”也正是我国出台《反垄断法》的根本原因。但《反垄断法》正式施行已多年,它对行政垄断权力的制衡作用和对市场竞争的保护作用似乎还不够明显。在现行行政法体系、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的制约下,《反垄断法》能在反行政垄断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较为有限。
其实,关于我国的反垄断法应否规制行政垄断的争论在法学界由来已久,部分学者认为反行政垄断是宪法和政治体制的问题〔20〕。诚然,以上途径固然可以彻底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但所需的时日可能很漫长〔21〕。本文认为,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利用好已经完成立法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去保护公民从事经济活动和企业参与竞争的合法权利,并保证公民和法人免遭不合理、不公正的行政垄断权力之侵害。
一直以来,我国的司法机关一直缺乏对行政行为的公诉权〔22〕。为此本文建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既然作为《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之一,理应获得对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垄断行为的公诉权。例如,乌克兰中央政府的“反垄断委员会”依据《反垄断委员会法》的授权,具有高于其他行政机关的权力。该委员会在1994年就曾查处国家铁路管理局的行政垄断行为〔23〕。当然,如果检察机关可以在《宪法》赋权下,获得对所有行政机关的公诉权,司法体系就会出现针对行政垄断的“双重”司法监督。
本文同时认为:《反垄断法》第51条必须予以修正,行政法和由行政机关自己立法的行政法规不应该作为《反垄断法》裁决行政垄断案件时的“上位法”。行政垄断是现阶段垄断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只有修改《反垄断法》第51条,才能让《反垄断法》真正发挥出“经济宪法”的重要作用。也只有让《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传统意义上的司法机关检察院参与行政垄断案件,我国才会出现更多敢于维权的法人和公民,这种“扭曲竞争机制,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24〕的行政垄断行为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行政垄断的法制工作才会稳步推进。
四、结 语
行政垄断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法律制度存在统一对立的矛盾,这是我国反行政垄断遇到实际操作困境的根本原因。其中,前一个矛盾的理论性更强,亦更为复杂,并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因此我国难以在短期内消弭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对立性。对于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如何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科学有序推进反行政垄断工作,是值得经济学界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行政垄断与法律制度的矛盾,则更多地表现为关乎今后反垄断法制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意味着,在试图解决行政垄断的这两个“二元性”矛盾时,轻重缓急显而易见——完善反行政垄断的法制体系,减轻行政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对立性,提高《反垄断法》的法律效力与司法效率是当务之急。正如张曙光和张弛〔25〕所言——“通过反对行政垄断来推进改革”,反行政垄断法制体系的完善必将推动垄断性行业的体制改革进程。
当然,本文只涉及反行政垄断的经济学层面,仅为管中窥豹。行政垄断理论其实具有多种社会科学属性,如法学、经济学及行政学等。张曙光和张弛〔26〕曾从行政学角度为反行政垄断提出建议——要设置一个合理的反垄断机构,“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现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即现阶段主管并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等行政垄断法规的投资主管部门)改造成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如此提法不无道理,国家发改委正是当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单位,其主任一般兼任反垄断委员会副主任。
行政垄断理论与反行政垄断工作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各界学者都应在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文仅为引玉之砖,对这一交叉学科的进一步探讨有待学界共勉。
注释:
〔1〕“经济宪法”之称谓来自于学术界,亦曾被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的曹康泰在2006年6月2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的说明》报告引用。
〔2〕〔21〕王晓晔:《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反垄断法》,《东方法学》2009年第6期;Gordon Y.M.Chan,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the Anti-Monopoly Law:An Examination of the Debate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9,18(59):pp.263-283.
〔3〕浙江省名邦税务师事务所也于2008年8月1日起诉余姚市政府违法《反垄断法》,该案最后以原告撤诉告终。
〔4〕〔24〕安建、黄建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46、147页。
〔5〕王俊豪、王建明:《中国垄断性产业的行政垄断及其管制政策》,《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2期。
〔6〕张维迎、盛洪:《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载于季晓南:《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反垄断法研究系列丛书》,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胡鞍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反行政垄断也是反腐败》,《经济参考报》,2001-07-11。
〔7〕滥用行政权力的行政垄断行为当然不合法,但合理使用行政权力的行政垄断行为便为合法。正如王俊豪和王建明的观点:“行政垄断既可能合法,也可能披着合法的外衣(如出于部门利益的立法)实际上并不完全合法,或者虽然合法但不合理”;“行政垄断又可分为合理行政垄断和不合理行政垄断,这是行政垄断的两重性”。
〔8〕陈林、朱卫平:《经济国有化与行政垄断制度的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经济史研究》,《财经研究》2012年第3期。
〔9〕厉以宁:《西方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10〕麦克康耐尔、布鲁伊:《经济学》,李绍荣等译,北京: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11〕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斯蒂格利茨:《经济学》,黄险峰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12〕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13〕〔23〕王晓晔:《依法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14〕郭连成、刁秀华:《转轨国家的竞争政策与立法研究——以俄罗斯为例》,《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
〔15〕刘小玄:《收入不平等的政府根源》,《中国改革》2007年第11期。
〔16〕姜付秀、余晖:《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10期。
〔17〕张原:《行政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8〕如《行政许可法》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他行政法与《反垄断法》亦提出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八条)。
〔19〕孙广厦:《宪政视野下中国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0〕陈秀山:《我国竞争制度与竞争政策目标模式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史际春:《关于中国反垄断法概念和对象的两个基本问题》,载于《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沈敏荣:《法律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规则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温观音:《产权与竞争:关于行政垄断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
〔22〕如1954年版《宪法》只赋予检察院以“检察权”而非“公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1954年版《宪法》第八十一条)”,“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1954年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而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与《宪法》也未赋予检察机关以“行政公诉权”。
〔25〕〔26〕张曙光、张弛:《扩大开放与反行政垄断并重》,《决策与信息》2007年第4期。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Rationale for Banking Regulation〔*〕
- Approaches to Legalize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lish Teaching Model in China〔*〕
-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Language”——the Regional Linguistic System:Developing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 On the Systematic Dynamic Teaching Experiment of College English〔*〕
- The Explanation of the Vernacular Words in the Dunhuang Li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