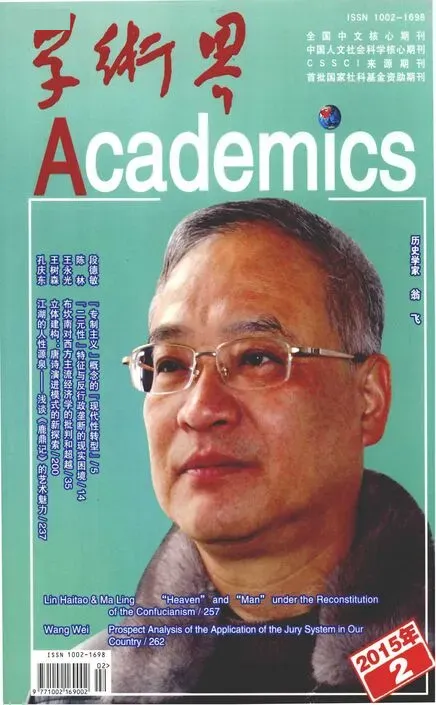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看《道德经》的英译〔*〕
○张小曼,胡作友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部哲学经典著作,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共81章。全篇虽只有五千余字,却包容甚广,不仅对哲学问题有系统的论述,而且对宇宙本源、万物变化、人生观、价值观等都有一定论述,对中国古老的哲学、政治、历史、宗教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铸成以及政治的统一与稳定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文主要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角度对《道德经》的英译进行研究,通过分析《道德经》不同版本的译文,探寻《道德经》翻译差异的影响因素,强调意识形态与诗学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为读者解读《道德经》译文提供新的视角,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及《道德经》的深刻内涵,使翻译研究摆脱纯语言转换模式的束缚,从而扩大翻译研究的领域。
一、《道德经》英译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道德经》的研究论著在英译本问世不久便产生了,主要是对老子思想和道家学说进行阐释或对《道德经》翻译策略和技巧进行说明。英语世界对《道德经》翻译研究较为深入的是茱莉亚·哈蒂和迈克尔·拉法格。茱莉亚·哈蒂〔1〕在对西方有影响的《道德经》翻译文本进行详细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将18世纪以来《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和形象变迁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中,西方对《道德经》的阐述带有明显不同的时代特色。迈克尔·拉法格和朱莉安·帕斯〔2〕撰写的《论道德经翻译》文中,从17个译本中取样,分析造成这些面貌不同的译文的主要原因。该文对《道德经》翻译的研究具有普遍影响,但只从西方的视角分析了文本解读中客观存在的差异,并没能对影响翻译的深层社会政治形态给予关注。美国金鹏程教授〔3〕曾批判这些不结合中国文化仅过度依赖于早期翻译的译本,由于语言的局限性从而导致《道德经》深刻内涵的简单化。
国内学者对《道德经》的研究较早。从中国知网上统计,近10年来大概有54篇相关论文。主要是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译本的分析与对比,关键字词的翻译,研究《道德经》文化意象的转换,运用某种理论研究《道德经》和综合研究《道德经》。魏志成〔4〕分析比较了《老子》的三个英译本,指出辜正坤的翻译更深刻地表达出了《道德经》中的哲理以及更接近于原文风格。郭燕〔5〕对《道德经》中“道”的翻译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指出“Dao”是最佳译法,因为“Way”过于简单化。王瑛〔6〕以Arthur Waley的《道德经》译文为例,把思维方式、语言和翻译三者结合,对中西方思维方式进行了探讨,论述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翻译从重视语言转换向重视文化转换方向发展的重要性。苗玲玲〔7〕指出译者主体性对《道德经》翻译的影响,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底本及注本的选择,对原文的理解以及由汉语到英语的转换过程。廖敏〔8〕运用阐释学原理分析了《道德经》翻译的多样性,她指出多样性的原因主要是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主体性。还有一些其他的作者例如邢怡和徐璐〔9〕把《道德经》中的文化元素与旅游翻译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很少有学者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道德经》的英译。
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
1.改写理论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勒菲弗尔和英国著名学者巴斯奈特共同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概念,突破了只注重语言文字层面转换的传统翻译研究范式,提倡从宏观文化层次来解读和分析文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勒菲弗尔指出,〔10〕翻译即是一种改写,或多或少受特定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诗学操控。为了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译者在改写过程中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或调整,因此译本不可能保持原作的面貌。勒菲弗尔还指出,翻译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语言转换行为而是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其中,诗学形态属于文学系统的内部因素,主要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控制;意识形态属于外部因素,由“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控制。
2.改写理论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对改写理论思想的介绍和批判性解读,这类文章主要关注改写理论本身;〔11〕第二类是改写理论的运用层面,这类文章主要以改写理论为框架分析其他文本。〔12〕他们普遍认为改写理论能够揭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宏观社会文化因素对改写的操控。但就改写理论到底包含两要素还是三要素,各学者分歧很大。如张南峰〔13〕认为是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蒋骁华〔14〕则认为是两要素: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还有人如郭建中〔15〕对勒菲弗尔的理论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深刻的评点,但没有明确列出要素。王峰〔16〕曾指出国内外学者都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进行了多种改写,也正是通过这些改写,勒菲弗尔的思想才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具有了深远的影响。
3.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
70年代以前,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以忠实于原文为最高标准,围绕着直译与意译进行探讨,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指导翻译实践的统一的、绝对的、公认的翻译标准,以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及钱钟书的“化境”为代表。〔17〕相比较这些传统的翻译理论,改写理论采用了描述性方法,增强了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度。不再注重一对一的对等翻译以及对原文的忠实度,而是从目的语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及赞助人角度解说译本的形成。将翻译活动置于文化背景下,以译文为中心,打破了原文本的权威地位。那么忠实于原文不再是翻译的最高标准,译本不存在好与坏,每一种译本都有其存在的道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大多都是经验之谈,而改写理论是在多元系统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更具有系统性,对翻译活动有更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道德经》英译的影响
1.意识形态对《道德经》英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 Destutt de Tracy)在1796年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体现。意识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也即观念形态。〔18〕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普遍存在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中,都有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其是由该团体所有成员共同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决定的。它反映了该团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
韦努蒂(Venuti)〔19〕指出,翻译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作为一种媒介,反映出译入语与原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定受到其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及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意识形态对《道德经》英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意识形态影响了译者对《道德经》内容的理解。译者在对文本进行解读时,必定会受到所处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影响接下来的翻译活动。从本质上说《道德经》的翻译应是道家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如《道德经》第一章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中的“道”是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中国学者如辜正坤在老子思想和道家学说的影响下,能深刻领悟此“道”的内涵。认为西方文学中没有能与此中的“道”完全精确的对等物。所以他们大多数都采用“道”的音译“Dao”和“Tao”。而西方学者多把“道”译为“Way”和“God”。因为他们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是全知全能的神。从这个意义上,与“道”的意义有相似之处。而“Way”则表达了西方人化“虚”为“实”的意识形态,“Way”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道路,“道”本身带有走之旁,与路有关,则“Way”自然带有一种直观的感受。
其次,意识形态影响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法国翻译家贝尔曼〔20〕指出,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选择的。《道德经》翻译的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译者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选用翻译策略的差异。如《道德经》第四章中:“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其意思是我不知道道是从哪里产生的,却知道道出现在上帝之前。亚瑟·威利将“帝”译为“the Ancestor”,同时加注脚进一步说明此“帝”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黄帝。威利选用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因为在西方人的潜意识里,“皇帝”和“上帝”是不能等同的,上帝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辜正坤则采用归化的方法,将“帝”译为西方文化中的上帝“God”。因为他考虑到西方的宗教和文化风俗,以便让读者更易接受和理解。
2.诗学对《道德经》英译的影响
关于诗学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学理论。《牛津字典》对诗学的定义为:“诗学是关于诗歌和诗作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诗学”的定义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勒菲弗尔认为,〔21〕诗学因素包括两个方面:(1)文学工具,其中包括文体范畴、象征,以及典型的场景和人物;(2)文学的角色:即文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Jean Delisle〔22〕也认为就方法论而言,翻译史家应该放弃从前的语言评估方法,而从原文历史和诗学再现着手研究。如果形式再现被忽视,那么原文的文学地位和诗学美感就会消失。一定的诗学传统,必定会影响译者的翻译方法,同时译文读者的审美爱好和译者本人的诗学修养及追求也对译者的翻译方法有着影响。
翻译诗学既是一种文学理论,又是一种翻译方法和技巧,涉及了翻译的很多方面,如诗歌的韵律和结构,文学翻译的可译性,忠实、语音和语法的对等与差异,古词和现代词汇的选择等。文学著作的表达诗学可能代表了原文化语言的传统,对译入语而言,由于诗学观的差异,可能会造成译者对原文有不同的解读。因此,《道德经》英译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受到诗学的影响。
诗学影响了《道德经》字词层面的翻译。汉语词汇不像英语单词,没有时态、单复数以及词性等的曲折变化。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变化,对于汉语词意的理解,往往需要译者的不断揣度。如《道德经》中“善”这个词,可以做形容词、名词和动词等,但它的发音和写法没有任何变化,再加上古汉语经常喜欢省略句子成分,从而使译者对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有了不同的理解,导致翻译的差异。如《道德经》第八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其中“心善渊”,威利则译为“If among thoughts they value those that are profound.”。他将“善”理解为动词“以……为善”,而将“渊”译为名词“depth”即“what is profound”。然而,辜正坤〔23〕则译为“he has a heart as deep as water”,则把“善”和“渊”译为两个并列名词“heart”和“water”。另外,通假字是古汉语中特有的现象,使用非常普遍。在一定程度上,给译者翻译带来了障碍。如《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里的“德善”通常被理解为“德是好的”,译为“Virtue is good”,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德”通动词“得”,意思为“得到了善”,译为“he gets goodness”。到底是名词“德”还是动词“得”,恐怕只有老子自己清楚。但是汉语的诗学特色影响了译者的翻译,从而造成了译文的多样性。
诗学影响了《道德经》句法层面的翻译。《道德经》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语言简洁凝练。文中经常使用三字句或四字句,构成对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但英语中却没有对应的句型。因此,为了传达出语义,译者不得不放弃句型上的对等。如《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威利〔24〕则译为:“To remain whole,be twisted!To become straight,let yourself be bent.To become full,be hollow.Be tattered,that you may be renewed.Those that have little,may get more.Those that have much,are but perplexed.”。译文明显没有原文三字句工整,也体现不出音韵美。由于受到英语诗学的限制,这种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汉语重“人称”,英语重“物称”。所以汉语主要使用主动句,而英语多用被动句。在英语语言中,凡是不必说出主动者、不愿说出主动者、无从说出主动者或是为了便于连贯上下文等场合都可以使用被动。如《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将欲翕之,必先固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威利〔25〕译为:“What is in the end to be shrunk,must first be stretched;Whatever is to be weakened,must begin by being made strong;What is to be overthrown,must begin by being set up.”。原文用主动语态,虽没有给出明确的主语,但并不影响我们阅读。在英译文中,主语物化了,语态也相应变成了被动语态。
四、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看《道德经》的误译
1.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误译
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中国人更加注重思维的形象性、整体性和主观性。而西方人则注重抽象性、分析性和客观性的特点。所以,中国人通常喜欢用一个具体的词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让读者更形象地理解,而这往往让西方译者误解,从而导致误译。如《道德经》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意思是知道刚强争胜,却柔和谦让。这里的“雄”是指“强劲”、“雄强”,“雌”指“柔弱”、“雌柔”,而并非指性别上的雌雄差异。威利却将其译为:“he who knows the male,yet cleaves to what is female.”,〔26〕译者受到自身思维方式的影响未能准确理解原文信息,从而导致误译。这不仅让读者读起来茫然,而且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这就是典型的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
2.诗学差异导致的误译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也会造成语言表达的不同。汉语比较注重“意合”,而英语则注重“形合”。所谓意合,指的是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子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组词造句中完全依据逻辑和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词语和分句的排列顺序。所谓形合,指的是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中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27〕如《道德经》第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意思是谁要掌握了“道”,必定人心所向,天下人都将向他投靠。前一句的主语是“君主”,后一句则为“天下人”,虽然主语不同,但省略之后,并不影响我们对句意的理解。因为这完全符合我们的表达习惯。而对西方学者来说,省略主语本身就会对句子的理解造成一定困难,更不用说省略的是两个不同的主语了。威利〔28〕将此句译为:“He who holding the Great Form goes about his work in the empire can go about his work,yet do no harm.”。他误以为两句的动作由同一个人发出,因此共用一个主语“he”。
数字虚指是古汉语中常用的一个手法。即用具体的数字表示一个虚指的概念。中国古代奉行阴阳五行说,许多事物都被冠以一个“五”字,而这个“五”是虚指。西方学者若不深刻了解中国文化,往往会造成误解与误译。如《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威利〔29〕就将这里的“五”处理成了实数,译为:“The five colors confuse the eye,the five sounds dull the ear,the tastes spoil the palate.”。读者读后会感到一头雾水,到底是哪五种色,哪五种音,哪五种味呢。《道德经》中有许多这种虚指的词,如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了避免中西方诗学差异带来的误译,译者需要结合原文历史背景,对这些独特的文化词语进行深刻理解和介绍,以减少译文读者的理解鸿沟。
五、结 语
任何一部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富有时代的气息,都符合大众的意识形态和审美习惯。《道德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内容博大精深,其译文层出不穷。但无论译得多么好,译文也无法达到与原文的完全对等。勒菲弗尔理论打破了以原文本为终极取向,追求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的传统翻译标准,将翻译置于文化背景下进行,这不仅为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学者研究《道德经》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差异和诗学差异对《道德经》英译的影响,从而造成译者对《道德经》原文理解的不同以及英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风格的不同。
注释:
〔1〕Michael Lafargue.(trans.)The Tao of the Tao Te Ching.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to New York Press,1992,p.9.
〔2〕Michael Lafargue and Julian Pas.Lao-tzu and on Translating the Tao te ching.Laotzu and the Tao te ching.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to New York Press,1998.
〔3〕金鹏程:《北美的中国竹简研究》,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676149/2011-06-24 16:03:44.
〔4〕魏志成:《简论〈老子〉的三个英译本》,《鹭江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8期。
〔5〕郭燕:《〈道德经〉核心概念“道”的英译分析》,《西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6〕王瑛:《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与翻译》,《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苗玲玲:《译可译,无常译——谈〈道德经〉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
〔8〕廖敏:《试析〈道德经〉翻译的多样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9〕邢怡、徐璐:《提高旅游翻译质量准确传播中国文化》,《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0〕Lefevere.Andrè.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11〕〔17〕张文君:《解读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琼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12〕王晓丽、陈晨:《从改写理论的视角看冰心的诗歌翻译思想》,《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
〔13〕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
〔1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15〕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6〕王峰、马琰:《批评性解读改写理论》,《外语研究》2008年第3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46页。
〔19〕Venuti,Law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New York:Routledge,1992,p.14.
〔20〕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Routledge,1993,p.48.
〔21〕Lefevere.Andrè.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p.56-60.
〔22〕Delisle,Jean.Translation:An Interpretive Approach.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88.
〔23〕辜正坤:《中西诗学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25〕〔26〕〔28〕〔29〕Waley,Arthur.(trans.)Laozi.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9.
〔27〕谭静:《〈道德经〉翻译中的中西思维差异》,《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10期。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Rationale for Banking Regulation〔*〕
- Approaches to Legalize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lish Teaching Model in China〔*〕
-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Language”——the Regional Linguistic System:Developing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 On the Systematic Dynamic Teaching Experiment of College English〔*〕
- The Explanation of the Vernacular Words in the Dunhuang Li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