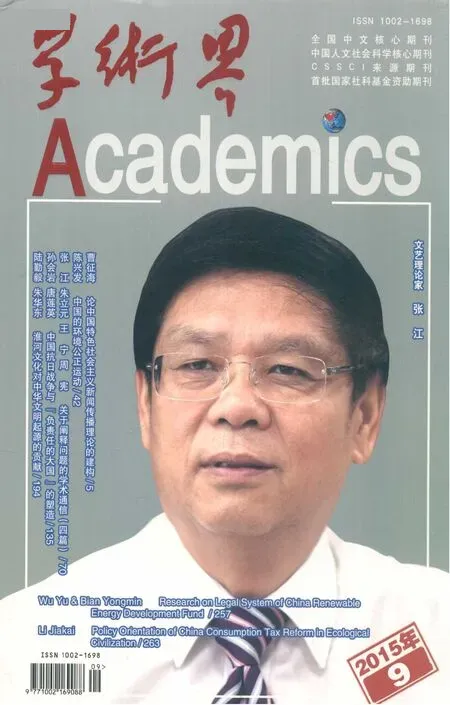论现代传媒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丁华东
(上海大学 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 200444)
社会记忆是维护人类尊严、增强国家民族认同、巩固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社会群体出于各自现实需要与利益诉求,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和传承社会记忆,让记忆“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并不断地改变其“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1〕反复呈现出来,这是社会记忆传承、建构和控制的过程,也是社会记忆的再生产过程。在这种反复呈现和再生产过程中,现代传媒不仅扮演着改变社会记忆“形式和外表”的角色,而且也扮演着将其纳入“不同观念系统中”进行表达和传播的角色,集改造者(生产者)、传播者、表达者(叙述者)于一身。现代传媒的发展增强了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力度、扩大了社会记忆再生产的途径和空间,提高了社会记忆再生产产品的可视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性质。对现代传媒与社会记忆再生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代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某些时代表现和时代特征。
一、社会记忆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是指生产过程的不断反复和经常更新,一般的理解都指向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两方面。随着认识的深化和运用的扩展,人们也将其广泛应用于精神文化和社会权力等领域,分析文化或权力等的反复生成与运作过程,如文化再生产、传统再生产、符号再生产、权力再生产、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等。社会记忆再生产也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方面,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其反复性,即社会记忆的延续、传承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反复进行记忆再现的行为或过程,具有再生产的性质,如孙德忠博士所言,是对历史信息进行反复编码、存储、提取、复活的过程;二是其加工性,即社会记忆再生产不同于物质再生产,不具备“初级产品”的生产性或生成性,如果说社会记忆的本源记忆(原初记忆)是“初级产品”,那么,这种初级产品是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具有“自然形成”或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点,其后的延续、传承、建构等则是对原初记忆的加工行为或复活过程,具有“再”生产特点。社会记忆的再生产,使“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2〕
社会记忆再生产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与我们的一切生产和生活相关联。孙德忠指出,“社会记忆是一种极其广泛、几乎触目皆是的社会现象”,“对于人类认识的形成和积累、文化的传承和流变、社会的启蒙和控制、历史的横向伸延和纵向深入等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推进机制和强化功能”。〔3〕因此,凡涉及社会记忆延续、传承、建构、重塑、复活、再现、控制、利用等行为都可视为社会记忆再生产活动,典型的有如史书编纂、文艺作品、历史教育、仪式重演、节日庆典、神话传说、口头传诵、传统延续、文化传播,乃至我们的知识学习等等。只是这些日常性活动在学者的眼中,大多采取了哈布瓦赫的记忆建构分析路线,缺少从记忆加工、传播的视角来论述,没有聚合、凝结成社会记忆再生产理论,因而也未能形成普遍性知识,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社会记忆再生产性质。
“如果记忆研究一定被认为是处理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研究,那么可以说,记忆是现在处理过去的方法。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表达出记忆是一种社会机制的观点,它可以生产和再生产某种意义,而这种生产本身离不开社会情境及其过程”。〔4〕出于各种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人们总是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社会记忆的再生产。
段春晖分析了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的生产路径,认为: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本身就具有政治象征符号的重大功能和意义。国民党非常重视强化社会记忆中孙中山的政治价值和实践功用,不断通过规训化的仪式、独白式的话语和操纵性的政治动员等政治手段对孙中山社会记忆进行重构,在努力塑造至善至美权威形象的同时,强化了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加深了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促进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体系不断合法化和秩序化。〔5〕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蔡政良教授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台湾都兰阿美人尚在进行中的传统领域恢复与争取运动过程进行考察,观察该部落内部的社会阶序文化特质如何与记忆结合,以再生产社会记忆来争取部落对于传统领域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主体性,既可以看作是社会记忆资本化过程的一个案例,也可以看作是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案例。〔6〕怀旧“几乎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它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意向性很强的、构造性的回忆,是我们以一种较为现实的方式重塑过去,以对当时情境、事态轮廓或参与人物的构想来弥补时间的流逝对生活细节的消损,通过主观的想象来重新经历当时的生活,重新唤起过去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即使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已然不存在的,即使过去充满了苦难,但隔着无法消弭的时空距离遥望过去,过去仍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赵静蓉将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怀旧作为现代性视域下的重要社会文化事件加以分析,认为“不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理念,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服饰返古、家居装饰自然化、休闲娱乐田园化等,还是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如摄影界的‘黑白艺术’、音乐界的老歌翻唱、建筑界的‘老房子’系列、文学界的‘怀旧系列丛书’、影视界的历史剧创作等,甚至是科学界的考古热、民俗学神话学的复兴、出版业对冠以‘记忆’之名的杂志的商业炒作等等,这种种社会及艺术现象都证明了怀旧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体成长中的心路历程,而是生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全民性的集体事件,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文化景观”。〔7〕
美国小说家福克纳曾借其塑造的人物之口说:“过去从来都没有死去,它甚至并未成为过去”。〔8〕我们或多或少地生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那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记忆。
二、社会记忆再生产与现代传媒
媒介是社会记忆的结构要素,也是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以及社会记忆传承体系的构成方式。社会记忆的存在和表现必然要通过一定的记忆媒介才能成为可能。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陈新指出:“我们与其让集体记忆停留在一种不可琢磨的状态,不如将它视为某个范围内被普通认可的主流历史记忆。它是主体间交往的产物。除了同时代主体的交往之外,不同时代的主体通过文字、器物等一切符号形式交往;除了主体自发状态的交往之外,有组织的交往更是集体记忆形成的有效方式,一如历史教学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博物馆的文物组织与陈列、大量历史纪录片的拍摄与播映等等。作为符号的文字、器物、图像等等,成为主体间交往的媒介,虽然它们所传播的内容并没有固化在这些媒介之上,而需要在接受者的理解中呈现,但可以肯定的是,缺少了这些媒介,交往也就无法实现,新的集体记忆的产生也将成为泡影”。〔9〕陈新教授的看法既指向社会记忆形成与媒介的关系,也指向社会记忆再生产与媒介的关系。但在现代传媒发达的时代,我们还要更深入分析现代传媒背景下社会记忆的再生产以及在此环境中档案记忆的展演。如余霞所言:21世纪,报刊、广播、影视等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加上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卷入与渗透,大众传媒将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形塑历史记忆方面,传媒无疑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10〕
社会记忆再生产是对社会记忆的加工、传承行为,需要借助一定的传媒来改变其原有的“形式和外表”,在此过程中,参与或承担社会记忆再生产功能的传媒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将记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现代状态、现代状态和后现代状态。前现代时期的特征在于人们和过去之间的联系是自然而非自觉的,他们的记忆环境维持着传统和仪式,这些传统和仪式为当地记忆团体的成员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感觉。在19世纪,随着因工业和社会的现代化而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加速,记忆所具有的魅力开始消逝。由于古老的传统和联系失去了意义,人们和他们的过去之间的关系就通过对自然记忆的首位刺激被重构。精英们在语言、纪念物和档案中制造记忆的故址,语言、纪念物和档案拥有一个共同的所指物:民族国家;而且,它们通过强制创造民族国家的传统来力保它未来的安全。20世纪后期的媒体文化使对过去的认同和表象喷涌而出,除开媒体消费疯狂的速度外,这些认同和表象与任何共同传统、生活世界或政治机构几乎没有联系。〔11〕
诺拉的论述描述了社会记忆再生产与传媒发展的一般性演进关系;同时,诺拉也指出,当今时代的整个演化却是在“即刻历史”的压力下进行的,其中大部分是媒体推波助澜的产物,而且产量还在不断地增加,在集体记忆的压力下,所形成的历史要远超从前,甚至远超不久以前。〔12〕如诺拉所言,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对社会记忆再生产产生着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一方面促使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方式、表现形式乃至传播渠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向现代影像化方向转变。
首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方式和表现形式是累积性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发明或使用的新媒体虽然对已有的传播媒介产生冲击,但并未让旧有媒体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在使用新媒体的同时,传统媒体仍在继续使用,比如口述、实物和仪式等等,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在使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实践作用力与人类生命惯性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一幅丰富多彩的记忆再生产画面,口述、仪式、神话、传说、故事、实物、遗迹、手稿、书籍、图片、摄影照片、绘画雕塑、报刊杂志、文学戏剧、建筑物、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等。文化学者徐贲在批评关于公共记忆导致个人遗忘时就注意到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多样性,他分析道:“他(詹姆斯·杨)说,‘在这个生产和消费大众记忆的时代……对过去纪念得越多,思考和研究反而越少。我们一朝给了记忆一个纪念形式,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记忆的责任。我们让纪念馆负起记忆的重任,而参观者自己则无须再有担负……就在我们鼓励纪念馆为我们记忆的时候,我们反倒是在遗忘……事实上,想记住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它的起源也许恰恰是想要遗忘’。〔13〕这样的看法并不确实,因为它只看到一些传统的公共记忆和纪念形式(如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而忽视了大众传媒时代更加多样化、更加普遍起作用的新的记忆形式。新记忆不再仅仅依赖不可移动的物质实体(石料、金属、建筑)。新记忆已经成功地转化为一些可移动的、便携带的、可以个别接触和处置并且是‘可复制’的形式。新记忆的有形体是书籍、影视产品和纪录片,可以用光盘或者其他方式储藏,也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书可以反复阅读,阅读片断或全书则随读者之意。数码技术更是让观众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随时随处寻找或者重复获取他关心的内容”。〔14〕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时代在发展,传媒的影响力也在变化,新媒体的出现,特别是现代电子传媒(电视、电影、网络、数码影像设备等)在创新记忆再生产方式时,也导致记忆再生产由传统的民间讲故事、说书、戏曲、地方性仪式等等向现代影视、互联网表达展示的急速转变,体现出“看图时代”或“观影时代”的特征。
记忆再生产的现代影像化转向及其影响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诺拉说:“现代记忆是档案性的。它完全依赖于踪迹的物质性、记录的及时性、形象的可视性……被人从内部感受到的记忆越少,只通过外部支架和外在符号而存在的记忆就越多”,它为生活增添一种二次记忆,即修复术记忆。〔15〕艾里森·兰德斯伯格(Alison Landsberg)也用“修复术记忆”来描述大众媒体(尤其是电影)使人们把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体验为记忆的方式。她解释道:“因为大众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何为体验的看法,所以它们可能是生产和流通修复术记忆的一个专用竞技场。特别是作为一种机构的电影,它使供大众消费的形象唾手可得,长期熟知自己生产体验和安置对体验的记忆的能力——成为体验的记忆,电影观众同时持有这份体验并感到被这份体验支配”。〔16〕在一次关于1970年代的法国电影的讨论中,米歇尔·福柯指出,(凸显法国抵制运动的)法国新电影参与了一场改编大众记忆和把用以解释当下的框架强加于人民的战斗,因此显现给人民的不是它们过去是什么,而是他们必须记住现在已经是什么。〔17〕其他学者如罗伯特·伯戈因讨论了电影在当代(美国)社会解释过去过程中以及在国家想象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认为“历史电影帮助形构数百万人的思想,在银幕上看到的描述对公众的历史主体观的影响经常比书本大得多”。〔18〕
网络传媒是现代传媒的重大变革和前沿领域,凭借其强大的数字化传播功能和多媒体合成技术,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社会记忆再生产能力和影响力。2011年,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一场题为“数字媒体与政治的记忆:揭开阿根廷历史的新篇章”的报告中,长期从事历史与媒体关系研究的学者杰西卡·斯泰茨·莫尔(Jessica Stites Mor)认为,在网络化时代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字媒体传播知识,重新审视历史。她以阿根廷独裁时期为例,认为伴随着文献的解密和上传,人们通过数字媒体可以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数字媒体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信息传播的有效途径。〔19〕
现代传媒对社会记忆再生产隐含着诸多的模式和机制,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分析,现有两项研究可以让我们领略其中的深意。一是余霞通过对报刊和电视等的考察,将大众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模式分为三种:即报道历史,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历史记忆;再现历史,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重塑历史,以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历史记忆;〔20〕另一项是学者对刘铮出版《国人》摄影作品集的分析,揭示“摄影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活动,其真正的目的是探讨摄影如何记忆,确认记忆与现实的关系,揭示记忆产生、再生、传播的构造”。〔21〕
三、现代传媒发展与记忆产业化
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社会记忆再生产使记忆超越事件最初发生的时空,处于广泛的群体之中,得到广泛而频繁的传播。“它们具有自己充满力量的、真实的个人记忆‘无法阻碍’的生命,而且作为无实体的、无所不在的、低强度的记忆,它们成为所有集体记忆过程的基础”,〔22〕塑造着大众的认同和世界。英国学者戴维·莫利认为:“没有考虑到传播技术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和出现”。〔23〕但社会记忆再生产在强化、扩大某些社会记忆的同时,也导致社会记忆的外部化、媒体化和视觉化,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现实的政治权力结合时,社会记忆再生产就成了制造“历史”、制造“真实”的过程,其结果就是政治与媒体“合谋”下刻意塑造出来的“人工产品”。“对历史的建构和陈述的本身,往往是‘现在’政治状况,‘现在’历史阶段的一种回身投射。现代媒体的发达,只是加强了这个过程的便利性与多种的可能性而已。但是,正因为它的过于便利化与任意化,使现代社会的群众,成为丧失记忆的一群。历史,对他们而言,好像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媒体的创作,哪一个版本最引人入胜,哪一个版本最符合现代人当前的需求,就会选择哪一个版本去认同。”〔24〕台湾学者陈龄慧说,这好像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谈的一种“文化工业”的现象,在充分现代化、媒体资本化、消费自由化的台湾,“历史”成了只是为了满足大众消费口味而设计、而生产的一种影像消费品。〔25〕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直接用“记忆产业”来表达现代传媒对社会记忆再生产的作用和影响。他指出:
“哈布瓦赫的最后一个观点是,集体记忆体现于记忆制品、各种纪念物之中,如神龛、塑像、战争纪念碑等,即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谓的‘记忆场’。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哈布瓦赫的记忆制品列表中加入我所谓的‘记忆产业’(The Memory Industries),即与耦合过去有关的那部分文化产业。虽说遗迹和博物馆是显在的例子,但我们也应加上大众媒体(包括电影)。记忆产业,就像它们构成其一部分的文化产业一样,生产各式表征(‘文化纪念物’),用以鼓励我们去思考、感知和认同过去。但是这些表征并非把记忆体现为如此,它们体现记忆的原料,它们提供可以生产‘集体记忆’的原料。”
“记忆产业不仅仅传播要记住之物,而且很重要的是,它们也不停地耦合可以被记住之物。”〔26〕
约翰·斯道雷通过好莱坞越战影片的生产来分析美国的记忆产业。他说好莱坞的越战已经为复述、阐释、解释和转述日益居支配性的美国越战记忆提供了素材,它与其他媒体合力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战争记忆,用一剂怀旧治愈了十年来一直未愈合的伤口,并把愧疚和疑虑转化成了职责和骄傲;用一种胜利者的得意为人们展示了其最为成功的作品,即愿意去打下一场战争的老兵。“越战记忆已经不再是抵制帝国主义野心的关键,它现在被援用成为下一次就这么干的明显警告”,这种记忆在海湾战争准备过程中,被乔治·布什“耦合”成授权的记忆。〔27〕
王炎在《奥斯威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一书中,从美国好莱坞对二战“屠犹”历史记忆的生产入手,分析影像记忆的生产及其产业化特征。他通过对比欧洲的“大屠杀”影片,认为好莱坞在不同时期再现犹太大屠杀历史时,历史叙述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国际政治以及美国族群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在政治上与利益集团共谋合作的同时,好莱坞梦幻工厂的生产线上,在不断拼贴、高速复制和产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记忆,不断生产着美国化的道德英雄,在全球同步上映的商业炒作中,塑造世界观众的主体意识和美国价值。他为此评论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马克思所说的金钱成为世俗上帝的时代,就连记忆也难逃出商品的逻辑,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有关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都会与生产和消费这两个貌似无关的商业环节结合在一起。这是个商品和消费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毛孔’的时代,当商品拉平了一切文化差异、削平一切民族个性时,当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将整个世界连接成无边无际的荒漠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思想已经被彻底挤压成一个平面,没有内涵,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突兀和空寂的当下。因为高速运转的电影工业正给我们生产着记忆,它的产品可以按照集成块的方式任意组合我们的过去,记忆的时间性被抽离了。我们有的只是影像化的超现实的、不可置疑的空间化的过去。人们不必再费神追忆似水年华,也不必争论历史的真实与再现的可能,更不必思考自己的身份与家族和民族史的关联,超大的银幕‘供应’给我们所需的一切,它告诉你是谁,应该如何思考,该如何回忆。”〔28〕
当代社会记忆再生产的产业化特征是现代传媒作用的结果,也与当代的社会记忆资本化或文化资本化、文化产业化有着直接的关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们都是当代社会特征的某些体现。如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T.W.Adorno)所说:“现代文化产业就是一种商品的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法则不再是什么灵性的表现或风格的追求,而是创造需要,占领市场,实现其最终的目标——交换原则,即把产品变成一种交换的商品”。〔29〕
注释:
〔1〕〔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82页。
〔3〕孙德忠:《社会记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4〕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第217-242页。
〔5〕段春晖:《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的生产路径分析》,《理论观察》2007年第5期,第53-54页。
〔6〕蔡政良:《记忆作为一种资本:都兰阿美人的社会记忆再生产案例》,http://www.oz.nthu.edu.tw/~ d929802/anthropology/austronesian/final-term-paper-20040629.pdf。
〔7〕赵静蓉:《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82-195页。
〔8〕转引自刘国强:《当代传媒形塑集体记忆的方式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70-74页。
〔9〕陈新:《历史思维三论》,新浪“大地长河”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b889490100pwjx.html,2011-04-02。
〔10〕〔20〕余霞:《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其社会框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1〕〔22〕〔美〕沃尔夫·坎斯特纳:《寻找记忆中的意义:对集体记忆研究一种方法论上的批评》,载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45-146、154页。
〔12〕〔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13〕James E.Young,ed.The Art of Memory:Holocaust Memory in History.New York:Prestel,1994,pp.8-9.
〔14〕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序言。
〔15〕Pieer Nora.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les lieux de memory.转引自〔英〕约翰·斯道雷:《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16〕〔18〕〔26〕〔27〕〔英〕约翰·斯道雷:《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139、142-143、152页。
〔17〕Michel Foucault.Film and popular Memory.Radical Philosophy,1975,p.28.
〔19〕参阅丁江伟编译:《数字媒体与政治的记忆》,《社会科学报》2010年报道。
〔21〕顾铮:《记忆·身体·意识形态——关于刘铮的〈国人〉》,http://forums.nphoto.net/thread/2003-10/21/ff80808108007a730108007ac2c268bd.shtml,2003-10-21。
〔23〕〔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15页。
〔24〕〔25〕陈龄慧:《历史记忆与媒体:政治广告的文化解读》,原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转引自千龙网,http://medianet.qianlong.com/7692/2003/12/18/33@1771632.htm,2003-12-18。
〔28〕王炎:《奥斯威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16页。
〔29〕转引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