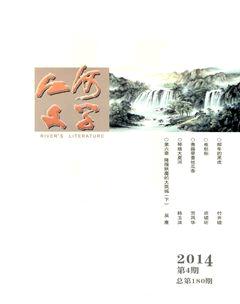夜航船
欢镜听
1、乡愁
人,抑或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动物。倘若把见异思迁这句成语里的贬意去掉,人的本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我竭尽全力从宁静的环境中一步接一步艰难地走进大城市、走进《大都市》编辑部以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感,宛如潺潺的溪水,流淌在编辑部里,流淌在我的心头。
在妇产科医生预言妻子还不到一个多月就将分娩的第二天,我请了十天假。通情达理的妻子为我收拾好了行装,然后自问自答:“那个地方有一位基础挺不错的作者,是吗?石河,你要早去早回啊!”
四周的景物跟过去一模一样:脚下是一片宽阔的沙地,沙地上铺满了野草,草地上开放着星星点点淡黄点的花儿。草地的边际,耸起绵绵无尽高高矮矮的群峰,氤氲的云烟在群峰之间缠来绕去,云团的外层又抹上了一层薄纱似的霞光。草地上有一条弯弯拐拐的小路,一头通向德感镇,一头通向几江渡。我沿着小路朝草地深处走去。青草叶儿蹭着我的脚,纸做的心扉被带齿的草叶儿渐渐锯裂开来。
夏季里的一个下午,天上翻卷着滚滚乌云,雷声从天宇深处扑下来,草地笼罩着一片闷热而又恐怖的气氛。一会儿,狂风吹起来了。狂风推着草浪从几江渡方向朝德感镇一层一层地扑过去。狂风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位小伙子,他一边跑一边呼喊:“红英,红英,红英……”忽然,他被潜伏在草丛里的一块石头绊倒了,他挣扎了一下,也许是疼痛,他终究没能站起来,索性全身扑倒在草丛里,呜呜呜地哭泣着。一边哭一边说:“红英,红英,红英……”尽管如此,他声声呼唤着的红英却不在他身边。
倒是另一位姑娘注视他很久了。
那位姑娘肩上扛着一圈纤绳,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姑娘认识他,知道他叫石河。石河也认识姑娘,知道姑娘叫水燕。他俩生活在同一座德感镇上。
水燕走到石河身边,俯视着他那痛苦不堪的样子,“唉……”她叹息一声,用脚尖踢踢石河的屁股,问:“石河,你哭啥子啊?”心里却想,狗日的,屁股瓣儿好软和啊!
石河慢慢翻转身来,终于看见了姑娘那张鹅蛋形的脸庞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喂,石河,你跑到这儿来哭啥子啊?今天又不是清明节,你家的祖坟也没埋在这儿啊!”
石河忿恨地盯住水燕,继而想到自己这一副哭相,便将双眼移开,望着渡口方向。许久,才喃喃自语道: “她叫红英,她住在江那边,她和我耍了两年的朋友,现在她不要我了。”他又恢复到那种痴呆呆的神态,说:“我要找她,我要过河去找她。”
“那……石河,跟我走吧,我划船送你过河。”
事后想来,当初,假如不是为了追回我那无法追回的爱情,我一定会仰面躺倒在草地里,任狂风和即将到来的暴雨扑打着我阴沉沉的脸。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也许就不会与几江河结下不解之缘,更不会有如今这许许多多萦绕心际的往事了。
一只小木船停泊在渡口。
石河和水燕刚刚走到渡口,暴雨便铺天盖地下起来。顷刻间,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轰隆隆的雷声没有了,哗哗哗的雨声响彻整个世界。水燕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朝着座落在沙滩上的一个窝棚独自飞快地跑去。窝棚的门关着,她跑到竹门前,转身弯下腰,将屁股朝那扇竹门呼一声撞去,身体随着竹门的移开倒进窝棚里面去了。
“喂,石河,快点跑进来躲雨啊?”
石河站在沙滩上,双眼望着雨蒙蒙的江面。
“喂,石河……”水燕从窝棚门里探出头来,望着木然站在沙滩上的石河。她又喊了几声,对方似乎没有听到。她缩回头,从窝棚角落找出一个竹叶编成的斗笠戴在头上,钻出了窝棚,雨点打在斗笠上,扑扑的响。她一步一步朝着石河走过去,然后在距他不远的地方站住了。她看见石河脸上流淌着的不全是雨水,还有比雨水更为晶亮的泪水。天下干啥会有这种男娃儿呢?她想,大不了就是人家不和你耍朋友了嘛,值得伤心落泪么?水燕取下头上的斗笠,掂了掂,呼一声朝着石河扔过去,斗笠在半空中旋转着,不偏不倚恰好套到石河的头上。石河骇了一跳,转过头惊讶地望着水燕。水燕望着他,忽然咯咯咯地大笑起来。然而,这笑声似乎把另一位少女的姿影恍恍惚惚地推到石河眼前,他顿时反常地快活起来。跟着也嘻嘻嘻地笑了。水燕走到石河身边,拍了一下他的肩头,问:“喂,石河,我们不过河了吧。”
石河的眼睛里突然闪出灼人的光芒,就像他第一次和红英悄悄约会时那样,他说:“我们不过河了,从今后,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
水燕的脸儿倏地绯红,做出一副恼怒的样子,用一根手指头点着石河的额头,嗔怪道:“喂,石河,说话小心点啊,要不然,我这根手指拇钉进你的脑壳里头,一勾,把你的脑水花花全勾出来。”
石河仍旧嘻嘻嘻地笑着,猛然抓住水燕的两个肩头,说:“红英,我们不过河了。”
水燕先是一愣,继而明白过来,石河把她当作昔日的恋人红英了。她重重打了石河一个耳光,又用力一推,将他推倒在沙滩上。然后双手叉在腰间,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一句话也没说。石河怔怔地望着水燕,渐渐清醒了。接着,他调头望着江面,像是说给水燕听又像是自言自语:“我们是在这个渡口分手的,她住河那边。我要去找她。”
水燕用脚尖轻轻地蹭着他的脊背,冷冰冰地说:“走啊,我送你过河,送你过河去找那个不要你的女人。哼,没出息的东西!”
石河瞪大眼睛,“你真的要送我过河?”
水燕弯下腰一把抓住他的头发,一边往上提一边说:“走啊,没出息的东西!”
2、媒婆
能够从喧嚣的都市中解脱出来,头上的云朵、脚下的草地、以及远方那些彼此手挽着手的群峰,全都默默地沉寂在我周围。这,反而使我感到一阵惶恐,胸中那些日日夜夜闹得我心神不宁的许许多多的情感,一刹那化为乌有。我停下脚步,宛如陀螺般旋转了一圈,宽敞的草地上渺无人迹。一只鸟儿吱一声长鸣,从半空中俯冲下来,潜伏在草丛里的一条小虫子被鸟儿叼在嘴里,腾云驾雾似的飞上天空。
我朝前走去,步子比先前慢了许多。
石河坐在船舱里,水燕手持竹篙,将船儿嗖一声撑离了江岸。
水燕的衣服被雨水泡湿了,身体的每一条曲线都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水燕撑船的姿势非常独特,就像她独特的个性一样:她双手将竹篙插进江底,双脚使劲往后一蹬,旋即跳起来,待重新落在船板上时,她已经从船舱中央站到了船尾上。
一只小木船从对岸划过来,撑船的是一位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的中年妇女。她看见了石河,也看见了水燕,打着招呼:“水燕,把船停下来,我给你说一件事。”
“啊,幺娘,是你啊。”水燕把竹篙竖起来,从船尾上的一个孔洞里插进河底稳住了木船,“幺娘,你又来给我做媒啊?”
那位中年妇女没有急于回答水燕,却狐疑地打量了石河一阵,问:“水燕,他是哪个?”
“他么?啊呀,幺娘,他是镇上的那个小白脸啊,叫石河,先前遭一个不知从哪条石缝缝里钻出来的女妖精勾去了魂,今儿个那个女妖精不要他了,他呢,拼死拼活也要过河去找人家。”
中年妇女笑嘻嘻地说:“石河,另外找个女娃儿吧,天底下,哪个女娃儿都是一样的生娃儿嘛。”跟着,她又转头望着水燕说,“幺哥明儿个要到渡口来哟。”
水燕笑容可掬的脸一下子阴沉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
“还有,”那位中年妇女说,“他老巴子(父亲)也要来。”
水燕将竹篙从船孔中抽出来,对中年妇女说:“幺娘,你给他们打声招呼,空手不要来。”一边说一边将木船撑得远远的。
“水燕,你听我说嘛。”身后又传来中年妇女的喊声,“明下午我跟他们到渡口来。”
雨还在下着。
《大都市》编辑部。
一天下午,我收阅了一份诗稿:《草绿花黄》。
这是一组用拟人手法写成的叙事长诗。
我尚未完全看完,浑身的血液便有悖常理地冰冻起来。
水燕气呼呼地将船划到江心,停住竹篙,又气呼呼地从船舱中跨到船头上,咚一声坐下来,索性连船也不撑了。小木船失去了控制,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他大惊失色地嚷道:“水燕,船……船……”
“船船船船船,”水燕狠狠瞪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船要漂到龙王爷那儿才好呢。”
他没料到水燕的气性会这样大,脾气会这么古怪。他扑过去,企图从水燕怀中把竹篙夺过手。那时候,他没有仔细想一想:竹篙对于他来说有什么用?他可不会撑船啊!但,没让他抓住竹篙,水燕猛地身子朝后一仰,张开双腿,他的头刚好伸到水燕的两条大腿之间。他还没醒悟过来,水燕又将双腿一夹拢,他的脖子顿时被夹住了。他没料到水燕的力气会这样大。他徒劳地挣扎了几下,脸孔臊的通红。于是,他奇迹般地破口大骂起来:“水燕,你他妈的这叫什么话,羞死你他妈的祖先。你他妈再不放开,老子要咬你的肚皮了。”
这一句话奏了效。水燕大喝一声:“石河,放开了,放开了。”她把双腿分开,石河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刚想把头抬起来,水燕突然重新将双腿一并,重新牢牢地夹住了石河的脖子。这一次,石河不仅仅是挣扎不动了,而且下巴颏顶在水燕的小肚子上,仰脸望着天空,嘴巴大张着,再也合不拢了。话,更是没法说出来。雨水浇到石河的脸上,然后又源源不断流进他嘴里。“喂,石河,晓得我的厉害了吧?哼!”水燕幸灾乐祸地说,话里充满了快乐,好像早先抑郁在她胸中的不快,在这时候、在小船中、在石河身上得到了痛快淋漓地发泄。把石河折磨够了以后,她才松开了双腿,两脚一蹬,将石河蹬倒在船舱中,等对方站起身握紧双拳想扑上来和她打一架时,她却早已手持竹篙站在船头,竹篙的一端顶着对方的心窝。“石河,老实点。要不然,我用竹篙从你的胸膛上穿过去,挂起来,晾成鱼干!”
几江河已经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廊。
愈接近那个地方,我的脚步愈慢。草地静静的,一种身临冥冥世界之中的心理上的感觉静悄悄地裹住了我那颗怦怦跳动的心。静谧中,我听到阳光渐渐热起来的轰轰声,听到一丝一缕的白汽从沙地里冒出来缭绕着草叶儿的沙沙声。不久,这些细微的几乎只能依靠感觉才能听到的声响神秘地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恍如一滴一滴的清水掉进心坎儿上发出的难以言喻的响声。
《草绿花黄》的作者就在本市。
我给作者寄了一封信去,约定星期天在湖畔公园见面。我明白《草绿花黄》是一组艺术质量较高的诗,那种低沉的灰色的调子宛如把读者的心儿放置在一座冰窖里,对着冰冷的雪墙面壁思过——冷静地面壁思过!但是,作者有做诗人的才华,有做诗人的激情,然而,作者缺少一种需要别人去提醒他(她)的东西:注意……
星期天,公园的水泥凳前。
一位西装革履的老头握住了我的手。老头不下八十岁,满头花发,但天庭饱满,容光焕发;尤其是系在他脖子上的那条燃烧着青春火焰的鲜红色的领带,迫使我不得不用新的目光重新估量这个老头。老头笑眯眯地说:“吃惊了吧,编辑先生——啊,不,石河先生,以后,你也许会疑惑不解地对别人说,一位有着万贯家产的海外华侨,到了快进棺材的年龄,为什么突然间心血来潮,眼红起那微乎其微的几块钱稿费来?”
那位老头在我身旁坐下来。
他说:“我从未有过做诗的雅兴,更没想过要当一名诗人。两年前,我从海外回到大陆定居,便到各地旅游。我不喜欢到那些名声在外的名山大川,反而去寻找那些无名的但充满了大自然野性情调的地方,因为那种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要质朴和真诚得多。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里,我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几江渡。在那儿,我遇见了一位神情呆滞的妇人孤伶伶地坐在江边。经过耐心的交谈,我终于零零星星地了解到一些情况。她被人欺骗了,她曾经爱过的一位男人抛弃了她。”
我的心忽然沉落在一条幽深的峡谷里……
水燕突然惊慌地嚷起来:“啊呀!船……”
她那锐利的尖叫声把石河吓了一大跳,他怔怔地望着水燕那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啊呀,石河!你看船都漂到哪儿来了。”
他醒悟过来,这才注意到船儿漂流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他惊慌地嚷起来:“水燕,咋办呢?”
“咋办?你问我,我又问哪个龟儿子?!”
船已经漂到几江河的下游了。越往下漂水流就越急。
水燕瞪大双眼,一只手持竹篙,另一只手指着他的鼻尖,责骂道:“石河,你这个昏脑壳的,你这个背时的,你这个挨刀剐的,你……你……你……你不是一个好龟儿子!”
天开始擦黑了,雨珠儿照旧啪啪啪地拍打着船板。
出于自尊,石河有些心虚地辩解道:“水燕,责任应该一分为二,你负一半,我负一半。”
水燕双眼瞪得更大,正要大大地发作一番,却猛然瞧见了手中的竹篙,她一下子想起了什么,没再理会石河那斤斤计较的话,将竹篙高高举在半空中,恼怒地说:“滚开点!我要靠船了。”
石河刚一弯下腰,水燕手中的竹篙立即从他头上嗖一声滑过去,竹篙穿过船尾那个小小的孔洞直插河底。船儿终于靠下来了。水燕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终于得到了缓和。
但是,他们跟着又犯起愁来:这半船舱水怎么办?
一片白色缓缓移进我的眼帘,我精神为之一振:几江河就在眼前了。
那消失了许久的情感又回来了,并且还融进了一种新鲜的灿然的色彩,重新轰击着我的心扉。
当我大步流星地朝前迈去时,那久违了的绿色草浪又呼呼呼地吹起来了……
3、舀水
几块青石板横七竖八地摆在河滩上,这就是几江渡。
一叶渔舟漂在江心顺流而下。我以为是渡船,没等开口呼唤,渔舟已经离我远去。
使我魂不守舍的几江渡原来这么简单。
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这么简单的渡口。
天,渐渐黑下来;雨,早已停了;风,轻轻吹拂着;船儿,在他们脚下摇晃着。
尽管是夏天,但一则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度早已被雨水冲散,二则他们又湿透了浑身衣裤,河风吹来,冷冷浸人,石河禁不住浑身冒出了鸡皮疙瘩。石河和水燕各自把手抱在胸前,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到后来彼此都苦笑起来。
水燕笑着说:“石河,你是个大灾星。”
石河苦笑着说:“任何事物都是辨证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水燕,你说是么?”
水燕半张着嘴巴,睁大双眼,说:“石河,我没有你那么多文酸气。你看,这半船水咋办呢?”
“舀出去。”
“舀?哼!你拿啥子东西来舀嘛?”
这次,轮到石河半张着嘴巴,睁大双眼了。可是,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水燕,我们用手舀,手不是很好的舀水工具么?”
“啧啧啧,你以为别人都是猪头?”水燕仍旧将双手抱在脑前,“用手舀?哼,说得轻巧,提根灯草。这种舀法,要舀到牛年马月啊?”
石河弯下腰,双手合在一起以掌当瓢,一下一下地舀着水往船舱外泼去。的确,这太吃力了。
水燕冷冷地望着石河。一会儿,她说:“喂,石河,书呆子,船中的水怎么没见少啊?”
石河直起酸胀的腰,看了看船舱里的水。
“喂,石河,快点舀啊!”
石河又弯下腰去——并非他要听水燕的话,而是在争一口气。他一边舀一边自我解嘲道:“愚公能够移山,我难道还不能舀干船舱里的水么。”
水燕吃惊地反问:“愚公?愚公是个啥子东西啊,能够把大山都搬走?”
石河说:“愚公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位老人,他要把挡在他家门前的那座大山搬走。”
水燕说:“那座大山挡了他们家的路,干啥子不搬家而去搬山啊?”
石河说:“故事中蕴藏深刻人生哲理。水燕,你不懂。”一边说一边弯下腰,继续舀水。
水燕静静地观察着他,眼神是复杂的。她觉得石河变了,不再提那个红英姑娘了。听着石河舀水弄出的哗哗声,她忽然童心大发,搞起了恶作剧:趁石河弯腰舀水时,伸出右脚插进对方的胯下用力一勾,没有丝毫防备的石河扑通一声翻过船舷栽进江水里。“哈哈哈……”水燕开心地大笑起来。突然,水燕吃惊地看见石河的双手在江水中乱摇乱摆。她明白了:这位在江边长大的男人原来是旱鸭儿。她立刻吓得面如土色。江边长大的男儿不会水,这倒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水燕急中生智,抱住靠船的竹篙用力往上一提。竹篙取出来了,可船儿又开始往下游漂去。她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如果船儿漂远了,那就……她不敢再想下去。她将竹篙的一端伸到石河手边,惊慌地说:“石河,抓竹杆。”
石河准确无误地抓住了竹篙。他呛了几口水,呛得他眼冒金花。
“喂,石河,抓紧哟。”水燕一边慢慢地收着竹篙,一边紧张地说道。声调里居然带着哭音。
终于,石河上了船。得救后,他感到软弱无力,全身似乎虚脱了一样,身不由己地瘫倒在船头上。水燕吓得脸色苍白,急忙靠住船,将石河抱在怀内。石河虚弱地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被水燕抱着,立刻气不打一处来,举起手打了水燕一个耳光。水燕没有任何还击的举动,也没说一句怨言。她更紧地抱紧了石河。石河挣扎了几下,没挣脱,于是满脸羞红地吼道:“放开我!”
水燕没有放开他,眼眶里反而掉出了一颗一颗的泪珠儿。一会儿,她忽然哇一声大哭起来,并把自己苍白的脸,贴到石河同样苍白的脸上去。石河被水燕拥抱着,而且拥抱的那么紧,那么牢。他挣扎了几下,却是连身子也动弹不了。于是,他放弃了这种徒劳的挣扎,也放弃了羞怯,软软地瘫在水燕的怀内。他太疲乏了。水燕把苍白的泪脸从石河同样苍白的泪脸上移开,带着哭腔轻声呼唤道:“石河……”一边说一边松开他,却又将另一只手贴到对方脸上。她流着泪说:“石河,我对不起你,我以为河边长大的娃儿都会浮水。”
石河冰凉的身子在渐渐暖和起来,水燕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的身子。
见石河露出不相信的样子,水燕着急地解释起来:“石河,哄你我就会变成……”后面的话,她感到难以说出口。
石河冷冰冰地仰视着水燕,其实,他的心早已被水燕的温柔和柔情所动。
水燕轻声问:“石河,你还不相信么?”
石河已经在心里答应了,可是该死的眼睛,却依旧冷冰冰地仰视着水燕。
水燕以为还没取得石河的信任,她神情庄重地诅起咒来:“石河,如果我哄你,我就会变成大伙儿的婆娘!”诅完咒,水燕的脸轰地烧得通红。
石河惊骇地从她怀抱中挣脱出来,木呆呆地盯住她。石河深知,对于一位未婚少女来说,她尽可以诅“挨千刀万剐”之类的咒语,却没有一个敢于拿自己的贞操和一生幸福来作诅咒。
水燕忽然声泪俱下地哭起来,“我诅这么大的咒都不能使你相信,我只有死了算了,呜呜呜……”
石河一阵激动,双手搭在水燕的肩头上,柔声细语地说:“水燕,我相信你。”
水燕停住哭泣,狐疑地望着他,轻声问:“石河,你真的相信了?”
“水燕,我真的相信了。”
她仍旧狐疑地望着他,“你诅个咒,我才放心。”
石河想了想,一眼瞟到几江河,便咬牙切齿地诅起咒来:“我石河说了假话,淹死在几江河里。”
水燕破涕为笑了,说:“石河,你已经死过一回了。”
石河一愣,是的,他已经死过一回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正要重新诅咒,却不料嘴唇被水燕的一只手捂住了。
“石河,我相信。”她把手缓缓移到石河的脸颊上,轻轻地抚摸着,然后又紧紧地抱住了对方湿漉漉的身子。
石河也把水燕紧紧抱住,那种暖暖的体温在他和她的身体之间融合起来。在渐渐浓郁起来的暮色中,在摇摇晃晃的木船上,石河感到有些离不开她了。
水燕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很不情愿地松开手,石河的双手却还搂着她的腰肢。她脸一红,似嗔似怒地瞪了石河一眼,猛然将对方一推,骂道:“呸!石河,不要脸。”
石河扑通一声仰倒在身后的半船舱水中。
“哈哈哈……”水燕大笑起来,是那种无拘无束的大笑。
石河狼狈地站起来,原本就水淋淋的衣裤现在更加水淋淋了。似乎是受到了水燕清越笑声的感染,他居然没发脾气,反而跟着水燕哈哈哈大笑起来。一阵开心大笑之后,他和水燕开始犯愁起来,望着船舱里的水,他们一时间都感到束手无策。
他愁眉苦脸地问:“水燕,你往常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水燕扁了扁嘴,说:“这种事儿我遇多了。”
“那……往常你是怎么舀干的呢?”
她直勾勾地盯着石河,慢条斯理的说:“往常?往常船上没你这个大灾星啊。”
石河疑惑不解地望着她,“我在船上碍了你什么事?”
“什么事?装疯卖癫的。告诉你,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我只需要把裤儿衣裳一脱,踩住船梆梆,一踩一跳,这船就翻个底朝天,再把船翻过来,水不就全倒出去啦。”
石河顿时高兴起来,说:“那我们一起来踩,一起来跳。”
“那好啊,”水燕仍旧站在原地,“只怕船一翻,又要淹死你。”
石河站到船头上,猛然醒悟过来,慌忙说,“不行,我不会游泳。”
“哈哈哈……”水燕又开心地大笑起来。
石河站在那儿,哑然无语,心里却在骂着自己,石河,你他妈的真是一个大灾星啊。
看见石河一副懊恼样儿,水燕收住了笑声,正色道:“办法倒是有一个……”
“什么办法?快说!”一听说有办法,石河便迫不及待起来。
水燕瞪了石河一眼,“把裤儿脱下来,裤儿脚脚挽成死疙瘩,两根裤脚就成了水桶。只要动作搞快点,这半船水一会儿就‘提干了。”
这算什么办法啊?他望着一本正经的水燕,哭笑不得。他和她都只穿单裤,脱掉了,岂不……这办法不行。他试探着问:“还有其他办法么?”
她挺干脆地答道:“没了!”
石河双手抓住湿漉漉的头发,自言自语:“这,该怎么办啊?”
水燕笑眯眯地望着他,用一种戏谑的口吻说:“喂,石河,你就把裤儿脱下来吧。”
“不行!”他说:“你怎么不脱裤儿呢?”话刚说完,他立刻后悔了——这句话说得多么蠢啊,这句话使得我斯文人的面子丧失殆尽。
水燕急忙双手按住自己的裤腰,仿佛对方真会强迫她脱裤子一样,急忙说:“石河,你好不害羞啊!你穿了窑裤(内裤)的都不脱,难道还要我这个没穿窑裤(内裤)的脱?哼!”
“不行,不可能。”
水燕误会了对方话中的意思,为了证明她的确没有穿内裤,她的手掌在屁股上飞快地摩擦着,说:“你看,石河,我屁股上伸伸抖抖的没得一点点楞楞角角。”接着,她将双手叉在腰上,抬起一只脚,大脚指拇翘起来,一上一下地活动着,像一个小小的蛇头,蛇头伸到石河大腿上,一上一下地刮着,脚指甲把贴在对方大腿上的裤子刮得刷刷直响。她说:“石河,你穿了窑裤(内裤)的嘛,你窑裤(内裤)的楞楞角角都现出来了。”
湿裤子贴到大腿上,现出里面内裤的影子,这没什么奇怪的。
石河啪一巴掌打掉了她的脚,旋即蹲到船头上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水燕也笑了,一边笑一边说:“我的脚指拇刮得你的腿皮子发痒,石河,是不是啊?”
石河站起身,揉了揉满眼泪花的眼睛,爽快地说:“好吧,我脱裤子。”
石河的裤腰带被雨水湿透了,不知怎么打成了死结,他解了许久也没法把死结解开。水燕看着他一副狼狈样儿,禁不住嘻嘻嘻地笑起来,说:“石河,裤腰带打不开了么?”
他难为情地搔着头皮,没说话。
水燕笑嘻嘻地走过来,笑嘻嘻地注视着他。突然,她一只手猛地插进他腰间。他大吃一惊,感觉到一条泥鳅滑溜溜地贴着他的肌肤,没等他醒悟过来,裤腰带已被水燕砰一声拉断了。水燕便笑嘻嘻地说:“石河,裤腰带断了,快脱裤儿啊!”
他刚一撩开裤腰,却又赶忙紧紧地捂住,脸孔比先前烧得更烫了。
水燕依然笑嘻嘻地催促道:“快脱裤儿啊!”
“我的内裤……撕破了。”原来,水燕把石河内裤的裤带也扯断了。
水燕又大笑起来,开心地说:“石河,你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灾星。”
他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与水燕继续扯下去,岔开话题,问:“水燕,怎么办呢?”
“石河,你脱吧。我转过身背对着你。船里的水呢,你一个人舀。”
他使劲摇着头。
水燕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如何办呢?”
夜色从四面渐渐逼近过来,渐渐染黑了他们眼前的景物。夜色启迪了他。他忽然想到了一个根本不能叫作办法的办法,高兴地说:“水燕,等天黑尽以后,我就脱裤子。”
水燕仍旧是那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摊开双手说:“石河,你真的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4、哨叶
我沿着曲折的江岸朝上游走去。古朴的土地,旖旎的风光,映衬着我心中一小片暮云般淡淡的哀伤。我想,一旦进入这块土地,被一片绿草野花包围,爽心悦目的色彩挤满胸膛,抑郁在心中的悲悲戚戚的愁云,没有理由不散开吧!
前方,一位挎着竹篮的妇女蹒跚着朝下游走来。
天黑了,就并非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夜色把他和水燕完全笼罩了时,当水燕伸过一只脚捅他时,他忽然感到羞愧极了,脸孔轰一下燃烧起来。他仍旧坐在船上,假装想什么心事,一动也不动。可是,水燕却火爆爆地大吼一声:“石河!”
石河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答道:“干什么?”
“我以为你死过去了呢。”水燕站起身,双手交错抱在胸前,两片嘴皮儿故作不满地翘着。
石河仍旧坐在船头上,头低垂着,“水燕,你喊我有什么事?”
水燕踢了石河一脚,笑着说:“天已经黑完了,你干嘛还不脱啊?”
“我……我忘记了。”
“呸!石河,你又瞒我。”
“嘿嘿嘿……”石河尴尬地笑着,然后装模作样地观望着其实什么也望不到的夜空。
水燕伸出一只手,半真半假地说:“石河,我来帮你脱裤儿,要不要得?”
石河大吃一惊,紧紧地捂住裤腰,躬着身,急忙告饶:“水燕,绝对不行!”
水燕往前跨了一步,手仍旧那么伸着,仍旧那么半真半假地说:“我来帮你脱嘛。”
“我脱 ,我脱我脱。”这一次,石河是真的脱掉了裤子。
万事万物都像凝固了一样,我和那位面容憔悴的妇人面对面地站着,彼此都吃惊地注视着对方。
她那灼热的目光唤醒了我记忆深处许许多多的往事,我不清楚这些往事是甜呢还是苦。
“水燕。”我轻轻地唤道。
水燕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说话。我细致地端详着她,我力求从她身上寻找到往日那位浑身野性又柔情满怀的少女的姿影。可是……我叹息道:我的确不应该现在回来;如果早几年回来,那么,往日那位少女的姿影,仍旧会在我的眼前翩翩起舞,她那既野性又柔情的迷人的气息,仍旧会弥漫在我身旁、萦绕在我心中。
水燕还是那么淡淡地笑着,每一丝纹路里都漾出母爱般的慈祥,她轻轻地说:“你,回来了。”
鼓起了好大的勇气,石河终于羞羞答答地把长裤脱下来了。他一只手提着随时都会滑下去的内裤,另一只手将长裤递给水燕,瓮声瓮气地说:“裤子在这儿,你拿去吧。”
水燕接过来,用力抖了抖,凑到鼻孔前闻了闻,笑嘻嘻地说:“好大一股骚臭气味啊,呸!”
她把裤脚倒提在手上,用力绞成一个疙瘩,又扯了扯裤腰,说:“石河,你提那边裤腰,我提这边裤腰,一起来舀水。”
石河左手紧紧地提住身上的内裤,右手捏住长裤的裤腰。
“石河,我喊一,就弯腰;我喊二,就灌水;我喊三,就倒水。马上开始了。”
“一。”
他和她一齐把腰弯下去。
“二。”
他和她一齐把整条裤子按进船舱的水里。
“三。”
他和她提起裤腰站起身,两只裤腿里装满了水,飞快地往船舱外倒去。
这种舀水法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可是,却害苦了石河,他既要应着水燕的口号声,弯腰、灌水、倒水,又要提防稍有疏忽就会滑下去的内裤。
水燕忽然喊了一声:“停!”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石河,像你这样,要舀到哪年哪月啊?”
石河把内裤使劲往上提了提,说:“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干啥子没有办法啊?你把窑裤(内裤)脱了,早点把水舀干,你早点穿裤儿。”
“不……”
水燕早料到石河不会这样做的,没等石河把“不行”两个字说完,她突然把手插进他的裤腰,用力一扯,随着嘶啦的清脆的响声,内裤撕成了两大块。
一切都无遮无掩地暴露在黑沉沉的夜空中。
石河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低头看了看被撕破的内裤,双手胡乱摸了几下,只摸到一块碎布条。他恼羞成怒地举起拳头,怒吼道:“水燕,老子打死你!”但是,他的拳头举在半空中没有打下去。
水燕早已转过身,背对着他,冷冷地说:“石河,打吧。”
石河愤怒地望着水燕,拳头仍旧在半空中高举着。
水燕转过身,幽幽地望着石河,说:“石河,这时候,你稍稍有点男人气味。”
石河的手缓缓地放下来。
“石河,我把眼睛紧闭起来,要不要得啊?”她果然把眼睛紧闭起来。那神态,那语气,严肃得不能再严肃,庄重得不能再庄重了。
石河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接下去,他俩又舀起水来。
“一。”
他和她一齐把腰弯下去;
“二。”
……
“三。”
……
“得!”
这一次,是石河喊出了声。他丢了长裤,双手捂住下裆,那副惊惶的模样把水燕搞得莫名其妙。
“石河,你又在搞啥鬼名堂啊?”
“你……你……眼睛睁起的,看见我……不行不行!”
“石河,你这个人啊!”水燕感到可笑又可气,原来她的眼睛真的睁着。可,闭着双眼又怎能舀水呢?想了想,她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说:“石河,把你的衣裳脱下来包住你的屁股,行了吧?”
他脱下湿漉漉的衣服紧紧系在腰上,前后左右地看了看,这才放心地说:“水燕,行了。”
“一。”
……
“二。”
……
“三。”
……
我和水燕朝上游走去。我们默默走着,谁也没说话。水燕的一只手紧紧的捏住我的胳膊,脚踩在沙滩上,听到细微的沙沙响声。我瞥见她挎着的竹篮装满了哨叶草。我张了张嘴,想问点什么,却终究什么也没问。
水燕主动打破了沉默,解释道:“我采哨叶草做成哨哨,卖给街上的小娃儿。”
“哦……”
水燕突然站住了,再一次细微地端详着我,然后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埋着头默默地朝前走去。
“水燕,几江渡怎么没人过河?”
“改了,”她指了指上游,“那上头去了,还是叫几江渡。石河,你不会无缘无故回来吧。”
我觉得心中一痛,急忙望几江河。
“你还记得这条河?”
“水燕,我……”
水燕平静地说,“走吧,你难得回来,我请你吃豆花饭。”
我望着几江河,心里一会儿激动,一会儿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