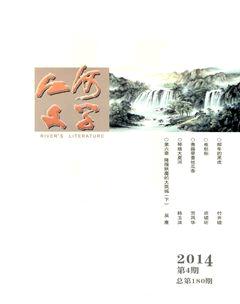日子悠长
石泽丰
麦子在田野中兴奋地抽着穗,和着尚未成熟的油菜荚,迟迟不肯成熟,仿佛是在等待着日子,等待着布谷远一声近一声的鸣叫,直到它叫得不依不饶。也就是这个时节,白天的时光一再悠长,在过去农村孩子的眼里,它似乎是延长了日子,延长着一种饥饿与无奈。儿时,面对拮据的生活,母亲总是这样说,过一阵就好了,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青黄不接的日子占据了我童年印象的大部分空间,那是一个少粮缺吃的年代,记得每到这个时候,我家土砖砌成的粮仓里,很少再囤有谷粒。母亲盘算着接上新谷还需要一些时日,便把头年晒干的山芋条搬了出来,混合在米里,一日三餐,其中就有两餐是山芋条稀饭,另一餐的干饭里,山芋条也占到了六七成。母亲用蓝边海碗给父亲盛着稀饭,山芋角堆出碗弦,几碗盛过之后,锅里的稀饭人影可见。即使当时吃饱了,可等不到下一餐的到来,肚子就饿得咕噜咕噜地叫。我深信父母也有我同样的感受,但是他们没有说,依旧到野外去劳作,或耕田或插秧,在劳动中等待着午季作物的成熟,等待着把它们卖出,再从乡村的食品站买回一些大米或麦面,掺和在贫穷的日子里,用爱温暖着这个家,抚慰着孩子们如饥似渴的心灵。
即便如此,我仍感觉到那些晴好的天气里,太阳总是早早地爬上山头,而且时间一天比一天提前。我憎恨过这种季节,它把农村孩子的肚子掏空,掏得有时让人流口水,直到上午九点多早餐的来临。我记得父母曾经教导过我,要向早起的鸟雀学习,它们天亮就飞出鸟窝,飞向田野,勤劳寻觅着自己的食物。也许是从它们的身上悟出了什么道理,父母在不着边际向前奔跑的岁月里,任劳任怨,早出晚归,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年年种出的稻谷除了能交掉公粮之外,还剩余一些,就用来维持着生计,填充着儿女们的饥饿。现在回想起来,为了让我和姐姐尽量吃饱,让我们感受到日子尽管悠长,但其中还是有着甜蜜滋味,他们默默地省吃俭用,默默地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自己的命运。透过父母诚实地劳作,看到长势很好的庄稼,渐渐地,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我也看到了丰衣足食的希望……
如今,同样是在这个时令节段,同样是太阳光白晃晃地照着万物生长。我因采访行走于乡村田野,目击之处,绿阴如从前,而农村里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们,在这个物质丰盛的年代,他们再也没有更多地关注农作物的生长,也无心无力地去关注这一切。虽然田地被抛荒,但农村的日子,再也不像以前我所感到的那么悠长。
村庄的静
车子在毗邻村庄的高速公路上飞奔,透过车窗,我看到那些房舍横七竖八地静立在那里,有的外墙装修尽显档次,有的则是毛坯模样,这似乎与村庄无关,仿佛是主人的能力所至。但无论怎样,我始终认为,它们都是村庄一根根知疼知痛的神经,构筑着村庄的躯体,让村庄的内涵深入人心。
每每路过村庄,我总爱关注那些接纳人和牲畜的大门,一户也好,两户也罢。它们在主人劳作归来时被推开,户枢在石头上转动,发出吱呀的声响,鲜活了整个村庄的灵气,构出了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这是我所欣然见到的。可是,如今更多的时候,我所注意到的那些门扉,常常处于关闭状态,门口的泥土空地上,长出了一些野草。事后一打听,这些门日日紧闭,它们的主人携带妻儿老小,终年外出打工。也许是主人背井离乡了,村庄空旷起来,寂寞起来,渐渐地,以一种忧伤的静,遮蔽住了当初温暖的意境。
在我的老家,村庄的外围,通往都市的高速噪音不断,开往京城的火车夹杂着嘶鸣从此经过,它们把村庄不愿倾听的声响,却无休无止地扔给了村庄,把夏日的蛙鸣和蝉声驱赶得一干二净。几年前,乡亲们因无法忍受这样的喧嚣,作出了搬迁的抉择,他们丢弃了老屋,丢弃了当年生我养我的村庄。这次出差,我从老家村庄边的高速上经过,打开车窗,外面是呼呼的风声,我的故乡安静得像一位洞穿世事的长者,不愿开口多说一句话,只是以自己静默之态,坐失自己的余年。作为被它哺育过的孩子,此时,我的心被它的静纠缠出了一种莫明其妙的伤痛,是我背离了故乡,是我们背弃了村庄。
记得儿时的村庄,哪怕是在深夜,都有虫鸣在墙角下弹唱,它们哄着村庄入眠,哄着孩子们进入甜蜜的梦乡。即使有陌生的脚步声闯了进来,最先是谁家的犬,吠着警惕,然后在主人的呵斥声中又归于平静。这样的夜晚,村庄安静地睡了,它搂着村里的人和物,搂着时光,安然地走过春夏秋冬。我想,这样的静,是村庄闭目养神所需要的,是我们在那里生活的福气。
然而在岁月的长河中,在开发与保护的较量中,是谁打破了村庄的这种宁静?让它承受着痛苦,让它默不作声。
就在前几天,我去深山采访一位老农的时候,他最后问我:“你在退休之后,是否愿意重回故乡?”看我长时间没有回音,老农叹了一口气,走进了自己生活一辈子的里屋。许久,他的话像一根银针,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肺。面对他生活的原始山乡,万木葱茏,我又何尝不向往这样的生活佳境呢!只是我的故乡,如今静得没有一点活气,听说早年一些年轻人搬家的搬家,打工的打工,出嫁的出嫁。现在开发商已经谈好了那块地皮,很快就会在那里盖起一个工厂,几个老年人也守不住了,他们被迫着离开。
我的村庄从恬静中走向了寂寥,从繁华中走向了落寞,最终,它将以生存不敌推土机的强攻之势,消失在我思念的尽头。
触到心底的痛
我承认,是我的到来惊动了这一方平静的水域,包括她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波澜。这是一个乡野,我的到访让鹅们惊恐着扑通到水里,溅起阵阵涟漪。看我们走了过来,那个牧鹅的小姑娘站起身,会心地向我们微微一笑。
在村委会主任的带领下,我终于找到了她。想从她那里了解更多有关她的信息和她内心的一些想法,这是我此行采访孤儿的目的。她两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而后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曾经念过五年书,后来为了撑起这个家,十二岁的她便为养殖户干起了牧鹅的差事……这是她爷爷向我所作的介绍。简单、粗略。事后,我对村主任说,我很想采访一下这个小姑娘,听听她还有些什么渺小的愿望。在村主任和小姑娘爷爷的带领下,我来到了她牧鹅的池塘边。
这里三面环山,一口池塘坐落在山坳里,无风,水面格外平静。小姑娘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鹅们在草地上快乐地啄着青草,脸上显出了极为舒坦而又满足的神情,仿佛只要鹅们不乱跑,就算是她最大的快乐了。置身于这样的快乐之中,她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忘记了失去父母关爱后的痛苦与酸楚。面对如此场景,我是不是该掉头回去,结束这次被安排的采访?我真不忍心探究小姑娘内心的世界,原本上天就对她很不公平了。我歉意地说,真不好意思,让你的鹅们全都跑到水里去了,它们很难赶上岸的吧?小姑娘摇了摇头,说鹅们还是比较听她的话的,毕竟她与它们相处已有近两年的时间。
也许是前两天就得知我要来采访,她仿佛有准备似的,向我道着她的境况,这与她爷爷向我叙说的完全相同。一道伤口本已过了剧痛期,如果向它投去一把盐,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岂不又在重演?想到这,我对自己说,随姑娘自己说吧,她想说就说,不说也不要去追问,以免让她更伤心。
我和她坐在草地上,她向我叙说了很多很多有关她的故事,包括有些爱心人向她捐钱、捐物,包括她与鹅们相处的一些趣事,我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说到伤心处,我极力安慰她,让她感受到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许多好心人都在关心她。在我们即将闲聊结束的时候,村主任当着我们的面说,其实,像她这样还不能算真正的孤儿,因为在她父亲去世之后,她的母亲就改嫁了,只是一直没有过来看望过她……这番话,着实让小姑娘为之一震,她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村主任,看着她的爷爷,泪水开始慢慢地溢出眼窝。小姑娘的爷爷低下了头,再也没有作声。村主任见状,很快就收住了自己的话。
是什么原因非要将这一信息隐瞒着小姑娘?母女十几年的感情就这样被一个谎言所掩埋,试图将它沉于岁月的海底,可是,村主任的无意之言,如今,让小姑娘如何去猜想,又如何去面对?我真的不敢多想。
车站
那年,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时,每天上下班,我都要经过这个乡镇的车站。走的次数多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站内没有多少乘客之外,与别的车站再也没有什么两样,也许这是一个乡镇车站,或是在单位上班,我总是早出晚归的缘故。无论车站与车站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作为乘客暂时落脚的地方,这一相似之处,总让我有太多的感慨。
1999年春节刚过,我怀揣那本中专毕业证,从安庆高河上火车,不知天高地厚地南下广州。我拿着那张检过的火车票,回望身后那些攒动的人头,顷刻间,心头涌上一股沉重的压抑感。我上了车,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拥挤的人流。我一会儿想,这些陌生的乘客,他们是从哪里来?或是到哪里去?一会儿又想,如果没有这个车站,他们又该在哪里歇脚……想着想着,我庆幸车站的存在,为他们同时也为我自己。
我与那些同路的人相聚在一个车站,离别在另一个车站,聚散本是一种必然,然而,生命之中,一些聚散却给了我们太多的无奈和伤感。
父亲与大姑本是同在石氏的这个车站上,但由于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生命如稗草的年代。灾难、饥荒困扰着每个贫困的家庭,父亲的出生,对于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祖父母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何况两年之后,大姑以一个不顾人世间疾苦的生命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她哇哇落地的时候,祖父在偏房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堂屋,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在大姑出生不到十天时,祖父曾轻声地对祖母何氏说:“将她送人吧!”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压下了多少母爱的砝码,留送非轻,都是两头不着岸的船……
不该来的是不是终究注定不该来?大姑三个月大的时候,被抱养给了同乡的一个木匠,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别人的家庭里生活。就在她十七岁那年,尽管是花样的年华,但在人世间这座站台上,她还是早早地下了车。据说她病得很突然,也很奇怪,先是头晕,呕吐,继而失语。其间也只是从家到车站一个小时的工夫,靠两个人吱吱呀呀地抬到车站,正准备叫一辆车送到县城去救治的时候,大姑一度清醒过来,她巴望在这个时候能看到生她的父母———这人生最初的站台。但在当时,我的祖父母踉跄哭喊着正在赶来的途中,谁知残酷的病魔在此刻就执行了她的死刑。在那个乡镇的车站,她含泪地坐上了开往天堂的“列车”,开始了更远更寂寞的行程……
往事就像一根知疼知痛的神经,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生前每每提起此事,思绪总是难以平静。也许这人生中的一页,于他,于我的祖父母,都是一个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
父亲与酒
父亲好酒。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到他生命的结束,这期间,我感到他把酒视为碗中菜,视为知己,尤其是在劳累之后,父亲常常用酒来解疲劳,仿佛只有酒能活活他的筋骨,只有酒才能让他有使不完的劲。
父亲本是一个寡言的人,三杯酒下肚之后,他便慢慢地总结起自己的不足来,并谈开一些想法,诸如要如何凭自己的力量把家庭营造得更好,把子女们抚育得更幸福。这是父亲的真心话,他平时也是竭力地按着自己这样的设想,一路前行。不说不知道,一说了,母亲常常为此感动。即使日子过得再艰难,母亲也要吩咐我和姐姐,到集镇上打壶散酒来,不能亏待父亲。记得儿时,双抢季节,烈日当空,农民一边要把稻子收割上来,一边还要抢时间把秧苗插下去,这个时候,父亲便是整个家庭体力劳动的主角。他清晨挑着箩筐走向田野,脱粒、运稻、耕田……累了,父亲就坐在田埂上吸一袋旱烟,咕咕地喝上几口茶水,便又开始劳作,直到暮色四合。
那时,因家庭的拮据,父亲总是控制着自己饮酒,哪怕是在农村双抢最劳累的季节。有好几次,父亲原本拿出了酒盅,看到壶里的酒不多了,他便将酒盅又放了回去,自言自语地说,还是明天晚上再喝吧。就这样,他把自己的喜好匀和地调在苦难的日子里,把儿女们拖养长大,自己却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在我印象中,有一年春节,父亲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一道去姑姑家拜年,席间,以酒待客的姑父陪他们喝了许多,最后,我的几个叔伯实在喝不下去了,各自杯中还剩有一杯酒,姑姑便在一旁建议,喝不掉就倒在桌子上擦桌子吧。父亲见状,却说,倒掉多可惜呀!全部给我吧,我来喝掉。说实在的,那酒也不是什么好酒,正因多喝了几杯,那一餐,父亲喝高了。
父亲总是刻意地控制着自己饮酒的量,节俭喝酒,即使后来年岁增高了,儿女们成家了,他都是如此。随着日子慢慢好转,父亲依旧不忘那些曾经走过的艰苦岁月。在乡下,他将别人送的瓶装酒放在柜子里,等着过年或有客人来了再拿出来,平时,自己却打散酒喝,每晚喝上几小杯。我结婚那年,父亲生日快到的时候,妻子便上街去买了两瓶价值近百元的白酒,托人捎给远在乡下的父亲。在电话的那头,他责怪不已,说是我们刚结婚,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何须为他买那么好的酒。事后,他告诉我,那一晚,他激动得没有睡着。那两瓶酒,一直藏在父亲的柜子里,直到我们回家过春节时,他才拿出来,与我们一道坐喝。
那顿晚餐,也许是因为喝了酒,我感到我们父子如兄弟。桌上,我和父亲杯来盏去,坐着平喝。我听他讲他的童年,我听他讲他对酒的喜好,我听他讲我小时不听话时,他打我之后心理愧疚的感受。他责怪过自己,情深之处,我便端起酒杯,向他敬上一杯。我觉得我的父亲,在一生的路上,为了这个家,他克制着自己的喜好,直到生命结束。
父亲,你视酒如友,这一辈子,也许,你却从来没有喝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