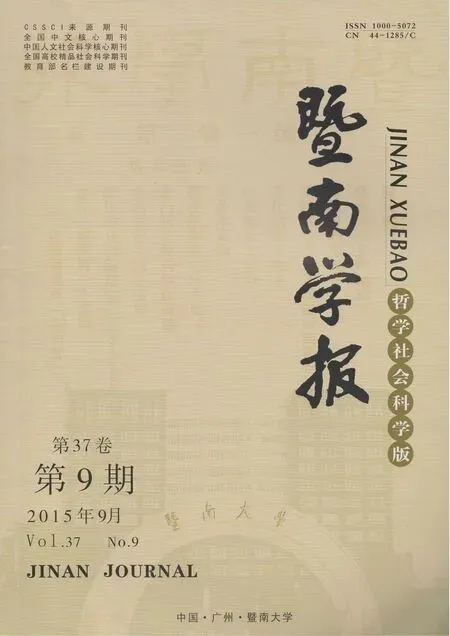民国时期南京公共交通工具博弈及政府因应
李沛霖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民国时期南京公共交通工具博弈及政府因应
李沛霖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民国以降及抗战前,随着南京空间扩展和人口递增,交通需求随之增加,城市公共交通结构由人畜力工具逐渐向机械交通方式转变。其中,作为公共交通系统中机械交通和人力工具的典型代表,公共汽车的蔚然兴起形成对人力车的形成竞争,两者的博弈从未间断。虽当局对身处劣势的人力车业加以安抚,但因公共汽车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其在博弈中被日渐征服,终而彰显机械交通取代人力工具的城市化时势。[关键词]
民国;南京;人力车;公共汽车;博弈博弈论(game theory)是指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在像市场这样的竞技场上相互作用,选择对每一方都产生共同影响的行动或策略。而城市社会学家豪默·霍伊特亦指出,城市发展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在城市主要发展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交通工具的影响。回溯往祀,民国肇始及1937年抗战爆发前,我国“水陆交通情形为之丕变,用石油、电气以为交通工具之原动力,于是电车、汽车络绎于途”,斯时南京已“为首都所在,轮轨交通、绾毂南北,水陆空交通相当发达,为国内重要交通中心之一”。作为彼时南京城市公共交通主流工具的公共汽车和人力车,竞相驰骋、博弈激烈,进而使交通方式进步和城市化进程赓续推演。然迄至现时,检视以往成果,似觉尚有探讨之可能。由是,对此做出研证,以期为该域进献绵薄之力。
一、机械交通对人力工具形成超越
一般而论,交通因需求产生,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给,交通工具是满足一定交通需求而生。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城市交通工具多由西方导入,“惟人力车为东方都市交通工具之一,此类工具原发轫于日本东京,故又名东洋车”,后逐渐普遍于“北平、上海、汉口、广州、南京等市,人力车皆成为重要交通工具,其他较小都市人力车亦所在多有”。譬如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人力车始为大众服务,出租营业用以载客。那以后,因城市空间狭隘(城墙内面积40.804平方公里)、人口稀少(1912年26.9万人),加之“城内道路历久失修,类多凸凹不平,道路甚狭竟有不能过两车者”,进而“马车、人力车络绎不绝”。斯时,“南京人力车大抵近路贵,远路反可略贱;往冷静地方贵,往热闹地方贱;夏时及雨天贵,冬季及晴天贱;车多时贱,车少时贵”。车价讲钟点计,约每点钟小洋1角5分至2角;且“城内除小火车与马车、人力车而外,直无较为迅捷之代步”。
嗣后,1920年南京人口近40万(39.2万人),加之当时“长途(公共,以下同)汽车简捷经济,世人殆莫不知。两年来各省提倡之声响,鄂湘浙粤猛进颇著成效,而逐渐放行者尤不可胜数”的影响,市民已感“交通不便,自城南至下关相距二十余里,虽有人力车及马车,费时既多,经济亦不见甚省,城内居人感觉有创设长途汽车之必要”,即“按近年南京人口日繁,此项交通实不可缓”。从而,作为城市机械交通的代表——公共汽车应时而生。如1924年4月宁垣汽车公司开行公共汽车6辆,“起下关车站至夫子庙附近的门帘桥”,途设三牌楼、鼓楼、东南大学、大行宫等8站,“旅客票价每站大洋五分(铜圆五枚),全线小洋四角”;虽“车资较人力车价略昂”,但“该公司乃应需要而创设”。然不可否认,其时全市公共汽车仅为6辆且“城内小火车机车损坏仅开单班,供不应求”,因而“人力车(仍)居本市车辆数目之最大多数,亦为市民交通之最重要工具”。
自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后,南京区域逐渐扩张。如定都初,“暂以江宁城厢内外及江浦县属之浦口为其区域”,面积157平方公里。至1935年“省市划界”,则“四郊之地尽入南京市区”,全市面积达465平方公里,并划十一区。彼时,“南京市面积居全国各市第一位,为世界有数之大城”,比明代其外廓扩大50%;全市人口由1927年36.0万人,增至1933年72.6万人、1936年100.6万人、战前达101.8万人,俨然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地理空间的大都市。由此,随着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导致人们出行距离逐步超出可使用非机动交通方式的范围,交通需求迅速增长,(机动)公共交通成为多数人必选的交通方式。即在“本市繁荣日甚、人口增多,公共交通设备需要日切”的情势下,南京市府以“公共汽车影响市民生活巨大,应由政府设立监督机关严密查勘,务使其能便利全市人民为主旨”,进而“为提倡交通及便利市民起见,多方规划公共汽车,促其实现”,1927年8月设公共汽车管理处、9月向全市招商承办。嗣后,关庙、振裕公司等公共汽车得以穿流行驶。

从上述大幅客流承载中易于看出,当时公共汽车已成为南京城市交通主干,对市民生活的影响至深至巨。具如全市1931年移入336047人、移出259327人,1936年迁入568122人、徙出574656人,人口流动量均超同期总人口1/2强。这一情形,如没有载客众、迅捷的机械交通予以承负,显然无法实现。从更广视角考察,战前南京面积持续扩张、城市移民不断增加,人口流动必然频密;而传统的缓慢的人力工具显然难以适应市民较长距离的交通需求,其才会对快速、舒适的现代公共交通方式产生迫切需要。譬如1927至1936年间,南京人力车数分别为5337、7352、9097、8407、9856、9026、10158、10544、10962、11180辆(其中营业人力车1929、1934、1936和1937年分别7000、8628、9799和9676辆)。而同期(1928—1936年)全市汽车(含公共)则由144辆增加至2119辆。具言之,此期汽车数量增长12.7倍,人力车仅增0.5倍,且1936年后营业人力车已呈递减趋势。推其总因,此与“南京建设国都以来,市政日趋发达,汽车业适以社会之需要”以及“下关、城内往来者有公共汽车之便利,谁雇人力车往来,以牺牲其宝贵之光阴者?”等情事息息相关。由见,交通方式是居民根据自身需求和爱好而选择的交通工具,如某种交通工具能更好地满足,那么其被选择的概率就必然会增加,就能生存并不断发展。所以,战前南京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虽呈现混合运行模式,但市民仍对容量大、迅捷的机械交通更为青睐。因而,随着公共汽车的蔚然兴起及其对人力车形成的不断超越,进而使两者之间此消彼长,日益繁盛抑或逐步窳败……
二、人力工具与机械交通的博弈和冲突
博弈论的基本方法是,从竞争对手的角度出发,考虑什么才是它们所关心的利益,然后根据这种估计来选择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时,南京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关乎的核心利益,是生存与发展。但在市场竞技中,因公共汽车的性能和前景较人力车更具优势,使后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生计被威胁,本能的反感与畏惧让两者的博弈和冲突从未间断。
风起于青萍之末,定都前关涉公共汽车与人力车的争议已逐而显现。诚如时人论,“南京人力车极端发达,苦人靠此苦力生活者殆近万人,汽车畅行,伊等生机半绝”。即“金陵五方杂处,劳力尤多,以拉人力车资生者,就月缴车捐核计约在万人之谱。若汽车通行势必侵夺彼等利益,以此等劳力之人与之争利而使顿失生机,似非仁人所忍出……即使官厅强为批准,何足以杜车业之口,而服劳动人民之心”。然反对之声亦言之凿凿,认为“南京自下关至城内一段路广人稀,改乘人力车与马车,则四野荒凉又有暴客之戒,是故下关于城内,俨若秦与越商业之不兴盖有由来也”。“顾于此,群众鼓吹声中,南京方面乃有反对长途汽车之说,斯诚异矣……且伤害生命只可视为非常之事,不可藉此反对也。”事实上,1918年南京已有“金陵长途汽车公司之筹设”;然历六年之久,公共汽车才得通行,这与人力车业的抗争不无关系。如1923年12月6日,宁垣汽车公司筹备完成际,市人力车同业公所“以汽车通行后与人力车营业大受影响”为由召集同业开会,决议换购车捐执照“前十日收车进厂,停止营业以示反对”。而警察厅“恐一经停业,此万余苦力难免不发生暴动。即饬派长警至各车行通知不许停业,有何问题尽可商议并召集再次开会。”嗣后,“各车业公所召集同业开会,讨论结果仍照前议,一致停业并散发通告,大有无可调停之势”。由此,车捐局和汽车公司负责人迫于开会次日前往公所,应允其所提五项条件,主要有“向地方公会士绅承诺,汽车公司须严格考求驾驶人才;不得驶于所定路线以外,得各方谅解”等。
事态并没有戛然而止。1924年3月,宁垣公共汽车将通行际,人力车业公所“对于反对之运动,大有再接再厉之势,非达到取消该公司之营业执照不可”。实“因该公司车辆业已运到,不日即将行驶。车业公所特开会讨论,当场议决:倘长途汽车一旦上街行驶,即由公所派人前往阻止开行,如不遵从,即将车辆扣留”。江苏省长为免冲突,“又饬令警厅妥为防范、免滋事端”。警厅遂“令其(汽车)暂缓行驶,一面委派专员向车业公所关切疏通、俾免冲突。惟车业公所因维持生活之故,反对甚为坚持,苟官厅许其行驶则全城车辆预备一律罢工,并从长途汽车开行日起,一律不购捐票以示抵制”。虽情事愈加紧张,但公共汽车发起人“内部仍进行未懈,此年来路政发达之证验”。经历诸多波折,次月公共汽车终驶于南京。然不及一年,人力车夫再为抗议公共汽车通行而罢工,“并阻碍全市四千余马车、汽车之交通”。由见,人力车与公共汽车的冲突在当时已持续凸显。
值得指出的是,定都后由于“首都斯奠、中外具瞻”,南京当局已不能无视公共交通业如此前的无序,进而做出管控。即“因南京车辆价目极不一致,人民感受痛苦至深”,市工务局规定“出租各种车辆之价目应为划一,(并)以当下生活情形重行规定价目”,于1927年9月1日正式施行。翌年8月,“市府前增订定各项车辆价目,惟去年情形已与现在不同。最近市工务局复提出车辆雇驶价目提案,经第九次市政府会议通过,即日由工务局颁布施行,亦旅行之指南也”。如据当年工务局规定各项车辆价目显示,人力车乘价(小洋)为一日24角、半日12角、一点钟3角;每里小洋5分,不足一里者以一里计。而公共汽车每小站小洋5分,不足一站者以一站计。即彼时人力车乘价已实行一点钟、半日和一日的计价标准,并兼以里程计。进一步言,其一点钟乘价虽较定都前有所提升,但较斯时公共汽车每站定价5分而言,则无明显优势。
至1933年,当局再将全市人力车乘价重新厘定:一华里铜圆20枚(每公里10枚)。是年11月,江南公司则将市区票价定为每公里铜圆6枚且二站起售,仅行一日即引纷争。如南京市人力车、马车同业公会联合向首都警察厅和市长“乞增高江南价目,俾免纠纷”。因“窃属会等据各方报告,谓江南汽车公司减低价目,影响马车、人力车等营业实非浅鲜,已人人危惧、个个寒心……人力车夫皆属各地逃荒来京就食之贫民,彼为生计必当必重受其害。如其不加入减价竞争则无生计,即加入竞争亦难求一饱,而家口更无法维持,更何来车租以交车主……倘照以上所得之结果,而发生更重大之恐慌者,即此失业之十数万人生计更何法维持,其影响全市之治安秩序至如何程度则不忍言矣”。嗣后,南京市府第283次市政会议议决,自当月27日起公共汽车票价改为每公里铜圆7枚、二站起售,由夫子庙至下关的票价定为70枚、以资一律,“并饬工务局分别通知江南与兴华两汽车公司,遵照办理”。
面对人力车咄咄进逼的气势,公共汽车则处于防御地位,而当局为维护稳定,会要求其再度妥协。如1934年6月,南京市长交议“本市人力车夫因公共汽车发达后,营业衰落、生计困窘,殊堪轸念”。拟将江南、兴华公司汽车原定最低票价铜圆14枚改为21枚(三站起售),“以资救济人力车夫”。此议经市政会议通过自7月16日起实行,由“工务局饬两公司,遵照办理”。然江南公司并不想坐以待毙,向市长呈文,“惟于限制票价一事,市长念及人力车夫生计起见,自不得不恪遵办理,拟请试行半个月,以觇效果……公司营业关系司机售票员之数百人生计,望市长一视同仁,当不致视人力车夫为重而以公司员司为轻也”。至16日,该公司按规定执行的票价已较人力车为昂,致使营业日颓。如其7月上、下半月乘客分别为377,667、285,984人,日均减少7,303人;市区票款分别是21,790、21,154元,日均减少130余元;且“四路车下半月行驶较上半月日均增四辆,否则减少数将更巨”。由此,公司申辩“长此以往不特公共汽车交通无从发展,即欲勉维现状实属不易。垂余公共汽车关系全市民行,赐予妥筹救济办法,俾维久远而利交通”。然市政会议最终议决,“碍难照准、令仰照此”。是年9月,工务局正式通令全市公共汽车改为每站铜圆7枚、三站起售。虽此后江南几度力争请求改回,然市府均不应允。直至1935年11月,因铜圆市价渐涨,当局才饬令公共汽车改每站6枚,但仍规定三站起售其后按站连加6枚。但仅实行一月,人力车夫即为公共汽车减价影响生计,发起斗争;而后汽车扩展市区新路线时,车夫又麇集市府请愿、哀求制止。
具如上述,在人力车与公共汽车的博弈和冲突中,前者并无明显优势。实因战前“南京公共汽车在国内官办商营事业中比较尚为独廉”,且“全市公共汽车票价为京沪区各地汽车票价中之最低者”。虽虑及人力车夫生计,当局对“公共汽车票价一再变更,(江南)公司及乘客均感不便”;但公司仍“营业昌盛、盈利颇丰”,如开业首日营收120元,战前每日达五六千元;1933、1935和1937年度则分别盈余4.8、8.4和41.2万元。由见,尽管当局对于公共汽车的乘价一再干预,但从长远眼光看,公共汽车业的日益进步和人力车业的逐渐衰败,已成为无法避循的历史事实。
三、博弈引致的生存危机和政府方因应
民国时期,“中国是处处都落后的国家,(东)洋车不但未曾遭受天演淘汰,而且还异样、普遍的发展起来”。如战前人力车曾是南京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但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在社会不靖和农村凋敝的背景下,本应作为城市交通补充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力车已不仅是一种工具,某种程度上成为贫困、失业民众的谋生途径。譬如“南京人力车夫拉车前职业,以种田者为最多,此可见农村经济之衰落,破产程度之深刻。农民徒以破产又乏熟练技能,生活驱使率迁往都市,遂不得不以拉车为谋生途径。都市人口增加之所以迅速,此盖一因也”。且因“甲等(人力车)造价略高百元上下,乙等造价六七十元之间”,多数人无力购车便向车行车主租用,所以“人力车主有设行者,有一人置备一辆或数辆出租以牟利者”,而“车夫多来自农村逃荒来宁谋生的贫苦农民,车主乘机觊利,愈加制以供其求”。如南京人力车行1920年仅90家;1936年达2000余家,其中大车行约167家,每家20-50辆不等,小车行居全市7/10,每家3-4辆。全市人力车夫至1936年达19598人,“车夫有携家眷者有独身者,令姑以三分之二车夫有家眷计算,本市直接间接依靠人力车为生之人,其数当在五万人以上”。
易言之,博弈论的基本准则是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即公共汽车的开行,不可能不对人力车产生一定影响。长效观,这是一个逐步取代的过程;短期看,则表现为人力车夫的生计更加困窘。具如其时南京人力车夫每日须纳5-6角租金与车主,多数分两班“二人合租一辆,轮流日夜营业”,少数则拖一班。据南京市1350位人力车夫的调查显示,车夫每月净收入5元以下及5-19元占调查总数的75%。车夫家庭中,他人无收入者747家占总数55%,即“家庭大部分专赖一人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其负担之重可以概见”。同时,家庭支出10-29元占总数72%;如将最大占比的收支等级相较,则收不抵支。并且“人力车夫家中,食品费实为重要一项”,每月5-14元食品支出的家庭已超总数70%。如以“恩格尔系数”分析,南京人车车夫的家庭状况为“贫困”。因而,车夫常需借债度日,家中负债者有547家占总数40%;家庭全年改进费为“无”则占71%;即“以南京生活费昂贵,车夫收入低微,衣食住等费用负担已属不小,若望再有余钱改进其生活,实难得也”。推其总因,“车夫为社会劳工中最苦工作,终日奔波流尽血汗。其所得代价除缴纳车租外,仅能维持最低限度之生活,如有疾病危困或遇天气变化,则连最低限度生活亦将不能维持”。诚如甘圣哲《南京人力车夫调查报告》中所云,“南京人力车夫以牛马式劳动代价之所得,其收入之数几不足以活命养家,工作之苦、生活程度之低,几非吾人所能想象”。
不难发现,彼时公共汽车与人力车的博弈是引致后者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即“近自公共汽车行驶以来,人力车业日形衰落,目下车夫之生活状况更非昔比。如过去京市人力车最发达时期达一万辆以上,车工共二万人。自江南与兴华两公司公共汽车加增行驶后,于城南至下关各处沿途设站,该业大受打击,向政府数度请求救济。至现时(1934年)全市人力车受马达淘汰仅剩九千辆,但事实上仅五千辆上市服务,各车行搁置共达四千辆竟乏人承租。至各车行共达三百余家,因车工减少、捐税加重,现下车辆多停顿不能出租,故对业务前途,莫不深抱悲观”。是年,人力车夫每日劳动所得仅小洋6角(过去可获一元),除应给车行捐款4角外,剩余2角充作本人及家属养活之资。可见,“南京近自公共汽车行驶后,人力车业确受其影响。京市车夫无不告以生意冷淡,营业情形迥非昔比。其每日之所得远不及一二年以前,而车租仍须照付,家庭负担依然,其困苦情形可想见矣”。至1936年,人力车同业公会表示“入夏以来大小车行生意一落千丈,较往年生意仅有十分之三四成,其根本原因即江南汽车车价便宜,以致人力车不能发达,上届营业实有天渊之别也,请求设法救济”。翌年,“王维记”人力车行再向当局呈文,“人力车业自通行江南汽车即告苦万状,营业颓败。今十三辆实口食难度,无力购买车捐……”
进一步言,人力车业面临的生存危机,已不仅是简单的公共交通工具博弈问题,引申到实质则为政府方必须因应的社会问题。因为“人力车夫问题如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处,直接与间接依此为生者,多至数十万人少亦数万人,在数量上已占各大都市社会生活重要的一角……其收入低微、生活困苦,工作不合卫生等,凡此种种,不仅减少车夫个人精力,且妨害民族前途之健康,其成为我国都市社会问题之一,亟待研究与解决者也”。鉴于此,当局不得不对车夫进行帮扶及安置,否则大量失业将引发社会革命。具如1929年当局颁行的《首都计划》中已为人力车预留出生存空间,“南京原有道路不放宽者将概改为内街,作为人力车及步行道路”;“所有干道穿过城垣处皆筑两旁拱门,备人力车及人行之用”。嗣后,南京市府鉴于“本市人力车夫及靠车夫为生之人,约占全市人口三十分之一,车夫问题俱占社会问题中之重要地位,所以改进车夫生活、增进车夫福利,均为极应举办之要政,实为刻不容缓之图”的理念,进而“筹设人力车夫福利会或俱乐部。拟将上海、南京二市人力车夫先行组织、切实办理,如有成绩再行推及全国”;并制定《人力车夫合作社组织计划》、《人力车救济会组织与实行计划》两份,对车夫的疾病和丧亡救济、嫁娶贷款,浴池理发、诊所食堂、平民住宅、俱乐部等诸多事项具体规定,以求“人力车夫生活当可日渐改善,……社会问题无形中解决一部分了”。至1937年1月,南京市人力车夫合作社正式成立,社员73人;经四次向银行借款购车分给各社员使用,各员每日缴该购车费2角6分至8分间,“此虽类似车租,实则完全不同,该社各社员按日所缴之款即为购车之款”。开办至战前已缴足210天,得车1辆者34人,“将来推而广之,务使全市人力车夫,皆能达到拉者有其车之目的”。
然深究而论,政府帮扶人力车业的初衷并非本意,此举仅是为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的权宜之计。如其认为“(虽)以南京目前事实论,在新式交通设备尚未完成前,失业问题方兴未艾际,人力车亦不能遽即废止”。但问题之实质在于,“人力车不仅在欧美各国无之,即在人力车发轫之地——东京亦渐归淘汰。日本因应用机械代替人力,现在东京之人力车已不复认为该处一种交通工具,并预料不久有行将绝迹之可能”。即“文明进步的今日,机械如此发达,残酷劳动如拉人力车者,按理想而言根本应行废除。不独公共汽车在南京交通方面应尽力提倡,即电车及其他新式工具亦当竭力筹设,夫如是,人力车方有消灭之一日”。由此,政府对人力车业仅行安抚之策,并无发展图景。如1930年《南京市陆上交通管理规则》第三十四条中明确规定,人力车、马车不得在公共汽车设站地违章载客、停放车辆,“如违应予重惩”,并“请首都警察厅分饬各局协助执行”;1936年再向全市宣告,“人力车以一万辆为限,过此即不发牌照,以资限制”。易于看出,当局对“人力车费时多而劳工苦,欧美各国均不采用,吾国生产事业不发达,以此为调剂失业平民,原属权宜之计”的意识清楚,仅因畏惧取缔后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故取权宜之策;基本原因是“南京载客之人力手车,自公共汽车设备后,亦只内街小巷尚有需要,将必受天然之淘汰”。
依前而述,人力车夫对于公共汽车的抵触,很大意义是有感与其博弈所引致的生存危机。虽有政府方的应对和帮抚,但交通工具的更迭演替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其症结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政府如何安置这些被逐步淘汰的旧式交通工具的劳动者。
四、结 语
由历史考之,近代“我国交通事业蒸蒸日上,各处交通机关大多采用新式运输利器,旧式舟车渐趋淘汰”。抗战前“人力车(虽)为现今都市重要交通工具之一种,人力车夫亦为维持都市交通重要之一员”;但前已述及,当时南京公共汽车业的日益猛进和人力车业的逐而窳败,已为既成事实。机械交通替代人力工具成为历史时势,前者的暂时退缩并不能为后者提供永续保障。既如此,面对种种囿限和对决失意,人力工具与机械交通的博弈终局,已荦荦大端。诚如时舆所述,“京市交通自公共汽车增加行驶以来,人力车夫叫苦连天,车夫失业而达万余人。一般用血汗与马达竞争之人力车工,日渐处于被征服之境地。迄至现时,行驶市面之人力车辆较前锐减,直接间接影响之贫苦劳工家属共达六万之多……”由是看来,战前人力车虽在南京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有政府方的应对及安抚,但这仍无法逆转机械交通替代人力工具的城市化趋势。换言之,城市交通从人畜力向机械工具递嬗的阶段中,人力车与公共汽车的冲突虽无有宁时,几乎伴随后者产生、发展与壮大的整个过程,但两者间的博弈终局,仍是“马达征服血汗”。而双方博弈引致的此消彼长,最终使得公共汽车成为城市交通的力源中心。属文至此,本题之鹄的虽是以民国南京人力车与公共汽车的博弈为基本预设,然更希冀由中管窥其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交嬗和城市化进程演替的掠影。

【宗教与社会】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嬗变研究(1907—1937)》(批准号:13YJCZH08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共交通与城市嬗变:以近代南京为中心》(批准号:14HQ013)。[作者简介]
李沛霖(1979—),男,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收稿日期]
2015-03-28[中图分类号]
K2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15)09-007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