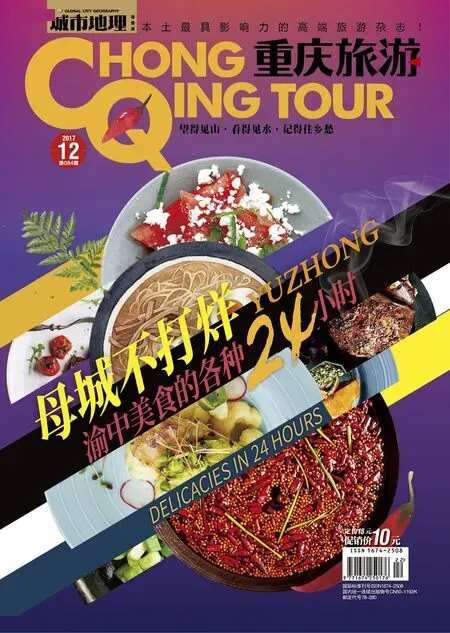桥来桥往
文+赵靓
2009年腊月,我第一次来到重庆。火车在傍晚时分停靠菜园坝站,将我送达这座城市最美妙的时刻。呼——我撅嘴冲公交车窗哈了一口热气,用手套顺时针擦开玻璃上的白雾,一座令人兴奋的城市透过车窗一点一点亮起来。同伴大呼:“快看!这有桥,那有江。”只见高低错落的山城或远或近、或明或暗,在茫茫雾色里穿梭闪烁,犹如“天上的街市”。
对于一个家乡没有大江大河的外地人而言,重庆的桥,是山城的魂骨。江北、渝中、南岸——主城区的三块领地,均由大桥相连。恐怕连土生土长的重庆崽儿也难说出家乡有多少座桥?我能数得出来的是高家花园大桥、石门大桥、嘉华大桥、渝澳大桥、嘉陵江大桥、黄花园大桥、千厮门大桥、朝天门大桥、东水门大桥、长江大桥、菜园坝大桥、鹅公岩大桥、李家沱大桥、马桑溪大桥……,这些桥将重庆城参差隔离的山水重新整合。夜色之中,每座桥婀娜多姿,展示着自身特有的结构与光晕。或直如坦途,或弓如彩虹,或由粗壮的桥墩挺着,或任坚韧的钢条牵着。桥梁的曲线在彩灯照射下映在江面,荡荡悠悠,将人的视线引向那被车龙点亮的远方。而对于城市的那些固有认知——南与北、高与低、远与近——也在桥梁的沟通中被不断刷新。桥的修建,融成了一部山城特有的地方史;桥的分布,化作了一副重庆珍藏的袖珍地图。
重庆的桥与路最让人看得见却摸不着,在重庆找路,可列入“人生中最摧毁斗志的事件”之一。起初我几乎是脚一沾地脑袋就晕,没有朋友帮忙不敢出门。曾有一次想赶公交到朝天门,看见“朝天门大桥站”六个字便果断跳下。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朝天门大桥与朝天门恐怕隔着十万八千里!
上午八点、下午六点,重庆人像其他城市的上班族一样,在住所与单位间奔走,“过桥”是很多人的必然选择——当我意识到,这座城市的人们每天都要跨过中国第一大河流上下班时,顿时对其肃然起敬,因为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能享有此等荣耀。
在每天最“堵”的大桥下,我尤爱傍晚时分的朝天门。坐在梯坎之上,可以看为数不多的“棒棒军”下班回家的身影,听各种摊贩用方言叫卖“冰粉”、“小面”、“可口可乐”的声音,闻空气中越来越浓烈的火锅味道。一群男人在桥墩后脱去衣服,生猛地蹦入江中泅水;年轻的音乐人拨动吉他,只听见歌声在江面上回荡。这时候,长江与嘉陵江两岸亮起灯火,朝天门游船生意迎来最红火的时段,手握喇叭的小贩对游客招揽道:“游长江、嘉陵江,到洋人街参观游览……”
在旱季,长江水位落到河心,大块灰色岩石与黄色沙土显露出来。好奇的当地人拿着鱼竿和相机,直接步行到桥墩下,坐在大石块上钓会儿小鱼,拍张照片发朋友圈说:“哥子我在长江河底!”当雨季来临,长江洪水也爱从山城而过。人们穿着拖鞋踩在河岸边,兴致勃勃,任激荡的江水从脚趾丫拍打到小腿肚。而平日的大趸船已快开到马路上,高高耸立的桥墩也消失在了湍急的水流里。
2015年元旦凌晨,为参加解放碑跨年敲钟活动,我不得不步行通过黄花园大桥。在辞旧迎新的这一夜,黄花园大桥上汇集了一大队前去集会的人,大家欢乐地呼喊着,天空中有放飞的气球,脚底下是日日流淌的长江,过桥而来,过桥而往,不经意间又走进了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