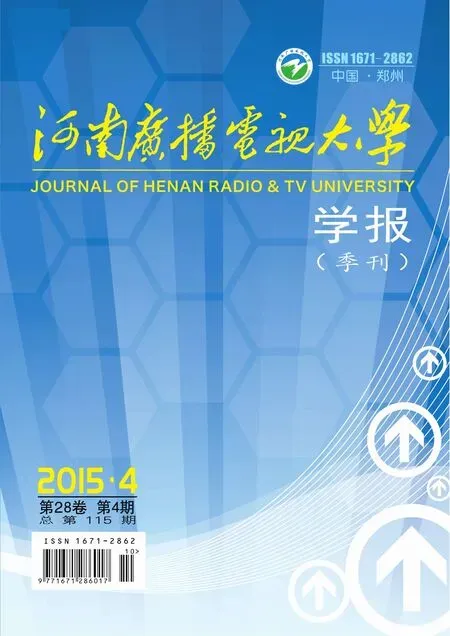诗歌与中原文明
贾文丰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河南郑州451400)
诗歌与中原文明
贾文丰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河南郑州451400)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原民族是最早跨进中华文明大门的民族。诗歌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中原是诞生诗歌最早的区域和沃土。从古诗到《诗》,从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的传《诗》,到汉代的“引诗”和传《诗》,从诗歌发展到鼎盛期的唐诗,到其后的诗歌创作和“引诗”的整个流变过程,可以说,诗歌对中原社会乃至中华民族的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也折射了历代中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明程度,反映了中原民族的传承和创新精神。
中原;诗歌;文明
诗歌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样式。现存最古老的诗歌,诞生于中原大地,是中原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产物。其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又对中原社会的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庙堂奏议,到外交辞令;从祭文颂辞,到墓碣碑铭;从史传著述,到稗官野史;从小说诗话,到围炉杂谈;从饯行送别,到接风洗尘;从宴会酒令,到饮茶趣谈;从君臣唱和,到情人宴私,等等,往往引诗为证,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其意图。可谓无诗不能现其志,无诗不能表其意,无诗不能骋其情,无诗不能示其趣。其诗意有劝,有规,有慨,有慕,无言而无不言。谈到“引诗为证”,不能不谈到“诗”“《诗》”。从古诗到《诗》,从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的传《诗》,到汉代的“引诗”和传《诗》,从诗歌发展到鼎盛期的唐诗,到其后的诗歌创作和“引诗”的整个流变过程,可以说,诗歌对中原社会乃至中华民族的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挥了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也折射了历代中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明程度,反映了中原民族的传承和创新精神。
一
何谓诗歌?诗歌始诞生于何时何地?诸如此类问题,古籍多有述及。《尚书·虞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1]东汉班固说:“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2]东汉郑玄《诗谱序》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唐孔颖达疏:“《正义》曰:‘上皇谓伏羲,三皇最先者,故谓之上皇。’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大庭,神农之别号。”又,“《正义》曰:‘虞书者,舜典也……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于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1]以上是说,有文字记载以来,诗歌之名始见于《舜典》。我们说,天地肇始,万物遂生,而诗之理已寓其中。那么上古之时讴歌吟咏必然有之,即令土鼓、苇籥伴奏,但无文字记载,充其量停留于口头相传而已。
但自《舜典》之后的典籍中,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到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古老的诗歌——《弹歌》。汉赵煜《吴越春秋》卷五载:“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之谓也。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3]陈音,是中原陈国(都今淮阳县)人。陈音见越王勾践时,陈国已被楚国灭掉。据《史记·陈杞世家第六》载,陈愍公二十四年(前478)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愍公,遂灭陈而据为己有。[4]陈国遗民,便以国为氏。而陈国故土,相对于楚国国都郢来说,属于边远地区,所以陈音自称为“楚之鄙人”(即楚国边鄙的人)。陈音所言的“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古老的《弹歌》,仅仅六字,以二言句式概括地描写了中原先人创制弹弓工具驱赶禽兽的全过程。这一先进工具的诞生时间,正是中原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伏羲王天下之后,神农氏、黄帝王天下之前,它蕴含了中原先人的聪明才智,启发了神农氏、黄帝创制了最先进的战场武器——弓箭。对于这首《弹歌》,学者大都认为是首猎歌,是我国渔猎时代劳动人民生活的反映。究其实,其诞生的基础则恰恰是基于儿子对父母的朴素深情,而这种深情又正是后之孝道的始源。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弹歌》是中原先人进入文明社会的产物,充分展现了中原先人的聪明才智。
这是因为,中原民族是最早迈进中华文明社会的民族。《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1]包牺氏,即伏羲氏。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载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宓羲为天子,都陈,在《禹贡》豫州之域……于周,陈胡公所封。故《春秋传》曰:‘陈太昊之墟也。于汉,属淮阳,今陈国是也。’”[5]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三十也道:“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有圣徳,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二十五弦之瑟,木德王。”[5]其中的大皞、太昊均指伏羲。又《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则“河图”之“圣人”,也指伏羲。
伏羲是中华民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迈进的一个圣明帝后,列三皇五帝之首,都于陈,死后也葬于陈。伏羲活动的场所也主要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是他带领中原先人首先跨进了中华民族文明社会的大门,是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作“八卦”,将具象义理化;结网罟,教民渔猎;创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别婚姻,制定嫁娶之礼,推动社会文明;驯养禽兽,以充庖厨之用;将“龙”作为图腾,以龙名设官,肇始了中华龙文化;创制了弦琴,促进了音乐的发展,是当之无愧的“人文始祖”。所以,中原的百姓得人文教化沾溉之先,较早迈进了文明社会,尤其是伏羲所制定的“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使人们建立了家庭,人们不但知其母,而且识其父,于是才有了《弹歌》诞生的基础。
二
随着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和完善,适应了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到了西周时期,诗歌所反映的内容不但丰富,而且广泛地应用于大致国家的典礼、外交场合,中至授徒、教子,小至人们的宴会、娱乐生活中。其间或引诗言志,或引诗表情,或引诗讽谏,或引诗以现风俗。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4]其中的“三百五篇”,即指今通行的《诗经》。至于孔子“删诗”与否,且不去论。但其出于政治目的和授徒的需要,对《诗经》加以编订和整理,是毫无疑问的。
孔子及其弟子对《诗》的传播,也是功不可没的。孔子对《诗》极其重视。《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论语·季氏》载孔子教导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1]孔子教导弟子和儿子的这些话,既阐明了《诗》的重要性,又充分说明了《诗》对于社会文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是他的切身体会之言,也是他对春秋时期诗歌所产生作用的高度概括。
孔子的贤弟子中原人子夏对诗和《诗》理解得最为深刻,他在《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此语不仅回答了诗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而且阐释了其对社会文明的作用,可谓精当详备!
我们说,文化的真正形成,始于封国。而中原在春秋时,封国便多达40个。清王士俊等《河南通志》卷三说:“古初九州,至虞舜肇十有二州。沿革代殊,自唐虞已然矣。成周以后,分合靡常,繁简不一。河南在春秋时,凡四十国。”[5]《诗》反映当时风土人情的诗篇,主要集中在“十五国风”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文化。“十五国风”共有160首诗篇,而产生于中原大地的《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陈风》《桧风》就有84首,加上《周南》《召南》《魏风》《曹风》中的部分诗篇,以及《小雅》中的《宾之初筵》,《大雅》中的《抑》、《崧高》和《商颂》五篇,也就更为可观。因而清王士俊等《河南通志》卷七十二中说:“古诗首‘十五国风’,而在豫者居半。二雅若《宾筵》《抑戒》为卫武诗,《崧高》为申伯作,《商颂》五篇作于殷,传于宋,皆不出豫土。诗教之兴由来懋矣!”就《诗》的内容来说,其反映了中原的诗河文化、神祇文化、婚恋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可称得上多方位地展现了中原文化。[6]同时,其也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再现了中原社会的文明程度。
不容忽略的是,孔子及其弟子在中原的传诗,也大大地促进了中原的社会文明。孔子周游中原列国,前后用去了15年时间。这15年时间,正是孔子年富力强的壮年时期。其间他率领弟子在中原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思想,而《诗》自然是其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正式办私学,是在他68岁回到鲁国之后,到他去世时,前后不过5年时间。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有一番成就,对当时的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
据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记载和孔庙东西两庑奉祀先贤先儒名单可知,孔子中原的贤弟子有名可查的便有20位之多,诸如陈人子张、陈亢、公良孺、巫马期,卫人子贡、子夏、廉絜、琴牢、高柴、公孙龙、勾井疆、奚容蒧、狄黑,蔡人漆雕开、漆雕从、漆雕憑、曹卹、秦冉,宋人原宪、司马耕等。另外,虽为孔子弟子但不在贤弟子之列的也为数不少,如子路妻兄颜仇由、卫司寇惠叔兰等;还有虽不属于中原人,但生前长期在中原从事传播儒家思想,死后葬在中原的孔子贤弟子也不乏其人,如子路、冉伯牛、闵子骞等。这些儒家先贤在孔子生前追随老师传播《诗》学,而在孔子去世后,更是继承老师的遗志不遗余力地传播儒家的经典,以致儒分八派。《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7]
就传《诗》学来说,孔子贤弟子子夏居功甚伟。子夏,即卜商,为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对诗有深入的研究,能通其义理。孔子去世后,子夏居西河(今安阳市一带)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儒林列传》载:“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4]《后汉书·徐防传》也载:“《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8]他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李悝、吴起及商鞅,俱出其门下。孔门弟子有著作传世者,也以子夏为最。《毛诗》传自子夏,《诗序》也为子夏所作。
三
论及“引诗”问题,不能不提中原春秋时期的诸侯大夫们。在外交场合或生活中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一种礼仪和时尚。“引诗”现象表明了《诗》在当时的权威性以及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诗》的道理,具有普遍性,其不仅适合于外交场合,也适合于治国治家和为人处世。《诗》在春秋人物的生活中,运用时涉及各个方面,或游说诸侯,使其易于接受自己的主张;或赞美某一事情,以委婉表达自己的看法;或反驳他人的观点,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或撰文著述,作为论据。
“引诗”现象,又大多出现在儒家的经典中,而以《春秋左氏传》“引诗”为最。其提到《诗》277条,“引诗”则达255条。请看,晋杜预、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卷十九载:“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1]《鸿雁》《四月》《采薇》均为《诗·小雅》篇什,《载驰》为《诗·鄘风》篇什。子家,乃郑国大夫公子归生。季文子,即季孙行父,乃鲁国的正卿。二人一唱一对,均用《诗》的篇什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可称得上典型的“引诗”例子。再如,《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七载:“(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1]宣子,即晋国卿大夫韩起,此时出使郑国将回。子齹、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为郑国六卿大夫,为韩起饯行。郑六卿应韩起之请,分别为他赋《诗·郑风》之《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萚兮》,从而得到了韩起的赞扬,为郑国赢得了好的名声。在《春秋左传》中,中原诸侯大夫们“引诗”的此等例子,不一而足。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中原各国公卿大夫如此“引诗”,士民也起而效之。于是,丰富了中原民族的精神生活,促进了中原社会的文明。
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诗》的权威性遭到一定的破坏。在中原的先秦诸子中,墨家、道家、兵家、法家的著作,很少或者根本不引用《诗》句。秦朝实行“焚书坑儒”,其“引诗”现象可谓绝迹。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施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又使中原儒家“引诗”复兴,使诗风得以不衰。汉代中原儒家著作中的“引诗”现象,便足以说明这一情况。
西汉梁人所编著的《大戴礼记》“引诗”23处。其族侄戴圣所编著的《礼记》则“引诗”99处。尤其是东汉汝南召陵人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引诗”竟达441处之多。《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其经朝廷的发行和推广,无疑对之后的社会文明起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作用。其后,汉献帝时的颍阴(今许昌市)人荀悦所撰写的《汉纪》,“引诗”也有34处。
随着汉末时势动荡和诗歌自身体式的发展变化,《诗》的影响渐微,以致诗歌变于汉魏,极于盛唐。清康熙《全唐诗序》:“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赓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燕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5]在清彭定求等所撰的《全唐诗》中,有世次爵里可考的中原诗人便有162位。其中“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皆出于中原。中原诗歌于当时的繁荣景象便可想而知,其对社会文明程度的影响,也不言而喻了。
自汉以降,随着儒、释、道诸家思想的相互融合,以致有唐及其以后,“引诗”趋向于泛化,人们表情达意不仅仅限于《诗》句,往往引用他人或自己的诗句。这些现象的出现,又不能不说是与中原社会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密切相关了。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2][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3][汉]赵煜.吴越春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4][汉]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5]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6]贾文丰.中原文化概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7][战国]韩非.韩非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Poetry and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Plains
Jia Wenfeng
(Wanfang College of Science&Technology HPU,Zhengzhou,Henan,451400)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n China,the ethic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 the first nation who entere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t earliest.Poetry is the produc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re the earliest area and fertile ground of the poems.From ancient Chinese poems to'Book of Songs',from the spread of'Book of Songs'by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quotations from poems and the spread of'Book of Songs'in Han Dynasty,from the Tang poetry in the heyday of poems to the subsequent poetic creation and quotations from poems,poetry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gener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plain and even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and played an immeasurable role.Meanwhile,the process also reflects the social life and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of the people in all ages in central plains,and the spirit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s.
central plains;poetry;civilization
I207.22
A
1671-2862(2015)04-0044-04
2015-09-01
本文系2012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BWX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贾文丰,男,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教授,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古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