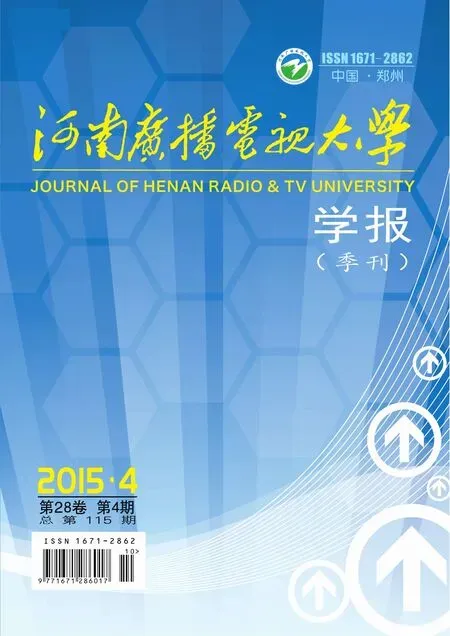李锐小说中的“困境”书写——以《人间》《张马丁的第八天》为例
彭迎
李锐小说中的“困境”书写——以《人间》《张马丁的第八天》为例
彭迎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郑州450000)
李锐的《人间》和《张马丁的第八天》延续了他对人类困境的关注。《人间》中白蛇、粉孩儿、秋白陷入了作为异类被人群排斥的困境,《张马丁的第八天》中的张马丁为了坚守内心真诚的准则,而陷入多重困境。李锐在探寻困境产生的原因时,聚焦到了人类自身,并在不断的逼近、审视中,探测人性的深度,他用真诚而艰难的探索,表达了对人性中善良、真诚的珍视,对人性疯狂、狭隘、偏执的慨叹,言说着全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
李锐;困境;异类;人性
李锐是新时期以来一位重要作家。他“拒绝合唱”,始终以一种清醒独立的姿态,在众语喧哗的新时期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纵观李锐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从《厚土》到《太平风物》,从《旧址》到《银城故事》,从《无风之树》到《万里无云》,从《人间》到《张马丁的第八天》,他锐意创新,不断变换着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构以及叙事方式,但不变的是他始终表达着对人类困境的关注。“从个人出发去追问人类的困境”可以看作是李锐一直以来的文学追求。因此,许多研究者对李锐小说中的“困境”书写有着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吕梁山人物质与精神的困境,多以《厚土》系列和《太平风物》系列为研究对象;二是下乡知青虚妄理想破灭的困境,多以《黑白》《北京有个红太阳》《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为研究对象;三是芸芸众生在无理性历史中的困境,多以《旧址》《银城故事》为例。这几个方面的论述较多,也比较完备,但对于李锐的《人间》和《张马丁的第八天》这两部作品,相对分析较少。然而,通过研究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李锐对人类困境的追问又有了新的质素。
一、“异类”:被排斥的困境
李锐的《人间》是对中国传统白蛇传故事的重新讲述,小说以套层结构讲述了白蛇、秋白前世今生的故事,并穿插了言仕麟(粉孩儿)与香柳娘、小青与范巨卿的故事。
《人间》的主人公白蛇,修炼了三千年,只是为了“做人”来到人间。她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收起自己的法力,严格按照人的准则生活——在西湖边开起绣庄,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怒斥小青依靠妖的法力投机取巧的想法。和许宣的姻缘,让她更加安于人间生活。然而,随着法海的到来,打破了一切平静。为躲避法海,白蛇夫妇和小青来到遥远的碧桃村,开起了药铺,并生下粉孩儿。碧桃村也不是世外桃源,白蛇的回春丹救了村民的命,也暴露了自己妖的身份。在碧桃村的一场瘟疫中,她用自己的血拯救了碧桃村的村民,但善行换来的却是人们对她“妖”的“本质”的更加固执的认定。她所救的人们,此时却义正辞严地要杀死她。许宣在白蛇的请求下,和邻居顺娘带着粉孩儿逃离了碧桃村。在众人的集体压力下,小青死于她所深爱的小生范巨卿的刀下,白蛇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小说前世今生的结构中,白蛇转世到20世纪初的杭州城,成为知识分子秋白。秋白延续了白蛇的困境,在那个“鸣放”的春天,因为几句抱怨,成了人群中的“异类”。大字报、批判会接踵而至。秋白的丈夫更是在批判会上将夫妻二人的夜半私语,将她的愤懑不满全盘托出,说她是包藏祸心的“美女蛇”。在众人激情澎湃的口号中,秋白就像她的前世白蛇那样,被人们“以正义之名驱逐到了人群之外”[1]。
小青是个无忧无虑的小蛇妖,因为惊异于人间花红柳绿的美景,来到了人间;因为不舍与白蛇相依为命的感情,留在了人间;更因为与俊俏的小生范巨卿的男女之爱,留恋这人间。她不辞辛苦地千里奔波,找到身染瘟疫而被同伴抛弃的范巨卿,用自己的鲜血治好了他的病。然而,范巨卿终于得知小青是“妖”这一事实,亲手用剑刺入了小青的心脏。
粉孩儿作为白蛇的儿子,无法摆脱蛇类天生的本能。有了白蛇的悲剧在先,他的父亲和后母知道,粉孩儿的怪异举动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对峙,甚至招致杀戮,于是极力隐藏他的蛇类本能,期待他能像普通人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粉孩儿为自己不得不掩藏的隐疾痛苦不已,只能偶尔偷偷释放自己的蛇类本能,在这种秘密的宣泄中,粉孩儿感到愉悦和兴奋,却不免产生深深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他明白自己“永远都将是人群中的一个异类、妖异”[1],他为此感到苦恼,但是“他身上奇怪的癖好和习性,那让人群惊异害怕”的东西,“不是他想甩脱就能甩脱的”[1]。身为“异类”的困扰,压抑不能言说的痛苦,使他感到孤独,他只有和天生残疾、只会笑不会哭、同样被人们视为异类的香柳娘结为知己。他一次次在梦中与香柳娘相会,互相倾诉,互相安慰,尽情哭泣。香柳娘在自私的族人逼迫下,选择自缢身亡。粉孩儿则厌倦了压抑本性的生活,他躲开容不下异类的喧嚣人群,进入一个全部由畸零人组成的杂耍团,尽情释放本性,像蛇一样狂舞……
白蛇等人的悲剧,是众多人合力绞杀的结果,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法海以除妖、维护人间正义之名,使白蛇的身份被发现,间接杀了白蛇;胡老爹的贪婪、自私、恩将仇报,有意煽动村民对白蛇的敌对情绪,直接造成了白蛇的死亡;还有碧桃村以及附近的民众,他们冷酷无情,加上偏执、盲目的群体造成的狂热力量,虽然没有人亲自动手,却是白蛇自杀的直接原因;还有范巨卿,在偏见和众人的蛊惑下,他亲手杀了为他奉献真心的小青……
在《人间》中,古代的白蛇、青蛇、粉孩儿与20世纪秋白的故事相互交织,为读者展示出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几乎相同的人生境遇——被指认为“异类”而被排斥、被残害的人间悲剧。人们对于异类的警惕、恶意和排斥无处不在:众人看见粉孩儿像蛇一般扭动起舞时的如临大敌,发现白蛇的妖异身份时反戈一击,胡老爹“是妖必害人”的无理论断,人们对秋白的声讨和揭发……人类对异类的排斥万古如斯。在李锐看来,这些悲剧的原因,来自人性自身的弱点:“没有什么生灵比人类更不能容忍异类的”[1]。
二、受难者:无处真诚的困境
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人类的精神困境依然是李锐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主线讲述了清朝末年,乔万尼·马丁跟随主教莱高维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传教,成为天石镇教堂的执事,改名张马丁。在与当地迎神会的教派冲突中,张马丁为保护主教,遭石块击中死亡。莱高维诺主教对官府施加压力,要求在拆除娘娘庙和处死迎神会会首张天赐二者中选其一。张天赐为保住娘娘庙,选择以身殉道,被判斩首。三天后,被误认为死亡的张马丁“复活”。张马丁不顾主教劝告,执意要向世人坦白自己没死的真相,激怒主教被赶出教会。在流浪了七天后,张马丁倒在了娘娘庙,被张天赐的遗孀张王氏救下。几近癫狂状态的张王氏认定张马丁是张天赐转世,执意与他交合……
张马丁的困境可以从几个层面分析。第一个层面是张马丁“选择的困境”。张马丁“复活”后,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接受主教的安排,把复活当作天父的恩典,隐姓埋名,平安度过一生,但是必须隐藏自己没有死的真相。第二是选择说出真相,承认自己没有死,却意味着与他如父亲一样崇敬的主教决裂,面临着被逐出教门、众叛亲离的后果,并随时可能被愤怒的天石村村民当作杀害张天赐的凶手。虔诚的信徒张马丁因为坚持信仰“不可作假证陷害别人”,而成为“叛徒”;但若不被当作“叛徒”,却要背弃自己一直以来真诚的信仰,成为真正的叛教者。这是张马丁面临的选择悖论,也是他的第一个困境。
张马丁面对内心的真诚,不愿看到张天赐因为自己枉死,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不希望有任何人被强迫而信天主,哪怕只有一次,只有一件事”,于是他选择了说出真相。最后,他走出了教堂大门,忍受着饥饿、寒冷对身体的摧残。更令他难受的,还有精神的折磨。不但当地普通民众骂他“洋鬼子,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连教民的孩子也把石子、土块、口水投向他,骂他是犹大、叛徒、魔鬼、毒蛇……当他真的成了人们口中的“叛徒”,他一直虔诚信仰的教义似乎动摇了,“叫他伤心不已百思不解的是,自己只不过按照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做了最诚实的决定,却一下子就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莫非自己真的选择了一条不归的迷途?”[2]张马丁以一个受难者姿态,接受着世间给他的惩罚。
流浪了七天的张马丁昏倒在娘娘庙,被张王氏当作转世的丈夫而救活了。尽管张马丁极力说明,自己不是她丈夫,而是间接害死她丈夫的罪人,但悲伤的张王氏始终不相信。张马丁想要公布真相,却不被受害者接受。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接受惩罚,死亡是他救赎自己的方式。但面对这个绝望的女人,“丈夫的转世复活成了这个女人活下去的最后理由和希望”,张马丁连赴死都成了过错。他一直坚持的真诚,却可能让这个伤心的女人绝望而死。张马丁再一次独自面对这种精神困境,善与恶、真诚与虚伪、生与死,在此时此刻,成为一个个无解的追问。这是张马丁的又一个困境。
当莱高维诺主教不惜使用权势要将天主教堂矗立在娘娘庙的废墟之上,当义和团的“天兵天将”像一股狂热的火焰横扫一切,留下横尸遍地时,张马丁却用生命坚守着自己的真诚。
三、困境书写的意义:叩问人性
李锐作为一位思想型作家,他的作品离不开他的思想起点——“文革”。在《厚土》中,“文革”作为虚化的背景,隐藏在叙述之后;《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中作为实实在在的环境和书写对象;到后来,他对“文革”的思考,逐渐成为一种思想资源,向更遥远的历史深处追溯,在《人间》《张马丁的第八天》中,他的笔触也延伸到“反右”时期,以至于近代历史,甚至是神话传说。始终不变的是李锐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反思和对人类存在方式的追问。
在李锐以往的作品中,给人类带来困境的,要么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难以捉摸的命运,要么是无理性的历史。在《人间》《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李锐将困境的制造者聚焦到了人类自身,并在不断扩大的矛盾中逼近、审视,探测人性的深度。
《人间》涉及族群界定、政治斗争,《张马丁的第八天》写到了文化冲突、教派纷争,都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困境。人们为了不同的理由,各自盘算,互相争斗、倾轧、屠杀。胡老爹和众人,因为“妖必害人”这一看似正当的理由,对从来没有害过人的白蛇等人行屠杀之实,这源于人性中的自私、狭隘和群体的盲目;秋白的丈夫为了赢得组织的信任,求得自身的安全,不惜出卖了妻子,这是人们软弱、自保、从众的心理作祟;法海因为师父教导“不可因小善而忘大义”,陷入情与理的挣扎;莱高维诺主教牺牲一切来到中国传教,甚至以性命相许,但当他传教遇到阻力时,“为了侍奉他唯一的神,他不能容许异教杂音;为了成全无上的大我,他否定任何小我”[3],这源于人性中的执念、“我执”;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大师兄”等一众人,不但屠杀了洋人和教徒,也伤及了众多无辜者,这则更凸显了人性中的丑恶和兽性。人类为了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理论、观念,打着各自不同的名义,互相残杀。从古到今,从远古时期野蛮人的部落战争,到文明社会中的族群界定、政治运动、教派纷争,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异类”的屠杀。即使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仍然阻止不了人类群体之间的纷争。人们依然生活在自己为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这就是李锐深深体会到的人类无可解脱的宿命。“当迫害依靠了神圣的正义之名,当屠杀演变成大众的狂热,当自私和怯懦成为逃生的方法,当仇恨和残忍变成照明的火炬的时候,在这人世间,生而为人到底为了什么?”[4]
白蛇拯救了瘟疫笼罩下众人的性命,反而被人们的自私、残忍、疯狂所绞杀。张马丁直面真相,以身殉道,就像为了拯救众生来到人间的耶稣。张王氏对不同派别的教徒一视同仁的救助,如同救苦救难的菩萨,最后张王氏在绝望中顺着天母河漂流而去……李锐叹息,“在所有的拯救者离开之后,在诸神退场之后,这个无神的世界,这个无可寄托的人间就只剩下了人自己”[5]。李锐对人性一直抱以悲观态度,不愿意给出廉价的救赎或希望,就像鲁迅说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当我们反观现实,我们如今生活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的交流、碰撞逐渐增多,人类该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冲突中走向交融?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难题。李锐用真诚而艰难的探索,表达了对人性中善良、真诚的珍视,对人性疯狂、狭隘、偏执的叹息,始终言说着全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这就是李锐困境书写的意义。
[1]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1-151.
[2]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7.
[3]王德威.一个人的“创世纪”[M]//人间:重述白蛇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0.
[4]李锐.偶遇因缘(代序)[M]//人间——重述白蛇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
[5]李锐,傅小平.历史从来都是万劫不复的此岸——关于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的对话[J].黄河文学,2011,(10):108-116.
I207.4
A
1671-2862(2015)04-0056-03
2015-06-25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李锐小说中的‘困境’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QN-541)的阶段性成果。
彭迎,女,文学硕士,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