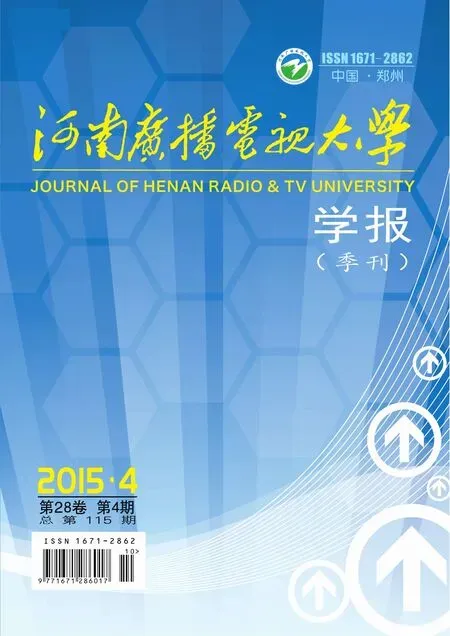论苏轼自嘲的“不合时宜”对其诗词创作的影响
王献峰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论苏轼自嘲的“不合时宜”对其诗词创作的影响
王献峰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一颗璀璨的天才巨星,无论是在诗词歌赋的创作上,还是其自身所散发的人格魅力都受到了后人极大的追捧和敬仰。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学界的诗词大家,却在北宋时期一度自嘲其“不合时宜”,并且更是做出了在后人看来也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举动,使其宦海风波起伏不定。本文试图从他自嘲的“不合时宜”入手,深入分析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根源及对其诗词创作从主题到诗词风格的种种影响,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一下这位诗文大家的卓然风姿。
“不合时宜”;思想根源;诗词创作;影响
一、苏轼自嘲“不合时宜”的出处及其界定
(一)“不合时宜”的出处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诗词史上的大家,其文学成就和影响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政途上面对着接二连三的打击和迫害,身临窘境却显示了文人的张力:居庙堂之高则以“忘躯犯颜”“直言不讳”自许,也以“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自负;处江湖之远则超然物外,将政治上的壮志抱负泼墨挥毫到诗词领域,成为中国古代豪放词派的第一人。正是这样的风姿绰约的文坛领袖,却一度自嘲自己一肚子装着的不是满腹经纶,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那么苏轼所说的自己一肚子“不合时宜”到底是什么呢?
苏轼的“不合时宜”主要见于明人曹臣所编的《舌华录》,“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个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合适。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1]
(二)“不合时宜”的界定
那么苏轼大笑认可的不合时宜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苏轼的宦海浮沉的经历或许会略知一二。
苏轼生活在积弊积弱的北宋王朝,内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状况,外是夷人虎视的危急处境,用风雨飘摇形容似乎也不为过。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积极倡导变法革新,但在推行新法时操之甚急,出现种种弊端,苏轼上书批评王安石推行新法引起的种种弊端,建议神宗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2]甚至斗争的矛头直指变法当权派王安石,他在《王莽》《董卓》这两篇咏史诗中,借古讽今,把王安石比作篡权夺位的王莽和董卓。在《商君说》的文章中,其文云,“其生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而死有车裂之祸,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涡者,吾为之惧矣”。从文辞字意中我们也不难推测出其所谓的“后之君子”无疑指的也是王安石。[3]这些行径直接触怒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苏轼受到他们的排挤,十多年里辗转在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湖州等地任职,直到神宗死后才得以回京任职。而当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总揽朝政,废除新法时,苏轼却又唱起了反调,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4],新法和旧法各有利弊,即使要废除新法也要循序渐进,不可贸然废止。司马光完全不采纳他的建议,苏轼就又上书陈述,被保守派归于变法派而又加以排挤打击。这样,他就既不被变法派所容,又不见容于保守派,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历尽磨难。
可见,苏轼所说的“不合时宜”不是不识时务的顽固不化,而是一种敢于直言的率性,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坦言不讳。这种“不合时宜”的执着和执拗,无论是在其誉满京城时还是远谪天涯时都未曾改其本色分毫,所以我们想要真正走进苏轼,走进这位诗词大家,探究其风雨人生后那看破真谛思想的结晶,必须真正地懂得那看似自嘲似的“不合时宜”却蕴含着苏轼的真切深情,这种明知“不合时宜”却在飘渺半生中从未放弃,并不断渗透到其血液中,浓缩在文笔里,影响着这位大家的诗词创作。
二、“不合时宜”背后的思想根源
苏轼,作为一代名士文臣,少年就以进士之誉晋升朝廷,为政多年,以其之聪明,如若说其不谙世事,不解官场风情,想必任何对其才智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那么为何如此聪慧的人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并对于这种不合时宜大有咬定青山不松口的愚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苏轼的思想。
苏轼,生活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代文化背景下,一生三教并蓄。在这种三教合流的大文化背景中,苏轼却没有盲目吸收各家思想,而是有着自身的选择:一方面他继承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摈弃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消极成分;另一方面,又汲取道家超然世外的精神,三家思想就这样有选择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轼在人生中既追求现世功名,又追求自由的精神家园和独立人格的特殊内心境界。
在北宋嘉祐年间以及元祐初年,苏轼可以说官运亨通,政治得意。这时候,儒家的孔孟思想无疑在其思想体系中起着主宰作用,而当他遭贬黄州甚至远迁海南,政治失意的时候,他也明显倾向于老庄哲学的超脱旷达。但即使如此,儒家的入世思想依然在其思想和言行中起着支配和控制作用。可见,苏轼吸收的是三教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而且在其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儒家思想,那么苏轼自嘲的“不合时宜”就不难解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在苏轼内心根深蒂固,而儒家的这种积极入世更不仅仅在于有官可做,为了政治前途可以不顾一切,而是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一切以民生社稷为重,所以苏轼会那么的“不合时宜”。在变法派执政时斥责变法的种种弊端,在保守派得势时又阻止废止新法成果,他所有的这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荣辱声名,而是从百姓的利益出发,是一种不自觉的操守。这种以忠君爱国为主旨的儒家思想是苏轼自嘲“不合时宜”的根源,并不自觉地将这种“不合时宜”的表现体现在其诗歌的创作中,影响其一生的创作。
三、“不合时宜”对其诗词创作的影响
(一)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苏轼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吐之。”[2]这可以看作是苏轼“不合时宜”态度的最精妙的诠释:不做察言观色的“墙头草”,不当计较得失的“金算盘”,不慎言语,任真而动,不愿意违心办事,更不愿意违心做人。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态度,使其诗词成为了他最酣畅淋漓的表达,批判现实成为其诗词最重要的主题。
熙宁四年,苏轼自认为以其性情不适合在朝廷上做官,于是上书皇帝请求外调出任。后任职于杭州。杭州当时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大都市,官员们迎来送去的酒宴成为一种很普遍的风气。而苏轼却再次呈现出那种“不合时宜”,深恶痛绝地称其为“酒肉地狱”。尽管远离朝堂,只是作为一任地方父母官,但在全国都大肆推行变法的背景下,苏轼仍然难以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尽管苏轼一直能够灵活多变地“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但在目睹了新法带给人民灾难的时候,依然不顾众所赞誉的变法,写下了许多反映变法弊端的诗词。并且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里,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4]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就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饱不及黎元。”[4]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赋:“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做河伯妇。”[4]苏轼这种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不合时宜”的态度使他的诗词区别于一般人流于平俗的浅薄认识,或者人云亦云钻营讨巧,而是使诗词的批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是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如,他晚年所作的《荔枝叹》。
他的这种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不合时宜的态度,使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性,即使在常人眼里进贡荔枝、习以为常的贡茶献花,都能从中嗅到官场腐败倾轧的腥臭: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在别人眼里或心照不宣或噤若寒蝉,而苏轼却对此如鲠刺在喉,不吐不快,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用诗词畅快淋漓地描绘了一幅百官群丑图。
(二)诗词形成了一种旷达的风格
对于苏轼诗词的风格,后来学者对此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或将其归结为豪放,或说其婉约,或称之为旷达,等等。其实,作为大家,苏词风格是复杂多样的。那么,东坡诗词的主要风格是什么呢?
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王国维中的这一“旷”字,可以说精确把握了苏轼诗词的精髓。旷者,狂放不羁,超然尘外,空灵洒脱,正所谓“一洗万古凡马空”。叶嘉莹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中说,苏词“以超旷为主调”;刘勤慧认为,“传统的观点把苏轼看成豪放派词人,但从苏轼的全词作看来,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并不占多数,代表苏词主要风格的应该是‘旷达’”。的确,从苏词创作实践来看,在其三百六十多篇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表现其旷达情怀的作品。[5]他在自杭州赴密州途中,作《沁园春·赴密早行,马上寄子由》,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有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卡键,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4]这种旷达的豪情,丝毫不逊色于盛唐时期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豪迈,而苏轼的这种旷达风格,客观上无疑也受到了其“不合时宜”的影响。
苏轼的“不合时宜”使其成为政治上一个“不入群”的怪人,受到各派的排挤打击,为其宦途增添了许多的风波:宋神宗熙宁四年,正是变法派和顽固派激烈党争的时候,苏轼不去明哲保身,而是不合时宜地去同当权的变法派进行论争,受到了无情的排挤,不得已自请外调,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知州,这是他政治上受到的第一次打击;而后将一肚子的牢骚发而为诗,如《咏桧树》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4]两句,在中国古代,龙是象征天子,说“蛰龙”就是讥讽天子,于是朝廷把他打入御台史(乌台)的天牢,最终受尽折磨和痛苦,被贬至黄州做团练副使;五年的隐居生活后,应宋神宗之召回到京城做官,得以重温了他“致君尧舜”的理想,而依然未改其分毫,“不合时宜”地与朝廷唱反调,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与当政者不同的意见,再次被贬谪惠州。
政治上的失意促使他远离了官场问津于山水之间。作为深受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影响的苏轼,在不同时期,形成其不合时宜的思想根源呈现在不同方面,如在诗词中的呈现。身处宦海,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和“奋厉有当世志”的进取精神使其更多的是嫉恶如仇,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如蝇在食,吐之乃已”。而当远离政事纷扰,徜徉于山水之间时,苏轼那种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则呈现出一种率性任真,更倾向于道家的通脱旷达,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这种不吐不快、流连于山水明月间则成就了其诗词的超然旷达的风貌。著名的《水调歌头》是其宦途险恶生涯的升华与总结,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却把酒问青天,所问何事?问的是拳拳赤子之心,却不见容于天地的愤懑不平,正如其词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本是一片丹心向明月,却遭到了连番的贬谪远调,生发出高处不胜寒之感,那琼楼玉宇不正是人间的封建朝廷吗?这种对封建秩序的怀疑也只有苏轼这种“不合时宜”不懂明哲保身的人可以大肆生发,而远离朝廷而生发的短暂牢骚就被其豁达率性的心性所替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双绾自然和社会,用变幻不拘的自然规则,说明人间合少离多自古已然,意境豁达开旷。
初贬黄州时的《初到黄州》中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圆外置,留费管家玉酒囊。”一方面是牢骚满腹的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一生不为权贵,遇不平之事必吐而后快,却到最后只是远贬荒野,功名抱负都付了笑谈。另一方面则率性任真,发而为诗,无比旷达:本是穷山恶水的不毛之地,却在他眼里成为了“长江绕郭”“好竹连山”的鱼米之乡。正如有学者所说:“不屈的精神、性格与旷达的人生观不仅使苏轼并未失去生活的乐趣,反而超然自得,自乐其乐。”[6]政治上“不合时宜”的率性使他惨遭贬饬,而这种“不合时宜”的任真在远离官场倾轧纵情山水时,却成就了其诗词的旷达不羁。
四、结语
苏轼作为文坛上的大家,其人格魅力令后人敬仰,或称其旷达,或颂其乐观,无不把握了苏轼的某些特征,但只有一句“不合时宜”才真正是对苏轼性格最精妙的概括。这种“不合时宜”在不同的处境使苏轼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并且潜移默化影响到其诗词的创作。当身居庙堂之时,苏轼则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秉承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这时的“不合时宜”则更是一种敢于直言的率性,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坦言不讳,发而为诗,则出现了众多主题鲜明的批判诗词,并且对于社会弊病的批判在力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当远谪蛮荒之时,这种“不合时宜”将政治上的坦言不讳呈现出一种率真任性的旷达不羁的风貌,诗词风格则随之显现出旷达。自古以来,苏轼的诗词成就被后人所称道,认为其开启一代新的文风,独领风骚。而笔者认为苏轼的诗词创作其实更是其思想和性情的载体,以千变的形式承载亘古永存的风情。想为文者必先学会为人,才能在嘈乱纷杂的社会中能如苏轼那般诗意地栖居于乱世之外。
[1]童叟.“不合时宜”的苏轼[J].学习月刊,2008,(10):46-48.
[2][宋]苏轼.苏轼文集[M].顾之川,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
[3]王伯英.论苏轼的政治态度[EB/OL].China 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http://www. cnki.net,1994-08-06.
[4]王文浩,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M].孙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李勤香.论苏轼诗词中的旷达风格[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8.
[6]陈美华,肖付华.试析苏轼思想的旷达与矛盾[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03).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s of Su Shi Self-deprecating 'Unacceptable'on his Poetry Creation
Wang Xianfeng
(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071000)
As a brilliant talen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terary world,Su Shi are much respec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for his creation of the verses and its own personality.However,such a great poet in literary circle derided himself'unacceptable'in North Song Dynasty and even did unacceptable behaviors consider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made him unstable in his official career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this kind of 'unacceptable',the influences on the poetry creation from subject to poetry style from his self-deprecating 'unacceptable',and then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to this great poet from a new Angle.
'Unacceptable';ideological roots;poetic creation;impacts
G207.22
A
1671-2862(2015)04-0059-04
2015-06-06
王献峰,男,河北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明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