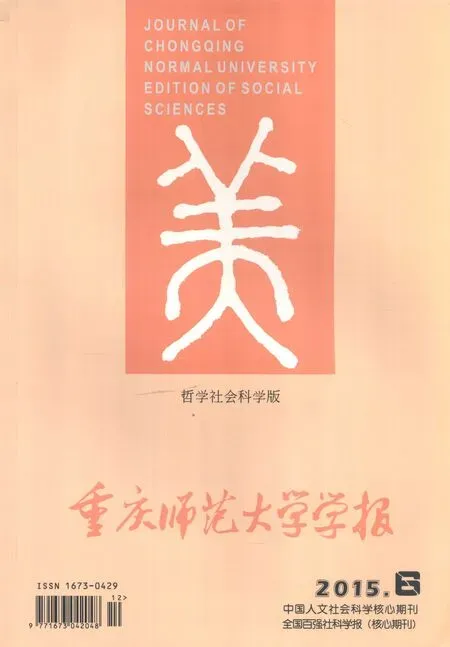宋代文学批评新领域的开辟——评潘殊闲教授的新著《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
宋代文学批评新领域的开辟
——评潘殊闲教授的新著《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
沈文凡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宋代文学批评文献数倍于前朝,但梳理这些研究可以发现,有关宋代文学批评话语特色的研究还不多;从民族“象喻”思维特性出发,系统审视宋代文学批评的话语特色,则几乎没有见到。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潘殊闲教授新近出版的《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一书,可谓独辟蹊径之作。
宋代因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加之新兴的文学批评样式“诗话”的勃兴,文学批评文献富集。潘殊闲教授研究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些浩繁的宋代文学批评文献。只有通过细致的研读,才可能从这些浩繁的文献中沙汰出有关的信息,进而对之研判分类和阐释评论。翻阅潘殊闲教授的这部著作,可以清楚地发现作者对宋代文学批评文献竭泽而渔式的占有与析取。这些文献要而言之有:《宋诗话全编》、《宋诗话辑佚》、《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宋集序跋汇编》、《历代文话》、《宋代笔记丛刊》以及上百种宋人的别集等。这样的沙汰择取,确保了所引用材料的原真性、准确性和稀有性。翻检《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基本上是以材料为基础立论的,真正做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本人曾随手核对了数则该书的引用文献,都完全准确,没有差错。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书中所引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包括宋代文学批评在内的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中难以见到的,这种稀有性,几乎在该书的每章每节中都随处可见。这样的研究态度足以让人信服其立论之允当,特别是在浮躁学风蔓延学界的当下,这种精神尤令人敬佩,也特别值得提倡。
潘殊闲教授通过对宋代文献的广泛阅读和提取,对宋代文学批评中的象喻特色进行了客观而全面的总结。作者将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概括为自然象喻、生活象喻、身体象喻和复合象喻四类。作者对这些从众多批评文献中筛取出的不同象喻文献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论述。这些论述将人们已经熟悉的文学批评史常识、尚不熟悉的文学批评史作者、观点、现象和特征等有机地串联了起来。如第二章第一节饮食起居象喻文学批评中,关于饮食象喻文学批评,作者就梳理出了十五条,分别是:肆筵犒设;脂腻气;吃烟火食人语;饮水、啜茗、啖饼;食小鱼与煮彭[左边为“虫”,右边为“越”]; 咀嚼冰雪;笑蔗与食藕;水中着盐;蔬笋气;食大羮饮玄酒与烹龙炰凤;尝鼎一脔;甘露蠲渇与清泉濯垢;山肴野蔌;齐王食鸡;食蜜。这些文学批评中的生活象喻有的是我们熟悉的,有的则很陌生。作者通过文献钩稽和析解,让我们有豁然开朗之感。而起居象喻文学批评,作者更梳理出十八条:坐、立与走;做客;小儿就学;作家书;镜取形与灯取影;暑天凉风袭人;印印泥;炼形与绝粒;至宝丹与腰金枕玉;隔靴搔痒与拖泥带水;戛釜撞瓮;诗评与医方;入天陛赤墀;黄收纯衣与鹬毛翠帱;行正路与行狭隘邪路;五谷疗饥与药石伐病;小儿随人入市;盲者见三光与聋者闻古瑟。再如第二章第二节“琴棋书画与歌舞戏曲象喻文学批评”,作者从孔平仲的《谈苑》和吕本中的《童蒙训》中引出黄庭坚的“作诗如杂剧”的象喻。此前有关宋代文学批评史的各类著述鲜有触及这个问题的。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发现了这个有趣的象喻,并予以有说服力的阐释。在作者看来:“诗歌不是综合性的艺术,但从杂剧的基本元素出发,可以看到,诗歌无论长短,总还应该有这些基本的元素。比如,诗歌写的是谁——这便是角色;诗歌总要叙事抒情——这便是故事情节;诗歌需要音韵节奏,需要语言词汇——这便是表演;诗歌需要意境韵味——这便是效果。所以,杂剧与诗歌可以互通互喻。”[1]82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陈善的《扪虱新话》及费衮的《梁溪漫志》,结合苏轼的一首诗题,发现诗歌与杂剧相同的地方还在于“切题可笑”,因为“诗歌还是需要跌宕,需要起伏,需要有吸引人的看点,而不能一览无余,一如杂剧之插科打诨”。[1]83这种论述非常符合苏黄的创作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对深刻认识宋人的文学批评特色有相当的启迪和帮助。而在“矮人看戏”和“俳优散场”的戏曲象喻批评阐释中也发人深思,颇有意味。类似这样的新奇发现和新颖阐释在书中还有很多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潘殊闲教授并没有停留在对宋人象喻文学批评的现象陈列和基本阐释上,他更上溯到《周易》,探寻中国人的象喻思维及其审美心理的特色,并由此去分析宋代文人的艺术生活与象喻追求。该书的后面二章即是这种宏大层面的观照。在作者看来:“中国人对大自然始终充满了敬畏和爱戴之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人是天地宇宙之一员。《周易》阴阳二爻是对世界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物质的模拟。由阴阳二爻组成三画卦的八卦,再由三画卦的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由三百八十四爻组成。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架构起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万千世界画图。这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观察与表达方式,蕴育了中国人无比丰富的象喻思维,给中国文化氤氲着一层灵动的色彩和气度。”[1]82这种“灵动的色彩和气度”就表现为宋人“诗意的栖居”。在潘殊闲教授的眼里,这种“诗意的栖居”就是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具体而言,潘教授从三个维度予以阐释,分别是:耽美:生活与艺术的共同目标;诗话与话诗:宋人的艺术生存之道;和陶:宋人开创的诗歌新范式与人生新愿景。三个维度实为三个关键词,他们确乎是宋人的时代“风景”,对后世文人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此为基础,潘殊闲教授在本章的第二、三节通过大量案例分析了宋代文人象喻文学创作与象喻文学批评的关联与区别,再进一步,作者剖析了文学批评的语言按摩与心理释放的功能,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揭示了文人追逐象喻文学批评的发生学原理、内在诉求及其相应的文学文化生态,非常具有说服力。
作为世界东方民族的一个代表,中华民族有自成体系的语言、思维、审美及其生产与生活活动。如何总结、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是摆在当下中国人面前的一件历史重任。古人云,学术文章为天下之公器。潘殊闲教授探索的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虽立足于宋代,虽局限于文学批评,但其开放的视域、成熟的方法以及独特的样本示范,可以给我们相当的启示。简而言之有三:
第一,为探究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术话语特色提供了借镜。毋庸讳言,中国人具有鲜明的象喻思维特性,在这种思维特性的晕染下,整个学术文化氤氲着浓郁的诗性智慧。《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虽然仅仅限于宋代的文学批评,但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其他的学术文化研究之中。
第二,为研究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特色提供了样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审美心理,这些民族审美心理或明或暗,或强或弱,有些甚至已经“百姓日用而不知”。《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从“象喻”出发,探析了宋代文学批评的话语特色,实际上就是对渗透在宋代文学批评中的民族审美心理的一种揭示。而众多领域中类似的这样的揭示,也就从不同的角度梳理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特色。《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虽然研究的时空范围有限,但不失为一种样本。
第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和世界作了新的疏解。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需要用现代的语言进行阐释疏解。宋代虽然版图疆域并不广大,综合国力难称雄盛,但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却独树一帜。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宋代的各类文献(自然包括文学批评文献)留存非常多,这些文献当中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特质尤为宝贵。《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立足于宋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研究其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特色,这对当下国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让古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潘殊闲.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陈忻]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沈文凡(1960—),男,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收稿日期:2015-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