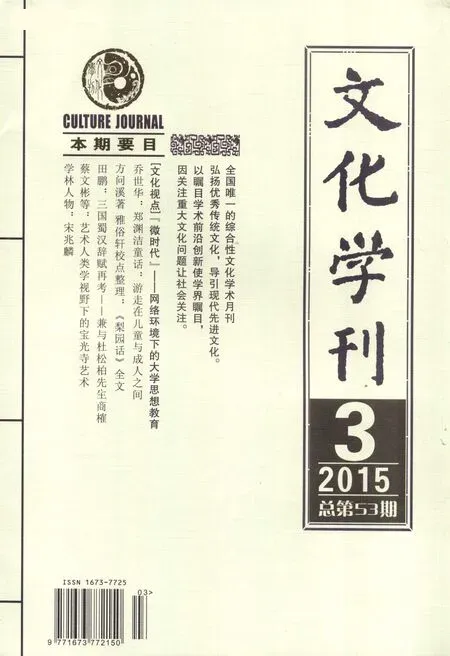民族与宗教之间
——试析郭道甫政治实践中的宗教因素
孟盛彬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50)
民族与宗教之间
——试析郭道甫政治实践中的宗教因素
孟盛彬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50)
郭道甫为内蒙古近现代史上著名政治家,早年信奉基督教,并将基督徒的拯救思想转化为寻求“蒙古问题”的解决,毕生以“民族自决”为己任。支撑郭道甫从事革命斗争的思想动源主要有:深厚的乡土情结;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拯救思想和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郭道甫;政治实践;基督教;藏传佛教
郭道甫生活的清末民国时期,维系满蒙与内地民族关系的八旗制度已然解体,新秩序还未完全确立,军阀、盗匪横行,各派军阀互相对立,连年混战,中国国内情况每况愈下。而丧失体制依托的蒙古王公旧贵无力应对急剧变迁的局势,缺乏统一组织、力量与自主性的内蒙古形同俎上之肉,成为军阀和外国势力觊觎和侵占的目标,民族地区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不安局势,势必引发一些青年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去探索振兴民族的路径。
如果将1917年从北京俄文专修馆辍学返乡、组织呼伦贝尔学生会、兴办教育、革新除弊活动视为郭道甫政治生涯的起点,那么,至1931年进入俄国领事馆失踪为结束,在短暂十几年的时间中,郭道甫就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在云谲波诡的政治舞台上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为内蒙古近现代民族运动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学者针对当时内蒙古形势认为:“回顾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内蒙古革命史或民族运动史,如果德王为三、四十年代民族运动的首倡者和推动者,那么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人物应该是郭道甫。而乌兰夫等人的历史地位是1946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1]
郭道甫先生主要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创立政党、革命暴动及兴办教育等活动宣传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将《蒙古问题》推向了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同情。
郭道甫青年时期就立下“以民族自决为己任”的鸿愿,在多种政治力量的夹缝中左右腾挪,为民族解放事业殚精竭虑,上下求索。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远及海外莫斯科、乌兰巴托、乌兰乌德等地,会见各地名流和党政要人,谋求民族解放的途径。据史料记载,在他社会关系网络中出现的著名人物有:政界的孙中山、梁启超;军界的冯玉祥、张学良;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教育家陶行知、张伯苓;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福民泰;共产国际、苏联、蒙古党政要人;基督教的余日章、司徒雷登、诚静怡;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蒙疆政权领袖德王及佛教的班禅大师等人。其中,拉铁摩尔和宗教界的班禅大师、德王在以往的著述当中所论不多,据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郭道甫先生与他们也曾有过比较密切的往来,对内蒙古自治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拉铁摩尔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蒙古语老师郭道甫(Merse)有所追忆,他说:“接下来的三年(1930—1933),我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一笔研究员基金和小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接连提供的两笔研究员基金的赞助下,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在这几年里,日本人完全占领了东北,并把侵略扩大到华北和内蒙古。我开始学习蒙古语,在花了一个冬天跟一位讲汉语的蒙古教师——我是通过来自海拉尔的蒙古民族主义者墨斯(Merse)认识他的——学习蒙古话和蒙文写作之后,我告诉他我已经认识到内蒙古的政治重要性,为了理解蒙古人的观点,有必要掌握蒙古语。我必须能够同普通人民交谈,同那些既不是封建贵族也不是政客的人,同那些最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不讲汉语的交谈。在他下一次访问北京时,墨斯(Merse)替我找到这位好老师。这是墨斯在一次政治谋杀中遇害的前几个月。
1931年9月,沈阳事变发生后数日,墨斯突然出现在北京,他显得非常不安,非常紧张。显然他正同在京的其他外蒙古人联系,尽管他不愿意告诉我详情。他们肯定一直在商量:“作为蒙古人我们该怎么办?日本干涉满洲对蒙古人意味着什么?”……墨斯曾是一所学校的校长,该校为张学良治理东蒙训练蒙古翻译官。正如同印度民族主义者在接受英国教育的印度人中蓬勃发展一样,受过教育的蒙古民族主义者也常常在汉人统治下的这类学校里产生。墨斯的办学方式似乎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怀疑。”[2]
1929年,班禅大师接受了张学良的邀请,东去沈阳。德王也与这位大师同行。由于德王英俊的仪表和他在蒙古王公中不凡的表现,因此使这位张少帅非常重视,优礼有加。在这种盛大的欢迎中,凡是到沈阳顶礼班禅大师的蒙古人士们,自然也有机会与这位青年翘楚的蒙古王爷接谈,其中对德王印象极深而且有所影响的则是前蒙古青年党领袖之一、呼伦贝尔达呼尔蒙古闻人莫尔色Merse(汉名郭道甫)。他早年曾在北京法政专科学校读书,思想积极,以蒙古民族自决为己任,联络东蒙古青年组织蒙古青年党,以蒙古独立为目标。他也曾加入白云梯氏所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事活动。白氏被极左分子所迫,离开乌兰巴托后,莫尔色也回到呼伦贝尔。1929年秋,乘苏俄红军占据呼伦贝尔、黑龙江一带地区之时,与富民泰(达呼尔人)共同集合一部分东蒙青年宣布独立。不久苏俄红军撤退,莫尔色与富民泰之间也发生了龃龉。当张学良收复苏军占领区之时,富民泰去了乌兰巴托,莫尔色留在张学良的这一边。思想比较开明的张氏,非常器重这一个蒙古志士,就叫他到沈阳来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培育蒙古人才,发展教育。在这所学校出身的许多东蒙青年,对于这以后的蒙古历史都有他们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莫尔色氏的功劳。在政治上受到挫折的莫尔色,多少也改变了他左倾的路线,转而与呼伦贝尔的实权者凌升靠近。凌升也为了安抚莫尔色和呼伦贝尔的青年们、同情他们的遭遇,主动的与莫尔色接近。后来以凌升代表到南京迎接班禅大师的就是莫尔色其人。由于这种关系德王有机会而且也很和谐的和他谈古论今。两人对于蒙古民族的将来和出路都有同感,希望能借班禅大师来蒙古的机会,使从不往来的蒙古王公领袖们多有机会接触、加强团结,为了民族的自由同心合作。[3]
纵观郭道甫的一生,除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坚卓努力之外,还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求学时代就接触到基督教进而产生了信仰,对基督教在教化人心、培养高尚道德、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了深刻的理解。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非常深远,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影响因素之一。韦伯这样表达他的看法:“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阐明宗教运动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基本方向。只有相当准确地阐明之,才可以去估计,在什么程度上现代文化的历史发展可以归结为那些宗教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其他因素”。[4]由于国内特殊历史时期的原因,从事历史人物的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淡化处理这些宗教问题,有意忽视或无意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宗教因素,片面地强调其他因素,经过这些技术处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很难得到完整的呈现。
探讨郭道甫人生的运行轨迹,考察革命行动的起因与意义背后的宗教因素,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他的思想体系和转变过程。从现存的几部著作中反映出了贯穿郭道甫一生的很多观点,充分显示了追求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或许与基督教精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做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设想,下面以郭道甫的宗教观为中心展开探讨,力求还原和显现郭道甫波澜壮阔一生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郭道甫早年曾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崇信,产生于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1915(1917年期间,俄文专修馆原为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创办于1899年,是清政府为了培养俄文涉外人才而创建的学校,辛亥革命之后,归入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改组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校址在东城东总布胡同,1922年改名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以后又并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5]作为中国早期的外国语学校之一,俄文专修馆聘请了众多俄国人来华执教,其中不乏虔诚的基督教(东正教)信徒,郭道甫耳濡目染之下渐生宗教兴趣也合乎情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徐宝谦称:“郭摩西字道甫原名浚黄,三年前肄业北京时同予研经进教信道后,即以拯救蒙古民族为己任。”摩西为郭道甫接受牧师洗礼之后所取的教名。北京读书期间的郭道甫患难于家毁人亡,长子早夭,遭遇精神伤痛的郭道甫极有可能选择信仰宗教来获取精神慰藉以求摆脱人生困境。根据学者的研究结果:“宗教可以定义为信仰和实践的体系,根据这种体系,组成某种社会团体的人们,与人类生活的最根本难题展开斗争。从个人的立场观点来看,宗教的性质,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相信邪恶、痛苦、妖术和不义的存在是基本的事实;其次,一整套实践和相对神圣化的信仰,表达了人类最终可以从那些不幸之中获得拯救的深切信念。”[6]将基督教精神内化为精神动力的郭道甫回到呼伦贝尔地区,创办合作社、兴办学校致力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呼伦贝尔地区寺庙林立、僧众遍布,郭道甫在一系列社会改良实践探索过程中,至少在意识层面上拒斥着地方上盛行的藏传佛教,他表示:“然近年来喇嘛教流弊特甚,有识之士皆引为隐忧,又新进少年怀抱如荼如锦发奋改良之志愿,故对于喇嘛教颇不满意,咸有改弦更张择走新路之势。而对于基督教之服务社会,铸造人格之能力颇为赞叹,是为基督福音传播蒙古千载一时之机会。吾辈基督徒之责任其重大为何如耶。”[7]他把蒙古社会应对藏传佛教予以排斥的原因,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藏传佛教在蒙地的发展,是出于愚弱蒙古的政治企图,从而达到柔化蒙古人的剽悍性情,消减人口滋生,奴役其人民的目的,这是造成蒙古民族清代以来智识闭塞、积弱困苦的根源。怎样改变当下萎靡不振的境况?他提出了解救良方:教育——学校,“必先以教育开其端而促其成。今日蒙古民族之愚弱衰微可怜万状,实因教育未兴学校未立之故。”[8]
郭道甫对宗教所持的激进态度,从最初论著《为蒙古代祷文》与稍后出版的研究成果《蒙古问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并有所变化。在1923年发表的《蒙古问题》第六章《蒙古之现在与将来》中,认为:“若有大发心愿誓救蒙古不辞备尝艰苦,将来欲为我蒙古民族之恩人者,亦当留意于基督教,以立我蒙古民族社会事业之基,庶能达其救我蒙古之志乎。其他所有喇嘛,凡道心深者听其独身传道,其道心浅者亦可还俗娶妻,仍当进修智德体三育,以自救救人可耳,又何必伈伈伣伣,徒自苦而苦我民族也哉。呜呼,上自活佛呼图克图下至各旗喇嘛皆能若是,则仍不失蒙人之崇拜信仰,而为我民族之灵魂,岂不伟哉,岂不大哉。”早在忽必烈时期,蒙古就已接受并信奉藏传佛教,历经数百年的积淀,经过清朝的中兴,其教义思想、宗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与蒙古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逐渐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经过几年的接触与交流,郭道甫意识到藏传佛教在蒙地的深厚根基和巨大影响力,蒙古民众始终执着于地方和佛教的传统,很难彻底接受基督教的思想意识,因此,他的宗教态度也转趋于温和包容,称喇嘛教为蒙古民族之魂,企图通过分化和消解僧侣阶层享受的特权来恢复社会秩序和活力。
郭道甫先生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矢志不渝地探索解救民族危亡的途径。“等到一九二一年以后,外蒙方面的平民革命,业经成功,这种潮流,也就输入了呼伦贝尔。而接受这种潮流的,就是这一般有组织的青年们了。不久也与外蒙平民革命党,发生关系,完全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法。这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事情。”[9]这些主张和方法中包含了打击喇嘛特权的宗教政策等,“现在外蒙古喇嘛教之大势,国民政府随不干涉其诵经讽呗,礼拜活佛等事。然因其既失政治上之势力,又因屡经外侮之蹂躏,及国民党青年党大声疾呼,输入国民常识之结果。凡属喇嘛人,一面感生活压迫之艰难,一面受失去信仰之影响,自由散回各旗而为普通国民者渐多。此亦蒙古国民政府消极取消喇嘛教大害之一种方法也。”[10]1925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通过了由郭道甫执笔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宣言》,其中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停止在宗教事务上向人民强制摊派官差。除知识分子等精英人物外,宗教人士也在内人党初期的组织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伊克昭盟、雍和宫、多伦淖尔等党部的牵头人和党员大多是活佛、喇嘛,他们的支持是早期的内人党得以展开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1]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支撑郭道甫毕生从事革命斗争的思想动源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其一,乡土情结是人类固有的情感。郭道甫在《呼伦贝尔问题》小引中坦承“鄙人是呼伦贝尔人,也是关心呼伦贝尔的一个人,所以也来谈一谈呼伦贝尔的问题。”他在正文中则用赞美的语言来描述家乡呼伦贝尔“他的形势,是好像一个躺着的老虎,呼伦湖是他的眼睛;贝加尔湖是他的舌头;额尔古纳河是他的脊梁;奇乾金厂是他的尾巴;兴安岭就是他一伸三收的四条腿。……呼伦贝尔的山河哟!他是何等的美丽哟!”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炽热情感和爱护之心,而呼伦贝尔的实际情况却是,腐朽官僚统治和外国势力威逼之下,“每天都向着自然淘汰和自取灭亡的地狱里走下去。”这样就不能不激起有识之士的抗争和革命。二十世纪初期,面临亡国危机之际,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的反日运动、五四运动、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等风起云涌。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12]郭道甫深受这股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家乡和民族怀抱的朴素、真挚情感成为郭道甫日后孕育民族自决、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其二,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拯救思想和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郭道甫早在学生时代就接受西方文化熏陶,受洗入教,成为基督徒后即以拯救蒙古民族为己任,被徐宝谦赞誉为“蒙古信道之第一人”。郭道甫的论著中也多次强调基督教在解决蒙古问题中的重要性:“基督教尤能解脱人类奴隶贫穷愚昧病弱罪恶之重轭。蒙古民族数千年来即负此种重轭至今未释,非基督教何以救之。”革命时代的郭道甫面对残酷的现实斗争,促使他超越基督教理念而趋向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郭道甫早年就读北京俄文专修馆时期就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的巨大影响。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论题”的决议,决定积极支持殖民地民族运动的方针。这项决议无疑对探索民族出路的郭道甫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转而对马克思主义寄予期望。1923年,郭道甫受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委派出访蒙古、苏联,与共产国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生了联系,并完全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法。1929年,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期间,郭道甫指定学生读的书目就有《社会科学概论》《唯物史观》和列宁的关于殖民地与民族问题、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问题以及苏联革命等小册子(都是上海出版)。[13]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促使他转而客观平等地对待各类宗教,包括早年信奉的基督教和尖锐批判过的藏传佛教,站在唯物主义层面上审视和批判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宗教现象。
本质上郭道甫是具有学者气质的政治家,才思敏捷而且兴趣广泛,对任何问题都有寻根究底的热情,例如谈蒙古问题就不止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上,他说:“窃以为关于蒙古方面问题,吾人应当研究之事项不胜枚举。如元史学也,文学也,宗教也,政治经济也,风俗习惯也,均有重大之意味,此种讲演不过发凡而已,实不足以谈蒙古问题。”[14]如果假以时日、如果生逢其时,他将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无尽的追思,去缅怀这位革命先驱轰轰烈烈的一生。
[1]周太平.1920年代的郭道甫及呼伦贝尔暴动试谈[D].大阪:大阪大学,2010.
[2]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M].吴士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23.
[3]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60.61.
[4][美]乔治·瑞泽尔.古典社会学理论[M].王建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225.
[5]贵钧.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略记[N].人民政协报,2006-07-24.
[6][美]J.M.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M].金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7][8][9][10][13][14]奥登挂编.郭道甫文选[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6.7.129.80.178.88.
[11]朝鲁孟.1925—1931年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探述[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3.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20.
【责任编辑:王 崇】
B911
A
1673-7725(2015)03-0221-05
2015-01-0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
(项目编号:12YJC730006);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项目(项目编号:MZWHD2014—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孟盛彬(1978-),男,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宗教与民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