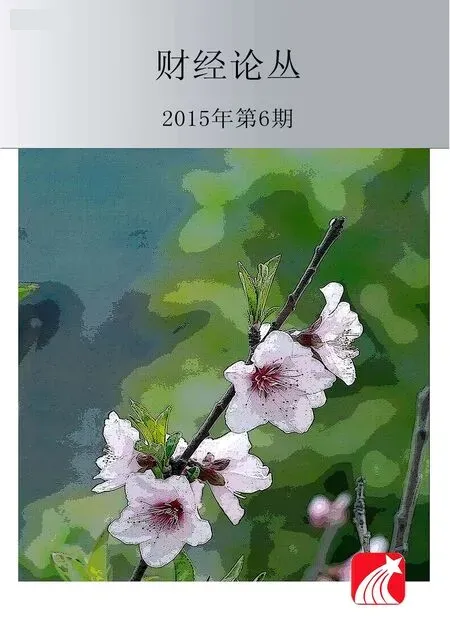就业合同能促进受助群体再就业行为及收入吗?——基于异质企业的度量、探索与诠释
王增文,邓大松
(1.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 言
目前,中国正面临“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格局,这一局面同时伴随着低工资的现状,折射了中国当下结构性失业的危机。而社会救助家庭作为弱势群体,其再就业问题比非受助群体更加困难。鉴于此,本文把社会救助家庭的再就业分为正规再就业和非正规再就业两种形式,而作为两者划分的标志——再就业合同起到的作用是要求用人单位对签订就业合同采取相对积极态度来履行这一法律职责。
国内外学者就有关就业合同问题从不同的视角作了研究。在就业合同签订率方面,2004年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总报告组,2006),边缘群体(包括农民工和贫困群体等)就业合同签订率仅为12.5%[1]。Dominique et al(2001)采用1988-1992年1000家法国公司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这一系列面板数据展示了在不同的就业合同下雇佣和离职的员工数量,发现不定期就业合同下单位解聘职工的成本远远高于雇佣成本[2]。而中国的用人单位解聘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成本趋近于零。另一个影响就业合同签订的重要组织就是工会。在中国,工会的力量和权责远远小于欧美等发达国家。Ayala et al(2002)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研究发现集体谈判降低了工作替代率和失业率[3]。Tribó(2005)对西班牙的就业市场做了实证研究,发现集体谈判覆盖该国就业人员的68%[4]。工会的作用既降低了失业率,又常常为保持与企业的博弈能力而签订集体短期合约,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刘辉等(2007)对杭州市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近60%的进城务工人员未签订就业合同[5]。学界在就业合同对就业人员收入影响的显著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孙丽君等(2008)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劳动关系和谐性与企业绩效的互动问题,认为企业与员工签订就业合同会达到双赢的效果,既能提高企业业绩,也能增加员工收入[6]。刘林平等(2007)通过对珠江三角洲进城务工人员问卷调查资料的研究发现,就业合同对该群体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7]。陈祎和刘阳阳(2010)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有影响,但这仅仅是合同法本身,而不是签订就业合同这一行为,因为在中国仍存在不少有法不依的情况[8]。上述学者只关注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有的仅限于理论分析,即使有实证数据检验,也由于样本所限只侧重一个方面。鉴于此,本文将从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就业合同的签订及就业合同对其再就业收入的影响这两方面来分析。
二、签订就业合同产生的效应
(一)用人单位与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签订就业合同的经济学分析
受助群体的再就业行为可分为不努力找工作和努力找工作两种,努力程度为a,产出为h,而不努力的概率为π,(1-π)概率得到的产出为0。为简化研究,假定一类单位重视再就业群体的利益,设为δ1;另一类单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设为δ2。假设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签订正规就业合同行为记为γ1,不签订就业合同行为记为γ2。


(二)就业合同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收入的影响

上述情况仅展示了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工资变动范围。在此区间内的任何值都是由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互博弈而得到的均衡值,故在不签订就业合同状况下的博弈工资为I2=I0+v2(v2+1)-1。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对博弈能力增强时,其工资也会相应地提高。因此,受助群体的再就业人员一旦签订就业合同后,其博弈能力会进一步提高。如果双方签订了明确的就业合同会使博弈能继续进行,用人单位违约时付出的成本用m表示,那么用人单位遵守合同的前提应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收入的提高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签订就业合同后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来提高收入,这是一种间接效应;其次,由于加大了用人单位的解雇成本,这为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保障;最后,签订就业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在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从而使其在工作岗位上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此外,由于可支配收入变化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签订就业合同后用人单位解雇成本的变化趋势及双方博弈力量的对比,这种力量对比的结果较为明显,即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的正规就业对其收入的影响效应远大于其他非社会救助群体。根据上述博弈结果,本文将实证检验如下两个问题:(1)用人单位是否更倾向于跟文化程度更高、受过更多培训的群体签订就业合同;(2)签订正规再就业合同后的再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能否得到显著提升。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南京财经大学对中国四省份社会保障制度调查问卷,问卷设计样本1274个。调查涉及的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来自中国的各个省市,样本较为集中的是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占比分别为18.68%、21.67%、29.24%和16.35%。本文研究涉及的二分类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二分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签订就业合同的正规就业的比重仅为17.13%,说明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中的就业属性为非正规就业并以中年群体为主,这主要是由受助群体家庭性质所决定的。

表2 定距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签订就业合同的正规再就业人员获得的收入总体上高于未签订就业合同的人员。从月工资收入来看,前者均高于后者。从工作强度来看,未签订就业合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远远长于签订就业合同的人员。签订就业合同的再就业人员多数是自身条件较好,受教育年限和培训次数远比未签订就业合同再就业人员要少。从家庭赡养状况来看,未签订就业合同的再就业人员远大于签订就业合同的人员。就业合同能显著地提升受助群体的再就业收入。此外,在年龄方面,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平均年龄为40.47岁,表明该群体多数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层”群体。在接下来的实证检验模型中,本文将验证上述模型提出的假设(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影响再就业合同签订因素的实证结果(样本N=1274)
从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个体特征的Logistic二元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状况变量对其有显著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助群体,其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的概率越大,这符合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中的教育带来的复合型效应:一是提高了从事正规再就业人员的就业概率;二是增加了收入。另一个显著性的变量是性别,男性从事正规就业的比率远高于女性,收入亦是如此,而其他变量均未通过检验,表明虽然工作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但对其从事正规再就业并无显著性影响。培训次数变量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接受的培训次数对其从事正规再就业的行为并无显著性影响。
在引入工作特征变量后,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事业)单位对再就业人员从事正规就业有显著性影响,受助群体的再就业人员与私营企业签订就业合同的概率变小,这可能与所有制企业的用工制度有关。在私营单位就业的受助群体中,仅有39.28%的人员成为正规再就业人员,而国有(事业)单位的这个比率高达73.12%,其他类型的单位(如外资、合资企业)仅占20.1%。第三产业对其从事正规再就业的影响效应是负向的,表明第三产业中再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的人员比率显著低于从事第二产业的再就业人员,这主要是由第三产业人员的流动性决定的。本文将通过如下的模型(1)检验签订就业合同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工资收入的影响状况:


表4 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工资收入方程OLS估计结果
从中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及就业人员的个体特征来看,就业经历会影响受助群体再就业方式及收入,因此本文将先前的就业经历变量单独考虑:

由表4可见,受教育程度和先前的就业经验变量系数是正的①先前的就业经验系数远大于其他系数,这验证了先前的就业经验也是决定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先前的就业经验平方项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先前就业经验的收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缩减趋势。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个体特征因素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收入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女性的月工资收入比男性群体低近20%,而婚姻状况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效果不显著,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中多属中老年群体,属于已婚群体。然后,我们进一步考察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工作单位性质对其收入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在国有单位与私营单位的收入明显低于其他属性的单位,主要原因是其在国有单位和私营单位工作,但所处的工作岗位属于非正规就业部门。其他检验变量不具显著性,但先前的就业经验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就业合同这一虚拟变量,发现先前的回归系数均无显著性的改变,而正规就业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正规再就业收入将提高15.41%,而引入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变量后对回归结果均无显著性的影响。从检验结果来看,正规就业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收入有显著性的正向激励效应。
四、结 语
本文研究发现用人单位与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签订就业合同的概率与其自身的技能状况具有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及接受的培训次数越多的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其从事正规再就业的概率就越大,收入提高幅度也更大。受教育程度和接受培训的次数能显著影响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签订就业合同的概率。签订正规就业合同的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比未签订就业合同的再就业人员的工资高出389.10元。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均显示,是否签订就业合同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影响更大的是贫困群体中技能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那一部分成员,原因是用人单位更愿意与其签订就业合同。签订就业合同能增强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对职位的忠诚度,这是一种良性互动效应,用人单位和再就业人员同时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对受教育程度低和接受培训次数少的那部分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而言,签订就业合同也会提升其再就业收入,但概率相对较低。如果政府通过法律等强制性的手段促使用人单位与该群体签订正规就业合同,用人单位便会采取“逆向选择”行为,特别是部分亏损的中小企业会减少这部分群体的用工数量。从长远来看,这部分弱势群体仍会走上失业的道路。
因此,本文认为就业合同的签订及合同长期可持续性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对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进行专业化的技能培训。政府可根据用人单位的属性,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订单式”培训,既可给用人单位输送合格劳动力,又解决了受助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最终形成用人单位、政府和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的“三赢”格局。
[1]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2]Dominique G.,E.Maurin and M.Pauchet.Fixed term contracts and the dynamics of labor demand[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3):533-552.
[3]Ayala L.R.Martinez and J.Ruiz Huerta.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unemployment earnings inequality trade[J].Applied Economics,2002,34(2):179-195.
[4]Torib J.An analysis of the length of labor and financial contracts:A study for Spain[J].Applied Economics,2005,37(8):905-916.
[5]刘辉,周慧文.农民工劳动合同低签订率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3):18-21.
[6]孙丽君,李季山,蓝海林.劳动关系和谐性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08,(21):34-35.
[7]刘林平,张春林.进城务工人员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决定模型[J].社会学研究,2007,(6):114-137.
[8]陈祎,刘阳阳.劳动合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影响的有效性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0,(1):687-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