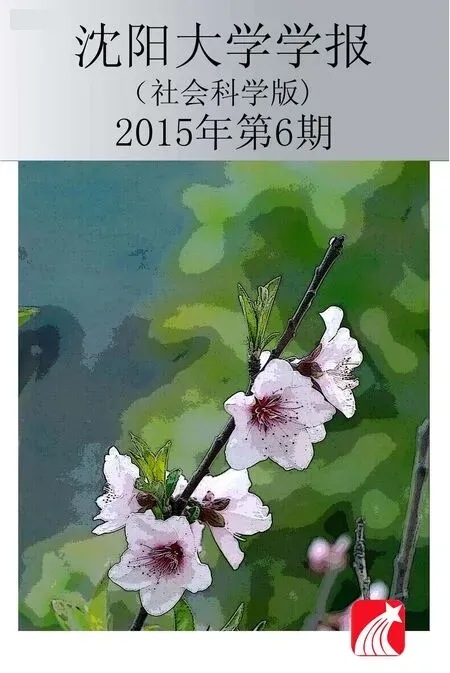执著的精神道德守望者拉斯普京
——以《活着,可要记住》为例
陈慧敏
(沈阳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4)
执著的精神道德守望者拉斯普京
——以《活着,可要记住》为例
陈慧敏
(沈阳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4)
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拉斯普京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该作家是一个执著的精神道德的守望者,肯定了作家对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社会状况的担忧良知,介绍了作家致力于完善人的精神道德的探索情况,拷问了社会道德良知。
拉斯普京;《活着·可要记住》;精神;道德;抉择;蜕化;拯救
道德问题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古至今都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但在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发展,而疏于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很多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常常无视道德规范的存在。大家都知道,现代社会有一个重要的口号——为更多的人谋最大的幸福。在为这个目标奋斗时,人们要切记,一切的幸福都应建立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及公共秩序上,即便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也不要违背道德原则。纵观俄罗斯文坛,在悠远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寻求道德力量和精神支撑的作家不计其数,其中,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一、作者简介
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1937—2015),是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具有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同时还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获得者(1987年),“乡村散文”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可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都是塑造道德危机下“众生相”的杰作。他的笔下多是些“农民卫道士”及传统的“村社文化”精神的捍卫者的形象。这些形象与那些失去根基、半农民半城市化的人物典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家深刻地认识到,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自己的道德根基和精神支柱时,一切都将陷入无序之中。面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一社会现象,作家表现出强烈的担忧,于是他用自己的作品发出呐喊,表达自己的强烈谴责,以此来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帮助这个社会筑就牢固的道德堤坝。在拉斯普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蕴藏着俄罗斯人民所拥有的强大的精神财富:善良,有良知,爱国,富有同情心,愿意与人同甘共苦,互助友爱,忠诚,豁达,理性等。他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满怀对祖国的爱、内心装有本民族的道德精髓的人才能得以生存。作家本人也是一个极具优良道德品质的人,他时刻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德意识。他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人们不仅在俄罗斯国内为道德蜕化而做斗争的群体里可以听到他的名字,而且在保护俄罗斯生态环境的战斗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是当代俄罗斯的“良心作家”,他有理由被称为真正的人民作家。
二、作品分析
《活着,可要记住》这部作品在探索精神道德之路上具有深刻的意义,是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表现道德主题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并没有用浓重的笔墨去描写恢宏的战争场面,而是把战场作为一个背景,从道德的角度去观察、思考战争所带来的人性问题,由此提出更深层次的道德问题,作者想以此探究由战争引发的激烈的道德冲突的实质,即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公民责任问题[1]。主人公安德烈背弃了祖国和人民,逾越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固守的道德底线,成了一名逃兵,他人虽还得以苟活,但他在道德上已经彻底堕落,他在精神上已经彻底死亡,由此他必将自绝于人民和祖国。
作者凭借自己对人民大众生活的深刻了解,以及对平凡小人物心理的仔细研究成就了这部作品。作者把小说的主人公放入一个复杂的场景中:年轻的小伙子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战争结束前一直任劳任怨地在前线打仗,虽说不上英勇,但也还中规中矩。但到了1944年,一切发生了变化: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进了医院,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他本以为,自己受了这么重的伤,完全可以被批准回家,所以,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就想象着该如何回到家乡,该如何拥抱双亲和妻子纳斯焦娜。他坚信事情会如他所愿,他甚至在自己受伤期间都没让亲人来医院探望自己。结果事与愿违,伤愈后他被重新派回前线,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击垮了他。他的计划瞬间被打乱了,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
在内心感到极度不安和绝望之际,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在返回前线前,抓紧一两天的时间,回家看一看。也正是这个冒险的决定彻底毁掉了他的一生,扭曲了他的灵魂,使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感觉到,安德烈这一艺术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作者十分熟悉该人物,对他的行为并没有孤立地去加以评判,他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界限。越仔细品味小说,越更能进一步地分析出主人公的道德水准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原因,这也正是拉斯普京艺术创作中最让人欣赏和信服的地方。读他的小说,会不自觉地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思考,一起决定此时此刻该怎么办。
总之,安德烈·古西科夫做出了抉择:决定回家,哪怕在家停留一天也好。从那一刻起,他的生活完全被另一种生存法则所驾驭,由此他就像污水中的一块木片,随波逐流。由于路上发生了意外,他不能按时返回前线,按照规定,他就是逃兵,会被处以极刑,于是,他选择了逃亡。作为一个性格十分敏感的人,他知道,这将让他远离正常而诚实的人们,他想要回到从前生活的愿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命运开始捉弄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安德烈所处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为怕被别人发现,他只能与妻子在寒冷的、没有生火的浴室里幽会。
作家十分熟悉俄罗斯民俗,他知道,每到夜晚浴室里便会出现各种“妖魔鬼怪”,于是作者就以“妖怪”作为主线贯穿整个故事。在大家的潜意识中,这个“妖怪”就是“狼人”安德烈,因为在当逃兵的日子里他学会了狼嗥,身上具有了狼性,就连他的妻子纳斯焦娜也怀疑,他难道成了传说中的“鬼怪”。同时,安德烈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无情,越来越残忍,在他身上甚至出现了虐待倾向。当他偷偷射杀山羊时,他不会像其他猎手那样,去补射第二枪,而是站在那儿,用心地看着这个不幸的家伙是怎样受尽折磨而死的。在山羊濒死之前,他会拎起它,注视着它的眼睛,为的是记住它绝望的眼神。此时,山羊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对视着他……他等待它做出最后的挣扎[2]。他渐渐失去人性,失去一个正常人所应具有的道德良知,他充满血腥的外表似乎决定了他接下来的举动以及他所说的话:“你要是说出去,我就打死你,我才不在乎哩[3]”。安德烈离正常的人性越来越远,在同村人的眼里他无论遭受到何种惩罚都不为过,因为他就是一个“妖魔鬼怪”、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在民间,人们常把行为诡异的人称为“妖魔鬼怪”,也就是说,“妖魔鬼怪”就该与人类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就不该有人性,也就不该受道德的约束。但是,作者也为自己的主人公留下了痛苦的思考:“在命运面前我犯了什么错,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安德烈好像找不到答案,但这也说明,他只是不想、也不敢窥探自己的内心,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有了问题的答案。因此,他更愿意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改变命运的想法也曾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他把对自己的救赎放在那个未出世的孩子身上,他认为孩子的出现是上帝的旨意,孩子能够指引他开始正常的人生。可是,为此他又铸下一个大错,致使他的纳斯焦娜和未出世的孩子一起走向了毁灭,这是对他这个道德蜕化的人的又一次惩罚,一次更为惨烈的惩罚,因此,安德烈的一生必将受到更为残酷的道德惩罚与良心谴责。由此,纳斯焦娜发出“活着,但要记住”的呐喊,正是这句话一直在撕咬着安德烈的内心。一句“活着,但要记住”,不仅是说给安德烈听的,也是说给全体阿达曼诺夫卡村村民听的,更是作为一个道德教训和警示,说给读者听的,作家要告诫人们的是,如果一个人游离于社会之外,脱离人民和祖国,他是无法生存的[4]。
由此,人们从小说中得出一个结论:“活着,但要记住,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祖国就没有我们的生存之地。”目睹即将发生的悲剧,没有人去阻止,作为妻子,纳斯焦娜本想阻止自己丈夫的兽行,劝他去自首,但她害怕因此失去丈夫——“他毕竟是为了看自己一眼而回来的”。她不敢向亲人敞开心扉,也不敢向自己的女伴倾述,她只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承受着别人对她人格的侮辱。为了保护丈夫,她彻底丧失了道德底线,在道德蜕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但良知告诉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在精神和道德的双重压力下,她最终选择了一个可怕的方式——自杀,以此来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永久的解脱。在作者看来,自杀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病”,要知道,她在自杀的同时,又扼杀了自己腹中的胎儿,这是双重罪孽,是道德沦丧所导致的又一出悲剧,也就是说,又有一个人为此遭受磨难——虽然这个人还没有出生。道德沦丧似传染病般开始在阿达曼诺夫卡村蔓延,人们不仅不尽力去防止“病情”的扩散,而是加剧了它扩散的进程。
每个人对道德的定义都有自己的理解,就算是学者,对这个术语也不能给出准确的定义,可以说,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的表象;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行为准则及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在生活领域里调节人的行为的必要方式,其中包括劳动、日常生活及人对周围环境的态度。当然,作家对道德问题是十分关注的,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作为俄罗斯当代优秀作家之一,他以一个公民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来表达亘古不变的道德理想和人类的本真精神。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常常涉及当今严肃的社会道德问题。在《活着,可要记住》这部作品中,拉斯普京就选择了一个人生命中的紧要关头来测试这个人的道德水准,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讲述:主人公屈从于内心的懦弱,没有返回前线,而是踏上了从前线到家乡伊尔库斯克的列车,他不知道,他的行为会给他和他的亲人带来什么。或许,他也不敢往下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他只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地猜测到了事情的走向。从安德烈逃离战争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逃开悲剧的结局,而是向悲剧的结果更近了一步。小说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预示了悲剧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在小说的开头,拉斯普京设定了这一场景:安德烈·古斯科夫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一条路通往面临危险的战场,另一条路带他远离战场回家。他选择了后者,他把自己的命运孤注一掷地交给了后者,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使他远离正常的生活轨迹,彻底背弃了人民。
三、结 语
拉斯普京走过了漫长的创作之路,他创作的许多作品提升了道德问题的高度。在当今社会,这些问题都是热点话题,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孤立的、个别的现象,片面地去研究它,而是在探究故事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同时,全面地分析了这些问题间的相互联系。
作者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即命运的抉择问题。作家告诉人们,不要向诱惑屈服——无论诱惑多大,都不要放纵自己。虽然安德烈很幸运,最终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他的内心永远不会得到安宁,他将永远遭到人们的唾弃与谴责,对他精神与道德上的审判永远不会结束,这种心灵的煎熬、道义上的审判或许比被处决更让人难以忍受。虽然安德烈的行为有其发生的主客观因素,但作者在对其进行了冷静分析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任何背离人性、道德蜕化、丧失对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被人所不耻,他们必然会自绝于人民。
这部以道德为主题、具有强烈艺术感作品的诞生为整个社会道德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让人们感到欣慰的是,正是因为有一批像拉斯普京这样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去帮助祖国固守住本民族所拥有的精神道德财富,才使俄罗斯的当代文学闪耀着灿烂的人性之光。
拉斯普京作为一名英勇的道德斗士,用自己细腻而犀利的笔锋,为只注重经济建设、忽视道德理想构筑的当今社会敲响了警钟,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一言一行,以此来拯救整个社会的道德操守。
[1]吴元迈,张捷.当代俄罗斯作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144 145.
[2]瓦·格·拉斯普京.活下去并且要记住[M].丰一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3-60.
[3]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268.
[4]李明滨,李毓榛.苏联当代文学概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34-235.
【责任编辑 张跃双】
Persistent Guardian in Spiritual Morality:Rasputin
Chen Hu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44,China)
Rasputin,the master in realistic literature,and his works a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He was a persistent guardian in spiritual morality,showing concern about social situation,such as the lack of faith and moral depravity.Therefore,he worked at the exploration of perfecting spiritual morality of human beings and contributed pieces of magnificent works which could be the reminder of message and torture of moral to the world,with the conscience of a writer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citizen for his country,society and people.
Rasputin;Alive and to Remember;spirit;morality;choice;degeneration;rescue
I 106.4
A
2095-5464(2015)06-0812-04
2015-05-12
2013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L13DYY050);辽宁省高教学会“十二五”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专项课题(GHYB13197)。
陈慧敏(1967-),女,山东蓬莱人,沈阳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