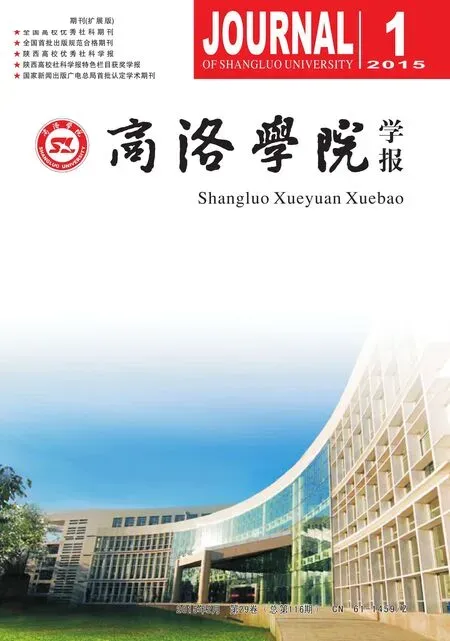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批判与继承
——基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高锐
(延安大学学报编辑部,陕西延安716000)
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批判与继承
——基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高锐
(延安大学学报编辑部,陕西延安716000)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首先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对人类具有先在性问题,来确立他唯物主义的立场。关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施密特从非本体论的层面提出了自然与社会“互为中介”的一对逆命题。其实,马克思在理解自然概念时,既从物质层面注重自然的先在性和客观实在性,又从实践角度强调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特征。社会无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还是作为自然界的对立物,都可以中介自然;但自然只有作为社会的外部环境和生产要素时才能中介社会,当把自然看作全部存在物的总和的自然时,它包含人类社会,总体中介部分显然在逻辑上行不通。所以,施密特的这个“双向中介”理论中的“自然”的内涵不同,把它作为一对逆命题来理解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先在性;“双向中介”理论;本体论;非本体论
关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初步的探讨,表达己见。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给予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都对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施密特。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就是一部研究马克思自然理论的专著。在此书的序言中,施密特开宗明义地申明,他所坚持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在一种独特的情况下对马克思所作的特殊的解释”,在这种批判理论的指导下,施密特开始了对马克思著作中自然概念的研究。这部著作是目前研究马克思自然观最详尽的一本书。鉴于这篇著作论述的内容本身以及所阐发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国内外的学者对这部著作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意见和观点各不相同。鉴于此,有必要基于文本,实事求是地解读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论述,探寻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研究中的合理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这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
一、是否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规律性的问题
承认外部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他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人依赖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依赖人。同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具有客观规律性。他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样或那样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2]言下之意,人类在利用自然时,只能改变自然的存在形式,但绝对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本身。正因为如此,施密特在其著作的第一章就指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前提的区别,并承认马克思关于外部自然界的“先在”地位及其规律性。他指出:“把物质看成是存在于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的认识论意义,与青年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从社会劳动的角度给物质作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3]64一般说来,“唯物主义意味着认为自然规律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与意志而独立存在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也意味着这一点,只是它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他们劳动过程的各种形态才能证实这种规律性。”所以,“破坏自然力完全是不可能的,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支配自然力”[3]100。由此可知,施密特关于自然界的先在性以及规律性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承认自然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具有客观规律性。在此基础上,施密特肯定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论的批评,认为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才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且马克思关于自然的社会中介的观点更确切地证明了自然的“先在性”。他还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详尽地论证了人类依靠劳动和自然物创造一个人化的世界、使用价值的世界或“第二自然”世界这个问题。在这里,强调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人所以能创造对象,是因为他首先被对象所创造。“如同还未被人所渗透的自然物质,在其原始的直接性上和人对立一样,劳动产品、劳动加上自然物质而构成的使用价值的世界——人化的自然——一旦作为客观的东西,就和人相对立。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以赖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3]63施密特在这里很明确地指出,无论是未被人所渗透的原始自然,还是打上社会烙印的人化自然,都具有客观实在性。
可以看出,施密特通过马克思著作中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和研究,肯定了外部自然界——无论是原始自然,还是人化自然,对于人类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并指出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积极地干预自然。对自然先在性及其客观性的肯定是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继承,也体现了这部著作的唯物主义立场。
二、如何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
就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始终是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自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是马克思自然观的主要特征。纵观马克思的学说,他大致从三个方面来使用自然的概念。一是把自然看作全部存在物的总和的自然,相当于物质概念;二是作为人类社会外部环境的自然;三是作为人类活动的要素,首先是生产活动要素的自然。这三个基本含义是相互联系的,既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最广义的自然概念的理解上,而忽视自然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历史中的发展;又不能在强调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特征时,忘记自然物质本来的先在性和比人更为恒久的客观实在意义。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
施密特非常注意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来考察自然概念,他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序言中就指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的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3]2施密特在这里的“其他种种自然观”,指的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所使用的自然概念,他认为费尔巴哈强调的自然具有原始性、直接性,是纯粹的自然、永恒不变的自然。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是理性和客观精神的体现;而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由于马克思正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自然,施密特表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做了这样的尝试:“试图阐述自然与社会相互渗透是在自然作为包含这两个要素的实在之内部演进。”[3]3正是在这种尝试的基础上,施密特全面展开了对马克思自然—社会理论的论述。
施密特首先强调了自然史与人类史辩证统一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把整个客观实在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他的“自然历史”概念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在反对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排除历史过程的同时,马克思想到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过程,还考虑到了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从不承认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绝对划分,而且非常反对各类制造“自然与历史对立”的哲学家。施密特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个现实部分”,这样,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界的一般特点将“继续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忽视“自然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的历史过程的特殊差异”。由此得出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史和人类史则是在差异中构成统一的,他既没有把人类史溶解在纯粹的自然史之中,也没有把自然史溶解在人类史之中。”[3]38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相互制约,密切联系。
其次,在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施密特提出了他的“双向中介”理论,即:“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关于“自然的社会中介”理论,施密特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指出,马克思之所以不是从本体论的层面来理解自然概念,是因为他加进了一个社会实践的中介:“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由此克服了这种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性质。……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直接性与费尔巴哈所说的相反,它是打上社会的烙印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人及其意识来说,仍然保持着它在产生上的优先性。这种人的外部实在性既独立于人,同时又以人,或者至少以人为中介。”[3]17施密特强调,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优先性是从非本体论的层面,即是在一个批判性的保留中呈现出来的“中介”了的优先性,这里的“中介”是客观实践的历史性的“中介”。
为了突出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施密特进一步指出了“工具”所具有的中介地位,认为工具取代了人的身体器官,作为人与自然的媒介,“人和自然通过工具的中介达到高度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业”。据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具是工人与劳动对象之间实存的、物化的中介,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5]的存在物,是工具使得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施密特的“自然的社会中介”的思想就很明确了,自然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才能向人表现出来,这里的自然既指物质层面的自然,也指外部环境和人类的生产要素的自然。
施密特在突出“自然被社会中介”的同时,认为社会也被自然所中介,二者是“双向中介”。他在著作的第二章首先为自然的含义提出鉴定:“自然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仅仅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但未经创造的物质,而马克思的自然物质已经是被创造的东西”[3]59在这里,虽然我们可以看出,施密特错误地把自然物质看成是可以创造的东西,其实人可以改变物质的形式,却不能创造物质本身。但他在这里想突出作为与人对立的自然界的规律性在人类生产实践中的作用,他指出“自然物质有自己的规律,也正因此,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这时,这些目的的内容不仅受历史的、社会的制约,也同样受到物质自身结构的制约。”[3]59可见,人可以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中介自然,而自然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也通过自身的规律性来中介社会生产实践,自然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他坚持马克思关于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坚决反对“把自然消溶到用实践占有自然的历史形态中去”,并对青年卢卡奇关于“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范畴。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溶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么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因为,“自然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但只有运用社会的范畴,有关自然的陈述才能定型、才能适用。如果没有人为支配自然而努力奋斗,就谈不上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的社会烙印与自然的独立性构成统一,在其中主体方面完全不像卢卡奇归诸给它的那种‘创造的’作用。”[3]67从中可以看出,施密特批判卢卡奇社会本体论的有力证词是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他认为在社会范畴外始终存在着一种自然物质,当然这种自然物质是被社会中介了的自然物质。在批判卢卡奇的基础上,施密特正式提出了“双向中介理论”:“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实现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那里所隐含着的自然辩证法特征”[3]78。
施密特认为他的“双向中介理论”是把隐含在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中的联系直观地表达出来了,言下之意,“自然被社会所中介”和“社会被自然所中介”这对“逆命题”是马克思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误读。因为如果“中介理论”是一对逆命题,那么,二者中的“自然”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必须一致。但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时,既没有只停留在一般的最广义的自然概念的理解上,而忽视自然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历史中的发展;同时也没有在强调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特征时,而忘记自然物质本来的先在性和比人更为恒久的客观实在意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他关于“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中的“自然”无论对于客观物质层面的自然,还是对于外部环境和人类的生产要素的自然,都可以被社会中介。因为人与社会作为自然界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当人与社会作为独立部分与自然相对立时也一刻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要进行物质变换。所以,“自然的社会中介”是自然存在形式的提升,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施密特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自然被社会所中介”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辩证统一的关系是正确的,自然与社会的确相互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与“自然的社会中介”互为逆命题的理论,即“社会被自然所中介”的理论,但由施密特的论述可知,他提出“社会的自然中介”理论时,忽视了自然物质本来的先在性和比人更为恒久的客观实在意义,只从狭义的角度把“自然”仅仅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即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然”而言来“中介”社会。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社会也的确被这个“外部环境”和“生产要素”所“中介”,但这个中介仅仅是“社会物质过程中的子系统运转”,它不能作为“自然被社会所中介”这个理论的逆命题而提出,如果“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中介在理论逻辑上并行化是有问题的”[6],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
三、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与“非本体论”的理解
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是“本体论”,还是“非本体论”,施密特在其著作的第一章就开始对其进行断定,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非本体论”的,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本体论”的。那么,“本体论”究竟指的是什么?施密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与“非本体论”的?这些问题的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在哲学史上,所谓本体是相对于现象的一个哲学术语,指的是本源、本质。所谓“本体论”在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指的是关于存在的抽象的普遍定义的“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本体论”这个哲学术语最早出自17世纪德国哲学家戈克兰纽之手,但是本体论的哲学内容,却从亚里士多德就已开始,之后经阿奎那、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直至康德、黑格尔等人进行进一步的论述,虽然几代实证主义哲学家都坚持主张抛弃“形而上学”,但最终也未能成功。本体论哲学在各派哲学家那里,以各种方式出现着。可以说,关于世界或“存在”的本源、本性、本质的哲学研究,始终在哲学中存在。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包含有关存在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但由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般不使用“本体论”这个术语,一般不使用不等于绝对不使用,马克思关于自然概念的第一个基本含义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的,“作为全部存在物总和的自然”中的“自然”就相当于物质概念。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自然理解为“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认为人的感觉、激情之类的东西只有通过“感性地存在”着的这种本体论本质的对象事实才能“真正肯定自己”。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虽然较少使用这种广义的自然概念,但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在他较多的使用“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自然要素”这些狭义的自然概念时,却都是以广义的自然概念为前提的。
施密特在强调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构成要素的自然概念时,常常会忘记“自然—物质”这个大前提,因而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会做出错误的评价。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同样,它也不是像普列汉诺夫从精神史去解释的那样,即它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综合’。”[3]209显而易见,施密特在这里的评判指向主要是针对恩格斯所持的自然辩证法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属于“非本体论”,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本体论”的。施密特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来证明他的判断:“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由此克服了这种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性质。”[3]17与此同时,“马克思把自然——人的活动的材料——规定为并非主观所固有的、并非依赖人的占有方式出现的、并非和人直接同一的东西。但他绝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绝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3]14。由此可见,施密特在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非本体性。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他的著作中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概念是人的实践的要素,又是存在着万物的总体”[3]15,这样的表述又表明,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具有本体论的性质。从中似乎可以窥探到施密特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理解的纠结与矛盾。
与此同时,施密特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本体论”的,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阐释物质的话语进行论述。“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实物概括的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物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7]233“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像‘物质’和‘运动’……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7]214在施密特看来,恩格斯关于物质概念的颇具辩证意味的诠释,进一步印证了恩格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意识到哲学本体论的危险,并极力想避开这种危险。然而,他在解释宇宙起源问题时,又从抽象物质的形而上学原则出发,自然不可能避免本体论。正是依据这个立场,施密特开始了对恩格斯的批判,认为“恩格斯一方面确认‘物质本身’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实际上只存在着物质的特定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他认为,物质之所以能解释宇宙进化的问题,不在于它的规定性,而在于它是作为世界的最高原则出现的。因此,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根结底仍然是本体论的。”[3]52
施密特将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结为本体论的判断是武断的、不公正的。从施密特所引的恩格斯的那两段对物质的解释来看,第一段是恩格斯针对自然科学企图用感性的手段感觉到抽象的统一的物质本身而言的,后一段则是恩格斯在论述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时,就“物质”“运动”不能离开其存在方式——时间和空间而言的。人类的思维需要抽象,但又不能感觉到抽象,共同的、抽象的属性只能非感性地把握。可以说,在这两段论述中,关于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人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客观实践的辩证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恩格斯并没有从纯客观的角度上来解释人类史前的和外在的自然领域,他始终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指出“德意志自然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是“微乎其微”[7]209的。在论及思维与自然存在的关系时,恩格斯做出特别的强调:“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强劲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5]209。正因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所以恩格斯不止一次提醒人类要注意正确地对待自然界。可见,施密特对恩格斯本体论的批判、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错误的、极不合理的。正如周义澄所言:“施密特这部著作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实际上否定了‘自然辩证法’”,“实际上,他在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同样否定了马克思有关的自然理论”[8]。
四、结语
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解是深刻的。他强调了自然界的先在性以及社会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并强调了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并强调人类在处理和观察自然问题时,要遵循自然规律。应该说,施密特的这些思想极具合理性,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的“双向中介”理论作为一对逆命题来提出,这其实是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误读。马克思在理解自然概念时既从物质层面注重自然的先在性和客观实在性,又从实践角度突出自然的社会历史特征。就社会中介自然来讲,社会无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还是作为自然界的对立物,都可以中介自然;但自然中介社会,只有作为社会的外部环境和生产要素时才有可能。所以,这两个中介理论中的“自然”的内涵不同,把它作为一对逆命题来论述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不准确的。此外,施密特看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对待自然问题上的差异,恩格斯的自然观注重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马克思的自然观则倾向于对人化自然的研究,这本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工的需要而致。但施密特忽略了这一点而武断地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非本体论”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本体论”的论述,是有偏颇的、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否定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因为二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自然观是熔于一炉的。那种把马克思的自然观仅限于社会历史范围内,把恩格斯的自然观仅限于自然范畴内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3]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6]张一兵.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关系本体论之证伪——《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深度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0(3):60-66.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8]周义澄.自然理论与现时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288.
(责任编辑:刘小燕)
Schmidt's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on Marxist Natural View——Based on Marx's Concept of Nature
GAORu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Yan'an716000,Shaanxi)
Schmidt first inherits Marx's idea of nature first to human beings in Marx's Concept of Nature so as to establish his materialistic stance.I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Schmidt puts forward a pair of converse propositions of mutual intermediary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at the level of non-ontology.In fact,Marx's concept of nature not only focuses on nature's first position and objective reality at the material level,but also emphasize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of nature at the level of practice.Society,whether it is a part of nature or the anti-thing of nature,can mediate nature;but only when nature i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ve factor can it mediate society.When nature is regarded as the sum of all entities,it includes human society,it can not be a general mediator logically.Therefore,the connotation of nature in Schmidt"bidirectional intermediary theory"is different,it is a distorted understanding of Marx's concept of nature if nature is taken as a pair of converse proposition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Schmidt;Marx'sconceptofnature;firstinnature;bidirectionalintermediary;ontology;non-ontology
A811.6
A
1674-0033(2015)01-0003-05
10.13440/j.slxy.1674-0033.2015.01.001
2014-10-29
高锐,女,陕西子洲人,硕士,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