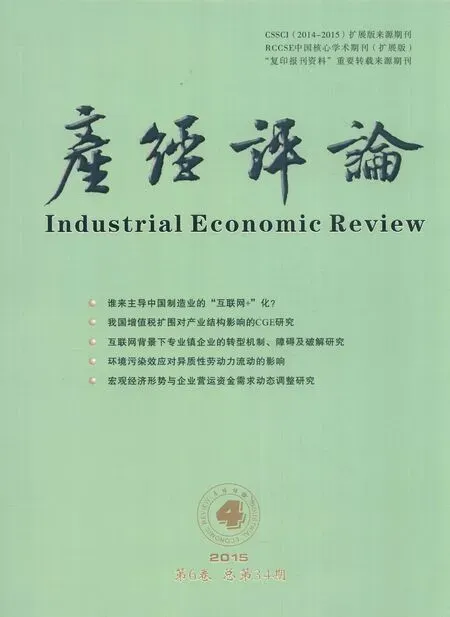互联网背景下专业镇企业的转型机制、障碍及破解研究
——兼对揭阳军埔“淘宝村”跨行业转型案例分析
张耀辉 齐玮娜
互联网背景下专业镇企业的转型机制、障碍及破解研究
——兼对揭阳军埔“淘宝村”跨行业转型案例分析
张耀辉 齐玮娜
基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通过理论与案例研究,理顺企业转型、专业镇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剖析专业镇企业的转型机制与转型障碍,理论上探讨如何破解转型障碍。主要结论:企业转型的本质是引入新型高质量要素,构建企业新的生产函数;企业转型决策取决于转型前后企业竞争优势提升带来的预期转型收益引导,是基于外部环境和企业自学习能力的综合判断与选择;专业镇企业转型具有外生性,企业所在集群出现创业精神衰败和新要素进入机会不足以及企业内部难以独立形成新要素,会反向固化不转型文化,共同导致企业转型障碍的内生性以及企业转型中的市场失效。为此,克服转型障碍需重视市场外力量的重要作用,也需激励企业内创业。企业内创业是破解企业内生转型障碍,并促进新型要素涌现的机制。实践上,破解集群内生障碍可以从增加区域内新型要素供给、提升集群整体能力、重构专业镇发展模式与构建企业率先转型的诱发机制四方面入手。
专业镇; 企业转型; 自学习能力; 企业内创业; 互联网+
一 问题提出
专业镇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空间经济形态,萌芽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期得到蓬勃发展。目前,专业镇已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集中地,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集群的主要组织形式。以广东省为例,截至2013年底,全省专业镇达363个,创造GDP总量超过1.85万亿元,占全省GDP的30%,其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已超过60%。可以说,专业镇未来发展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走向,而专业镇及其内部企业的转型也将对中国经济转型起重要作用。换言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镇”现象的出现与快速发展,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之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专业镇企业转型存在着巨大障碍。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传统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的“新常态”,这对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倍增。与此同时,随着近些年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在传统产业内应用的不断渗透,互联网已成为迄今为止信息处理成本最低的一种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基于移动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收集、挖掘、分析及整合等能力而形成的新的业务体系和新的商业模式,也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但企业界流传的“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说法或魔咒仍为困扰中国企业发展和新常态下企业转型的巨大阻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依然是很多企业获得利益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企业家们可能存在着借此方式向政府讨要减免税负或补助等优惠政策的动机,以及其他可用于解释企业惧怕转型的理由,使中国专业镇企业集群难以整体转型。
企业任何行为都会受环境制约,企业转型行为亦是如此。而我国现有针对转型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企业与外部环境尤其是具有高网络交互关系的集群环境对企业转型的制约,一些针对集群演进和集群风险的研究又往往忽视了企业个体转型对集群转型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从专业镇视角探索企业转型障碍的理论和机制,并以“互联网+”创新驱动为时代背景寻找破解障碍的思路,进而基于企业转型构建专业镇新的发展动力,探索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新突破口,力求回答“为什么专业镇企业存在着转型的共同困难”、“通过何种机制能够推动专业镇企业突破集体的转型障碍”、“这种机制是否可以通过公共投入形成”等问题,并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理清企业转型、专业镇转型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实现理论上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新认识。
二 专业镇及企业转型理论综述
1.专业镇形成与演进
专业镇的概念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末由理论界根据广东省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提出,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企业簇群(王珺,2002a)[1]。专业镇经济的实质是大量中小企业的地理集聚、衍生和发展壮大, 并通过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企业集群(郑海涛和周海涛,2005)[2]。这种网络化的组织形式有利于引导分散而孤立的中小企业资源向专业化整合,以自然村或乡镇为单位,将一家一户的生产与地区乃至全国和国际市场相结合,形成有地区性行业规模效应的专业镇,从而不仅与城市经济构成相对合理的分工格局,也是进入国际化竞争的模式创新(李新春,2000)[3]。我国专业镇发展最具规模的首推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美国的“好莱坞”、硅谷与128号高速公路,意大利北部和我国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出口加工区,日本和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的“一村一品”、 “一镇一品”等,都是典型的专业镇范例。
根据现有研究,企业集聚与专业镇的形成存在两种内在驱动力:一是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据马歇尔最早提出的分工“外部性”原理,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和相互依赖源于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供应、运输便利及技术扩散等带来的“外部经济”,这种资源的共享和知识的流动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也指出,企业集聚会产生集聚效应,即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企业间分工协作会带来规模经济,同时集聚区域内由于基础结构改进而获得便利条件,也会使企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实现总体生产成本的下降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二是构建企业协作网络,降低交易费用。以Storper(1989)[4]为代表的“新产业空间学派”从交易成本角度提出企业的集聚是为了使交易费用最小化,即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台湾高科技企业集群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由同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并维持了网络内的运作秩序(陈介玄,1994)[5],网络内形成的承诺与信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共享知识信息、消除环境不确定性,并促进网络内的分工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吴思华,1995)[6]。
由此可见,获得集聚与分工带来的正外部性是形成集群的主要内在机制,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克鲁格曼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中心-外围模型,成为研究集群问题的核心理论。克鲁格曼(Krugman,1991)[7]通过引入规模报酬递增、人口流动和运输成本揭示了制造业企业区域聚集的原因,并认为企业集群为什么在某些区域出现,源于历史和偶然事件以及一旦区域内形成专业化格局所产生的累积因果效应。也即是说,在领先创业活动的引领下,当以上驱动力与区域资源禀赋、文化制度环境等有机结合后,便会孕育和自发形成企业在一定地理区域集聚的专业镇现象。冯德显(2003)[8]将这种主要由区域内部力量,如区域内部资源、技术和市场以及工商业传统和居民创业精神等引导发展起来的企业集群称为原生型企业集群,而将由外部因素或力量,如外资带动或政府主导组织等驱动形成的企业集群称为嵌入式或外生型企业集群。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专业镇尤其是原生型专业镇,大多属于低端的低成本集群,即参与竞争的基础是低价格、廉价原料、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及低成本性等特征(Sengenberger和Pyke,1991)[9]。同时,从分工与企业组织联系的视角看,原生型专业镇在发展初期通常是以水平专业化为基础,尚未形成沿产业链条的纵向生产网络关系,因而缺乏积极的集体经济效率,生命力脆弱,但如果在规模扩大的同时能进一步深化分工,密切企业间的纵向联系,就可能进入向高级化演进的发展轨道(王珺,2002b)[10]。也就是说,专业镇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的企业群落,它的出现、增长与发展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根据Ahokangas et al.(1999)[11]的研究,区域集群的演进可分为起源和出现、增长和趋同、成熟和调整三个阶段。在起始阶段,由于地区优势或其他原因,一批快速增长的新企业在某一地点相互集聚,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利用其独特的私人关系和接触,来建立并加强企业间的联系。随着各种新企业的不断进入,集聚的经济效益凸显,推动集群进入实质增长阶段。大量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会加快各种思想、技术和信息的传播,同时也导致了企业间经营活动的模仿与同构化,这种模仿和同构化的普及会导致集群呈现同质竞争的特征。在成熟的集群环境中,集群规模因空间环境的限制会达到饱和,出现拥挤现象,集群内的高聚集密度、高竞争强度和高要素成本会使集聚经济被逐渐耗散,此时,随着集聚不经济的持续和集群内创业活动变得日益保守,整个集群会进入衰退期,严重时甚至会走向毁灭。
2.集群与企业转型
企业集群是一个动态的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演进过程,因此当集群面临衰退甚至解体危险时,就需要通过转型实现集群由低级向高级的升级和发展。波特(Porter,1998)[12]曾指出,集群因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集群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更替,如果企业群落实现了产业组织的成长和环境条件的改善,进而由初级向高级演进,则为正向更替,反之若企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环境条件恶化,使集群走向衰退和灭亡则为反向更替。Capello(1999)[13]曾将企业集群的演化划分为地理接近型集群、专业化产品区、工业区和创新区四个阶段,并认为这一演化过程并不会自动实现,在升级的每一阶梯上都有可能停滞不前,而升级的动力来源于集群转型。我国学者王珺(2002b)[10]结合广东省专业镇经济的实践,把簇群经济划分为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展型三个阶段,为专业镇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转型升级的路径。此外,由于企业集群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其演进和发展会受到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魏后凯(2003)[14]将技术和需求的变化视为最为关键的因素,并认为,当技术和需求的变化对集群产生很大冲击时,集群必须要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再定位,通过鼓励和强化创新、完善市场组织网络、制裁欺诈性行为、促进企业转型等方式保持集群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量针对成熟集群风险的研究也为分析集群转型提供了线索。Markusen(1996)[15]指出,区域集群越成功,越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进而逐步丧失获取应对市场变化所需的能力,导致集群竞争力不断下降,直至集群消亡。De Vol(2001)[16]的研究也发现,促使集群形成及带给集群竞争优势的要素也许最终会成为导致集群衰败的风险因素。这些结论都隐含了构成集群优势的自身性质,同时也是集群风险产生根源的观点。我国学者吴晓波和耿帅(2003)[17]借助植物学描述自花结实的术语“自稔性”将区域集群由于自身特性,包括专业化分工、地理邻近性、群内企业相互关联以及协同与溢出效应,在构建集群优势的同时而滋生的集群风险称之为自稔性风险。具体表现为,专业化分工使群内企业以最优规模生产,但也加大了群内企业的调整难度;空间邻近性有利于群内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但也容易导致群体思维和战略趋同;群内企业间相互关联能够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但也容易导致集群走向自我封闭;协同溢出效应能使企业获得外部经济,但也滋生了群内企业的创新惰性。
以往的集群转型研究注重对集群的整体描述,却常常忽略企业这一微观主体的作用。企业的创新与转型是决定集群发展方向的微观基础,如果在集群面临衰落时,企业能保持旺盛的活力,积极创新并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将有助于企业集群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目前,企业转型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国内企业普遍面临转型压力的背景下,企业转型理论更是备受关注。Adams(1984)[18]最早将企业转型定义为在思考和行为上彻底且完全的改变,以创造出一个不可回复、与先前不连续的系统。也有学者从组织视角将企业转型看作是一种发生在组织对自身认识上的跳跃式变革, 并伴随着组织战略、结构、权力方式、模式等各方面的变化。国内学者吴家曦和李华燊(2009)[19]通过与“升级”概念的对比来定义转型,即转型是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通常以跨出原有核心技术或经验领域而言,表现为企业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转变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转换,而“升级”是在原有核心技术或经验领域上提升更为精进者。王吉发等(2006)[20]认为,要深刻理解企业转型,必须剖析转型的本质动因。根据“外在成长理论”和“内在成长理论”,他们将由于企业资源、能力的非优化状态导致企业竞争优势降低,进而促使企业组织变革的转型称为内生型转型,表现为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业务过程或产品与市场的转型;由于外部行业环境变化导致企业成长衰退,进而迫使企业转型的称为外生型转型,表现为跨行业的多元化策略或退出原行业进入新行业的行业转移。
综上,现有对专业镇及企业转型的研究基本围绕着专业镇转型的原因、转型的路径以及企业转型的特征与表现等方面展开,却未能从理论上回答企业和专业镇如何实现转型、企业转型和专业镇转型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等。也就是说,即使企业知道自己的死亡是源于没有转型,但却无法基于现有理论谋划出转型的方向与对策。
三 “互联网+”时代的专业镇企业转型机制
根据现有研究对转型的定义,本文认为企业转型体现了企业生存发展方式的本质性变化,包括企业赖以为继的核心资源、商业逻辑等,进而导致了企业的价值主张、产业链定位、组织流程及商业生态等一系列的变化,但其基础是新型高质量要素的注入和对旧的低质量要素的替代,以此影响企业运行模式的根本改变。在“互联网+”时代,典型的新型要素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以及高质量人才等,通过引入这些新的技术和能力,将有助于企业形成新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进而完全改变传统行业的效率和能力。这种跃变是基于企业对长期竞争优势提升的期望,并以此摆脱环境束缚甚至影响环境变化。率先的企业转型行为如同出现一个新物种一样新奇和困难,一旦出现企业率先转型,这个集群的转型涌动便有可能开始。
因此,转型对企业而言是一项涉及整个组织的战略上的变革,不仅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动态性,还具有显著的系统性、跳跃性和高风险性。虽然企业做出转型决策的直接动因是竞争优势的下降,但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企业转型决策的复杂性,即企业是否要转型、如何转型不仅涉及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等状况,还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市场竞争及制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尤其对处于集群环境中的企业而言,簇群经济一旦形成便成为每个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个体企业无法支配和改变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王珺,2002a)[1]。虽然企业可以借助该环境获得更多的外部性收益,但集群进入成熟和衰退阶段后,外部性收益便会下降,此时企业就需要做出决策,是维持现状等待,还是冒险进行集群内转型,又或是退出集群。如果企业普遍选择维持现状,则有可能与集群一起步入衰退,面临在危机发生时一起灭亡的风险;如果企业普遍选择退出,则集群会逐步衰落,企业有可能在新的行业或地区重新起航;但如果集群内有企业率先选择冒险转型,并带动其他企业跟随则有可能带动整个集群的转型与升级。
1.企业转型的微观机制
基于王吉发等(2006)[20]的研究,本文将微观企业转型的动态模型进行拓展,以描述集群内企业转型的微观机制与途径。
首先,对企业个体而言,假设外部环境为静态恒定的封闭系统,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要素的投入与要素的价格,则企业的竞争力函数可表示为:
s=f(r)-rpr
(1)
其中,s为企业的竞争优势;r为企业的要素投入矩阵;pr为要素的价格矩阵,为企业不能控制的外生变量;f为生产函数关系。
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在要素约束下,通过相应的决策手段获得竞争优势的最大化。因此可构建如下的企业优化方程:
Max{s=f(r)-rpr}
(2)
(3)
其中,m表示企业可用于投入的要素类别数。
由此可见,在静态外部条件的假设下,企业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改变函数关系f,而基于要素价格的变化调整投入要素的种类与数量组合,此时该模型的求解可归结为一般的最优化问题,不属于企业转型范畴;二是改变函数关系,即在既定的要素约束下,通过构建新的函数形式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该情况接近转型的内涵,但由于企业转型是一个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需放宽假设,在外部条件可变的情况下对第二种情况进行分析。
外部条件可变意味着由于外部资源价格和易得性以及市场竞争态势的改变,企业随着经营活动的积累,不仅可以改变生产函数的关系f,还可以拓展和调整要素类别及两者的数量组合。如果将r看作是企业传统生产中投入的可在要素市场购买的一般性要素,如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等,新加入的要素u为以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为基本特征的高质量要素,如创新技术、高级人才等,则企业转型的决策函数可表示为:
Max{Ω=[g(u,v,r′)-upu-r′pr]-[f(r)-rpr]}
(4)

(5)
g(u,v,r′)-upu-r′pr≥f(r)-rpr
(6)
其中,r和r′分别代表转型前后企业投入的传统要素矩阵;u为新注入的高质量要素矩阵;pu为新要素的价格矩阵;n为企业可投入的新型要素的种类;v为企业拥有的有利于企业转型的能力矩阵,本文将其统称为“自学习”能力;g为转型后新的生产函数形式,则g(u,v,r′)-upu-r′pr表示转型后企业获得的竞争优势。
由该模型我们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如果将企业转型后与转型前相比所获得的竞争优势的提升幅度称为企业的转型收益,那么企业转型的目标就是实现转型收益,即Ω的最大化。因此,企业转型前的竞争态势越糟糕,转型后预期可实现的竞争优势提升越大,企业的转型收益就越大,企业转型的动力也会越强。
(2) 转型收益的大小会受到新型要素的种类与投入数量、新型要素与一般要素的价格及相对变化以及企业转型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转型所需要的新型要素供给缺乏或者企业获取新型要素所需付出的成本即pu过高,导致无法实现转型收益,则企业将不会做出转型决策。
(3) 企业转型除了要获取新要素,另一个关键环节是企业需基于外部环境变化构造新的生产函数,以实现新型要素与一般性要素的重新配置组合,进而带来企业价值主张、产业链定位、组织流程及商业模型等一系列的变化。这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需要企业进行持续、反复的尝试与摸索。本文将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学习新知识、探索新要素从而构建新的有效的生产函数的行为统称为企业的“自学习”,那么在面对同样的外部条件时,这种“自学习”能力在不同企业间的差异就导致了企业所实现的转型收益的不同。
(4) 企业实现转型的途径可划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不脱离原行业,仅通过向企业内引入新要素逐步实现企业转型。新型要素不仅包括具有集约和知识积累特征、有利于提高企业附加价值的新资源,还包括企业新能力的培养,如创新和品牌构建能力等。此时,转型就是新型要素与原有要素之间的部分替代、匹配与融合的过程。受新型要素注入的影响,该方式会伴有对原生产函数的改造和优化,但由于企业并未脱离原产业,因此转型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新的生产与发展方式,构建企业独有的新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进而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并提升企业在产业内的地位。当转型企业形成的新发展模式与商业逻辑在行业得以扩散后,往往会激发原产业焕发新的生命力,进而带动和实现产业整体的转型升级;二是企业进行跨行业转移,即通过构建适应新行业的全新生产函数,并对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以实现转型。新行业与原行业的差异性越大,企业的转型越激进,转型的风险也会越高。企业进行跨行业转型决策一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原行业已属于夕阳产业,市场规模正在逐渐萎缩,企业不得不从该行业转移;其二是受新行业发展潜力和盈利预期的吸引。基于第一个原因的转型通常会使企业完全脱离原行业,而基于第二个原因的转型多表现为企业的多元化经营。
由此可见,企业转型的关键在于企业可以以一种可承受的成本水平获取新型要素,同时克服转型障碍,培养有利于转型的新能力。新型要素的获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外部要素市场进行购买,另一种是通过自我生产从企业内部提供。第一种方式显然取决于整个外部环境中要素供给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无法保证新要素足够的供给导致新要素价格过高时,企业将由于无法从外部获得要素支持而被迫陷入“等待”状态。而由企业内生提供新型要素的方式,则意味着企业一方面需要通过“自学习”对现有的知识与经验体系进行更新甚至颠覆,另一方面也要为新型要素的培养付出时间与资金成本。当企业内部不具备内生新型要素的条件或面临的障碍与风险过高时,企业也会失去转型动力。
2.企业转型与专业镇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如果将外部环境设定为专业镇的集群环境,则企业转型必然会受到企业所处集群的约束。对于已趋于成熟和饱和的专业镇而言,集群内激烈的竞争环境已经使企业竭尽所能在既定的资源与能力水平下实现两者的最优组合,此时企业转型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资源日益匮乏、环境容量制约加大、消费市场萎靡和国际市场动荡等新经济形势,一方面会导致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被稀释,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企业的生产风险,由此便会促使一些面临生存威胁和迫切渴望提升竞争优势的企业产生转型动机。
假设专业镇内的企业通过引入新的更高质量的要素实现了转型,那么通常会给企业带来三种结果:一是企业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种类和构建新的生产函数,以技术创新和品牌化经营等方式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地位;二是企业将自身的优势资源与新要素相融合,剥离低效率业务,在缩小业务种类的同时扩大高效率业务的规模边界,以获取纵向分工的规模经济;三是企业完全脱离原行业,基于新要素进入全新的业务领域。第一种结果会促进专业镇内龙头企业的产生,并带动专业镇向集约化和高附加值的高级阶段发展;第二种结果会导致专业镇内企业沿产业链的纵向分离,从而使专业镇向更高层次的纵向一体化阶段演进;而第三种结果有可能导致专业镇内传统产业的萎缩和退出,此时若能将专业镇内原本形成的生产网络、合作关系和商业传统顺利地转移到新产业,则势必会带来专业镇整体的跨行业转移。由此可见,克鲁格曼所说的分工深化的空间效应并不会自动的随着企业集群的发展而一直持续,而企业适时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集群整体转型才是实现集群持续发展的关键。
企业转型与专业镇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在由企业转型带动专业镇转型的整个链条中,企业与专业镇对新型要素的供给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引入、培养和有效地使用新型要素均需要企业自身具备“自学习”能力,以形成一个有效的知识更新机制,从而促进新型要素功能的发挥;其次,专业镇内的集群环境应有利于为企业转型提供可行条件,吸引新要素向集群内聚集,从而丰富新型要素的供给数量与种类,降低企业从外部获取新型要素的成本。同时,在由企业转型的个体行为向专业镇企业群体转型的扩散过程中,率先转型企业所发挥的示范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是实现专业镇整体转型的核心机制。根据齐玮娜和张耀辉(2014)[21]的研究,如果将企业转型看作是企业的一次内创业,那么率先转型企业的商业实践会通过商业知识溢出向其他跟随转型的企业提供一种观察学习的手段,为其传递成功引入新要素并实现这些新要素价值的途径和方法,降低其他企业对转型风险的感知,增强转型的信心,从而带动集群内企业的群体转型。

图1 企业转型与专业镇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
四 “互联网+”时代专业镇企业转型的内生障碍
以上分析为揭示专业镇企业转型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对企业个体决策而言,当外部环境变化使企业面临转型压力时,企业是否会主动选择转型?如果外部存在转型的可行条件,企业会如何做出率先转型的决策?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专业镇企业转型可能面临的障碍以及障碍的形成机制。在集群环境下,企业转型不仅会面临来自自身的障碍,还将面临共同的来自于集群内生的转型障碍。
1.企业转型障碍
如前所述,转型意味着企业需要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以更新、补充甚至替代原有的知识体系,但原有的知识体系通常是一个正常存活的企业随着经营的持续逐渐积累形成并被企业成员广泛接受的,具有很强的根植性,若要对其进行更新甚至颠覆必然需要克服重重阻碍并付出巨大的学习成本。例如,要将“互联网+”的理念融入传统产业,以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绝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实现企业整个业务体系和商业模式的重构,从而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因此,转型首先面临的障碍就是难以放弃企业原有的知识体系。通常,人们都存在对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不能轻易给予否定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个体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传统,形成一种个人的知识缄默。企业家作为原知识体系的缔造者亦是如此。同时,由于这些经验和知识已经通过知识包围的方式控制组织中的每个人,那么组织中必然会不断出现其他成员挽救原有知识,动摇企业家放弃原知识体系的决心。其次,新知识的学习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新的知识体系往往涉及企业家们完全陌生的市场运作、生产流程及资源管理方式、新业务下的企业治理以及新的核心人员管理等领域。企业家们的传统业务知识多来自于经验积累,而新知识往往需要通过带有强迫性的学习获得,当学习产生的绩效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时,则会在企业家中形成对学习的恐惧和抵触心理。此时,企业家通常会在两种知识体系间徘徊,使新知识的接受效率大打折扣,成为企业家无法轻易跨越的隐性转型障碍。
另一个来自企业自身的转型障碍源于企业对新型要素的吸收和注入过程。首先,从企业获取新型要素的两种途径不难看出,对于以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为基本特征的新要素,企业独立培养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物质成本,尤其当企业一直以竞争与低成本战略为核心发展时,很难具备对新要素进行长期培养的条件和能力。此时,如果企业外部即社会也无法提供新要素或新要素价格过高导致高转型成本与风险时,企业从理性决策出发,不会做出转型决策。也就是说,当社会无法提供满足转型的外部条件时,企业主动谋求转型往往就是“找死”。其次,假设社会已经具备了适应转型的条件,则新要素要发挥作用就需与企业既有要素和企业内部的结构条件进行融合和匹配。若企业内存在阻碍新要素发挥作用的因素,则需要企业家创新思维突破阻碍,这需要一定的魄力并能承担决策责任。然而,如果新要素无法在短期内给企业带来利益,就会招致企业内部成员的非议,甚至导致转型中断;若企业吸收新要素后因急于追求近期局部业绩而采取不利于整体转型目标实现的措施或新要素进入后反被原有系统同化,也有可能使转型半途而废。研究发现,现实中越是以往曾有过辉煌业绩的企业,越容易因原有知识经验体系的根深蒂固和巨大惯性导致新要素无法与原体系相融,甚至被原体系同化(Capello,1999)[13]。而转型尝试一旦失败,一方面会打击其他同类企业转型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也会使新要素因无法在该区域获得价值实现而离开,导致区域内新要素供给的匮乏,从而恶化企业转型的外部条件,加大转型障碍。
由上不难看出,企业内生的转型障碍,同时也是阻碍企业进行“自学习”的主要因素。该分析隐含着企业的“自学习”是以外部具备可行的转型条件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企业不可能独立地创造出主动转型的条件,进而也不可能为其他企业创造出转型条件。因此,当所有企业都没有采取转型时,我们有理由怀疑是由于外部转型条件欠缺导致企业群体等待的结果。同时,即使具备可行的外部条件,若转型不能为企业带来适当的利益,企业也不会有转型行为。当以上两个条件都满足时,企业是否可通过“自学习”吸收新要素并顺利实现生产函数重构就成为转型的关键。因此,本文认为企业转型具有外生性和被动性。其中,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企业竞争优势下降和对企业生存的威胁是企业转型的充分条件,外部是否具备转型条件构成企业做出转型决策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企业的“自学习”能力则是转型得以成功的保证。
2.专业镇内集群内生的转型障碍
以上分析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企业,而对处于专业镇内的企业而言,其转型的动机与决策还会受到集群内生的转型障碍的影响。结合企业转型模型与现有对集群风险的研究,本文认为集群内生的转型障碍来源有两个方面:
第一,专业镇的发展和成熟导致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衰落和对转型的抵触。
Galor和Michalopoulos(2012)[22]的最新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风险承担与增长驱动倾向的人获得进化优势,从而带来区域创业活动的繁荣和经济发展步伐的加速,但到了成熟阶段,风险厌恶个体会获得进化优势,削弱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该规律在企业集群中更具有代表性。集群最初的形成与发展壮大源于大批具有创业精神的创业者的冒险和领先活动在区域内的集聚,但随着集群进入一个稳定和比较封闭的发展状态后,企业家心智模式趋同,使集群内的创新行为减少,模仿行为增加(黄文静和赵江明,2005)[23]。此时,集群内会出现企业战略趋同的现象。当外部环境有利时,每个企业的经营情况都得到改善,从而形成企业不转型也可生存的错觉,而这种情况并不是来自于企业的努力,而是来自于企业的共同争取或者等待。比如,因为集群内企业同步的低利润,造成了政府压力而出台一些扶持政策,或者由于国际市场环境变好,他们同时感受到终于等到了转机;但当市场变差时,每个企业的状况均发生恶化,企业之间的交流并不会让企业家感到转型的紧迫性,反而产生期待政策扶持的心理。这两种情况导致了专业镇中没有转型突破的榜样,相反却形成了大家同步等待、叫苦、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行动协同,使集群内形成一种对转型的情绪性抵触。
第二,新型要素供给不足,且缺乏新型要素进入的机会。
专业镇中的企业处于相同产业链条下的产业同构状态,所需要的要素类型几乎相同,这可以使企业增加要素使用的冗余,但也给企业转型获取和注入新要素带来困难,因为很难有新要素自我学习、获得成长的环境,进而形成了要素交流来源的僵局。同时,集群内过度竞争而处于微利状态的企业,通常缺少花巨资引入新型要素的动机、魄力与能力,由此便形成了人才进入的死结和技术的锁定。下面我们分别以创新技术、品牌和高质量人才三种新要素为例进行详细分析。
Keeble和Wilkinson(1999)[24]认为,集群中企业长期的集体学习和连续的知识积累可能会使集群的技术发展停滞。因此,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附加值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还是集群转型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专业镇中,由于存在大量相似企业,这些企业又共同与外部企业结成网状结构,这便形成了两个重要现象:一是相似企业之间通过直接传播、相互启发、人员交流等途径使技术非常易于传播,当某企业通过研发或购买获得新技术时,企业将无法阻止相互间的模仿。同时,企业基于新技术形成的新商业模式也会发生溢出,使模仿者获取后发优势。因此,创新投资的高风险和创新产品较强的外部性会导致集群内企业失去研发创新的动力,而更愿成为免费“搭便车者”。如果所有企业都选择该策略,专业镇的技术创新就会陷入“囚徒困境”(王珺,2002b)[10];二是对纵向分工关系的企业而言,上游企业不仅为某下游厂商服务,还为其他下游厂商服务,当某下游厂商创新,而其他厂商不创新时,上游企业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从而存在上游企业不会支持下游厂商创新的情况,并有可能导致集群纵向网络的解体。因此,当企业追求或严重依赖于网络化集群效应时,其创新决策会取决于上游企业的态度,显然这会放大创新的不确定性,从而阻止创新技术这一新要素的引入。
打造和培育品牌是企业获得高附加值的另外一个重要方法。但在专业镇以成本为导向的集群化生产方式下,企业往往缺少品牌意识和品牌能力,而且成本导向的发展方式必然会内生出价格竞争的市场行为,这种行为也与品牌战略相悖。也就是说,虽然企业品牌化战略仍然可以依赖原来成本导向的生产体系,但在以价格竞争为主的集群环境中,品牌的树立是十分困难的。在专业镇中,订单的进入往往是因为集群产品的低价、质量保证和充分的供货选择性,而低价又经常会使企业附加值与利润双双变低,企业因此缺少资金积累,投入品牌的能力也因此受到限制。同时,在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下,每当有品牌受到强化,就会有盗名者参与其中,这也使得企业品牌投入成为这些外围假冒者的公共投入。此外,品牌战略所要求的生产体系的高保障性也与集群化生产方式相悖。集群化生产中的上游企业主要是以标准化生产方式为所有下游企业服务,而不可能为有特殊要求的某一下游企业提供特定的服务,这会迫使品牌战略企业自主建立生产体系,从而导致集群生产方式面临解体。也就是说,只有企业适当脱离集群才有可能继续从品牌战略中获利。综上所述,当以成本为导向的竞争行为变成一种社会行为时,就会成为当地社会的主流意识,进而挤压品牌意识,造成专业镇内企业普遍不重视品牌,不愿学习品牌经营,不愿培养和引进品牌经营管理人才,使企业集中的地区难以培养出龙头企业品牌。
无论企业采取何种转型策略,新型要素的注入都需要高质量人才的引进和配备,以提高企业的转型能力。但集群环境下的企业趋同和锁定很容易使人才培养形成死结,即你没有用这样的人才,我也没有用;你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也没有。而企业的微利状态也往往使其失去了在企业内培育人才的能力。如果企业花巨资对外引进人才,则很可能面临新要素与企业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与组织惯性相冲突的困境,导致新要素要么被同化,要么因无法发挥作用而离开。此外,集群成熟后形成的自我封闭状态也会导致外部高质量人才由于受到区域内人口流动的限制和对外来人口排斥的威胁而缺乏进入集群的机会,从而使专业镇的发展受到区域人力资源的限制(李新春,2000)[3]。
以上分析把新型要素提供的易得性作为企业转型的前提,识别了专业镇企业转型面临的共同障碍。对专业镇而言,企业转型受到集群环境的制约,如果集群内不存在企业转型的可行外部条件,那么很可能出现企业转型与集群转型相互等待的结果,即集群等待着率先转型企业来推动集群转型与升级,而企业则等待着集群为其创造可行的转型条件。此外,技术创新中的“囚徒困境”及品牌构建的外部性问题也揭示了集群内率先转型决策面临的障碍。根据前文所述,企业的率先转型行为会导致商业知识的溢出,形成对其他企业的示范效应,尤其在集群环境下,企业间联系紧密,知识和信息非常易于传播,由此也更容易导致“搭便车”的模仿者。而与模仿者相比,率先转型的企业却需要面对更大的转型风险,付出更大的转型成本。因此,当集群内企业都希望通过对率先转型者进行模仿以获得后发优势,则有可能使整个集群陷入转型的“囚徒困境”。
因此,专业镇转型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活动,不创造外部条件的转型推动,只是一种号召和理想,不可能转换为企业行动,因此也就无法发挥企业这一微观基础对专业镇转型的推动作用。而外部条件并非是由企业传统生产过程提供,需要有外部治理的力量。同时,由于率先转型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性往往无法通过企业自身进行内部化,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协调和补偿机制,集群内将难以出现率先转型效应。由此可见,专业镇内企业转型的障碍具有内生性,而企业转型决策具有外生性,这其中存在市场失效机制,要弥补这种失效,就需要发挥非市场的力量,通过创造可行的转型条件与激励企业率先转型的诱发机制以推动企业率先转型进而实现专业镇的整体转型。加入了非市场力量的专业镇转型模型如下图2所示。

图2 加入非市场力量的专业镇转型模型
五 专业镇企业转型的障碍破解
企业转型模型和对企业转型障碍形成机制的分析为障碍破解提供了理论逻辑。对企业自身的一般性障碍而言,排除传统体系的干扰是转型的核心,内创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对集群内生的转型障碍而言,如何在集群内创造转型的可行条件,激发企业转型动力并敢于领先转型是其中的关键。
1.企业的内创业转型
1983年,Miller首次提出公司内创业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已有组织通过创新、更新及风险投资等活动追逐创新发展机会,实现企业获利能力和竞争地位提升或组织更新的过程(Miller,1983)[25]。与个体创业相比,公司创业侧重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重新组合,并表现出创新、风险承担、先动、竞争积极和自治等五大特性(Lumpkin和Dess,1996)[26],其目的在于通过增强组织的创新能力及柔性适应能力,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从而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克服企业惯性,以实现基业长青(Morris和Kuratko,2002)[27]。由此可见,内创业的本质与企业转型非常契合,或者可将企业转型看做是内创业的一种形式。因此,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内创业理论可为从微观层面探讨企业转型的途径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根据现有研究,内创业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组传统业务或用全新业务代替传统业务。乔布斯在1996年重新回归苹果公司后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虽然遇到很大的阻力,但却充分动员了企业资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进而鼓励了企业员工支持企业变革,形成公司持续创业的文化。这种退旧立新的创业有利于破除业务知识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的决心与推进策略是决定创业成败的关键。但也必须意识到,这种内创业有可能仅是通过对企业现有资源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为企业带来创新,而未必一定会带来企业转型。第二种是在原来业务系统基础上延伸业务,但不采取组织分离。延伸的方法包括空间延伸,即在其他地区组织分公司;纵向延伸,即在原来业务基础上向其他业务延伸,比如淘宝向支付宝网络金融业务延伸;多元化业务,即通过为主业服务培育经营能力,然后再面向更大的市场形成新的业务;第三种是以治理区隔方式组织新的公司,母体企业仅相当于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或天使投资者,对企业里有创业欲望的人给予创业支持,共享股权,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新公司的业务可以与母体企业有关,也可以无关,但母体企业可以通过对投资方向进行规定,使创业活动为企业转型服务。
以上三种内创业类型对企业选择具体的转型方式均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第三种以组织区隔方式进行的内创业。该类型的关键是共同出资,母体企业不再是全部资本的出资者,而只是部分出资者,这种股权分配的意义在于调动创业者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母公司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有意识地将母公司与创业进行隔离对推动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根据前文对转型障碍内生性的分析,企业转型最主要的自身障碍在于无法越过传统的经验体系导致企业“自学习”效应的缺失,而将传统业务系统与新业务系统隔离,可避免传统业务系统内的障碍因素传递到新的业务系统,从而实现对新业务系统的有效保护。同时,企业还可以有计划地对传统业务系统进行战略性收缩,将相关人员逐步向新业务转变,以使传统业务能顺利退出。以这种方式进行企业转型一方面可以使传统业务产生的现金流和利润用于支持新业务的开展,另一方面传统业务系统中的一般管理职能、金融担保能力、市场信誉、供应链经验等也可能为新业务所利用,从而降低内创业的初创成本和企业的转型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内创业作为企业转型并获得发展的方法是以企业作为风险投资者来看待的,这和现实中存在的大量的企业多元化经营有本质差别。在波士顿矩阵中,企业业务被分解为问题型业务、明星型业务、金牛型业务和瘦狗型业务的组合,并建立了从问题探索到培养明星、金牛获利收回投资,直至退出企业的多元化业务循环。但是,企业转型发展并非是为了建立这样的业务循环,而是为了退出旧的业务系统,进入新的业务系统,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用产业链延伸来培育新的业务能力,放弃那些以数量要素为依托的业务系统,通过引入新的高质量要素推动企业业务中心从产业链的低附加值区域向高附加值区域转移。这一过程需要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转型障碍,积极地促进内部要素通过学习、培训转移到新业务中去或被新要素替代而退出企业。
2.专业镇企业的群体转型
如果从理论上将某一特定企业集群看作一个具有封闭边界的组织,那么我们可将企业转型模型进行拓展,从专业镇层面分析破解企业群体转型障碍的途径。同样,假设在静态条件下,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函数可表示为:
S=F(R)=RPR
(7)
其中,S为专业镇内企业集群整体的竞争优势;R为专业镇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数量矩阵;PR为要素的价格矩阵;F则反映了专业镇基于其要素禀赋实现竞争优势的映射关系。根据我国专业镇的形成与发展现状,这里的R主要指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低成本的土地、基础设施、资金和技术工人以及宽松的制度环境等,这些资源对每个企业而言都是共有的,且属于一般性生产要素。同时,由于专业镇的能力主要体现为生产与营销等功能性能力,技术与产品的创新与开发能力、品牌构建与运作以及现代管理能力尚十分欠缺(张海梅,2009[28];刘城,2014[29]),因此决定了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以产品低价、质量保证和供货多样为主。
随着集群空间越来越拥挤,一般性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升,制度环境尤其是对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监管的加强,集群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转型的压力日益增大。若以提高生产附加值和提升集群竞争优势为转型目标,那么专业镇就需要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函数,如式(8)所示:
S′=G(U,V,R)-RPR-UPU
(8)
式中,U表示专业镇内的新要素的数量矩阵;V表示专业镇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异质性能力,该能力需有利于促进专业镇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R表示被新要素替代后剩余的必要的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数量矩阵;PU表示新要素的价格矩阵;G表示基于新要素和异质性能力所形成的新映射关系。
由此可见,克服集群转型障碍的关键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专业镇的转型目标,增加区域内新要素的种类和数量,并逐步对传统要素实现更新和替代,从而改变企业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同时通过新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促使企业引入新要素,实现新的要素配置方式;二是提升企业集群整体的能力层次,形成集群的异质性能力;三是重构专业镇的发展模式,摆脱传统的依赖低成本数量要素投入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生产方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定位。这三方面的措施可为企业转型创造可行的外部条件,但要使企业主动实施转型行为,构建企业率先转型的诱发机制是不可或缺的第四个关键因素。
不难看出,以上对集群转型障碍的破解均需非市场力量的参与,因此政府功能在专业镇转型前和转型初期不可或缺。具体操作方案需要不同的专业镇结合自身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但总体而言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要促进新型要素向专业镇内流动和聚集,需要构建一个开放、宽松和宽容的集群环境。李新春(2000)[3]曾指出,在广东珠三角一带,虽然外来人口流动规模较大,但大多形成了本地人为老板,雇佣外地人打工的格局,而外地人要在该地区创业非常困难。同时由于本地人口有限,本地人中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资源更加稀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创业精神的持续。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显著改善。因此,要提高区域内新要素的供给,一方面需要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使专业镇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优质资源的地区,另一方面还需构建宽容失败、崇尚创新和冒险的创业氛围与文化,鼓励企业的内创业行为,为新要素的注入提供机会。
其次,要健全市场法规体系,提高地区信用水平,通过降低企业间交易费用和诚信风险激励企业突破集群封闭的网络,增加外部资源的来源,增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集群内企业通过长期的合作,很容易形成一种稳定和封闭的基于信任的网络化交易,降低整个集群对外部知识、技术的获取能力和对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因此,突破这种网络的束缚,实现更大范围的跨界社会组织的交流与联系,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新的异质性信息,保证企业创新所需信息的有效性,从而为企业提供进入新机会的途径(蔡秀玲和林竞君,2005)[30]。
再次,要构建企业率先转型的诱发机制,核心在于对率先转型企业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其中,通过特定的补贴、奖励、提供额外的服务或通过政府性平台与企业合作等方式降低率先转型的探索成本和转型风险,都是值得尝试的激励方式。
最后,构建创业型政府,积极发挥政府在促进集群转型中的作用。目前,以政府力量主导形成的各种为专业镇服务的集约平台,包括专业化市场、各种市场化服务和公共服务多与专业镇企业当前所处的产业链阶段有关,而专业镇要实现整体转型和提升必然会对公共平台提出新的要求。但是在企业和专业镇转型之前,新平台的存在价值较难确认,在保守的政府决策倾向下,容易导致企业转型与平台探索的相互等待。因此,一个具有开拓、冒险精神和市场意识的创业型政府将是启动专业镇企业转型的关键力量。例如,为克服专业镇内技术创新的囚徒困境,有必要借助政府力量引入创新源,通过建立面向所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推广的公共机构、由政府主导建立技术开发公司等,用价格低廉的公共平台诱发企业应用新技术以实现转型突破,然后通过新技术的扩散带动其他企业转型。
六 基于“互联网+”理念的转型案例:揭阳军埔“淘宝村”
揭阳揭东区锡场镇军埔村,原本是一个“食品专业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军埔人把食品产业做得有声有色,经济总量迅速跃居锡场镇前列,2003年还曾被广东省科技厅评为“食品及食品机械”专业镇。但近年来,军埔的食品厂和很多传统产业一样面临着生存困局,产品档次低,销量下滑以及恶性竞争都导致了该地区食品行业的衰败。由于食品行业的没落,不少本应继承父业的年轻人将阵地转向电子商务,将淘宝店开的风生水起,实现了军埔村向“电商村”的转型。阿里巴巴2013年发布的监测显示,中国已经发现了14个成规模的“淘宝村”。广东揭阳揭东区锡场镇军埔村名列其中,这也是广东第一个有据可证的“电商村”。2013年的“双十一”当天,军埔村全天交易额就突破了1500万元。目前,该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投入到了电商中去,还吸引了700多位外地入村创业者,小小的村子里分布着大大小小1500多家网店。随着揭阳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扶持,未来的军埔村将不仅是一个淘宝村,还将被打造为“电子商务第一村”。
电子商务是互联网背景下一种新的商业形态,其扁平化程度较高,是打破物质和空间限制的重要商业现象。但是淘宝村的出现颠覆了人们的这一认识。虽然淘宝村有淘宝网站为了推广网上商业、扩大自己业务量的商业意图,但如果不存在空间经济规律,则即使刻意培养企业集群,也难以持久。在“互联网+”理念下,如果将互联网技术看做一种新型要素,那么基于该要素实现专业镇向新业务领域转型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在本案例中,以传统行业的外贸代工业务为主的专业镇是如何实现向电子商务领域的跨行业转型?以及为什么广东第一个电子商务村出现在揭阳军埔村?是经济规律的作用,还是偶然现象?这些问题都有待识别。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专业镇转型。
1. 互联网要素在专业镇企业转型中的作用机制
对外贸企业而言,代工型企业的两高一低人所共知。由于前期世界经济形势较好、需求旺盛,代工型企业可以借助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以及对资源与环境的透支获得较高的利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需求下滑,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抬升,代工出口的模式难以为继,若不开拓国内市场,企业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但是相比国际贸易,国内结算环境差、回款周期长给企业造成了资金成本高、风险大的商业困扰,所以外贸企业即使利润下降也不愿意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但是,电子商务的兴起使企业营商环境有了根本性改变。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的“互联网+”战略成为企业转型的有效途径:第一、电子商务可以重新建立全新的销售渠道,不必在乎传统渠道的区域性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某些经销商的控制。这种打破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新兴商务活动进行的,面对着新的商务知识,传统经销商在一定程度上居于劣势,由此为创业者进入市场、建立新型渠道、成为新型渠道商提供了条件;第二、扁平的电子商务网络方式大幅度降低了环节费用,包括经销商的库存、店面、利润分成等成本,形成了行业性整体竞争力。随着行业转型浪潮的进一步形成,如果企业能够以某些方式利用这一浪潮,则可以有效地推动企业转型;第三、结算环境大幅度降低了企业资金成本,对B2C而言,结算周期可以压缩到零,甚至可能是负值,因为一些订制,可以在没有生产之前就完成结算。这种结算环境相对外贸而言已经形成了比较优势,可以成为推动企业向内需满足转型的重要动力。第四、淘宝对网店的严格管理正在形成中国全新的诚信环境。淘宝网管以平台性企业的控制力,对网络电商设定一套针对诚信的管理程序,要求电商必须交纳诚信押金,也必须接受类似行业监管一样的诚信管理。当违反了诚信管制相关条例,他们可以通过罚款和取消交易资格等对网络电商进行惩罚,从而营造出有利于加工型企业转型发展的商业环境。因为品牌经营需要渠道商诚信,缺少诚信不可能获得品牌的忠诚度。如果代工企业向品牌企业转型,这种环境便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
由此而见,互联网要素的引入可为企业转型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降低转型的成本和风险。同时,由于我国互联网浪潮已经形成,电子商务经过20多年反复曲折的发展,相关产业配套环境与市场需求认知已经完成,使得电子商务具备了进入门槛较低、市场潜力巨大和经营灵活等特点,此时一家企业的成功吸引了众多模仿者跟进,从而促进电子商务在区域内的普及,由此带动整个专业镇的要素向新业务领域内转移和集聚。本案例的军埔村最初就是由在外打工积累了丰富电商经验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开办淘宝店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影响和带领下,村内淘宝店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形成了以电子商务为主要业务形式的新的企业集群。目前,村内企业已逐渐开始进行专业化分工,形成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业务模式,并出现了专门从事仓储分拣、货源与物流管理、视觉包装、专业培训、软件开发、快速采购等业务的专业服务商,集群的集聚效应不断凸显。综上所述,军埔村由“食品与食品机械”专业村向“淘宝村”的整体转型是由新要素的注入(领先创业者、互联网与电商技术及高速网络等)启动,并伴随着新生产函数的应用与扩散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跨行业转移实现专业镇转型的典型范例。
2. 军埔村实现跨行业转型的外在因素分析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企业转型是外生的,需要以存在可行的转型条件为前提。因此,电子商务企业在军埔村内高度集聚,而不是选择其他地区,意味着军埔村为这一新企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关键性要素,从而为专业镇的转型创造了可行条件。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了三个具体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自由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创业氛围。军埔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经商传统,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进入环境和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创业氛围。目前,该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从事创业活动,其中有近1/3的创业者不是本地人。同时,军埔村交通便利,生活设施市场化程度较高,没有进入障碍,为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提供了良好条件。第二个因素是大批年轻的高素质创业者群体。在军埔村从事电子商务的基本都是年龄不满30岁的年轻的“创二代”。他们不仅敢想敢干,不怕吃苦,还善于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创业前在外打工积累、培养的市场经验和商业意识也使得他们更具前瞻性和应对市场的能力。第三个因素是行业协会与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了规避企业集群内出现的价格战与过度竞争现象,村内的父辈创业者为年轻的创业者们指明了方向。他们通过签署联名倡议书,鼓励大家自创品牌,拒绝互相抄袭。之后,成立了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以行业协会的名义与所有相关协作者谈判,如与电信企业谈判,为村内企业提供了国内最快的网络速度和最大的宽带移动通讯环境;与物流企业谈判,形成了最低价格的物流服务体系和最便捷的物流环境。同时,村内还培植了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免费的网络培训机构。这些低成本或者免费的平台服务为大量创业者进入创造了条件,而同类的大量企业进入又形成一系列相关的共同需求,如网络美工、供应链管理、金融、包装等机构,使之很快进入斯密-杨格循环,创业者迅速向此地聚集,产生了电商集群现象。随着新要素供给越来越充足,价格越来越低廉,区域内的要素资源不断向新的业务领域转移,由此带动了传统企业的转型,也最终导致了专业镇整体的转型。如今,军埔村正在打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电商村”的道路上前进。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与本案例的具体情况,军埔村的转型过程和内在机制可归纳如下图3所示。

图3 军埔村的转型过程与转型机制示意图
七 结 论
通过上述理论与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为企业转型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构建企业转型模型,本文将企业转型界定为新型高质量要素的引入和企业新的生产函数的构建,体现了“互联网+”理念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并由此带来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商业逻辑和组织战略等的本质性变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跳跃性和高风险性。企业的转型决策取决于转型前后企业竞争优势提升带来的转型收益,该收益受新型要素的种类与投入数量、新型要素与一般要素的价格及相对变化及企业“自学习”能力的影响。
第二,集群内企业的转型是专业镇转型的微观基础。企业通过引入新型要素实现转型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引入新型要素和构建新的生产函数,实现企业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二是将自身的优势资源与新型要素相融合,剥离低效率业务,在缩小业务种类的同时扩大高效率业务的规模边界,获取纵向分工的规模经济;三是脱离原行业,进入全新的业务领域。企业不同的转型方式会带来专业镇不同的转型方向。
第三,企业转型面临的一般性障碍和集群环境内生的转型障碍决定了企业转型的外生性。其中,一般性障碍来源于企业对旧知识体系的更新和替代以及新型要素的获取与进入。集群环境的内生障碍源于集群演进过程中创业精神的衰落和“自稔性”风险带来的新型要素进入机会的不足。以上障碍的存在导致企业不可能独立创造主动转型的条件,即企业转型具有外生性和被动性。其中,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企业竞争优势下降和对企业生存的威胁是企业转型的充分条件,外部是否具备转型条件构成企业做出转型决策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企业的“自学习”能力则是转型得以成功的保证。
第四,对专业镇而言,企业转型受集群环境制约。如果集群内不存在企业转型可行的外部条件,就会出现企业转型与专业镇转型相互等待的状况,同时,率先转型的外部性也有可能导致集群陷入转型的“囚徒困境”。因此,专业镇内企业转型的障碍具有内生性,而企业转型决策具有外生性,这其中存在市场失效机制。要弥补这种失效,需要发挥非市场的力量,通过创造可行的转型条件与激励企业率先转型的诱发机制,以推动企业率先转型进而实现专业镇的整体转型。
第五,对企业自身的一般性障碍而言,排除传统体系的干扰是转型的核心,内创业理论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思路。集群内生的转型障碍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破解:一是根据专业镇的转型目标,增加区域内新要素的种类和数量,改变要素市场的供给结构,促使企业引入新要素,实现新的要素配置方式;二是提升企业集群整体的能力层次,形成集群的异质性能力;三是重构专业镇的发展模式,摆脱传统依赖低成本数量要素投入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生产方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定位;四是构建企业率先转型的诱发机制。
[1] 王珺. 企业簇群的创新过程研究[J]. 管理世界, 2002, (10): 102-110.
[2] 郑海涛, 周海涛. 广东专业镇集群品牌发展战略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54-58.
[3] 李新春. 专业镇与企业创新网络[J]. 广东社会科学, 2000, (6): 29-33.
[4] Storper, M.. The Transition to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in Industry: External Economi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rossing of Industrial Divides[J].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 1989, (13): 273-305.
[5] 陈介玄. 协力网络与生活结构——台湾中小企业的社会经济分析[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1994.
[6] 吴思华. 科技体制与产业发展[M]. 蔡敦浩主编. 高雄: 文图书出版社, 1995: 197-231.
[7] Krugman, P..GeographyandTrad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8] 冯德显. 产业集群及其对河南经济发展影响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3, (3): 21-25.
[9] Sengenberger, W., Pyke, F.. Small Firm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Local Economic Regener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Issues[J].LabourandSociety, 1991, (16): 1-25.
[10] 王珺. 产业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广东专业镇经济的理论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1): 89-95.
[11] Ahokangas, P., Hyry, M., Räsänen, P.. Small Technology-based Firms in Fast-growing Regional Cluster[J].NewEnglandJournalofEntrepreneurship, 1999, (12): 19-26.
[12] Michael E. Porter.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BusinessReview, 1998, 76(6): 77-89.
[13] Capello, R.. Spatial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High-technology Milieux: Learning Versus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es[J].RegionalStudies, 1999, 33(4): 353-365.
[14] 魏后凯. 对产业集群与竞争力关系的考察[J]. 经济管理, 2003, (6): 4-11.
[15] Markusen, A..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J].EconomicGeography, 1996, 72 (3): 293-313.
[16] De Vol, Ross. Talents are Attracted by the Quality of Place: Connected Clusters Stick[J].BrainHeartMargzine, 2001, Mar.
[17] 吴晓波, 耿帅. 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分析[J]. 经济地理, 2003, 11(6): 726-730.
[18] Adams, J. D..TransformingWork[M]. Alexandria: Miles Review Press, 1984: 135-138.
[19] 吴家曦, 李华燊. 浙江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调查报告[J]. 管理世界, 2009, (8): 1-6.
[20] 王吉发, 冯晋, 李汉铃. 企业转型的内涵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06, (2): 153-157.
[21] 齐玮娜, 张耀辉. 领先还是模仿:基于商业知识溢出的创业决策机制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 35(7): 128-137.
[22] Oded Galor, Stelios Michalopoulos. Evolution and the Growth Process: Natural Sele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raits[J].JournalofEconomicTheory, 2012, 147(2): 759-780.
[23] 黄文静, 赵江明. 企业家心智模式与企业集群成长的关联机理[J]. 经济论坛, 2005, (4): 37-39.
[24] Keeble, D., Wilkinson, F..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luster of High Technology SMEs in Europe[J].RegionalStudies, 1999, 33(4): 295-303.
[25] Miller, D.. The Correlat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ree Types of Firms[J].ManagementScience, 1983, 29(7): 770-791.
[26] Lumpkin, G. T., Dess, G. G.. Clarify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 Construct and Linking it to Performance[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1996, 21: 135.
[27] Morris, Kuratko.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Within Organization[J].HarcourtCollegePublishers, 2002.
[28] 张海梅. 广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与出路[J]. 岭南学刊, 2009, (5): 115-118.
[29] 刘城. 广东专业镇向创新型产业集群转型的模式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4, (16): 88-93.
[30] 蔡秀玲, 林竞君. 基于网络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J]. 经济地理, 2005, (2): 281-284.
[引用方式]张耀辉,齐玮娜.互联网背景下专业镇企业的转型机制、障碍及破解研究——兼对揭阳军埔“淘宝村”跨行业转型案例分析[J].产经评论,2015,6(4):80-96.
Mechanism, Obstacles and Crack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in Specialized Tow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Taking the Cross-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obao Village” in Jieyang as an Example
ZHANG Yao-hui QI We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echanism, obstacles and the crack methods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in specialized town through the theory and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era background of China’s new normal economic state and internet+.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essence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is to introduce new high quality elements and construct new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decision is contingent on the transformation income and it is a comprehensive judgment between the type, quantity and price of the new factors and gener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then by inference,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f specialized town is exogenous; secondly, because of the decline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the supply insufficiency of new elements in enterprise cluster and because the enterprise is difficult to form the new elements independedly, the barriers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re endogenous. So, there is a kind of market failure during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ower outside marke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trapreneurship is a sufficient way to break the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barriers and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new elem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luster endogenous barriers can be broken by the means of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new elements, enhancing the cluster overall ability, reconstruct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specialized town and designing the induced mechanism of leading transformation.
specialized town;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self-learning ability; intrapreneurship; Internet+
2015-04-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项目编号:71333007,主持人:胡军);广东省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专项“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建设发展与管理研究”(项目编号:2012B091400053,主持人:张耀辉)。
张耀辉,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创新与创业、产业转型;齐玮娜,经济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创业管理。通讯作者:齐玮娜。
F207
A
1674-8298(2015)04-0080 -17
[责任编辑:陈 林]
10.14007/j.cnki.cjpl.2015.0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