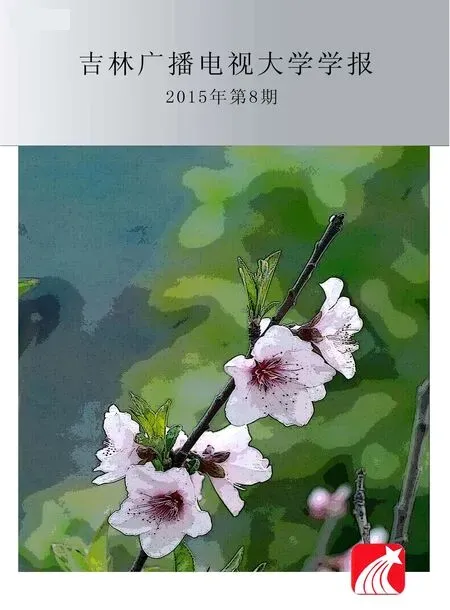浅论《红楼梦》的红颜薄命观——作为被发现的女性的悲剧
刘素敏 王 健
(长春光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1;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鲁迅先生称《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情世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①明斋主人在赞赏《红楼梦》时说:“小说家结构,大底由悲而欢,由离而合,是书则由欢而悲,由合而离,遂觉壁垒一新。”②其实,他们说的都没错,《红楼梦》在题材、主题及结构上都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但《红楼梦》在观念上的突破更不容忽视。正是由于观念上的突破,使《红楼梦》的立意隽永,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使《红楼梦》成了永远被人言说的《红楼梦》。
在观念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从传统的“红颜祸水”观中突破,形成意蕴丰富的“红颜薄命”的悲剧观,构成了全新的悲剧性。脂砚斋称《红楼梦》是“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仅此一语即充分的表达除了《红楼梦》的悲剧性。然而,《红楼梦》的悲剧性是特定的悲剧性,是作为被发现的女性的悲剧性。
一、从“红颜祸水”到“红颜薄命”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中,有很深的“红颜祸水”的观念,这在那个完全的男性中心社会是不足为奇的。倒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现出来的意蕴丰富的“红颜薄命”悲剧观不能不令人拍案称奇。这事实上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当时的社会规范,是冒着不见容于社会的巨大危险的。
论是在民间传说中,历史故事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红颜祸水”观念的比比皆是。妲己断送了商朝,褒姒葬送了幽王天下,骊姬乱晋,西施败吴,杨贵妃搅乱了盛唐的大好局面,……在传统的观念中,“祸水”陪伴着昏君,而祸国殃民的罪责自然是在前者。这事实上都是男性视野中的“祸水论”,他们只是凭着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力,对这些柔顺的女性横加鞭挞,把她们看成是妖艳、诱惑、罪恶的魔鬼,把女性妖魔化。殊不知,他们只是在男性单一的声音中独白,决不让女性有任何辩白的机会。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讥讽的:“中国的男人们,大抵是可以成为圣贤的,可惜都被女人搞坏了。”
虽然在《红楼梦》之前的文学中也曾经有过“红颜薄命”的说法,但那只不过是高高在上的男性虚伪地为作为第二性的女性,作为他们附庸的女性施舍一些廉价的同情,与《红楼梦》中对女性的新发现、女性的美的由衷赞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便如此,就连这种同情的施舍的声音也是微乎其微的。在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的文本中,我们能发现大量的污蔑女性的观念。元稹在《莺莺传》中虽然给了莺莺一些同情,但在主观上又骂莺莺是“妖孽”,“不妖其身,必妖其人。”在《水浒传》中,虽然出现了三名女性,但却被冠以“母大虫”、“一丈青”、“母夜叉”等诨名。而宋江在劝好色的黄英时所说的话更能代表那个男性社会的声音。宋江称“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好生惹人耻笑。”逼上梁山的那些英雄好汉中,又有很多是遭了女性的“害”:阎婆惜断送了宋江,潘巧云的通奸逼走了石秀和杨雄,卢俊义也是因为妻子的通奸,另外诸如武松、林冲等人也都是因为女性的牵连……书中描写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是“善人”。这样的文本中透露出的一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女人,尤其是那些不遵守当时社会规范的女性是和可怕的,她们是男性社会的“祸水”。即使连《金瓶梅》这样在文学史上有进步意义的优秀人情小说也难以突破“女性是泼不掉的祸水”的观念。
唯独《红楼梦》以大开大阖的气势,纵横肆虐的笔调,隽永的抒情境界的塑造,突破了“红颜祸水”的陈腐观念。曹雪芹寄情于“红颜薄命”,情专于女子,给予女子以无限的爱和关怀,批判了传统的观念。明斋主人称黛玉、宝钗“要之皆属红颜薄命耳。”③曹雪芹更是借黛玉之口,在第64回黛玉“悲题五美吟”中,发出了“红颜命薄古今同”的感叹。
二、被新发现的女性
《红楼梦》中群芳图的塑造,逈异与此前的小说所塑造的女性人物,这主要表现为女性是作为被新发现的独立的人物出现的。借用明斋主人的一句话说,《红楼梦》“全部一百二十回书,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④这“真、新、文”三字都通过女性的被发现表现了出来。《红楼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世界,而这全新的女性世界才是真实的女性世界,是超越了男性视野的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带有个性解放痕迹的世界。
《红楼梦》一书大体谈“情”,在它之前谈“情”之作已有《西厢记》、《牡丹亭》等优秀作品,但所描述女子无非是那一二人而已,像《红楼梦》这样出现众多女性还是第一次。“总核书中人物,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已。”⑤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女性从来都只是一股从属的力量,这在古代中国的抒情诗词中也能找到根据。古代中国虽然号称抒情的国度,但友谊与酒充斥了大量的诗作,即便像柳永那样极少数讴歌女性的诗人在当时也受人嘲弄。“中国的抒情诗极少赞美对女人的爱情,而讴歌男人之间的友情。”单就《红楼梦》中众多女性形象的出现而论,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突破——这标志着女性已经作为被正视的群体在文学中出现了。虽然小说和抒情诗不可一概而论,但《红楼梦》与抒情诗所创造的境界是一样的,《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的抒情境界的继承⑥。
而且,《红楼梦》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谈“情”文学。书中对女性的描写是建立在对女性的人格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的,而且在谈“情”的外壳上罩上了一件神话架构的外衣,使“情”字有了更深的蕴涵,使全书有了寓言的深意。全书对黛玉和晴雯等叛逆女性形象的讴歌,对班姑之属的旧价值拥护者宝钗的批判,分明表现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宝黛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的,有别于那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曹雪芹在开篇及借贾母之口都曾经批判了“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的才子佳人等书。女性有了自己的个性,有了自己的价值追求,这不能不说是新出现的新女性,多少带有一些个性解放的味道。
三、大观园的悲剧: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的冲突
《红楼梦》创造了两个对立的世界,大观园及现实世界,而大观园是女性的世界,现实世界则暗喻着男性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事实上也是曹雪芹的抒情的自我之境与现实世界间的冲突。
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说出了女儿是清灵秀美,男儿则污浊不堪的话,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寄予在了大观园的女性身上,而对男性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明确提出《红楼梦》是要使闺阁昭传,是要为女儿立传。而这又通过一段怀金悼玉的故事来加以敷演。
书中描写的情大抵是苦情,是悲情。而这都导源于现实的男性世界对大观园的不断戕害。大观园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之境,代表着女儿之心,它是容不得哪怕是一丁点儿污浊的,当它与外界的现实一接触,它就免不了分崩离析的厄运。在整个社会中,只有大观园能给那些女儿们提供土壤,尽情呼吸的空气。这事实上也就是曹雪芹的审美理想不能见容与当时社会,自我抒情之境在现实的世界中被粉碎的象征。曹雪芹通过大观园的人物寓意化了整个人生观。
女儿们的“红颜薄命”正是在这种充满了寓意性的行文中得到了深化,形成了曹雪芹崭新的悲剧观。这种悲剧观深深的烙上了曹雪芹的人生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又是和大观园的女儿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死亡的意向得到了表现。《红楼梦》与传统文学作品很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红楼梦》描绘了众多女性的悲惨死亡。可卿之死、金钏之死、晴雯之死、尤三姐之死、司棋之死、二姐之死、黛玉之死、迎春之死、贾母之死、鸳鸯之死、凤姐之死、妙玉之死……这些死亡景象的描绘,一方面彰现了“红颜薄命”,另一面则透露了曹雪芹的幻灭。人至于死,无不一也!
开篇中“太虚幻境”中对大观园中女性命运的暗示,使全书深深印上了宿命的烙印。太虚幻境是另一个女儿之境、女儿之心,然而却根本就不在现实中存在。《红楼梦》中的诸多人物都被置于了一个表现理想关系的奇幻空间中,而这理想关系注定将归于毁灭⑦。曹雪芹在给出了一理想的生命境界的同时,却处处在暗示着这生命境界的破损,但他却仍愿依附于这境界,同时又真诚地表达了希望的破灭。
注 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04.
②③④⑤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上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1,18,17,19.
⑥埃利埃泽?梅勒坦斯基原作,让?贝西埃审定.社会、文化与文学史实[A].昂热诺等著,史忠义,田庆生译.问题与观点:20 世纪文学理论综论[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25.
⑦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附录,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