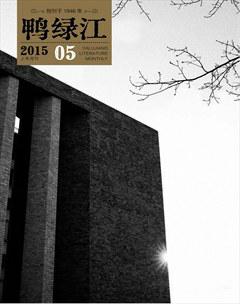废墟上的旧时光
万一波
遥远的祺州
远远看,坐在土岗上的那个黑衣人活像一只蹲着的鹰。
羊群,在耕作前的玉米地里吃草,牧羊人坐在土冈上眯缝着眼睛。西南方向刮来暮春的风,经过一座辽塔,吹向野地,便有了旷古之感。
风吹千年。这座古塔虽已修缮,也还遗存着旧时面孔。坐佛、协侍、飞天等绝非今人所为,漶漫是漶漫了些,但依然达意甚至传神。
放羊的老汉眯缝着眼,一动不动,像一个哲人陷落思索状态。而村民讲,此老汉并非哲人,却是一个嘚瑟的主儿。去年春上,老汉在犁地时,翻捡出一坛古币,抱得家来,逢人便拿出把玩。后有村民家里造屋上梁,向老汉求要几枚铜钱镇宅,遭老汉拒绝,遂起妒意,将此事报告当地派出所。警察来了把老汉和那罐子铜钱一起带走,铜钱被扣下没收,老汉也被扣下蹲了十五天拘留。
村民们翻地翻出铜钱是常有的事。有文物学家说,这些铜钱来自不同朝代,有唐代“开元通宝”,北宋“黄宋通宝”“景德通宝”“崇宁通宝”,金代“大定通宝”等等,有时还翻出过铁铡刀、镰刀、石臼、石磨等生活用具,至于遍地的陶瓷残片更是不足为奇。这是一块上好的玉米地,当地人称“佛眼珠”,旱年不干,涝年无灾,旱涝保收决无亏欠。
老汉坐在最北面的土冈,他的东面、西面、南面都有隆起的土冈环卫。而中间的这块地就是所谓的“佛眼珠”,大约有一百亩。奇怪的是辽宁中部土壤多为黄壤土,而这块地却是黑色的熟土,尽管遍布瓦砾残片,但不影响耕作和收成。
这土冈围拢着的就是祺州——一座耶律阿保机时期的辽代古城。
走在古城东西向的官道上,我的思绪辽远起来,自己俨然成为一个一千三多年前的市井人物。遭掠时的惊恐不定,后来的安身立命,繁衍、兵燹,盛大直至消亡一下子涌上心来。我断定,这些黑土就是一个个朝代的生活印证,也是一次巨大的火焰熄灭后的残存。
祺州城是一座牢笼之城。有史为证。祺州城建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天赞、天显年间,即公元922年至926年。当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战掳掠,俘获了大批中原、渤海国百姓,“投下州城”,祺州古城便是这样一座城池。
在儿时的连环画中,我见过契丹人。那些留着特殊发髻,眼睛细长的人,坐在马上,手持狼牙棒,个个彪悍无比。当时,我视他们为魔怪,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不想,我脚下的这块地方就是他们当年驰骋并享有荣誉的地方。此刻,祺州城内的刺史、县令、百姓仿佛刚从我的身边经过,我被一些牛羊包围着,酒肆的大锅正在冒着热气。
在这个地方待久了,与久远的际会感越来越强烈。现在看来,中原也好,契丹也罢,还有后来的金、元、清虽种族不同,却本属一脉,大可不必兵戈相见,杀伐无期。看看祺州东门外那条逶迤的辽河,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了。如果祺州古城是一只装满故事的瓜,辽河就是脐带。那么,那些远古的和现在的异族人等,便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共同拥有一个不老的母亲!
城是辽代的,塔也是辽代的。这座高十三丈的砖塔,陡立高冈,千百年来守卫这座城池,从繁盛到衰亡,矢志不渝。因此,距离古城仅仅五十米的这个村庄,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小塔村。
在康平县辽河西岸,一座古塔,一座古城,一个村庄。
圣经寺上空的风
1841年盛夏,养息牧河水静静地流淌,绿草茵茵的两岸,羊群散落悠闲的时光。
远处,八山静耸,环卫着一个小小村庄。村庄的北边,有一名叫龟山的小山,枝茂林密,鸟雀欢洽,湿润的蝉鸣扯出正午的懒散。
龟山之上,旗杆高挑风旗,圣经寺高耸,香火缭绕,香客络绎。五百多喇嘛齐声诵经,南科尔沁天辽地广。
村庄懒散地卧着,一如一百七十多年前的样子。当下,彰武县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村也在正午里懒散着。
一排瓦舍前,两只石狮孤独端坐,刻有铭文的底座已经半埋进流沙,想来这就是龟山了。龟山已经沦落为村子里的一道高冈,而石狮也失去了当年的威武。远远看只是两块石头,不是天成,也没有精工,更无神韵,怎么看都像两只分开很远的眼珠,平常而呆滞。
两座石狮的背后,应该是山门,却被一排建于六七十年代的瓦舍替代。穿过瓦舍之间的通道,但见一块空地托举着孑立的大殿,一种孤寂没落的感觉瞬间抓住了我。
在脑海里翻阅一本书,努力还原圣经寺原貌。山门内的转经亭和关帝庙,正殿后的大佛殿和白塔、左右斋房、喇嘛经舍等如今均不见。而藏式砖石结构、厚墙小窗的三层楼阁式大殿,却能依稀辨别木作的精美和新颖。那些有关转生、天文和传奇故事的壁画虽已漫漶,但形象传神,色彩艳丽。驻足期间仍能听到低沉的号角,感受到喇嘛加持的目光和来自佛国的暗示以及香客们的怡然自足。
沿着当年转经的路线,在没膝荒草的纠葛中徘徊,天色向晚。黄昏的光线穿过我的身影,打在墙体上显得轮廓清晰。而此时,我突然有一种被怀抱的感觉,那些来自于遥远的抚摸,让我在得到慰藉的同时,又生出些许孤单。
而此时风动。大殿上那些格子窗开始过滤风声,丝丝拉拉,嘈嘈切切,一阵紧似一阵。我知道山雨欲来。但我并不急于走开,站在大殿前的平台上,目光游移在两座石狮中间,那里除了有大朵的黑云急匆匆走过,还似乎该有些什么出现?是的,我等待的是一根旗杆,一根石质的旗杆以及它上面的一面风旗,就在此刻,我多么希望听到它荡出的猎猎之音!
此刻,只有风。
时间能够漶漫一切,而人为的灾难泯灭的将不止是良知。一场浩劫使活着的喇嘛作鸟兽散,脱胎换骨;供着的喇嘛也是庙堂被掀,臂断肢残。我无意为这些逝去的喇嘛喊冤,因为无论怎么说他们的存在都是一种形式,只叹息动乱之后的精神虚空和由此派生出的大把肆意和几近恶毒的无知。
好在圣经寺还在,并被尽量保护下来。好在烙刻在我们血脉里的传统还在,并被一些声音不间断地唤醒着。
风如旗。
逝去的帆影
如今,很难见到一条船了。水无舟,则失生动;舟无帆,则显呆板。辽河里因为没有船和帆,自然缺少许多精彩。
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小船,正在用即将风化的形容,追忆一条大河的莽莽苍苍,一座码头帆樯林立的过往。
通江口。一座水陆码头的旧址。
县志办老王从齐腰深的蒿草中翻现一坨发黄的夯土,告诉我这里就是原来的码头。而钩沉历史不能仅凭古迹,还需有典籍佐证,好在事先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关于这座码头,已经知道了许多。
“水路交衡,五方杂处,为北路商务总汇之区”,“自通江口达于营口,帆樯如织,擅水利之便”,“殆舳舻相接,帆影覆河之观”,“而往来河上者,尚艨艟如卿,大有掩江之势”,这是20世纪初徐曦在《东三省纪略》和日人小越平隆在《满洲旅行记》里的描绘。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当年也考察过辽河,他的说法是,通江口“共有商铺一百七十四家,其营业以粮为最大,栈主皆山西巨富……昔年积粮多至百余万石。”
站在那块夯土台子上,我的思绪被绊住,仿佛置身于帆影叠嶂、人潮熙攘的历史岸边,心中搏动挑夫沉郁的步子,血脉激荡响亮的号音。
因了一条大河,南方的百货,营口的海盐得以北运;东北山珍、木材、粮食每每集中于此,装船南下,经由牛庄(营口)散布全国。这条汩汩流淌的大动脉,不仅交流了物产,也造就了大大小小的城镇,通江口便是其中之一。
在现代文明的烘托下,大街显出今日繁华。若不经意,你会觉得这个小镇与中国北方任何一个小镇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当你细细打量,就会发现历史存留的些许密码,仍在讲述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
一堵残墙、一座旧屋就是一个标志。老王告诉我,光绪年间,由各地汇集到通江口的商船每年两万余只,自然形成粮谷、货物聚散地。各地资本云集而来,钱庄有官银号,粮栈兼大商业;有山西乔家的“广源达”“公源”,河北白家的“泉胜涌”,河南张家的“德兴广”等。小商小贩一百多家,专门推销大商号的杂货。许多小业主经营日常需用的小作坊也是生意兴隆。街面上旅馆、饭店、书馆、戏院、茶社、浴池、大车店等应有尽有,还有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以及各国商社和领事馆,通江口一度成为租界地。
心中杂陈未经细品,老王带我走进一座院落。这是四间普通民房,进得柴门,院落里一片青葱的玉米地,在老王的吆喝下,女主人顶着一脑袋蜘蛛网出门相迎。转过玉米地,但见一溜平房,平顶翘檐,细木门窗,颇具山西民居风格。房屋举架不高,七月的玉米就能轻松掩住,而开间大,我步量了一下,足足有七米,这样的房屋适合延引接洽和加工囤积,一看就不是普通民居。
这里就是乔家大院旧商号的遗址。
房屋破落,成了房主堆杂物的场所。透过暗淡的光线,依然可见当年油坊的影子,几台不完整的榨油机萎在墙角,地面上装机底盘还在,螺丝尚可扭动。女主人告诉我们,房子是生产队分的,丈夫当初是开油坊的,那年闪了腰,就干不了重活了。
望着老屋开裂的墙缝和屋顶日渐繁茂的青草,我竟然说不出一句话。逝去的生动已经完全逝去,而流在人们心底的大河依旧澎湃,并且正在以一种别样的姿态,高高扬起风帆。
柳堤渔事
法库县三面船。
一艘渡船切断了河水。河水仿佛止息,却有一些物事涌趸而来。
从村子到河边也就三四里,一条窄窄的草路。玉米拔节的季节,蜻蜓粘在抬杆梢随大哥一抖一抖地走,大哥一肩挎网,打伞样将抬网倒举在头顶,既为不伤庄稼,也怕刮漏网线;另一肩扛着根胳膊粗细且丈把长的抬杆走在前面。我则紧赶慢撵跟在身后。
盛夏的朝阳透过网眼斜打在大哥后背,极像五花大绑。而步履轻盈,口哨不绝,啁啾如山雀,婉转似百灵,引得鸟雀齐唱。
玉米拔节了,家家户户都挂起了锄头,田间静寂得绝无人影,像似一幅熏风铺展的水墨,安宁而美好。
河堤被垂柳浸洇着,是为柳堤。柳堤被蝉声缠绕着,那丝丝拉拉悠长而尖锐的鸣叫,把时光扯得很远,把天地扯得很远。碧水蓝天一窝柳,便是柳堤的写照了。
早起的都是捕鱼的人。辽河本无鱼汛,从第一股桃花水打出“开河鱼”到“三九”天凿冰取鱼,一年四季都是捕鱼的好时节。而盛夏尤为繁盛,河水里生机勃勃,鲤鱼、鲶鱼、白漂子、嘎鱼应有尽有,毛腿的螃蟹、几近透明的白虾更是凑趣似的热闹。
临河而居,靠水吃水,每家都有一个渔把式。或用旋网打或用懒钩钓,这是两种常见的、真正的打鱼方式。旋网者往往立定船头,根据经验先选择好鱼窝子,然后将一挂网抛成一轮满月,每一个网眼都张开到最大限度,以最大面积牢牢地扣在河水里。使用旋网打上来的鱼多是大鱼,有一年辽河涨水,隔壁秋生的父亲就打上来一条一米多长的“大怀子”,鱼头比他家老七(婴儿)的脑袋还大,后来听说这条鱼有二十八斤。我仔细端详过这条“大怀子”,很像鲇鱼,个头比鲇鱼大,就连须子也比鲇鱼多出两根。
懒钩也是能钓到大鱼的。所谓“懒”,就是省劲儿。将鱼钩拴在一米多长的柳树棍上,头天晚上沿河边插上一排,你就可以回家睡觉了,早上来起钩,线拽上来,多是一两斤重的大鱼,而且扑腾难抓。这样的鱼多数人家是舍不得吃的,往往用柳条笼悬卧水里,待钩子全起出,收拢起来,拿到市场沽卖,换作零花。
抬网是半大孩子的玩意儿。将两根竹条交叉弯起,四脚绑上一张网,网底扔进些窝头、豆饼或者土豆做诱饵,下到浅一点的河底等着便是。用抬网讲究准确把握时间,网下得久了,诱饵就喂了鱼,时间短了也不行,注定收获寥寥。用抬杆抬网时需使猛劲儿,要一下子就提上来,否则鱼就在迟疑的缝隙间随水溢出,所以太小的孩子是做不来的。我尤喜抬网这种捕鱼方式,因为它不仅能捕得上来各种鱼,也能捕到螃蟹和虾米,可谓花样繁多。螃蟹糊上河泥拢火烧透,其香入脾,其味入心。至于河虾,用做干炒或者和着小鱼做成辣椒焖子,更是一道上好的佐菜。
孩提时,过年前经常到辽河里凿冰挑水,嘴闲难耐便捞起一块冰,咯嘣咯嘣嚼,听老人讲这样可以去火;挑回来的水专门用来做豆腐、蒸豆包、煮肉、泡山里红皮,比井水要软,要好得多。
废墟上的旧时光
辽河在满都户拐了一道弯。古城子村像一颗痣,深嵌在母亲的臂弯。
凡是叫古城的地方,必有隔世的繁华。这是今人的附会,更是一种怀恋。历史不仅是写在卷册上的,也能写进人们的记忆,甚至演变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坐标。
辽中县满都户镇古城子村,就是这样一个村庄。而今,它仍守着一个几百年不变的姿势,依偎辽河,抱臂而眠。
相对于过去的繁华,眼下的村子显得寂静许多。时为晚秋,墙角处几个老汉在打盹儿,田野里三两农妇在拾秋。村子中央一块空旷地带,一排房屋即倒,院场上荒草萋萋,砖头瓦块零散地冷卧草丛。一只瞎了眼断了耳并且瘸了腿的石狮在疗伤,一块庙堂柱子的底座高擎着虚空。
从前,这里是一座小学校,再从前,这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寺院——兴隆寺。
兴隆寺建于何时,没有统一的说法。《辽中县志》上说:古城子兴隆寺建于1378年(洪武十一年)8月,但找不到任何依据;也有人根据鼓楼雕漆匾额上书有“天元”年号字样,说兴隆寺建于北元,也非确切。然不管是建于明代还是元后,这座寺庙都当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我在六百多年前留下的废墟上徜徉,翻检昨日时光留下的点滴鳞片,而历史像一条鱼仍在记忆深处的池塘里鲜活地游动。
在过往的时光里,兴隆寺的翘檐高耸着应有的尊严,一道巨大的石质影壁隔开梵俗两世,释迦摩尼高坐殿堂,韦陀立目威震四方。其晨钟催开生命之花,其暮鼓远播安康福音。庙产土地庇护众生,私塾经文兼济天下。兴隆寺大智大觉,自然是香客络绎,香火不绝。
村子里来了不速之客,那些趁着秋阳打瞌睡的老人明显活跃起来。其中一位被称作先生的老汉,一件灰得发白了的中山装胸兜里别着一管老式钢笔,穿着打扮还留有旧时光的影子。老汉只剩两颗门牙,但依然健谈。他告诉我,兴隆寺旧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击鼓鸣钟,告示附近乡民,向佛祖敬香叩首祭拜。遇有日食、月食等天象,寺内钟鼓齐鸣,以求消除灾难,拯救世人。每逢春节、灯节、端午和中秋都要开放山门,迎接香客,佛堂灯火通明,香烟缭绕。晚上燃放烟花,组织乡民提灯游行,热闹非凡。旧历四月十八日庙会,是寺院纪念佛祖诞生的日子,也是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深受广大乡民欢迎的时刻。十五早晨开启山门,十八最高潮,十九下午结束。四天半时间里,香客游人忙碌奔波于殿堂之间,或烧香拜叩,许愿施舍,或求神问卜,祈求消灾。
兴隆寺庙会更是一个大杂烩。各种艺人在山门外广场搭起许多临时小舞台表演节目,有耍猴、练功的,演杂耍、唱二人转的。逛庙的游人,在烧香拜佛之余,便集聚在这里观看演出,场内外人头攒动,欢声四起。各地商家也会在大庙周围,早早抢占好位子,经营各种吃、穿、用商品,既满足了游人消费需求,又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每年庙会参观人数上万,多数来自附近县乡,也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北一带的远方香客和游人。每届此时,古城子及周边村屯的农家,都有投亲靠友的,每个农家小院都变成了临时客栈。
我无意于复原兴隆寺的庄严和古城子的繁华,而是试图重构一种秩序。古城子各色人等杂处,却匪事不生,盗贼不往,伦理相携,路不拾遗。我想,这一切大概都与兴隆寺的晨钟暮鼓有关。
此刻,站在今天物质文明的光芒下,我的心中升起一种巨大的虚空。据悉,有关部门正在着手重建兴隆寺,以现在的建筑材料和工艺、机械,恢复一座寺庙是件很容易的事,可这种重建,能够恢复人们内心失却已久的东西吗?
头枕夕阳,我在古城子的旧时光中,缱绻着……
流动的河水,驿动的城
他抬手指给我看时,手臂伸向冬月。
凛冽的寒风中,牧羊人的鞭杆显得干、脆。即便摩挲日久,鞭杆已经变得通体油亮,也阻挡不了我一碰即碎的直观想象。
我和牧羊人并肩站在山冈上,脚下是干雪掩映着的写意辽河。这条从昌图福德店逶迤南下的大河,一路经过康平、开原、铁岭,到达这里时,变得宽阔、浩渺。
冰面上有孩童在打尜。他们全然不知,他们甩动鞭梢的每一个空响,都是抽在历史脸颊上的硬伤。就在他们身旁,这个叫作石佛的村庄,大辽时代的一座城池正在酣睡,并被反复抽醒,衣衫单薄地在呼号寒风中不停地打着寒噤。
牧羊人指给我看的,正是古双州城遗址。辽代双州是东京道属下的一个节镇州。《辽史》载:“双州,保安军,下,节度。”也就是说双州与祺州(康平)、同州(开原)、银州(铁岭)同属辽河沿岸重要的军事节度部门。这些城池里的军人,有的驻守码头渡口,有的镇节交通桥梁,而双州则是扼守水路要冲的屯兵之所。山川形要而有兵,有了兵便有了女人和孩子,也便有了烟火和城池。沿着古代兵制设置的路线图,我分明看到了一条大河的流向,在她沉稳地流经里,城镇和人民就是她收获的一枚枚果实。
辽河是生生不息流动着的营养,而城池的果子总有衰败的一天。眼下,这个叫作双州的古城,几段土棱,一把空旷,除了漶漫的身形犹可见及,所有的辉煌恐怕只能从考古学家测量的数字中揣摩了。历史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它可以冲刷和淹没一切事物。比如江山社稷、皇冠仪仗,比如交通要道、城池险隘等。在历史的河流里,一切都是过往,一切都是瞬间的占有。从这种意义上讲,双州城只不过是一个过客匆匆歇息的驿站,时过境迁便衰败得没了模样。就像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辽灭了宋,金灭了辽,沮丧也好,狂欢也罢,都成过眼烟云。
而故事不灭,总会像河流一样不停地流动。石佛村的孩子们都会唱一首歌谣:“石佛村,全是宝,青白瓷片满地跑,苞米地里种大辽。”一千多年前,耶律阿保机征服渤海国,改国号“东丹”,并分封辽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这个把大辽皇位禅让给弟弟的人,从渤海国故地将兵士、百姓、囚徒一股脑迁移到了这里,偏安一隅,大兴土木,建成了双州城,遂而屯田奖农,使这里终成“辽之农谷”,稼穑繁茂,人丁兴旺。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是唯一沉淀下来的,并且持续讲述着故事。耶律倍跟随大辽走远了,大清的儿孙们踏着金人的足迹又来到这里。清时,世居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锡伯族人也经历了一场迁徙,他们被清政府南迁到盛京(沈阳)巩固防务,尔后于18世纪中叶,又迁往新疆,在伊犁河谷屯田戍边。这个河流一样的民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迁徙,这段故事与土尔扈特人东归一样,悲壮得令世人震惊扼腕。
如今坐落在双州故地的石佛村,就是锡伯族西迁征程的起点。
村子东头的锡伯族民俗博物馆像一部打开的书,每天都在不停地讲述这段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其间,当然也包含着故土难离的深深眷恋和牵肠挂肚的动人篇章。
古双州在马蹄嘚嘚声中远逝,但留在大地上的记忆还在。锡伯族的祖先鲜卑人早已绝迹,连同他们的图腾也归于黑夜,而他们的后人仍在这里麇集有三万之众。契丹也好,鲜卑也好,如今仍在一条大河里脉动,在同一座城池里,说着同一种方言,吟唱同一首歌谣。
辽河滚滚,城池驿动,人心久远!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