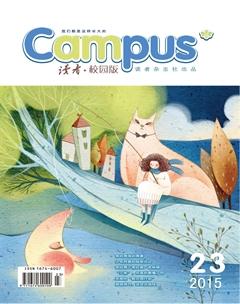三女神
路明,大学物理老师,《ONE·一个》常驻作者,代表作有《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与君生别离》《有一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关于浪漫》《睡不着》等。
黄潇潇
黄潇潇同学打小就是一个招老师疼爱的好孩子。小学时她在隔壁班,我常听说她的事迹:冒雨到学校画黑板报,组织同学去敬老院打扫卫生,并悄悄把偷懒同学的名字记下来。周一的升旗仪式,黄潇潇同学数次登台并发表重要讲话,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像一只骄傲的小母鹅。我那时身体差,每个月至少要请一个星期的病假。有一次,我生病惊动了少先队班委,大队委员黄潇潇在一帮中队长、小队长的簇拥下来我家慰问,给我补习功课。我不是虚荣吗,故意请教黄女神一道奥数题。女神想了半天,不会,于是我给她补课。
初中,我和黄潇潇同班。那时流行一种叫“踏脚裤”的紧身裤,黄潇潇同学穿上最好看。做完课间操回教室,男生们都喜欢跟在她身后上楼。
每个男生的心中,都有一个又骄傲又美丽的女同学吧。她们成绩优秀,风头出尽,是你妈揍你时的“看看人家”。她们时而楚楚可人,时而刁蛮无理,到处有男生谄媚讨好,偏偏她们一副谁也瞧不上的神情。青春期的男生谁没被她告过状,谁没幸灾乐祸地看着她考砸了“呜呜”地哭,谁没偷瞄过她做跳跃运动直到痴呆过去,谁没在课本上画过她的侧影又匆匆涂抹掉,谁没当着她的面打过架,以炫耀“男人”的武功,谁没恶狠狠地想,以后再也不喜欢她了,但第二天又故意在她面前卖弄才情?
青春期的男生最丑:变声,长痘痘,稚气的嘴唇上生出小绒毛爹妈还偏不让刮,最要命的是猥琐。我每次看自己那时的照片,都有想一头撞死的冲动。女生却个个像含苞欲放的花骨朵,“豆蔻梢头二月初”。黄潇潇这样的简直是万千宠爱集一身,一颦一笑牵动无数少男的心。
中考后,黄潇潇进了省重点高中,继续做她的公主。或许是“高处不胜寒”,整个年级的男生都在议论她,却没有人敢表白。高二时,体育委员写了一封似是而非的长信,当面对质时却极力否认。黄潇潇觉得很失望,“恋爱”远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
进了大学,黄潇潇的情窦终于开了。人生第一场恋爱便是网恋加异地恋加姐弟恋,不该赶的时髦全赶上了,轰轰烈烈谈了七年。对方很优秀,却是情场高手。刚学会“小米加步枪”的黄潇潇,迎战一场“全方位高科技战争”,不败才怪。
前年冬天,黄潇潇同学结婚了,跟初中暗恋她的一个男同学。
蒋方方
我和蒋方方同学算得上青梅竹马。我爸和她爸是发小,他们还是两条“光棍”的时候就醉醺醺地给我们订下娃娃亲。小时候常有不怀好意的大人问:“讨方方当媳妇好不好?”我就红了脸,忙说“不着急,不着急”,但谁都看得出我很着急。
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有一回我在她家看《蓝精灵》,和她争辩了几句阿兹猫是公是母,结果被她一脚从床上踢下来。这是平生第一个把我踢下床的女人。
方方同学的成绩好,外加擅长演讲和主持,一直深受老师的喜爱。她是一个强势的小领导,执政风格强硬,经常和各种不服她的男生单挑。比如,当言语管教无效时,她就吩咐手下反锁教室前后门,讲台前空出一块地方,和男生街头霸王一样地互殴,往往以男生哭着回家告终。只有一次,方方同学败了,前额撞到了粉笔槽,血流了一脸,被送进医务室缝了四针。后来她告诉我,她没哭。
初一那年,方方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架。对阵双方都是青春期蠢蠢欲动的小女生。方方挥舞着皮带英勇地冲锋陷阵,仿佛油画中振臂高呼的自由女神;喽啰们也一拥而上,揪头发、扇耳光、扯裙子,把对方那伙女生揍得哭爹喊娘,让一帮观战的男生看傻了眼。
这事闹得挺大,方方为此写了检讨,并被取消了市“三好学生”的资格,此后,方方在光荣榜中消失了。方方的穿着一天比一天时髦,成绩一天比一天滑坡,烫头发、戴耳环、穿高跟鞋,还跟镇上的一个小混混谈起了恋爱。小混混正是当年唯一击败她的男生。每晚放学,小混混倚着摩托车在校门口等她,两人肆意嬉笑一番,绝尘而去。老师们一声叹息:“这孩子废了。”
初中毕业,我离开了小镇。方方没考上重点高中,留在小镇读高中。听说她退出了江湖,又跟小混混做了了断,重新用功读书。无奈落下的功课太多,再怎么努力,也找不回昔日春风得意的蒋方方。
高考落榜后,方方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几年前她眼光独到,开了小镇上的第一家婴儿用品店,生意红火,今年又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段开了第三家分店。那些当年断言她“废了”的老师纷纷说:“早就知道她会有出息。”
小学是她的花样年华,呼风唤雨,万千宠爱集一身;中学是她的草样年华,狠狠跌落在地,迎着一片刺人的眼神,低到尘埃里;走上社会,经历了一番阵痛一番磨炼后,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舞台,冲天飞去,那是她的鸟样年华。
杨花花
杨花花是村里的姑娘,五年级才转到隔壁班。
数学老师是上海女知青,她很喜欢我和花花,常给我俩开“小灶”。那应该是我对花花的最初印象。我记得她瘦瘦小小,不爱说话,穿着土气。一次跟她争论“鸡兔同笼”,我说不过她,于是愤愤地想:“村里囡。”
上了初中,我俩依然不在一个班。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我在楼梯拐角处撞见了花花,才发现她长高了,皮肤也白了许多,却依然是“村里囡”式的害羞,红着脸一低头跑了。
那时我刚结束了人生的第五段暗恋。初恋对象是青梅竹马的蒋方方同学,直到那天在她家看《蓝精灵》,一言不合,被一脚从床上踢下来。之后有一次,在校门口被值勤的小姐姐拦住。小姐姐比我高半个头,小胸脯微微隆起,皱着眉问我:“为什么不戴红领巾?”仿佛正义的化身。在她训斥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以后只要是她值勤,我就不戴红领巾。后来她转学了,我只好去喜欢隔壁班的长发妹,一个很温柔、乖巧的女生。我一下课就跑去看她,上课铃响了三分钟,我才气喘吁吁地跑回自己的座位,异地恋真的很辛苦。一天放学,想着看一眼心上人再回家,结果发现长发妹正在用拖把殴打男同学。第四位暗恋的姑娘迟迟不发育,座位从倒数第三排持续推进到正数第一排。第五位是文艺委员,会弹电子琴,还参加过全镇的朗诵比赛,直到有一天她红着脸找我,打听另一位男生的生日。正当我一颗春心屡屡碰壁、无比烦恼的时候,花花出现了,适时地填补了我的感情空白。
觉得自己差不多算是情场老手了,于是我苦心制造着各种“巧遇”,没事就往花花的班里跑,由此还造成其他女生的误会。有花花在场的时候,我总是十二分不自然,不是大声说着幼稚的笑话,就是和其他男生扭打成一团,仿佛发情的公羊。放学了,我背着小书包目送她骑车远去,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美好。
初中三年匆匆而过。中考后,花花考上省重点高中,我到上海读书。我以为会就此忘记她,就像忘记值勤小姐姐、长发妹和文艺委员一样。谁知我还是常常会想:“那个村里囡今天穿什么衣裳?功课忙不忙?”
高考前,花花找我爸填志愿(我爸教高三多年)。我憋红了脸,打电话给我爸,支支吾吾地说:“把她留在上海吧。”电话那头是笑而不语。花花想学法律,我爸给她的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大学,哪晓得被她的班主任改成西南政法大学,理由是上海的高校太热门,把握性不大。分数公布,花花以高出华东政法学院分数线60分的成绩远赴重庆。我仿佛看到两人从此渐行渐远,尽管最近的距离不过是隔壁班。纠结了一个暑假要不要向她表白,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大学四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偶尔通一回电话,听她抱怨重庆阴雨连绵,食堂的炒青椒都要放辣子。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理工科很无聊,打篮球输了,或是又换了妹子。她笑我花心。事实上,我找的每个妹子都有点像她,要么是发型,要么是背影。
毕业那晚,我躺在草坪上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这些年的想念。我说:“这样吧,我以后就不喜欢你了。”手机那头泣不成声。校园里弥漫着醉酒的味道,有人大声唱着离别的歌。露水打湿了我的头发,这是我的成人礼。
回想那些漫长的日子,像一块赌石,切开之前,永远不知道石头里藏的是石头还是翡翠。赌,押上最好的年华当筹码,却迟迟不开口,迟迟不肯动那一刀。
三年后,花花结婚了。每年她的生日,我都会发一条短信:“生日快乐。”绝不多说一个字。她会回:“谢谢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