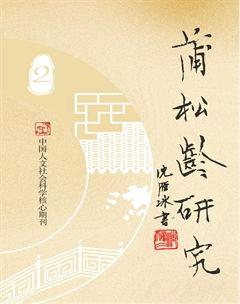“文人之能事,小说之渊海”
常金莲
摘要:《夷坚志》是宋代洪迈创作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内容庞杂,其中最具小说意味的是记载梦境和神仙鬼怪的故事,在小说题材开拓、叙事艺术发展、细节运用、语言通俗化等方面皆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对此后的小说和戏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文人之能事、小说之渊海”。
关键词:夷坚志;记梦;鬼怪神仙;叙事层次
中图分类号:I242.1 文献标识码:A
《夷坚志》是宋代文学家、学者洪迈倾其大半生心血创作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全书大约四百二十卷,按十天干顺序排列。洪迈在世时已有多种刻本,《夷坚乙志序》曰:“《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 [1]但因卷帙浩繁,创作历时太长,散佚十分严重,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二仅著录五十卷。涵芬楼编印的《新校辑补夷坚志》收录初志、支志、三志加补遗共二百零六卷,约为全书的一半。何卓点校的《夷坚志》即以涵芬楼印本为底本,另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佚文二十八则,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
《夷坚志》之名出于《列子·汤问》篇:“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正是这种好奇尚异、鸠异崇怪的嗜好,使洪迈这个严谨的史学家、学问家以大半生精力创造了文言小说史上的奇迹——《夷坚志》是卷帙最多的个人志怪专集,几与官方的志怪丛书《太平广记》等帙。《夷坚志》内容庞杂,凡神仙鬼怪、异闻杂录、灾详梦卜、文人逸事、诗词歌赋、风俗习尚以及中医方药等都有记载。但最具小说意味的还是那些记载梦境和神仙鬼怪的故事。
一、《夷坚志》之梦
梦是《夷坚志》的一大关目。全书共2725则故事(不包括有题无文者),以梦为题者为一百零一篇,再加未以梦为题实则记梦的故事,约占全书的二十分之一。这类梦的故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写梦征,即梦是对现实的预兆;一是写梦历,即重在记梦中经历,其预示性被淡化。
梦征故事重在写梦与现实的某种神秘对应关系,最常见的写法是将梦境的预示意义与现实结果先后排列。这些故事既有粗陈梗概的简短小文,又有叙述委曲细腻的文章。《甲志》卷十一《李邦直梦》叙李邦直慕同僚孙巨源季女,“一夕,梦至圃,见孙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蹑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觉惊寤。”语其妻,妻“大恸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谐也。君将娶孙氏,吾死无日矣。”已而果如其言。这是一个预示着婚姻的梦。此外,梦对文人科举的预示在书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正如《支庚》卷二《浮梁二士》所言:“士人应科举,卜筮之外,多求诸梦寐,至有假托神奇以自欺者。”《甲志》卷四《胡克己梦》记胡克己梦先入棘闱,其妻解之曰:“君不忆《论语》乎?先进者,第十一也。”果然。《丁志》卷四《梦登黑梯》记俞舜凯“绍兴十八年赴省试,梦红黑二梯倚檐间,有使登红梯者。俞顾梯级甚峻,辞以足弱不能蹑,遂登黑梯,造其颠而寤。是岁中特奏名一人。”《支乙》卷二有十则记梦征前程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大量产生是科举盛行的必然结果。唐人小说对科举梦应故事多有记载,至宋出现了专记科举梦应故事的小说专集,如北宋张君房《科名定分录》(又名《前定录》),元符间有佚名作《唐宋科名分定录》,南宋刘名世撰《梦兆录》也记此类故事。[2]洪迈在《丙志》卷十二、《夷坚支乙》卷三共从《梦兆录》引录了十六条。书中叙述梦境的手法灵活多变:或在文末由叙述者直接点明,如《郑侨登云梯》、《梦登黑梯》等;或由做梦者自悟,如《李似之》、《林孝雍梦》;或由故事中另一人物点明(此人物的功能即在此),如《李邦直梦》、《胡克己梦》等。
与梦征故事相较,《夷坚志》中的梦历(梦中经历)故事更具有文学意味。在这类故事中,梦成了一种形式因素,承载着光怪陆离和奇思异想。突出的一个梦历内容是梦中入冥(包括病中入冥),以宣扬善恶报应为主旨。《甲志》卷十二《高俊入冥》,俊登山遇鬼吏,“俊立仆地,即觉从而西。”入冥间,见生前作孽者在地狱受报,阴森恐怖之状历历如画。此类故事之用意正如叙述者所言:“岂非所谓地狱者,一方各有之,时托人以传,用为世戒欤!”而且本篇的叙述细腻生动,叙俊初被追时之惊恐和得归时之惶乱十分逼真。还有将梦中入冥与公案相结合的故事,如《甲志》卷十六《吴公路》写吴梦入阴间断狱事。《乙志》卷四《张文规》是书中篇幅较长的作品之一。张为英州司理参军,审理盗牛案公正仁慈,病中入冥对证,并因此案的公正判决而延寿。对这类故事的主旨表述最清楚的是《丙志》卷八《黄十翁》病中入冥事。黄“因病久心悸,为黄衣童呼出门”,遍观冥间“无忧阁”的安乐与地狱的恐怖痛苦、火山与刀山的残酷,临行阴吏告曰:“汝当再还人世,若见世人,但劝修善,敬畏天地,孝养父母,归向三宝,行平等心。莫杀生命,莫爱非己财物,莫贪女色,莫怀嫉妒,莫谤良善,莫损他人。造恶在身,一朝数尽,堕大地狱,永无出期。受业报竟,方得生于恶鬼畜生道中。佛经百种劝戒,的非虚语。”“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乐福;作恶者万劫不回,受无限苦。令闻此者口口相传。”借梦的框架叙地狱题材,以地狱恐怖作为对人们世间行为的精神威慑,宣扬佛家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观念,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
这种模式化的梦中入冥故事表现出叙事者在凝重的史学意识背后对奇思妙想的文学虚构的宽容与接纳。对入冥过程的描写最体现这一特点。最为轻松的入冥描写是《甲志》卷十九《误入阴府》。李成季得热疾,“数日不汗,烦躁不可耐。自念若脱枕席,庶入清凉之境,便觉腾上帐顶。又念此未为快,若出门,当更轩畅,即随想跃出。信步游行,历旷野,意殊自适。俄抵一大城郭,廛市邑屋,如人间州郡。”身随意动,入冥甚易。想象通脱自如、匪夷所思。最具戏剧性的入冥是《甲志》卷十二《高俊入冥》的开头一段:戍兵高俊“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发执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归。彼人随之不置。俊至家,举食器掷之,彼人怒扼起喉,俊立仆地,即觉从而西。”这一戏剧性的场景,将人对于地狱的恐怖及反抗的滑稽无力暴露出来。最不露痕迹的入冥是《乙志》卷十八《嘉陵江边寺》,王旦“尝晚饮霑醉,独行江边,小憩磻石上,望道左松桧,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顾而乐之,忆常时所未见也。乘兴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萧寺。”此时,人物和读者均未觉已入冥。既而王遇一故去之僧,留之宿。僧戒其勿出,旦起而窥之,见众人方饮熔铜汁,惊怖而奔。僧“命行者秉炬送归,中途炬灭,旦蹶于地,惊而寤,则身元在石上,了未尝出,殆如梦游云。”梦境的似真非真,冥间的似有若无,恍惚迷离而又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梦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因素,地狱也是虚无飘渺的虚幻空间,将二者结合,以梦的形式表现地狱,入冥、出冥更加灵活自由,避开了死后入冥再复活的生硬,使地狱具有了更普遍、更切近的威慑。endprint
梦历的另一个内容是将梦作为现实的补充和变形来记叙。它与梦征的不同在于,后者所记之梦是将来发生的事实,而前者所记之梦是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梦成了对现实空白的补充叙述。《乙志》卷十六《刘姑女》篇,村民刘姑弃家入道,一夕梦女,言“昨与夫婿忿争,相殴击,误扑户限上,蹙损两乳,已死矣”。寤而询之,女“果以昨日死,扣其曲折良是。”《三补》之《祠山像》、《甲志》卷十一《张端悫亡友》之梦亦属此类。从以上诸梦可见,《聊斋志异》的王桂庵之梦与此同出一辙。更多的此类梦的内容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梦在这里成了现实生活内容的载体。如《支乙》卷十《王姐求酒》写叶氏之妾王姐死后,因无子而“春秋荐奠勿及”,因此托梦于叶氏二妾,诉己幽独之苦,反映了多妻制家庭内部无子而又失宠者的悲苦命运。《支乙》卷八《胡朝散梦》则以梦的形式表现了家庭内部的妻妾矛盾。《丙志》卷十一《施三嫂》写一场阴阳阻隔的债务纠纷以梦为媒介得以解决。梦并不是叙述者表达的中心,而是一种叙述手段和形式。关于梦的形式化在《苏文定公梦游仙》(《支癸》卷七)中有明确的说法:苏辙卧病方愈,读《山海经》而入梦遇仙,作《梦仙记》记之。正所谓:“岂非心有所祈,意有所感而然与?”“或谓苏公借梦成文章,未必有实。予窃爱其语而书之。”借梦发议论,借梦成文章,不必实有其事,梦纯粹成了形式因素,这也代表了洪迈对梦的形式化的看法。
对于梦的记载与古代中国的文明一样久远。传说黄帝曾以占梦得风后、力牧两位名臣(《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尧有攀天、乘龙之梦(《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帝王世纪》),舜有长眉、击鼓之梦(《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帝王世纪》),禹有山书、洗河、乘舟过月之梦(《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吴越春秋》、《帝王世纪》),可见传说时期已经有了占梦活动。在殷人的甲骨卜辞中,保存着殷王占梦的许多记载。周王还专门设立占梦之官(见《周礼·春官·占梦》)。春秋以后,占梦从官方的神道活动降为世俗迷信活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不仅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占梦书 [3],而且历代官方正史及文人作品关于梦的描写和记载延绵不绝,更有现代学者撰写的梦文学史 [4]。而《夷坚志》对梦境的丰富描绘无疑是中国梦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夷坚志》之鬼怪神仙
《夷坚志》中的鬼怪神仙故事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鬼怪神仙与人的婚恋幽期故事。这类故事虽以志怪为主旨,但对世态人情的细腻描绘和成熟的叙事技巧依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一是人与鬼的恋爱故事。如《甲志》卷四《吴小员外》是比较著名的人鬼幽期故事。吴小员外清明节游金明池,慕一当垆女,明年再往,其父母言已死矣。归途中遇之,并邀吴同居。吴颜色憔悴,有法师来捉鬼。吴以剑杀鬼,误入狱,得女之父母证之方脱。后被冯梦龙收入《古今小说》卷三十,改作《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乙志》卷七《毕令女》是人鬼幽期和家庭矛盾相结合的故事。毕家仲女为鬼所祸,法师来,仲女娓娓而谈,叙己与继母所生仲女之间的矛盾:婚事为其所坏,怏怏而死;习九天玄女之法几成又为所坏,因而报冤。“盖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则大姐之言也。”二姐死后,毕令又言清明节见一士人,士人叙其与大女的情意。毕令发冢,“则大女正叠足坐,缝男子头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肤理温软,腰以上犹是枯脂。”此一节与《列异传》之《谈生》类似。这则故事描写委婉,人物颇具神采,大女的温柔、妩媚与仲女的蛮横、霸道皆栩栩如生,士人与大女的相处亦于平淡之中见真情。在这则人鬼幽期故事中透露出并不美好的家庭内部嫡庶关系和家庭势力对青年男女爱情的粗暴干涉。再者,对幽明异途的夫妻情感刻画得也十分感人。如《甲志》卷十六《郑畯妻》描写郑妻对丈夫与女儿的恋恋情深,感人肺腑。郑妻王氏死前嘱其勿再娶,善视女儿。后郑食言。一日,郑尚未起,“见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床畔,以手挂帐,拊郑与语死生契阔,且问再娶之故。”又曰:“既已成约,吾复何言!若能抚养泰娘,如我在时,亦何害?吾不复措意矣。”“又语过去它事甚悉。”妻子对丈夫的爱怜和对其再娶的幽怨以及对女儿的挂念,通过一个对话场景表达出来,读来既朴实平淡又缠绵悱恻,感人至深。《三志》己卷三《睢佑卿妻》写睢妻死后,睢于旅中暮投一舍,见到“痛念不曾忘”的故妻,“欢媟如平生”,后“竟悒怏成疾以死”。夫妇之情虽生死异路亦不能阻隔,而且丈夫为妻子相思而死,这在古代小说中不多见。《夷坚志补》卷十《杨三娘子》、《三志》壬卷十《解七五姐》也是对夫妻情爱的细腻刻画。
当然,这类人鬼幽期故事更多地是写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冤报型爱情悲剧。《丁志》卷十五《张客奇遇》可称作这方面的代表作。张客在旅中与一女鬼狎。女鬼本倡女,生前与一杨客约,而杨客三年不如盟,女悒悒成瘵疾,家人渐见厌,女愤而投缳死。从张客知杨客已别娶,女以色惑之,以利诱之,托张以归。终报杨客。这则故事塑造了一个刚烈、有胆略的女鬼形象。卷九《太原意娘》写王氏死后,韩师厚违约再娶,后被王氏索命。这则故事后来成为《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本事来源。《志补》卷十一《满少卿》描写的是忘恩负义、富贵易妻的冤报故事。满文卿富贵之后,叔父另为议婚,先是敬畏其叔,不敢反抗,“忽幡然改曰:‘彼焦氏非以礼合,况门户寒微,岂真吾偶哉!异时来通消息,以理遣之足矣。”这段心理描写暴露出其薄情寡义的无耻嘴脸。遂再娶。二十年后,焦氏报之。原来焦氏已抱恨而死,此是鬼魂索报。这个故事后来被凌濛初改编为《二拍》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这类男子负心故事与妇人改嫁故事的主旨一样,都是在批判、谴责的同时,从反面宣扬标榜夫妇之间贞与信的伦理道德。这类故事描写细腻、叙述委曲,虽为志怪,实类传奇,颇有唐人小说风致。
其二是人神恋爱故事。《夷坚志》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并不比人鬼幽期故事逊色。“上古神话中只有神之间的恋爱,如舜和娥皇、女英,禹和涂山女,人神恋爱大约始于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不过楚怀王遇巫山神女是在梦中,缥缈得很。汉世始有《孝子传》中董永织女及《列仙传》上述故事出现。这是神仙家的功绩。也正因出于神仙家之上,这类被我们称为人神(或仙)恋爱的故事其实并非表现爱情,而是传达仙凡相通及超世度人的神仙观念。” [5] 这类题材在后世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而且爱情也由含混到清晰,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主题。endprint
《夷坚志》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大多并不是表现爱情,志异的成分较多。如《丙志》卷十八《星宫金钥》记李氏子与紫姑神事。李氏子与一美女狎昵,后被邀至其家。“到一大城,瑶宫王缶砎,佳丽列室,气候和淑,不能分昼夜。”李“见珠球甚多,粲绚五色,挂于椽间,问其名,曰:‘此汝常时望见谓为星者也。”后李思亲,与女泣别。临行女赠以小襆,嘱路上遇奇兽异鬼百灵秘怪索物,则探襆中以一物与之。“既行,觉耳旁如崩崖飞湍,响振河汉,天风吹衣,冷透肌骨。”逢巨兽怪鬼则如女所戒而与之。履地后余“金钥匙一个”,货之归家。这则故事重在写李氏子的一次天宫游历,与紫姑神的欢爱只是这次游历的引子。《丁志》卷二《济南王生》描写一士子与龙女的婚姻。王生到龙母祠,慕龙女之美,遂感得龙女现身。龙女从出场、结婚到生子,与常人不殊。只是喜洁,“僮仆汲水时,只用前桶而弃其后,以为不洁。自携一婢来,凡调饪纫缝,非出其手不可,夜则令卧床下。”一日,假托不适,“震雷飞电,大雨滂沛,火光煌然”,遂失女与婢。倒叙点出龙女身份,解除了人们的疑惑。龙女因王生心动而来,又无由而去,既有情又似无情,让人莫名其妙。这类人神恋爱故事重志异而轻爱情的叙述倾向应与叙述者的志异意图有关。
有一篇特别的遇仙故事《蔡筝娘》(《支甲》卷七)记陈道光梦中遇仙事。陈梦中见彩衣童子告其三年后有所遇。后三年,陈道经蓝田,宿于蓝桥驿(蓝桥源自唐代裴铏《传奇》集之《裴航》篇裴航蓝桥遇仙事。后来“蓝桥”成为一个典故,暗示着遇仙)。梦向所见童子执节来,导之入仙境,见到姿态缥缈的丽女蔡筝娘。陈与之同饮,并作诗以记之,诗中多用遇仙典故。女命人度曲侑觞,曲终而寤。后陈复梦童子,告神女对其诗的评价:“‘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以见况,甚无谓。刘、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还,君何訾诋之甚?老子为九天之最尊,奈何辄斥其名?……”这个故事明显借鉴了《蓝桥记》、《游仙窟》和《周秦行纪》的遇仙模式,这在诗中已有暗示,只不过将其纳入了梦境,更显其虚幻、缥缈;而且借童子之口,讽刺了“人间文士”编撰遇仙故事的轻薄。而且,叙述者或许是不满“唐稗说”中诸仙之行为涉淫,因此借本故事做“翻案”文章,但特意表明蔡女之贞洁,只是暴露了其理学思想的浓重。这个呆板、拘谨的“翻案”故事反不如“唐稗说”洒脱自然。
另有一类人神恋爱故事是世间男子与庙中神女的爱情故事。这类故事的模式是先叙述男子和一神秘女子的交往,再写发现线索,证明女子身份。这类故事写得最好的是《支丁》卷二《小陈留旅舍女》。黄寅赴京试,宿于小陈留旅舍。“夜将二鼓,观书且读,闻人扣户声,其音娇婉,出视之,乃双髻女子,衣服华丽,微笑而言曰:‘我只在西边隔两三家住,少好文笔,颇知书。所恨堕于女流,父母只令习针缕之工,不遂志愿。今夕二亲皆出姻知家赴礼会,因乘间窃步至此。闻君读书声,欢喜无限,能许我从容乎?”女子之出十分别致,既从黄生眼中画其外貌,又从女子自述中加深对她的了解,活脱脱一个大方又妩媚的女性形象,令人不由得想起《聊斋》中的《绿衣女》。绸缪几半月,亲友拉黄生入都,女已知之,倏来告别,携手而泣,黄以银五两相赠。途中遇一庙,“见庙神坐傍侍女,宛然是所遇者。详观之,其色赧赧然若负愧之状,纸裹堕侧,银在手中,初未尝启视也。”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结尾的两个细节,“其色赧赧然若负愧之状”和赠银在手,不仅使女子的形象更丰满、更有人情味,而且使整个故事余韵悠长。这一结尾颇似《聊斋》中的《画壁》。另有《支甲》卷五《唐四娘侍女》、卷七《建昌王福》等篇。
其三,人妖恋爱的故事。《夷坚志》中人与妖怪的恋爱故事延续了古代志怪小说的传统,仍采用妖怪幻化成人追求凡人的故事模式,其中以女妖与世间男子的爱情最引人入胜,而尤以女狐与世间男子的爱情最多。
《丁志》卷十六《玉真道人》记高子勉与狐妖的爱情故事。高买美妾,筑竹楼居之,名为“玉真道人”。历数岁,当寒食拜扫,高邀之同出,辞不肯,强之,曰:“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高强之行。“有猎师过前,真颤栗之声已闻于外,少顷,双鹰往来掠帘外,双犬即轿中曳出之,啮其喉,立死。”“容质俨然如生,将举尸归,始见尾垂地,盖野狐云。”文末云:“此事绝类唐郑生也。”“郑生”即唐传奇《任氏传》。只是此不如《任氏传》婉约丰赡,人物也较单薄。《支乙》卷二《茶仆崔三》,崔夜遇少女来奔,不许,女以死哀请,二人遂合。女时时济恤崔。崔兄为猎者,访崔。女不至,“崔思恋笃切,殆见梦寐。”兄意为鬼魅,欲图之,崔曰:“弟与之相从半年,且赖其拯恤,义均伉俪,难诬以鬼也。”兄不听,网获一狸,“崔惨沮悽泪,不能胜情。”异日灯下,少女至则大骂崔无情无意,崔逊谢,“遂驻留如初,至今犹在。”在这个故事中,狐女已不是祟人的妖怪,而是和悦可亲、狡黠可爱的美丽女子,崔也是难得的痴于情者。人物对话的增多及在言谈中见出性格更为故事增添了几分光采。《支庚》卷七《双港富民子》全从富民子的视角写他的一段艳遇。富民子正独自守夜,一女子推户入,“状如倡女,服饰华丽,而遍体沾湿,携一複来”,言为路岐散乐子弟,途中遇雨,求寄宿。子以房小父严为辞。女又求就火烘衣,挽罗裙之际,“不觉裙里一尾出”。子击之,化狐而逃。“衣裳如蜕,皆淤泥败叶也。”故事不长,但描写细腻,情趣盎然。“短日向暮,冻雨萧骚,拥炉块坐”,环境的凄冷渲染了富民子的寂寥。美丽的狐女出现了,举止轻俏、言语轻浮,烘衣时自现其尾,湿衣竟是淤泥败叶。在这个阴暗的背景上,娇俏可爱的狐女像炉中的火苗一样令人欣喜。另有《三志》辛卷二《宣城客》、《支乙》卷四《衢州少妇》、《志补》卷二十二《姜五郎二女子》、《三志》己卷二《东乡僧园女》、同卷三《刘师道医》等篇,这些狐女身上的妖气已被人情冲淡,比《夷坚志》中的人间女子更惹人喜爱。
另有几个精怪故事也情致宛然、十分有趣:
一是芭蕉化美女的故事。如《丙志》卷十二《紫竹园女》,一女子“著绿衣裳”,与一仆合。仆几死,人欲执之,“女奋身绝袖窜。举灯照之,乃蕉叶也。”《支庚》卷六《蕉小娘子》写庭前芭蕉化为一“绿衣媚容”的女子与人狎昵。这类花妖故事在后来《聊斋志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endprint
二是猿化人的故事。这类故事中最优美的是《三志》己卷一《石六山美女》,虽为志怪,实有传奇之风。郡胥宁赏晓起见一女子“荷筠筒候门,徘徊羞怯,将汲井”,“所著布缞,浮白无垢污”。宁执而讯之,女自言新寡,姑翁严苛,强之每日负水。宁欲加以非礼,拒不肯。宁释之,忽不见。宁与友入山访之,逢一白猕猴,遗木叶诗,众人慨叹而归。十年后,一少年遇之,缠绵两月,犹眷恋不忍别。白猿以一个新寡的少妇形象出现,惹人怜爱;又是一个痴情而有节操的女子,让人敬佩。这个故事前后二部分以白猿联系起来,木叶诗末句“萧郎尚未来”起了过渡连接作用。
三是关于蛇精的故事。《志补》卷二十二《钱炎书生》,钱居寺中,“好学苦志”,一夕,“有美女绛裙翠袖,自外秉烛而入”,即留宿。“女雅善讴歌,娱悦性灵,惟日不足。”而钱日渐羸弱。法师一盆水照之,见一巨蟒,并付一符与生。其时女已孕,是夕来,“情志如初”。生以符示之,“女默默不语,俄化为二蛇,一甚大,一尚小,逡巡而出。”蛇女形象楚楚动人,特别是身份暴露后“默默不语”,或许是羞愧、委屈,或许是绝望,不辩词而去,让人留恋不已。《三志》辛卷五《历阳丽人》写蛇精化成的丽人,“商榷古今,咏嘲风月,虽文人才士所不逮”。《支戊》卷二《孙知县妻》中孙妻“颜色绝艳,性好梅妆……著素衣衫……容仪意态,全如图画中人。但每澡浴时,必施重帷蔽幛,不许婢妾辄至。”历十年,孙微醉,窥之,见大白蛇,怏怏成疾而死。《支癸》卷九《衡州司户妻》写其妻为蛇妖,不仅美色,而且和柔待下。这些蛇妖故事是民间传说故事的延续和反映,也是后世“白娘子”形象丰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是鳖精化人的故事。《志补》卷二十二《懒堂女子》是一篇优美的人妖恋爱故事。舒生在湖边“懒堂”读书,日晚呼灯,“忽见女子揭帘入,素衣淡装,举动妩媚,而微有悲涕容。”自表心意:“窃慕君子高致,欲冥行相奔,愿容驻片时,使奉款曲。”言继母不相容,且不为议姻,只好逃命,愿为婢女。舒生许之。女子作词歌之,情辞婉妙。已而事泄,家人掩之。“女奔忙斜窜,投室傍空轿中,秉烛索之,转入它轿,垂手于外,洁白如玉,度事急,穿竹跃赴池,紞然而没。”众散,女“蓬首喘颤,举体淋漓,足无履袜,奄至室中。”“舒怜而拊之,自为燃汤洗濯,夜分始就枕,自是情好愈密”。后舒生常恍惚如痴,家人请法师治之。法师架油锅,书符擒妖。“俄顷,水面喷涌一物,露背突兀如蓑衣,浮游中央,闯首四顾,乃大白鳖也。若为物所钩致,跂曳至庭下,顿足呀口,犹若向人作乞命态。”鳖赴油锅死,舒“独号呼追惜曰:‘烹我丽人。”故事叙述细腻生动,刻画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但其遭遇却令人怜惜。这是个凄美的爱情悲剧,女子坦诚胆怯、心灵手巧(为舒生制衣“工制敏妙”),而且一往情深,舒生也是痴于情者,不以异类见憎。故事叙述细腻生动,描写传神。女子的出场自然、动人,诗词的插入与故事十分契合,贴切地表达了女子当时的心情。女子受惊逃窜一节,画面感和戏剧性很强,只是最后对女子原形的描写,破坏了整个故事的美感。
《夷坚志》中诸多的人鬼之恋、人神之恋和人妖之恋故事,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此类题材在宋代的集大成者,对此后文言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题材和创作技巧方面的基础。
此外,《夷坚志》中还有许多佛教和道教故事,渗透了浓厚的佛道观念;还记载了相当数量的公案故事,这类故事大多搀杂了一些鬼神怪异成分,其主旨仍是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记载现实人物奇节至行的故事,以曲折的情节、复杂的人情和非常的人物性格见长,与鬼怪神仙等非现实题材相比,别有一种亲切的惊奇之感;还有专记江湖骗术的,这类故事以展示行骗者高明的骗术为主要内容,文末附以劝诫和讽刺,但是故事本身的戏剧性和趣味性仍是最为突出的因素。这其中的许多故事成为后来小说和戏曲的题材来源。
三、《夷坚志》的艺术成就
《夷坚志》内容博杂,鬼事、神事、怪事、人事皆收罗在内,佛、道、儒各家思想全融会其中。虽然“志怪未脱前人窠臼” [6],但其艺术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达到了宋代志怪小说的最高峰。
首先,《夷坚志》的题材领域较以前的小说大大拓展,市民生活故事大量涌入,市井气息十分浓厚。《夷坚志》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型著作。《夷坚志》所连接的志怪队伍十分庞杂,“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夷坚丁志序》)因而使志怪题材突破了士大夫的狭窄天地,扩展到市井细民领域。同时,市民社会的兴起也使故事叙述者更加关注这一阶层的生活。这也是洪迈的《夷坚志》及许多其他宋人小说的新特点,反映了古代小说审美趣味的通俗化、市井化倾向。如《乙志》七《布张家》布商张翁好心得善报的故事,反映了小商人的美德;《丁志》卷七《荆山客邸》赞扬的是小店主拾金不昧的美德;《乙志》卷十一《米张家》描写的是一个米商的遭遇;卷十二《成都镊工》描写一个镊工访道求仙的故事;卷十五《诸般染铺》描写的是染术之精,从中可看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丙志》卷十四《王八郎》写一商人的家庭内部矛盾;《支甲》卷一《生王二》记叙猎户的遇仙故事;《支戊》卷七《许大郎》记叙“世以鬻面为业”的小作坊主的故事。另外,医士卜者、僧尼道士、农夫屠户、仆役吏卒等等各行各业的人物和故事皆有相当数量的反映。
其次,《夷坚志》在小说叙事艺术上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叙述层次的复杂化,即一个故事有多个叙述层次。“高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低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也就是说,高叙述层次中的人物是低叙述层次的叙述者。一部作品可以有一个到几个叙述层次,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主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 [7]58 “主要叙述所占据的层次,亦即占了大部分篇幅的层次,就是主层次。”“叙述层次越高,时间越后,因为高层次为低层次提供叙述行为的具体背景。” [7]59endprint
《夷坚志》中的叙述层次复杂而普遍,这是有其原因的。严格而言,《夷坚志》并不是一部纯粹的个人创作。恰如书名的由来“夷坚闻而志之”一样,洪迈实际上是个故事记录者、加工者和编订者。洪迈在序中多次表白:“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支乙集序》)“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丁志序》)不仅故事素材来源较广,而且洪迈自称秉承史家著述传统,秉笔直书,不加虚饰:“盖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既所闻不失亡,而信可传。”(《支庚序》)“一话一首,入耳辄录,当如捧漏瓮以沃焦釜,则缵词记事,无所遗忘,此手之志然也。”(《志己序》)。所以,《夷坚志》的绝大部分故事都在文末注明“某某人说”,甚至整卷故事都来自一人,如《支癸》卷二三在卷末皆注“此卷皆吕德卿所传”,《支庚》卷九之末注“以上三卷皆德兴吴良吏之子秦传其父书”等。也就是说,《夷坚志》中的故事几乎都有一个明确的叙述层次标志和叙述者。在主叙述层次之外,还有超叙述和次叙述层次以及次次叙述层次。如《乙志》卷九《胡氏子》的主叙述层次是“舒州人胡永孚说”的胡氏子与鬼女的恋爱故事,文末又有“李德远说,忘其州名及胡氏子名。”这是对主叙述层次的叙述,因而是超叙述层次。《乙志》卷七《毕令女》篇幅较长,叙述层次也较复杂。文末“升(郭同升)之子氵石说”是故事主叙述层次的叙述者。主叙述层次之下又有两个次叙述,即毕令对书生解释女儿之死,书生向毕家吐露与女鬼的交往。这两个次叙述层次补充了毕令女的身世和遭遇,从而丰富了这个故事。还有《支癸》卷三《宝叔塔影》的叙述分层十分典型:
忠训郎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夫妇好奉释氏,斋施无虚日。淳熙初年二月,清旦焚香,日中有塔影七层现于侧,黄碧璀粲,宛若新饰。金书三字曰:“宝叔塔”。私窃自念:“此塔草创修治,全未成绪,我今自任其责。”乃捐力重建造,规范雄赫,胜于承平之时。寺僧塑其夫妇像于第一层上。后买给使减年恩补官。或云:“王生少年时,因在市斗殴伤人,捕系仁和县狱,适与一重囚同牢,语话款洽,因密言:‘我一生做经纪,今焉获败。念杀人负罪,决无生理,切有心腹事,为君陈之。我昔年曾掠宫室之物,得金银甚多,埋于宝叔塔之下左方,入地若干,可悉掘取。俟我伏法了,幸为收拾骸骨,瘗之高原。仍广作佛事,以资超脱。遇忌日时节,宜饭僧诵经,分明回向,则我瞑目不憾矣。王出狱,悉如所戒,往塔下启穴,果得物可值万缗,因此致富。故假影之,以盖其事云。”
这一故事是吕德卿所传,主叙述层次的叙述者即吕德卿。“或云”则是次叙述层次。“重囚”所言为次次叙述层次。不同的叙述层次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的复杂性进行了阐释。此外,《乙志》卷二《莫小孺人》、卷六《袁州狱》、《丁志》卷十八《路当可》、《志补》卷六《细类轻故狱》等篇的叙述层次也很有代表性。唐前小说的叙述分层并不普遍而且十分简单,从唐传奇开始,叙述层次问题突出出来。在小说史上具有过渡意义的《古镜记》,以古镜为线索,在主叙述之下产生出许多复杂的次叙述层次,这在以后的小说中也不多见。他如《离魂记》、《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异梦录》等等都有复杂的叙述分层。宋代传奇《赵飞燕别传》的叙述层次是一个发现书稿形式的别致的超叙述层次,主叙述自然就是书稿的内容。这种叙述分层形式最杰出的应用就是清代的《红楼梦》。
第三,叙述角度的灵活运用,也是《夷坚志》叙事艺术的一大成就。《夷坚志》中的叙述角度既有全知视角,又有限知视角。如《宝叔塔影》是以全知视角进行故事叙述,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进行分析。《晁安宅妻》以全知视角展示晁氏的一举一动。限知视角特别是第三人称视角的运用在志怪故事中更有艺术价值。如《甲志》卷八《金刚灵验》,从盗贼的视角写老妪和金刚神,平中见奇。《支庚》卷八《王上舍》写王元夕遇美,处处从王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金坛翁甥》记甥遇女鬼,全从翁眼中写来,使叙述更具有神秘感和真实感。《志补》卷八所记载的江湖骗术故事也多以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为主叙述故事,主人公和读者一起陷入骗子设计的圈套。这种限知叙述视角的运用使故事的戏剧性和讽刺力量大大增强,给读者带来的娱乐性也更大。运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最巧妙的故事当是《三志》辛卷二《永宁寺街女子》:
庆元四年五月十日,夜已四鼓,鄱城卜士有未寝者,在所居小楼上为人推演命历。闻庆善桥畔一人独行,且叫且喝,由永宁寺前街向西去。约过十许家,逢一女子立于门首,相呼问讯云:“阿姊深夜抵此,当是急干?”女曰:“莫要问我。”遽望东而行,才数十步,又与别男子语。男扣其所往,女曰:“记得四月内,小市下王嫂出到市上看道场,王嫂抱三岁小儿极可怜爱。我随逐颇远,欲撮取之,被师人赶逐,我只在彼不退。儿觉如中恶,昨日遂遭法师两次用符摄治,遣我于外,无缘再入,今须旦归。”男子曰:“适间向西去者似可恼害,三娘同一往可乎?”女曰:“我一处已受辱。岂宜至再!兼其人精神极旺,难亲近他。”男子曰:“三娘直如此识人,试一行亦不妨。”女曰:“七哥必要挠它,莫是曾相犯否?”曰:“恰在庆善桥上为它口巽唾喝我,故欲报之。”女曰:“既不曾相犯,何如且休。”遂寂寂而散。始知前人呼喝者此也。
这则故事纯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述,以“卜士”的听觉来结构故事,感官上的限制使叙述充满了张力。人物语言也颇见性格,女鬼之善良、胆怯,男鬼之睚眦必报,皆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古代小说中像这样全以听觉感官进行叙述的并不多见。对于搜奇记异的志怪小说而言,限知视角叙述似乎更具优越性。
《夷坚志》中有两则故事值得注意。一是《支甲》卷六《西湖女子》写一则人鬼幽期故事,女鬼曰:“我曾看《夷坚志》,见孙九鼎遇鬼亦服此药。吾思之,药味皆平平,何得功效如是?”另一篇是《三志》辛卷九《萧氏九姐》,易生好观星象,遇一绿衣女,亦好此道。易问之,“女因妲己能指九州灾异以对,仍言不欲说尽,恐或泄与徐谦其人得知,定写呈洪内翰,编入《夷坚》之书,非吾志也。”这两则故事显然是叙述者的虚构,讲述了一个关于小说的小说,类似于西方叙事学中的“元小说”。这既可以看作是叙述者的游戏笔墨,又可看作是对洪迈及其《夷坚志》的直接赞誉。《聊斋》中的《狐谐》与此有些类似。endprint
第四,细节的巧妙运用也为《夷坚志》的叙事增添了不少光彩。如《乙志》卷七《毕令女》,一面镜子不但使人鬼恋故事陡添人情味,而且又有着叙事上的功能。《丁志》卷十九《留怙香囊》,香囊是故事中的重要关目,叙述者对其进行了精细的描写。一个香囊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从而发现了与留怙来往的美女子,同时有着叙事上的功能。《支丁》卷二《小陈留旅舍女》最后,黄寅发现夜间美女原来是庙中的侍女,“详观之,其色赧赧然若负愧之状”。这一面部表情的细节描写,使女子由静态的偶像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间女子。卷七《双港富民子》对狐女的刻画也运用了细节。狐女就火烘衣,挽罗裙之际,“不觉裙里一尾出”,华丽的服饰,竟然是“污泥败叶”。细节描写使一个粗心大意而又娇俏可爱的小狐狸跃然纸上。此类细节的运用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拉近了志怪故事与读者的距离。
第五,人物语言的通俗化趋向也是《夷坚志》中值得注意的特点。这既是受宋代俗文化的兴盛的影响,也与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有关——许多故事的叙述者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农夫市民,因而故事中人物的语言不乏质朴、俚俗,生活气息浓厚。《支景》卷十《郑二杀子》以俗语写俗事,十分出色。武陵民张二嫁女,招邻里会饮,郑二夫妇预焉。郑妻素与王和尚通,人共知之。酒酣后,偶堕箸于地,张妻戏曰:“定有好事。”郑妻笑问故,曰:“别无好事,只是个光头子。”俄有外人唤之出,附耳语而去。众问为谁,曰:“王阇黎(梵语,即高僧)典袈裟在我处,将盐来赎。”写村妇戏谑口吻,泼辣生动。《支丁》卷九《陈靖宝》中樵夫的慨叹:“使我捉得陈靖宝,有官有钱,便做一个快活汉。如今存济不得,奈何?”野语村调,鲜活朴质。卷五《黟县道上妇人》记叙浮梁民程发遇异妇人事,写妇人之主动泼辣、程发之谨慎犹豫,惟妙惟肖。《支庚》卷一《丁陆两姻家》叙农民丁陆两姻家之间的财产纠纷,丁之奸猾虚伪贪婪、陆之愚笨老实都从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中表现出来。总之,《夷坚志》中的人物语言以文人雅言为主,但同样存在着比比皆是的民间俗语。这种混杂现象对于“闻而志之”的洪迈而言或许并非自觉,但至少说明正统文人对下层文化形态的宽容与接纳。
洪迈的苦心孤诣使《夷坚志》受到了广泛的推崇。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七《题夷坚志后》:“笔近反离骚,书非支诺皋。岂唯堪史补,端足擅文豪。驰骋空凡马,从容立断鳌。陋儒那得议,汝辈亦徒劳!”认为《夷坚志》不仅堪补史阙,而且兼擅文采。嘉靖二十五年田汝成《序》:“是惟天人交辅,以持世故,彝伦所以常存,而乾坤赖以不毁也。人之为治也,显而易见;天之为治也,幽而难明。略其易见而表其难明,此《夷坚志》之所由作也。……故知忠孝节义之有报,则人伦笃矣;知杀生之有报,则暴殄弭矣;知冤对之有报,则世仇解矣;知贪谋之有报,则并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则奔竞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则踰墙相从者恧矣。其他赈饥拯溺,扶颠拥孺,与夫医卜小技,仙释傍流,凡所登录,皆可以惩凶人而奖吉士,世教不无补焉,未可置为冗籍也。”从创作目的、内容及社会教化意义方面高度赞誉《夷坚志》。乾隆戊戌六月沈屺瞻《序》:“第观其书,滉瀁恣纵,瑰奇绝特,可喜可愕,可信可徵,有足扩耳目闻见之所不及,而供学士文人之搜寻摭拾者,又宁可与稗官野乘同日语哉!”称赞《夷坚志》内容丰富、新人耳目。光绪五年陆心源《序》:“自来志怪之书,莫古于《山海经》,按之理势,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遗》,干宝之《搜神》,敬叔之《异苑》,徐铉之《稽神》,成式之《杂俎》,最行于世。然多者不过数百事,少者或仅十余事,未有卷帙浩汗如此书之多者也。虽其所载,颇与传记相似,饰说剽窃,借为谈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隽永,层出不穷,实非后人所及。……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说之渊海也。” [1]“文人之能事,小说之渊海”道出了《夷坚志》在小说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这种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夷坚志》一出,即广为流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其一,大量《夷坚志》的仿作和节本的出现。如郭彖(字次象)的《睽车志》、王质的《夷坚别志》、沈氏所撰《鬼董》以及金元好问的《续夷坚志》等就是较为突出的模仿之作,至于那些在内在精神上受《夷坚志》影响的小说就更多了。节本的出现是为了检阅方便,自宋代至清代,有许多节本流传,其中叶祖荣编选、嘉靖二十五年洪楩清平山堂刊印的《新编分类夷坚志》是《夷坚志》的精选本,成为以后最通行的本子。
其二,《夷坚志》被称为“小说之渊海”,其中某些故事在后世以多种形式广泛流传。概括而言,元明许多文言小说汇编大量选材于《夷坚志》,更多的则是《夷坚志》中许多故事素材被吸收或改编成白话小说和戏曲作品。《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将《夷坚志》视为“无有不览”的材料库。以“三言二拍”为例,据谭正璧的《三言两拍资料》 [8]所辑,被吸收、改编入“三言两拍”入话和正话的《夷坚志》故事有四十九则,以“二拍”居多。另外,《夷坚志》作为小说资料宝库,某些新颖有趣的情节模式和故事原型被后世的小说家所借鉴。《水浒传》中的李逵遇李鬼、孙二娘开黑店等情节可能取材于《支丁》卷四《朱四客》、《三志》辛卷三《建昌道店》和《志补》卷八《京师浴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作品,如《夜叉国》、《酒虫》、《大人》、《禽侠》、《小棺》等,明显借鉴了《夷坚志》中的《猩猩八郎》、《酒虫》、《长人国》、《义鹘》、《异僧符》等作品的构思。《夷坚志》故事被戏曲所取材者也不少,宋元杂剧、金院本、戏文、明清传奇皆有演绎《夷坚志》故事的作品 [9] 。
参考文献:
[1]洪迈.夷坚志[M].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宁稼雨,编.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第三编)[C].济南:齐鲁书社,1996.
[3]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历代梦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傅正谷.中国梦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
[5]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96.
[6]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186.
[7]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8]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李剑国.宋代传奇志怪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57.
(责任编辑:谭 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