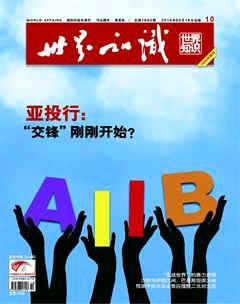从“两案”看我国周边海洋权益斗争面临的国际司法干预挑战
叶强

2015年3、4月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仲裁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分别对两起案件作出了裁决和咨询意见——毛里求斯诉英国“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仲裁案”(以下简称“查戈斯案”)和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提交的“专属经济区非法捕鱼的船旗国责任问题咨询意见案”(以下简称“咨询意见案”)。两起案件分别牵涉两大国际法前沿问题:领土、海洋混合型争端案件的管辖权困境,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权能问题。针对这两大难题,国际仲裁庭和海洋法法庭的裁决反映出法官们对自身权力所持立场不尽相同。立场冲突背后隐藏的是当前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在“权力自限”与“权力扩张”的博弈。这种权力扩张倾向已经开始侵蚀国家这一国际社会最主要行为体希望通过主权行为决定的事项,甚至于不知不觉中重塑着国际秩序。“司法干涉”作为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对“平权”国际社会结构形成挑战,应引起我国高度关注。
查戈斯案背后的国际司法干涉倾向
查戈斯案始于2010年。它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毛里求斯将其与英国之间围绕查戈斯群岛的领土主权争议“包装”成了海洋管辖权问题,仲裁庭如何裁决,关乎英、毛两国的利益,关乎仲裁庭如何看待自身的权力界限,也预示着国际仲裁庭未来如何对待类似案件。
查戈斯群岛是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领地,位于印度洋中部,最早由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在15世纪发现,18世纪初被法国占领,1810年被英国占领。1814年,该群岛被法国根据《维也纳和约》正式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属毛里求斯的一部分。1965年,作为获得独立的附加条件,毛里求斯“同意”该群岛从英属毛里求斯的领土中分离出去成为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国则承诺毛里求斯仍可在该海域享有捕鱼权,当该群岛不再具备军事作用时,英国将向毛里求斯归还该群岛。
毛里求斯独立后,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催促英国归还该群岛,英国不仅置若罔闻,还驱逐了岛上原住民以建设军事基地。2010年4月,英国外交部宣布,在查戈斯群岛建立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范围覆盖自该群岛向外200海里的全部海域,禁止商业捕鱼、深海采矿等行为。毛里求斯对此表示“愤怒”,2010年12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合法性问题提起国际仲裁。在诉讼请求中,毛里求斯不仅要求仲裁庭裁定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行为侵犯了毛里求斯的合法权利,还要求裁决英国不是有关海域“沿岸国”,无权划设海洋保护区。
不可否认,英国在殖民主义时代所推行的政策——诸如随意分裂殖民地国家固有领土,极大伤害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权益。在非殖民化及国际关系民主化之后,英国依然凭借其在国力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在关乎其重大国家利益的事项上拖延履行国际义务。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设立的仲裁庭能够加以评判的。仲裁庭只能审议并裁决《公约》所规定的事项,即各缔约国对海域的管辖权及其在海上活动的权利义务,对超越上述范围的事项均不能行使管辖权。
在审理查戈斯案过程中,五位仲裁员对此产生了分歧。部分仲裁员宣称,仲裁庭不仅在判断查戈斯群岛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不超越权限,而且还应该对非殖民化时代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所作所为的合法性加以判断。如果按照美国法学家凯尔森的说法,“国际司法机构是具有法庭性质的国际机构”,那么,部分仲裁员的观点不仅漠视了仲裁庭“国际机构”的特点,而且模糊了其“法庭性质”。实际上,持这种立场是危险的。
首先,国际机构不是“世界政府”。国际机构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与主权国家平等的,它们的职权范围是各个成员国通过缔结“组织协定”的方式确定的。如果这些机构超越“组织协定”规定的权限,就违背了成员国组建该机构的目的,其权力扩张必将破坏既有秩序的和谐稳定。
其次,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不是一般的国际机构,应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谨慎义务,即“司法节制”原则。这是因为,司法具有被动性的特点,司法机构不能主动寻找社会纠纷进行裁判,不能像行政机关那样“路见不平就出手”,只能根据当事方的请求受理案件,案件的审理也必须遵循严格程序。即使有权对案件作出裁判,还要考虑案件是否适于通过司法判决加以解决。国际司法机构在传统上都倾向于拒绝审理那些由严重政治矛盾或军事对立引发的争端。
最终,审理查戈斯案的仲裁员以3比2的投票结果拒绝受理可能对群岛领土主权作出裁定的诉讼请求,也没有对英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相关主权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评判。这一结果总体符合“司法节制”的原则,但由于仲裁庭在该案法律论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群岛领土地位的看法及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向毛里求斯所作承诺的性质,也就赋予了毛里求斯一些对其未来领土主权主张有利的司法实践依据。从这个角度看,仲裁庭已在很大程度上扩张了自身权力,只不过并未明确声称其拥有审议领土问题的权力罢了。所以,对这一裁决结果,英国保持沉默,毛里求斯表示“欢迎”。
咨询意见案反映的法庭权力异化
相较于仲裁庭处理查戈斯案的总体谨慎,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咨询意见案上要激进得多。20余位不同国籍的法官一致认为法庭具备所谓“咨询管辖权”。
咨询管辖权是与诉讼管辖权并列的国际法庭的基本权能。顾名思义,它的存在并非是为了审理争端当事方的诉讼,而是就国际机构所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和指导,以便各国和国际组织能“依法办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司法机构都具备诉讼管辖权,但只有少部分司法机构,根据“组织协定”的明确授权,才具备咨询管辖权。这是因为,咨询管辖权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容易突破“国家同意原则”,成为一国不经另一国同意就将它们之间的争端交由法庭裁判的“简便工具”。故而,必须由各成员国在缔结条约时明确约定,法庭方可行使这一权力。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没有任何条款赋予法庭行使咨询管辖权的权力(海底争端分庭除外),然而法庭出人意料地于1997年在自己制定的《法庭程序规则》中指出其拥有该权力。自此之后,十多年来并未有国家主动触碰这一“敏感神经”,直至2013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非国际组织“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向法庭递交了首例咨询案,要求法庭对如下问题作出判断:若悬挂某一国旗帜的船只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非法捕鱼行为,该船所属国家应承担何种义务和责任。
这并不是一个限于西非渔业组织的问题,而是牵涉全世界所有沿海国和船旗国权益的一般国际法问题。一旦法庭确认自身具备咨询权能,并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也就意味着法庭权力运行突破了缔约国的授权范围,预示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失去“安全感”。
因此,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引起众多国家警觉,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均明确反对法庭行使咨询管辖权。但法庭仍在最后发表的咨询意见中确认其具备咨询管辖权,给出的理由却很难令各国信服。在对法庭权力界限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即使作出判决也无法很好地执行,最终损害的将是法庭公信力。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往往以解决争议为形式,同时承载着实现正义的职能,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矫正正义”。但“主持正义”的前提必须是以特定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所能接受为限度。近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以来,国际司法和仲裁作为一种正式的争端解决方式,被明确载入《联合国宪章》,并被大量国际多边条约确立为可资利用的争端解决途径。一些拥有众多缔约国的国际公约,比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解决投资争端国际公约》,以及前述两个案件所涉及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均是如此。根据这些公约组建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仲裁庭等自成立至今已审理了数十乃至数百起案件,成功解决了当事国之间的不少争议,对促进世界和平、维护国际关系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特别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任何法律与道德可能都是脆弱的,正如美国社会生物学开创者威尔逊所言“没有什么道德义务比生存本能更加优先”。在国际司法和仲裁的历史上,部分涉及领土问题的案件宣判后很难得到执行,甚至争端继续扩大。再如,尽管美国自18世纪起就大量利用国际司法和仲裁途径解决与他国的争端,但当上世纪80年代尼加拉瓜以美国对其军事渗透违反国际法为由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而国际法院坚持审理此案并作出对美国不利的判决后,美国收回了其同意将管辖权授予国际法院的概括性承诺。
就国家而言,决定是否选择国际司法和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除了案件获胜之外,参与条约时的承诺、国际信誉、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合作的利益等,都是考虑因素。而国际法官们所应考虑的,则是在既定法律框架和政治秩序下,如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具体纠纷进行裁判,实现个案公正。如果法官们过多地考虑政治问题,甚至主动谋划国际政治格局,在当前的国际社会结构条件下注定要掀起波澜。
“两案”对我国处理周边海洋权益争端的启示
就咨询意见案而言,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国际海洋法法庭单方面行使咨询管辖权,形成这样的立场主要是担心周边国家有可能将南海或东海争议提交咨询,这显然与中国坚持的由直接当事国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张相抵触。
查戈斯案对我国具有更加直接和现实的意义。菲律宾于2013年单方面将南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本质上就是把中菲之间的南海岛礁主权争议“包装”成海洋管辖权问题,对此中国政府一直反对仲裁庭行使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南海仲裁案菲方代理律师——来自美国的保罗·莱克勒正是查戈斯案毛里求斯一方的代理律师。而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菲方指派德国籍的鲁迪格·沃尔夫卢姆法官为仲裁员,此人正是查戈斯案仲裁庭成员,致力于推动仲裁庭权力的扩张。
一段时间来,中国通过庭外法律斗争的方式应对南海仲裁案,取得了一定成效,仲裁庭决定2015年7月开庭先行审理对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如果仲裁庭能够尊重查戈斯案判决的先例,理应裁决不对菲律宾提交的诉讼请求行使管辖权。但本案也有不容乐观的一面。除了菲律宾的法律顾问团队会从查戈斯案吸取教训、沃尔夫卢姆法官可能更加强势外,我国目前的处境也不可与当年的英国同日而语:作为运用国际法进行国际斗争最富经验的国家,英国出庭参加了仲裁程序并提交了大量书面抗辩。
长远来看,应当考虑多种途径化解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因权力扩张而对我形成的司法干涉风险。首先,在外交层面,尽可能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大国形成“统一战线”,对国际司法机构权力界限问题达成共识,在国际组织中采取必要外交手段限制国际司法机构权力扩张。其次,适当加大参与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的力度,推动相关机构《规约》和《程序规则》的修订完善。作为政治大国,中国在重要国际司法机构中一直选派有法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国际机构中,中国籍国际职员的数量严重不足,阻碍了中国法律和政治文化在相应国际机构中显示影响。另外,也要加强对国际诉讼和仲裁制度以及英美普通法制度和文化的学习研究。国际司法和仲裁在实践中借鉴了大量英美法制度。如果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道路上不想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以外,不想背负“败诉”的巨大风险,那么主动学习研究、敢于亲身实践终将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