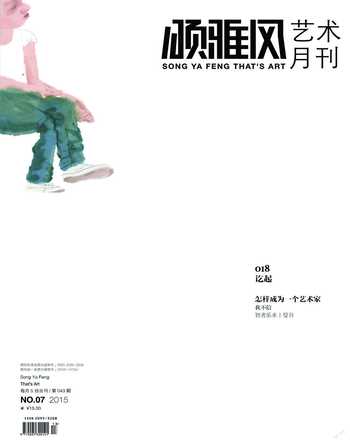怎样成为一个艺术家
林霖



展览对空间的拆解、再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部分。如今我们往往过于关注作品本身,而较少去思考作品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展览本身其实也是作品创作的一部分。当然,时下艺术界也愈来愈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大多还是依旧差强人意,抑或干脆没有新意。
怎样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震旦博物馆“画影之间:张恩利&杜可风”展览最后视频部分中的一个设问。张恩利想必已经通过他的展览解答了这一设问。
艺术家要会“无中生有”。在一个处处是巴洛克风格内饰的厅堂内如何搭出自己一以贯之的“空白空间”的展厅风格?如何在一个热闹的、商业的空间里展示自己“日常”的架上绘画作品?张恩利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幽默——他用一个个外表刷成白色的牛皮纸箱拼连起来,作为展厅的墙。而拼连牛皮纸箱的黄色胶带又呼应了外部的厅堂风格与地砖。张恩利笑言这些纸箱是空的,所以这又是一个“空”间。于是,内外的呼应并非是生硬的隔阂,而是自然地转换。
艺术家要会“提炼日常”。各种旮旯之物,在张恩利的笔下,被赋予一种通常只有价值连城的事物才会有的吸引力,也唤醒观者原本被忽视的观察力,发现不起眼的物体本身的意义。卫生间的水池、马桶、橡皮水管、瓷砖、球、电线……张恩利纯粹是因为想画就画了,他多次在采访中否认自己的画里有什么观念性的刻意诉求,他只是想“还艺术几分生活的味道”——但这个“味道”不提炼,哪会至醇至美。
艺术家要有想象力。比如画面中的光影,并非是你真正看到的光和影,它只能是依据你的想象而来。正如张恩利在视频访谈中所言:艺术家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室的这样的小空间里,很多零碎的东西都容纳其中,走来走去、想来想去,突然看到了什么,然后就画了这样的一张画——画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并非真正是你看到的东西,而是依据想象加工而来。
艺术家最好还要有善辩的口才。在访谈中,策展人对张恩利抛出诸如“你和杜可风的风格完全迥异,你们如何在一个展厅里一起做展览”这样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圆滑”:“我觉得我们看上去很不同,但其实还是有共同点的”,“而且这种差异放在一起做展览也没什么不好”没有什么非黑即白,艺术就是这样穿梭在各种缝隙中,艺术是自由的。当然,这种“自由”背后有隐藏的线,这根线应由艺术家所掌控。
回到“画影之间”这个展览,我们看到的,依旧是熟悉的张恩利,我们会发现如今艺术家不仅要搞好自己的创作,还要会搞展厅设计。可能张恩利对空间的营造更为熟稔,以至于大众更为熟悉的杜可风的存在感反而弱了。不过,事情往往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正如杜可风一向的观点:言语是一种病毒——他总是用镜头和作品说话。所以当人们要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似乎总是很沉默,或者总是离不开他已经说过的那几句。
展览中有一件名为《瓷漆中的黑色》的影像作品,倒是于轻描淡写中传达了杜可风的犀利观点:“大学都尝试教授创意是什么回事,但问题却是,如果我们找到方法教别人创意,让每个人都能解释创意的由来,那么一切便再无趣味。创意不可缺少的元素是神秘感,隐秘得像瓷漆中的黑色,难以看透却意味深远,成就璀璨的作品,任何人都无法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去探讨张恩利和杜可风的艺术,不如去探讨展览本身。展览对空间的拆解、再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部分。如今我们往往过于关注作品本身,而较少去思考作品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展览本身其实也是作品创作的一部分。当然,时下艺术界也愈来愈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大多还是依旧差强人意,抑或干脆没有新意。
虽说纸箱划分出了一个独立的展厅,但张恩利的艺术在震旦博物馆这个空间可以说无孔不入,比如他在巴洛克厅堂的大玻璃窗上绘制了他的“天空”、“树影”系列,富于装饰性的视觉表现使得玻璃窗有点哥特教堂玻璃窗花的意味,与巴洛克风格的厅堂相契合。另外,在对面古董展区,一排古代陶俑展柜相对的墙面上,则挂了张恩利的油画作品。走廊展区,挂着的是杜可风的摄影作品——在传统展厅用传统方式展出,在当代空间用创造性的方式做展览,从而让策展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也是震旦博物馆一贯的做法,常常将当代艺术作品与古董文物并置与对话。于是,在我们观看陶俑的时候,展柜那擦得明亮的玻璃上,映出了对面的油画作品,空间的交错与新生。
空间的再生,也体现在杜可风将视频嵌入老家具的做法,这种手法虽无新意,但在这个展厅这种“在一起做展览也没什么不好”——言下之意,这也是这个展览的亮点。熟悉两位艺术家的人会抱着诸如“他们两个一起做展览会是怎样的”疑问来看展,这也是这个展览的吸引人的话题所在。
至于杜可风是如何“嵌入”张恩利的,仔细看我们便会发现张恩利的作品其实是“背景”——他把“橡皮水管”画满所有纸箱搭出的“白墙面”。而“展厅”内的展品其实就是杜可风的一张张老家具桌子和老皮箱了,当观众走到桌子边上,透过嵌入桌面的视频,会看到了王家卫电影中一个个熟悉的片段和明星的身影……唯独一张大桌子的内容有点不一样,视频记录的是张恩利布置展厅的过程,只见张恩利不时拿着椅子举过头顶在纸箱展厅外徘徊,然后又端坐在纸箱展厅内沉思……这一来一去带有一种仪式的意味。这组视频是杜可风拍摄的,记录了张恩利为这个展览创作的过程。虽然之后他应策展人的要求也成为被拍摄者,但他自言自己的“进入”就像做一个卓别林式的作品,把个人的幽默感放进去了——幽默感,或许就是杜可风对这次两人联展的定义。回过头来再看这样的一个“空白空间”,确实是处处透露着他说的幽默感。如果从一进入展厅就仔细观看,便会发现拼连纸箱的黄色胶带远看颇有金碧辉煌的巴洛克内饰效果:白色的墙,金色的镶边,这难道不是张恩利玩的一把小嘲讽?
相比之下,杜可风的摄影却很庄重,严肃地拼贴、场景装置、摄影、涂绘。在这里,杜可风将三维的空间二维化,通过有意的拆解、介入、重组,其实是对摄影镜头真实性的一种反思。而策展人有意拆分这个“画影之间”的展览,将传统作品放置在传统展厅,将装置作品留给巴洛克展厅。因为“画影之间”无需门票,而古董展区需要另外买票,是否有很多不知情的观众会错过古董展区的“时空对话”,这或许也是艺术家和策展人看似随意的“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