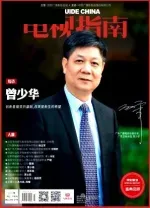《嘿,老头!》:让剧本回到原创
兰岚
本着“市场先行”的原则,制片方往往会在某些时期内对某类题材、某种类型乃至某个风格的剧本有特定诉求,这就要求编剧根据特定诉求来进行剧本创作——而且,业已成了编剧最主流的创作模式。有业内人士称,30年前国产剧是先有剧本再谈其他,但现在情况完全反了,写原创剧本的编剧尚不及1/20,剧本全都成了“命题作文”。制片方对市场既有成功案例的追崇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编剧闭门埋头吭哧吭哧写出的原创剧本并不一定受制片方待见,他要面对的是漫无止境的等待或妥协。“万一写了没人买呢,风险太大了”,抱着这样的心理,绝大多数的编剧都会选择“命题作文”。
从这个层面上讲,勇于写原创剧本的编剧都是木人石心,称得上志坚行苦。因此,当《嘿,老头!》以一种自成一格的面貌在“撞车”事故频发的电视剧市场出现时,它能够收获的不仅仅是收视率和口碑,还有掌声。
《嘿,老头!》是编剧刘东岳和俞露5年前就开始闷头创作的——在没有人约,也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的情况下。刘东岳和俞露是同班同学,也是夫妻、搭档,虽然在编剧圈夫妻档并不鲜见,比如李潇和于淼、王莹菲和周萌,但像刘东岳和俞露这样各方面都互补的却是不多。用俞露的话来说,他俩“一个北一个南,一个胖一个瘦,一个土一个洋,一个敢想一个敢为——是非常合适的相声搭子”。这对“搭子”的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嘿,老头!》的剧本品质,也正是因为他俩对原创剧本的坚持,使得《嘿,老头!》并不依靠噱头和狗血来吸引观众。
《嘿,老头!》是2015年春天的暖心之作,我们也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专访了刘东岳和俞露,同他们聊一聊创作中的那些事儿。
刘东岳,男,青年作者,创意人,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俞露,女,青年作者,创意人,编剧。中戏剧学院文学系编剧专业博士,后做了几年大学讲师。这对创意组合近年作品包括《赵匡胤》《蓝色骨头》及最近热播的《嘿,老头!》等。
每一种生活都有自己的柴米油盐
Q:你们俩这么年轻,为什么会选择写一个有关阿尔茨海默症的题材?
俞露:决定要和刘海皮爷俩一块儿过日子,是在2010年。五年前,我们俩一个快30岁了,一个则爬过了30好几,当满电视都是婆婆媳妇妯娌孙子的时候,我们却磨刀霍霍,一心想写一个不那么虚无缥缈的“年轻人的生活剧”。想来想去,便最早想出了主人公刘海皮,想出了父与子,想出了求之而不得的恋爱,然后我们再去寻找能推动故事发展的矛盾冲突。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会在患者和家人之间制造很多矛盾,而且得了这种病后,老人会越来越像孩子,亲子的关系会发生倒置,正好符合剧本创作的要求。再然后,我们一跺脚,就把海皮丢进了这样一个困境——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事无成一塌糊涂,落荒而逃回了已经不是故乡的故乡,一扭头竟发现曾和自己为敌的爹,突然得了老年痴呆,不认识自己了……这一次,当儿子的成了爸爸,当爸爸的成了儿子,一起面对人生百态,面对求之不得的姑娘,面对求之不得的一切——在老头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一切重新开始。
Q:阿尔茨海默症、一事无成、求之而不得,这难道不该是个苦情戏码吗?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以一个喜剧的面貌将它们呈现出来?
俞露: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喜剧,就像左撇子右撇子一样理所应当。我们在写创作心得的时候也说过,我们之所以热爱喜剧,本质上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关系:我们认为大多数的事情,最后都可以归到喜剧的行列去。喜剧不是一个人滑跤跌倒,不是他把袜子套到头上,而是因为对生活的超然态度而生出的一种幽默感。但是喜剧不意味着你就不会掉眼泪,我们这个戏其实也挺催泪的。不过泪水不只代表悲伤,心里觉得通了,被触摸到了,人既会笑出来,也会流泪的。喜剧是一张奇特的网,几乎网罗了一切更复杂的感受:怀疑、戏谑、讽刺……甚至包括泪水。“喜剧是最严肃的,喜剧是最丰富的”,可当“喜剧”的标签被滥用的时候,国内的影视剧又缺乏高质量的喜剧作品。
Q:“婆婆媳妇小姑子”的“家长里短”难道不够“接地气”,和年轻人的生活无关吗?
刘东岳:每一种生活都有自己的柴米油盐,就我们看来,年轻观众生活里的困境太多,但写给他们的现实主义作品太少。我们写这个戏的初衷是接中国年轻观众的“地气”,就写他们的现实生活、现实心态,就真的有一个刘海皮,不做作,不浮夸,就这么说话,就这么面对生活的高高低低。人人心里都住着个海皮,我们想叫大家觉得,不管今夕何夕,在你面对困境的时候,甚至看起来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你心里那个海皮陪着你笑了——你并不孤独。
Q:那你们是怎么定义“年轻人的生活剧”的?
俞露:“年轻人的生活剧”这个标签是我们俩的一个原创。我们对它的定义很简单:第一,和传统的“婆婆媳妇小姑子”的家庭伦理生活剧不同,它表现的是以70后、80后为主的这一年轻群体的生活,不仅接现实地气,更要接他们的心灵和情感地气;第二,和传统的青春偶像剧不同,它不狗血不夸张,不是虚无缥缈的王子公主,是生活;第三,绝对是中国的,不是韩剧,韩国人做不来;第四,我们的观众群体除了传统收视群体之外,还包括以互联网时代之后的70后、80后、90后群体,也就是我们的观演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重视互联网、APP人群。
Q:你俩是如何收集相关素材的?毕竟你们都还很年轻,生活阅历有限。
俞露:其实也不年轻了,不过我们会尽量保持年轻。素材对于原创确实很重要。我们对这部剧里的年轻人——刘海皮,易爽,老贼,狗子,凤姐,方子……都很熟悉,不光熟悉他们的外部世界,还熟悉他们的精神世界。至于老头,主要就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素材,其实刘东岳的爷爷在世时就是这个病,患了七八年,其他相关素材我们也一直在搜集整理。
劉东岳:这里还要说到,因为写了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希望传递给大家的,对于这个病症的关心越来越多,有人甚至把我们当成该病的专家,来问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作为创作者,肯定是不能取代医学专家的角色的,我们只是素材的掌握者,属于自学成才,而且还要加工。
俞露:至于其他作品都要搜集素材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是每一个作者都会面对的一件事,而无论年龄大小。毕竟无论生活阅历如何丰富,总有不能到达、不能体验的地方。就像我们说知识和智慧的区别一样,素材,不仅是干巴巴地堆积知识,更应该是提炼过的智慧——那心灵的感悟、情感的触摸,设身处地的思考和体会,其实才是搜集素材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文艺和真实,是并行不悖的
Q:《嘿,老头!》这部剧最难能可贵的是既文艺又真实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在创作之初就定下的吗?是如何驾驭的?
俞露:文艺吗?其实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没想过有意把它写成一种什么风格,而是一提笔,就是这样一个路子。很多的与众不同,既来自于本身的设计,也来自于创作者是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因为我们的焦点是做“作品”,那就和手工艺比较像,就跟烧一个艺术品一样,烧出来就那么一件,不是复制一大堆,那它本身就肯定饱含着一种风格,好坏先不论,总之是这件东西就你们能做,做出来大家不仅喜欢,还有辨识度,不是那种跟风的东西——这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小追求。我们觉得,风格其实和品质有关,而不是说这件事情我倾注了很多心血,简直要被折腾死了,就是“良心品质”。真正的良心品质的关键是:不认苦劳,主要认功劳,那么用心做出真的有风格的东西,做出有口碑的东西,才算是品质的要害。
至于文艺和真实,其实恰好是并行不悖的。文艺这个词最近有点被“妖魔化”,文艺肯定不是虚无缥缈,如果一定要做个小注脚,那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真实)的感情,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然后才会具有一些心灵上的发现精神。发现什么?发现情趣,发现真实之中、真实之上的另一些东西,还有,发现情感,发现诗意。
刘东岳:补充一点,我觉得文艺和文艺之间也是不同的,是不可复制的。文艺不是一个标签,一贴上去那就是怎样的一个路子。比如我们这个《嘿,老头!》,它就是一个轻喜剧。文艺就不能是喜剧了?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文艺”肯定不是一个标签。
Q:在创作这样一部剧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刘东岳:作为原创,本子是我们自己顶着一股劲儿写下来的,没人约,也没管能不能拍。这样的创作方式当然有好有坏。好处是足够真诚,足够有空间和时间去闪转腾挪,去设计,去风格洋溢,甚至是去享受彼此相互拍桌子,吵得鸡飞狗跳的过程——当你觉得干不下去大不了不干了的时候,往往反倒都干下去了。坏处是它已经成型了,风格特点又特别显著,作为囫囵的亲生儿子,我们又特别爱他。导演接手二度创作的时候,有的动,有的不动,怎么加分,就有个和原剧本的对话问题。
Q:能否描述一下二度创作的时候是如何“对话”的?
俞露:不是知心人,是绝不会通过一个剧本而坐在一起的。至于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的协作问题,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心得:演员其实是沟通剧本和导演之间融合的关键因素。海皮是我们这个戏的灵魂人物,他的定位,其实就是这部剧的核心。杨亚洲导演对这部戏全情投入,就人物问题和我们之前反反复复沟通了很久。说句实话,拍摄第一天刘东岳在现场,看到黄磊老师和李雪健老师的对手戏一出来,房契一撕完,豁然一下子,导演、编剧和主演的心,才是真的心心相印了。没有好演员,之前阐述得再热火朝天,也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认为,沟通主创之间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从纸面上到活起来的角色。这部戏,我们的海皮,老头,还有易爽,他们一旦在人物塑造上对了,乾坤就定下了,整个剧本就被立起来了——我们的本子是条灯芯,他们是点亮这条灯芯的火。
Q:剧中人物的台词屡曝金句,这在国产电视剧中鲜见,也是被很多观众认可的地方,那些出彩儿的台词都是怎么写出来的?
俞露:这一点,刘东岳同志居功至伟。这些台词,看起来很有趣,很流畅,甚至最开始有人接到剧本说,一场戏四五页纸,叫人害怕,太长了。但结果拿过来一读,哗哗哗就读下去了。因为台词好玩,有层次,又有变化,又行云流水。
刘东岳:其实看着自然的东西,做起来最费功夫。写的时候为了找语感,特别是不同人物之间的语感,就要花很长时间,然后一句一句琢磨,一句一句写。就是不想写出很“水”、很没意思的台词来。也有人说,这些台词很“贫”。我们有一点不同意见。这些台词不是单纯地抖机灵、耍贫嘴,不是为了热闹,它们底下得有内容。比如,第一集开头,易爽(海皮喜欢的姑娘,宋佳饰)第二天要走了,两个人喝了酒,海皮在那儿贫,表面上听起来繁花似锦,好玩,热闹,但细琢磨就能体味出底下还有一层求之而不得的孤独况味。一个失败者对于自己的未来,多多少少有点恍然的东西,但是海皮不愿意在表面上愁,不然就没意思了,那个不是他。所以台词不是语言本身,是人物。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关乎于一个人物性格、心灵和情感的一种东西。海皮的“贫”,是来自于人物的贫。如果没有人物,那就是在说相声,不是戏。
俞露:幸好这一点上,刘东岳是我们两个人里非常具有天赋的。但有趣的是,在生活里,他是个话不多,哪怕说起话来,也比我要正儿八经很多的人。
作品不可取代的未必是技术
Q:两人在剧本创作中具体是如何分工的?
俞露:我们的创作分工也是边打边磨出来的,刘东岳的喜剧才华在这部剧中居功至伟,而我就像是定海神针。刘东岳负责把水搅浑,搅出个天女散花的可能性来,而我则是清道夫,多浑的水,也能叫鱼缸保持干净。
Q:作为典型性学院派,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把“学问”转化为“生产力”的?
刘东岳:我们双双出身典型性学院派,俞露同志甚至在中戏文学系待了十年,还教了几年书,按道理讲,应该大谈技术。但这个问题和我们的观念有关:我们觉得技术是有底子、出手就有的东西,就跟画画似的。但是有的作品,不可取代、夫复何求的未必是技术,而是其背后的灵魂。所以我们更愿意回到创意本源、回到作者的身份上来做作品。其实创作是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如果原创,那就更加地从无到有。把海皮、老头、易爽等等人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如果非要回忆创作过程,我们肯定不去忆苦思甜。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甜头还远得很;二是我们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人人都在吃苦受累,很多年轻人都有挨穷受饿的迷茫日子,那很正常,而且我们在做的是真正喜欢的事。所以,我们把一些想和年轻观众聊聊的真心话放在了海皮的身上:年轻人对生活要有态度,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往前走。
Q:《嘿,老头!》的收视与口碑俱佳,这样的成绩是你们意料中的吗?
俞露:没有意料到,但我们是尽力了。有杨亚洲导演,有黄磊老师、李雪健老师、宋佳老师在那儿,还有华录百纳,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成了,就说真的是运气好。我们想说的是,在创作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尽力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尽力了,剧本能让杨亚洲导演一眼看上,能让黄磊老师不仅来演男一,还带着钱来,直接当了制片人,还能请动德高望重的李雪健老师,打动貌美如花演技如火如荼的小宋佳老师,招来华录百纳那么强的团队。
刘东岳:其实在创作的时候,这些后来的运气,我们是一点点也感应不到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这个影视行业,越是一流的专业人士,越是对于好作品有着高度的敏感和热烈的欢迎。
Q: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创作方向?
俞露:我們的行业需要好作品、好项目,绝不是一句空话。所以下一步,我们还会坚持创意之路,坚持品质之路。至于心态上,其实对于作者来说,喧嚣不多,我们俩又是那种神经比较大条、自动清零的人,下一步其实就是从零做起。至于创作方向上,我们的风格化肯定还是会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擅长做这样的年轻人的生活剧,擅长做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