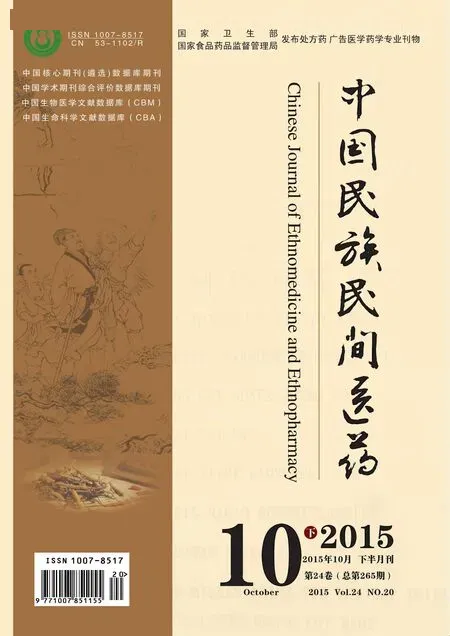敦煌遗书中梵文香药的应用探析
史正刚刘喜平辛 宝张 炜段永强
1.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甘肃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3.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4.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学术探讨
敦煌遗书中梵文香药的应用探析
史正刚1刘喜平2*辛 宝3张 炜4段永强2
1.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甘肃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3.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4.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香药通过丝绸之路和佛教的传入,纷纷涌入汉地中原地区,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地处丝路重镇,敦煌遗书真实记载了梵文香药在医方中的应用,梵文香药以单独组方、香药中药,交融配伍及广泛应用 “三勒”为特色。梵文香药的应用对丰富中医药学术产生了积极影响。
敦煌遗书;梵文香药;丝绸之路;应用研究
香药即香料药物,是一类具有芳香气味的药物,原产于古代西域诸国,即印度半岛、中亚、西亚等一带,故这类药物多以这一地区广泛应用的语言体系——梵文来命名。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交流日益频繁,香药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朝贡体制,纷纷涌入汉地中原地区。敦煌地处丝路重镇,撰著和抄写于汉唐时期的敦煌遗书[1],真实记载了梵文香药在医方中的应用。
1 丝绸之路与梵文香药交流
丝绸之路历来以丝绸交易而闻名,然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医药文化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和传播。这种交流在丝路开辟之后就已进行,如 《汉书·西域传》载:“宾有苜蓿大宛马,武帝时得其马,汉使采苜蓿种归。”李时珍亦称:“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可见,西汉时期内地与西域的植物、药物已开始交流[2]。迨至隋唐,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也步入了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的交流,使佛教得以内传和兴盛。起源于古印度的
原始佛教,自然科学成分在其中占较大比重,表现为对花、草、果、药等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香料药物则是其中的主要内容[3]。而梵文香药正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源源涌入中原地区,并为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4]。
考 《名医别录》首载沉香、薰陆香 (乳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苏合 (香)、紫真檀木等,梁陶弘景认为这些香很少入药,主要是供合好香用,而合香又主要是供进香者用。唐王朝颁布的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 《新修本草》,首次增录了许多来自西域及印度的药材,如密陀僧、诃黎勒、麒麟竭等,许多是以梵文音译的香料药物。李时珍 《本草纲目》引据书目中就有 《金刚经》、《金光明经》、《圆觉经》、《法华经》等佛教文献,并记述20余种外来药物的梵名[5]。
梵文香药的传入,对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白 《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就是其真实的写照。以至于盛唐时期的教坊乐曲中,出现了《苏合香》的曲词牌名,反映了中原文化对于接纳异域文化的开放、吸纳与融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梵文香药促进了中外多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医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如到了宋代由政府颁布的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大量使用香药组方,临床应用,可知梵文香药对中医药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敦煌遗书绝大部分属于佛教写经,中医药内容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医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等各科珍贵医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医学内容融佛医、藏医和道医等多民族医学为一体,以梵文香药组药成方的是其重要特色,见证了梵文香药对中医药的影响[6]。
2 敦煌古遗书的主要梵文香药
敦煌古医方以香药组方十分普遍,今以马继兴编 《敦煌古医籍考释》[7]、丛春雨编 《敦煌中医药全书》[8]和刘喜平编 《敦煌医方的理论与实践》[9]为蓝本,进行归纳总结,表明所载香药46种,相关方剂32首。其中仅P.3230(“P”编号,即Pellot Chinois Toven-hovang编号之缩写。该编号是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Paur Pellot窃取的敦煌遗书。下同)、S.6107(“S”编号,即Sir Auel Stein编号之缩写。该编号是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氏Sir Aurel Seejn窃取的敦煌遗书。下同)中的佛家香浴方应用香药就达32种,其中既用中文名称,亦用梵文中文音译名称,足见其交流融合特征。纵观敦煌遗书其应用频次较高的梵文香药如下表:
此外,在P.3230、S.6107中佛家香浴方中还有许多中医临床不常用的梵文香药如:苜蓿香 (塞毕力迦),合昏树 (尸利洒),枸杞根 (苫弭),松脂 (室利薛瑟得迦),零凌 (陵)香 (多楬罗),丁子 (索瞿者),婆律膏(曷罗婆),苇香 (捺刺拖),竹黄 (战娜),细豆蔻 (苏泣迷罗),茅根香 (嗢尸 [罗]),叱脂 (萨洛计),艾纳(世黎也),马芹 (叶婆你),龙花鬒 (那咖鸡 [萨罗]),白胶 (萨折罗婆)等。

中文名 梵文名 方源诃子 诃黎勒P.3731五香丸P.3378,疗发落方、疗人腹肚痛不止方、疗风冷热不调方、上气咳嗽方毛诃子 毗梨勒 P.3378,疗发落方、S.4329熏衣香方余甘子 阿摩罗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芎藭 阇莫迦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檀香 栴檀娜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香附子 目窣哆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青木 矩瑟侘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麝香 莫诃婆伽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藿香 钵怛罗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甘松 苫弭哆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郁金 茶矩么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菖蒲 跃者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雄黄 末捺眵罗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牛黄 瞿卢折娜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白及 因达啰喝悉哆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桂皮 咄者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芥子萨利教(杀)跛 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
3 敦煌遗书中梵文香药的应用特色
3.1 应用频次,首推“三勒” 在敦煌古医方中应用最普遍的梵文香药当属 “三勒”,即 “诃梨勒”与 “毗黎勒”、“阿摩罗”,亦称 “三果”。“三勒”为源自印度的三种植物果实,在印度医学中这三种果药有着广泛的医学用途,它们合用则组成三果药。其中 “诃梨勒”敦煌遗书中又写作“诃利勒”、“诃黎勒”、 “诃梨怛鸡”等,意译则称 “诃子”。另外敦煌遗书中还有 “诃黎勒皮”、“诃梨勒心”的记载。诃梨勒不仅在敦煌古医方中应用最为广泛,而且当时在敦煌寺院、官府乃至一般家庭都普遍使用。如敦煌遗书P.3850《酉年四月僧神威等碟残卷》记载某寺一次法会所得舍施物中就有诃梨勒;敦煌遗书P.3353《舍施文》记载道场舍施东西时,其中亦有诃梨勒;敦煌遗书S.5275《己丑 (929)应管内外都僧统为道场纳色榜》令受戒沙弥、沙弥尼等准例所税物中规定交纳诃梨勒;敦煌遗书P.4640《吴僧统碑》记载吴洪辩修建七佛堂时,“有僧王云胜,办诃梨勒二千颗,同助功德。”有学者认为诃梨勒是由粟特人带入敦煌的,并且粟特人将其入酒,胡酒可能就是指加诃梨勒等香药而酿造的药酒,敦煌遗书P.6292《酒帐》有粟特人纳诃梨勒的记载[10]。毗黎勒,又作 “毗梨勒”、“毗醯勒”、“鞞醯勒”、“尾吠怛迦”等,均为梵文音译词。毗黎勒的中药名称又称毛诃子,与诃梨勒一样均为使君子科植物的果实。阿摩罗,也是梵文的音译词,亦作“庵摩勒”,其中药名称为余甘子。以上 “三果”现已成为藏医常用药物,中医临床主要以 “诃梨勒” (诃子)应用最为广泛。“三果”在敦煌医方中的应用主要以除臭香身为主,如P.3230、S.6107佛家香浴方、S.4329及P.3877中的熏衣香方。同时,由于 “三果”甘涩性凉,故常用于治疗气血精津滑脱耗散的病证,如P.3378疗发落方、疗人腹肚痛不止方、疗风冷热不调方、上气咳嗽方等。3.2 梵文香药,单独组方 在敦煌遗书中存在许多大单独以梵文香药组方的医方,这些医方大多为外用方剂,如熏衣香方,集甲香、艾纳香、零陵香、麝香、薰陆香、安息香、青木香、沉香、雀头香、詹糖香、鸡舌香、苏合香、丁香等多种香药为一体,共奏芳香逐秽,调和气血,止汗除臭。用其熏衣物,可解毒杀虫。主要针对体臭不适,蛀虫损衣具有使身体、衣着芳香洁净、并祛除体臭的作用。又如敦煌遗书P.3230《佛家香浴方》与S.6107《佛家香浴方》中出现了以三十二种香药组成的方剂。
另外,敦煌遗书中的香药,在古代本草文献中特别强调要进行组合配伍,方可发挥最佳效用,如甲香,亦称 “流螺”。《本草纲目》集解:“颂曰∶海螺即流螺,厣曰甲香,生南海。今岭外、闽中近海州郡及明州皆有之,或只以台州小者为佳。其螺大如小拳,青黄色,长四五寸。诸螺之食之。《南州异物志》云∶甲香大者如瓯,面前一边直搀长数寸,围壳众香烧之益芳,独烧则臭。今医家稀用,惟合香者用之。”;艾纳香,《开宝本草》引 《广志》曰:“艾纳香,出西国,似细艾。又有松树皮上绿衣亦名艾纳香,可以和合诸香烧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而与此不同。”
3.3 香药中药,交融配伍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医方将梵文香药与产自于中原的中药材融合组方,体现了汉唐时期多民族医药文化在敦煌遗书中的交流融合。如P.3731中的“五香丸”以香药诃黎勒、麝香、沉香、丁香、青木香、薰陆、牛黄、雄黄、豆蔻与中药桃仁、升麻、当归、大黄、甘草、桔梗、槟榔等配伍,共奏温通开窍,行气化浊,治疗寒痰秽浊,闭阻气机的病证;P.3378中的“疗人腹肚痛不止方”以香药诃黎勒与中药当归、艾叶配伍,共奏温阳养血,散寒通脉,治疗血虚寒凝脐腹冷痛病证;P.2662紫苏煎以香药诃勒皮与中药紫苏、款冬花、桑白皮、桔梗、甘草、杏仁、贝母、通草等配伍以清泻肺热,化痰平喘治了肺病上气咳嗽,或吐脓血方P.3378上气咳嗽方以诃黎勒与中药、紫草、甘草配伍以清热止咳,凉血补肺治疗肺虚有热,气逆咳嗽的病证。
总之,敦煌遗书中梵文香药临床应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1]赵健雄.敦煌医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7.
[2]李灵祥.丝绸之路医药之路[J].丝绸之路,2000,44(1):57~58.[3]胡世林,唐晓军,王谦.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 [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6,2(4):5~6.
[4]李声国.重视佛教医学研究丰富传统医药内涵 [J].中国中医药资讯,2010,2(28):296.
[5]刘云,刘邦强,陈旗.《本草纲目》中梵语香药及其民间应用 [J].时珍国医国药,2007,18(3):725~726.
[6]刘喜平.敦煌遗书中的中医方剂学成就 [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3):75~76.
[7]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0~285.
[8]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22~586.[9]刘喜平.敦煌医方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10~213.
[10]郑炳林.唐五代敦煌医学酿酒建筑业中的粟特人 [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4,4(42):19~21.
R28
A
1007-8517(2015)20-0034-02
2015.08.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唐间多民族医药文化在敦煌医学文献中的融合性研究(12xmz008)。
史正刚,男,教授,研究方向:中医学。
刘喜平,男,教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Email:lxpd-25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