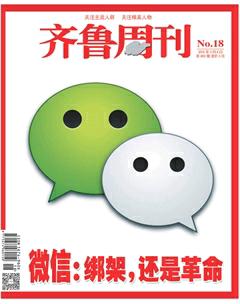微信潜规则与点赞政治学
周可
“社交媒体融入生活,这一切刚刚开始。”著有《虚拟幸福:新幸福阶层的阴暗面》的罗兰德·沃金说。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交工具,却越来越少地拥有一个真实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技术在一起,却吝啬把时间分给现实生活中的人?”
一位母亲,兴致勃勃约女儿逛街,女儿告诉她:只需把看上的物品拍下来发给她,微信支付即可完成购物。在这里,母女的情感互动简化为一种便捷却没有温度的技术。另一位繁忙的父亲,则建了一个小群给一家三口。起初,他会在小群里敲一句,“今天不回去了。”现在,他只有在要回家的时候,才在里面说一句“今天回去”。
“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技术在一起,却吝啬把时间分给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家雪莉·特克的疑惑。
1990年代初,她沉醉于网络聊天室和在线虚拟社区,写书庆祝网络新生活。20多年后,昔日的科技代言人变身科技反思者。
可以看到,在本质上,无论是微信、微博、图片分享,或是具备社交功能的手机应用,目前的社交网络工具仍然停留在探索和拓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不过,随着人工智能走进普通人生活和进一步深入应用,也许,科技让人类更孤独,将不再是一个伪命题。
新媒体观察者魏武挥说,“和弱关系相处久了,就会导致不会处理强关系。现在微信的用户很多都很年轻,他们不擅长处理强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不像上一辈那么密切。”
雪莉·特克采访到在同一张床上给对方发短信或者写电子邮件的夫妻。她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对此评论说:人们夜以继日地通过手机和电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社交网络繁忙喧闹,个人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孤立与疏离。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从未公开解释微信启动页面的寓意:一个孤独小人独自面对星球。人们乐意把它解读为微信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帮人解决孤独问题。但张小龙也承认,“通过技术解决不了人的内心情感需求”。
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交工具,却越来越少地拥有一个真实的社会。
约翰·卡乔波说,互联网只允许虚假的亲密。在《孤独是可耻的》中,他描述,“养宠物,结交网上朋友,是天生群居动物为了满足强制需求所做的可贵尝试,但是替代物永远无法弥补真品。”“真品”是指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与这世界相处的方式出现了问题,但我们又不知道如何解决。
微信的言行潜规则与点赞政治学:我们离世界更近,离现实更远
“当我们哭泣时,需要的是一个肩膀,而不是一条信息。”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邮件采访时,如此形象地描述社交网络与人的关系。
被鸡汤段子刷屏、被代购信息骚扰、被“美颜”照欺骗……微信朋友圈中大概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最近,网友自发编撰的“微信朋友圈礼仪规范”,在微信中被争相转发,部分条款引起大家的共鸣。
“每天发贴数量保持在10条以内,避免刷屏打扰朋友圈、避免发布比朋友圈大多数人生活质量高出一大截的炫富帖、一日三餐最多晒一餐,夜宵例外,聚会例外、发朋友圈应该彰显个人品位,反映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富足和精神文明……”
同时,朋友圈里的“点赞”,成为维持友情的一种低成本投资,也成为办公室的线上“纸牌屋”。
“点赞应本着礼尚往来、及时满足好朋友虚荣心的态度,积极点赞。评论应彰显诚意,避免单纯的笑脸等表情,典型评论案例如:小宝宝好可爱哦,哇美女,你真是天生的衣服架子,美女你好勤奋哦,加班注意休息,祝大卖等……”
大卫·梭罗说,社交是廉价的。他独居在瓦尔登湖边,偶尔观察两只蚂蚁在打架,他所描述的是惠特曼时代自然主义的美国。
互联网革命带来人类全新的文明和生态,意味着物质对人类的行为束缚日趋在削弱。我们通过电脑完成信息传递或者信息获取,这意味着物质形态变化了——我们不要纸、不要笔、不要剪报——我们只需要网络。如此重大的变化让我们理解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个普通的咖啡馆,一杯咖啡几欧元;而在另一个有概念有故事的咖啡馆,一杯咖啡十几欧元,你在喝咖啡的同时在咖啡馆里穿越了历史,重温了一个时代,体验了很多故事的感觉,所以十几欧元你也觉得很值。
微信时代在滋长个体最重要的观念,人类失去了共同相处的坚固土壤。当一个社会涌现出各种各样观点的时候,这会导致我们越来越多共识的丧失。比如说那些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信仰标准,这些共识可能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人文学者的参与,只有技术派在炫耀的时代会是可怕的。
一种新的社会性格——
我们时代的微信孤独症
不到4年时间,微信在中国的月活跃账户达3.96亿。一个人时、聚会时,在车上、在路上,在睡前、在醒来后,人们争分夺秒地刷着“朋友圈”, 现在新机器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一种新的社会性格正在形成。在中国,这种社会性格,有一个新名字:微信依赖症。这种依赖症背后,在社会学家们看来,是一种孤独的症候。
□方言
科技的文明悖论:“通过技术解决不了人的内心情感需求”
埃里克·兰纳伯格说,“每个时代人们都会感到焦虑,但这种焦虑常常伴随新的沟通技术出现。”
一个网络段子:“每天早晨,人类从微信中醒来,不刷牙、不洗脸、不下床……第一件事,用各种各样的安卓、iOS、iPhone、iPad、三星、HTC、联想、OPPO……奔向同一个App:微信。每参加一场活动,添加微信号成了标准动作,传统的名片退居二线。
根据微信官方数据,不到4年时间,微信月活跃账户达3.96亿。公众号数量超过了580万,日均增长1.5万。庞大用户的活跃,让微信估值飙升,里昂证券亚洲4个月前在报告中估值,说微信价值已达640亿美元,三倍于Facebook收购的WhatsApp。
微信让许多人患上了这种新病症:微信依赖症。严格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灶,一种社会性格和习惯的形成。一切微小的信息和图景充斥在我们的朋友圈:恋爱不再甜蜜,上床不再仪式,宏大被解构,无聊被消费,上下半身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进写满欲望的商业江湖。
“我一生中遇到过成千上万个身体,并对其中的数百个产生欲望,但我真正爱上的只有一个。”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写道。就社交意义而言,今天的微信和那时候的聊天室、QQ没什么不同,只是它在产品上做到了极致,让你可以有足够多的机会和陌生人发生联系——这种根植于中国土壤的商业模式,就连硅谷也学不会。
过度频繁的联系让人产生习惯性的心理饥饿感,“总担心错过什么,总担心失去什么。”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说,“我们联系别人不仅是为了减少焦虑,也是在追求一种存在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的学术著作《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竟然风靡一时,击中了人们在机器时代的脆弱内心。
现在新机器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一种新的社会性格正在形成。在中国,这种社会性格,有一个新名字:微信依赖症。这种依赖症背后,在社会学家们看来,是一种孤独的症候。
当社会被科技文明分解掉之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启蒙时代的莱辛说——所谓自由就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是对自由本质的最朴素的表达,即使是“末路骑士”堂吉诃德,“出门”也是他最重要的标志,理想在召唤他。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受的制约更日益在减少。比如工作可以不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状态,自由支配时间;比如以前几千公里距离,必须骑马一步步走过去,当你拥有了工业时代的交通工具,空间距离被压缩了,日行千里不是问题。
可以说,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完成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次“云的飞跃”。
这是一个真正的个体时代。你爱吃的餐馆,你喜欢的东西,你经常去的地方……只要你需要,各种信息都会因为你重新组合向你涌过来,你需要的生活会时刻向你“扑面”而来。
一个城市智能系统,使一切的东西有效纳入到你个人的需求系统当中,为你服务。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一座城市,一千个人有一千座城市。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如此下去,你不太会为别人的生活所感动,也不愿意为别人所付出,不愿意参与到别人的生活中去。
当个人化到达极致的时候,这个城市没有他人,他人只是数据。曾经,城市的魅力在于大家有公共空间,可以共同享受一些东西或者创造一种共同价值。我们要有一起集会、一起看戏吃饭的地方。将来,群体生活就是网络上的生活,所以回到现场,听场音乐会多么重要,和朋友在外吃饭多重要……这些都会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
微信时代社会的共同性变成了小圈子性。社会变成一群群人、一堆堆人,当社会被这种方式分解掉之后,人会出现物种退化的情况。
本来社会该有各种重合点,有公共性的存在,现在社会的共同性变成了小圈子性。欧洲曾经辉煌的原因在于欧洲各种族之间通婚,多元化的交融产生了优秀的人群。
社会变成一群群人、一堆堆人,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当社会被这种方式分解掉之后,最终会导致人类某种可怕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