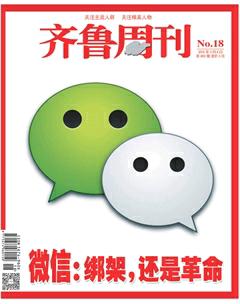收获的游戏:自然物产与自然偷盗
农村游戏的消失,预示着农村童年秩序的崩塌。这种秩序建立在土地之上,它之所以崩塌,是因为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不再亲厚。
这其中,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其中一个原由,但更重要的是,农村自生的人文美学,在功利十足的城市化浪潮里,不断地衰弱和自卑。
大院子弟回忆童年,总是要讲一些逼格很高的事情。比如说王朔,“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看什么吗?总参作训地图!”普通市民回忆童年,则免不了老城区,大杂院……像我这样的农村子弟回忆童年,勉强能提一提的便是那些年,在山河麦田里玩过的种种游戏。
这种游戏不是学校里规规矩矩的小把戏,而是发生在旷野里的胡作非为。
游戏是分季节的。因为每种游戏都需要季节里的物产和风景相配合。
对孩子而言,春天不是特别好玩的季节,尤其是早春,大地一无所有,只有阵阵黄风掠过孤寂的村庄。
这种平静的萧索需要一种特别的游戏来打破,那就是“放火”。
那时,冬雪早已消融,小河里的水量降到了最低点,岸边全是大片大片枯黄的野草。带上一盒火柴,你能看着火烧到很远的地方。
如果放火是在夜晚,那简直会产生一种打渔杀家、火烧连营的历史幻觉:星星之火映衬漫天星辰,而水面又像镜子一样将这一切截取下来……
当然,即便是在农村,这种行为也是不被鼓励的。老人们这样谆谆教导:小孩子不能玩火,玩火会尿炕……
一场春雨过后,大地开始渐渐温柔。或许记忆总是选取一些美好的东西存储,在我印象中,每年春雨到来的时刻,总是会在夜晚听到植物生长的声音。
极风雅的时刻到来了。一夜之间,柳条舒展,桃花开遍了河岸。在春天的暖阳下,半大的孩子便会去河里摸鱼。也没有什么钓具,只用一个罐头瓶子泡上几粒馒头渣,扔到水草茂盛的地方,不一会儿,便会有一些小鱼钻进来。
鱼都不大,一上午最多也就只能钓一小碗,裹上面糊炸了吃,很香。
一天的时间,只有这点收获自然是浪费大好春光,所以我们在岸边搜寻茅草芽,它类似于一个极小号的带皮青玉米,里面是白白的芯,吃起来略带清甜,诸城土话叫它为“扎银”。
当然,一些摸鱼高手是不屑这些小打小闹的。他们赤脚下河,空手便能掐出近半尺长的“大鱼”来,用柳条一串,举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在天光下过街穿巷,骄傲地如同战胜归乡的将军。
他们是孩子中的英雄,能下河摸鱼,能从很高的树上折下挂满榆钱的树枝,能从看似一无所有的土地中寻出地瓜和胡萝卜,还能在冬日的雪地里,带上黄狗撵野兔。
他们的骄傲源于收获。收获是一种最古老的人类仪式,从中生发的笑容则是最古老的人类表情。如今,我们已很少看到这种表情,因为我们失去了某种来自远古的技能,这种技能拒绝投机,是我们肢体最初的荣誉和骄傲。
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收获,那就是偷。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农村少年,都有着偷瓜摸枣的经历,在讲起这些行为的时候,心中也不会有太多的愧疚感。
盗亦有道,孩子们的偷只限于土地上的物产,它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不过是在游玩的时候,看到田里翠绿的西瓜,便去偷一个来解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更像是一场学习生存的自然偷盗,是在未知土地上的一场冒险。
当然,有时候也会被看瓜人抓住,狠一点儿的,便扒光这些七八岁孩子的衣服,然后通知家长来领这些“光腚猴子”。家长到了后,通常都是怒不可遏,劈头盖脸一顿打,看瓜的人便会劝住家长,如此这般地讲一番,最后又硬让孩子带上几个西瓜走,当然,家长一定会满面羞愧地放下钱,看瓜人又一定会追出来把钱再塞回去……
这是一种乡邻式的惩治程序,有一点儿滑稽,但程序完备,仪式十足。
作死的游戏:英雄荣誉以及孩子群中的角色选择
除了这些关于收获的游戏,我们还会玩一些“作死感”十足的游戏。
比如夏天去河里洗澡,从很高的拦河坝上一跃而下,跳进下面十几米深的水中。姿势掌握好的话,水花较小,自然会迎来一阵掌声,反之,肚皮或者脊背就会平拍在水上,甚至会有被拍晕的可能。
那时,我们还玩过一种更“作死”的跳水游戏:十几米深的大机井,抱着分量很重的石头跳下去,为的就是能够潜到最低处,然后抓一把井泥上来。
这些行径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跳烟筒的行为有些相似,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把叛逆视为英雄壮举,把“作死”当成荣誉勋章,可惜并没有女孩旁观。
几乎是每一年,我都会听到有小孩淹死在河里的消息,学校和家长对下河洗澡一事严防死守。每次游玩回家,爸妈都会用指甲在我手臂上划一下,如果显出白色印记,那肯定是又去洗澡了,于是便免不了一顿打。
每个游戏都会聚集起一大帮孩子。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孩子王,他精通所有的技艺,除了念书,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每一天都能想出一个新的玩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圈子中,学习好并不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它无助于增长你在圈子里的威信,只意味着一种柔弱胆怯和面对自然的无能。
那时候,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于是便在伙伴中有些自卑,这让我不得不去做一些更危险的事情来证明自己。
有一年夏天,我们正在潍河里洗澡(我一直不用游泳这个词,游泳是在池子里,是城市孩子们戴着救生圈玩的把戏。),忽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抬眼一看,黄色的水浪连着天际,席卷而来。河堤上的人大呼:墙夼水库放水了,大家快跑啊!
我跟着队伍跑了几步,不知怎地就觉得有些羞愧,于是便停了下来,双手叉腰,看着即将到来的水浪。
水声越来越大,伙伴们已经跑上了堤坝,他们在喊什么已听不太清,但我向他们大喊一句:操!你们不行!
为了这种“作死”式的装逼,我还背诵了一段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这些都做完后,才装作不紧不慢的样子向岸边走去。
那时候,我怕的要死,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铺天盖地的水。上了堤坝之后,大家看我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了,带我出来玩的堂哥先是揍了我一顿,然后又把此事告诉了我爸妈。结果可想而知,又是一通胖揍之后,我还迎来了将近半年的禁足期。
作死之后,我也迎来了一个对孩子而言极其重要的收获:从那以后,我不再是堂哥的小跟班,而是孩子群中名副其实的“三巨头”之一。
他们像姑娘一样安静
狭义上的童年游戏有很多,比如撞拐、弹玻璃球、“打元宝”、过家家,这些游戏至今仍在延续着,但我所讲述的那些关于收获、关于“作死”的游戏却几乎消失不见了。
即便是我们这些生于八五前的一代,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也开始不自觉的淡化身上的野性。
从那时起,孩子们开始分流。街机、网吧的兴起让一帮孩子沉迷其中,升学的压力又让另一帮孩子足不出户。而我的堂哥,彼时名震乡村的孩子王,在这种潮流面前,孤独寂寞,无人诉说。
从初三开始,他就辍学了,而我则不得不去实现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这是我父亲的梦想,起码在最初时候,它不属于我。
我们之间开始变得陌生。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他在一棵榆树上摘榆钱,树下围着一群小他很多岁的孩子。他向我打招呼:哎!上来玩啊!
“不玩了,一会儿还得去上课。”
他笑了笑,挥手让我走。没走多远,一株挂满榆钱的树枝丢到我身前。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召唤还是一种告别,我只是捡起树枝,向他挥了挥手,继续走开。他吹了一句口哨,旋律大概是《真心英雄》。
或许从那时起,我们就走入了不同的世界。从此,我的世界逐渐通往城市,而他的世界在某种不可抗力之下,也变得面目全非。
如今再回到农村,我发现,不论是街道上,还是田野间,成群结队的孩子几乎不见了。他们大都规规矩矩,无论对人还是对田野,都带着一种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冷漠。
“其实孩子们聚到一块儿挺有好处的,这对他性格的发展,以及未来在团队中的角色选择都挺有好处的。”我对堂哥说。
“……现在住在村里的年轻人本来就少,都去县城买房子了,小孩自然就少,聚不成堆了。”堂哥这样跟我说,他的儿子坐在一旁玩着电脑,安静的像一个姑娘。
“就是想出去玩也没什么可玩的。小河早就断流了,苇子地也没了,大树也都被砍了,潍河全是挖沙炸鱼的,到处都是险窟窿,还有什么好玩的。”
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了,所以,孩子们只能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此时,电脑已经普及到了农村,他们熟练地打开网页,但当你注意到他们时,他们又赶紧关掉,盯着XP系统那张经典的蓝天草地图片,那是他们父辈们曾肆意玩耍过的场景,而他们视若无睹,装作发呆。
(丁爱波,《齐鲁周刊》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