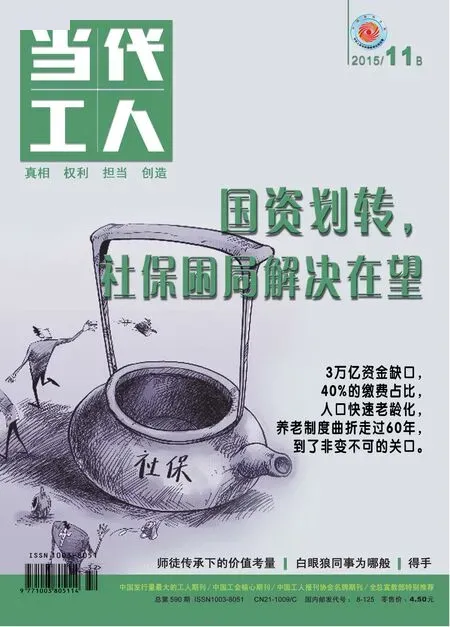留学青年胡深明:我不想死在体制内
文/青阳
留学青年胡深明:我不想死在体制内

文/青阳
第一次看见胡深明时,他正在做圆桌发言:“虽然国内都说日本怎么不好,但是东日本大地震那次(2011年3月),我感觉……”他稍作停顿,看了台下一眼,“日本社会还是挺好的,非常有秩序,每天免费给民众发饭团。”
那是五四青年节的前一天,浑南区团委组织了一批留学青年做主题发言,胡深明曾留学日本,故受邀参加。他讲话的工夫,台下端坐着沈阳市和浑南区的几位领导。
民间反日情绪浓重,又是在政府官员面前,这么说好吗?我暗自忐忑。“不管下面坐着谁,我都会这么说。”胡深明一脸轻松,“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呀!”
这就是他的生活状态:真实,放松,不做作。与那些绷紧神经的年轻人相比,他活得很自得。更让我吃惊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千方百计往体制内挤时,他却主动辞去了令无数人羡慕的工作。
因为这次转身,这位31岁青年的青春,有了一抹异人的色彩。
少年有天赋
胡深明学的是电子信息自动化专业,也就是常人所理解的机器人控制。当年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他戏言是“误以为自己有天赋”。
高二,胡深明被学校选中参加全国物理竞赛,一举获奖,“全本溪市也没有几个(得奖的)”。老师的赞扬、同学的敬佩,让他倍感振奋,“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天赋。”
彼时,大多数学生对未来之路还懵懵懂懂。老师建议胡深明,报考大学瞄准物理学科的自动化方向,他深以为然。“就这么上道了。”
2003年,胡深明顺利考上辽宁大学自动化专业。编程、电子电路,很多人眼里枯燥无味的知识,他却学得很愉快。“觉得挺有创造性的。”经过两年打基础,他开始驶入学习的快车道。
家里有位亲属专门做产品研发,水平颇高。胡深明跟着亲属,写程序、画电路图、焊电路板,软件硬件一起学。一年多的时间,原来书本上模糊的知识,一点点变成可触及的操作,胡深明提高很快。
他还未满足。大四开学伊始,他就跑到招聘会上求职,“我觉得应该到企业里锻炼一下,检验自己到底掌握了多少。”并非盲目寻找,胡深明选了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家下属企业,投出简历。“它起点比较高,能学到更多东西。”
他开始一年的实习。企业经营的产品是焊机,用在汽车生产中的点焊,技术高、难度系数大。作为实习生,胡深明只能做最基础的工作:焊接机器主控板,“这是进企业的必修课。”早8晚5,他跟正式员工一样奔波在学校和企业之间。
当然,学校的学习不能落下。实习进行到一半时,胡深明请假回校复习考试,深夜挑灯抱佛脚,居然顺利通过,“好多在学校上课的同学挂了。”至今说起,他还有几分得意,“这算是有天赋的表现吧?”
一年实习期未满,胡深明决定继续考研深造。经历了实战,他觉得自己书读得不够、见识得也太少。“在这种高精尖企业里,本科生的生存空间太小了。”
他瞄准了日本的大学。
求学并不易
当下,中国被誉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不过,中国制造占据的多是中低端行业,日本却一直占据着高精尖行业的制造优势。特别是其机器人技术,可以说称霸全球。而在背后推动日本机器人技术发展的,正是各大学的项目研究。
胡深明选择了筑波大学。这所学校位列日本大学前10名,机器人研究非常顶尖。2007年,在国内学习一年语言,翌年胡深明东渡日本,奔赴距离东京东北约50公里的筑波市。
这里,仿佛是科幻电影里的未来世界:形形色色的出行辅助机器人、机器人套装,在街头随处可见。“筑波市被日本规划为机器人城市,允许机器人上街。感觉挺震撼的。”
按照日本大学制度,胡深明要读一年预科,在准备报考的导师实验室里学习。预科结束后,通过入学考试、导师讨论允许后,方能正式入学。
他的求学之路差点在这里终结。“这个导师对中国人有点偏见,老爱训我们。”与胡深明一起准备考研的还有其他4名中国学生,在实验室里挨训是家常便饭。
胡深明小心翼翼,尽量不触碰导师的脾气。但麻烦终究躲不过。有次导师找他谈话,让他学习一门基础课,并写一份学习心得。
心得交上去,导师声严色厉地训了他一个小时,“说我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胡深明觉得挺委屈,“我都没有正式入学,而且你也没指导,一个学生怎么提出观点?”
导师的一句话差点把他吓倒:“他说,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的入学问题。”当时,距离胡深明入学考试仅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如果被导师否定,即便考试通过他也无法入学,只能再读一年预科。后来的一周里,胡深明几乎夜夜失眠,不知该如何是好。
好在胡深明比较乖巧。他找到老师自我批评,说时间紧张,以后入学一定认真学习,争取提出观点。他最终得以入学,而其他4名中国学生未能如愿。
入学后,导师的脾气依旧,胡深明细思极恐,“以后能不能毕业都不一定呐!”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换导师。他向校内一位副教授提出了申请。日本社会很重视同事间关系,这位副教授怕得罪同事,不敢答应。胡深明一个多月里与对方恳谈了四五次,最终打动了老师。
“他挺同情我的遭遇,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进入体制内
自此以后,胡深明的学习一帆风顺。他在日本经历的最后磨难,就是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
那天,春和景明,胡深明正坐在自习室学习。突然间,地动山摇,“像是万马奔腾的声音。”地震后,学校停水停电,他和同学们挤在体育馆里避灾,每天只能靠社会组织发放的饭团和矿泉水度日。
很快,新闻爆出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胡深明回国待了一个多月。当时,很多学子都没再回去。父母也劝胡深明,“日本要完蛋了,还回去干啥?”他有主见,“这么作难才考上,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2012年夏,胡深明学成归国,他求职第一站是首都北京。投简历,面试,笔试。跟所有学子一样,他在偌大的北京城中穿梭往来,追寻属于自己的未来。
凭着留学经历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胡深明很快获得了本田中国的工作机会。但他略作考虑,放弃了。“就是觉得在北京生活太压抑了。”
到北京后,胡深明暂住在回龙观,而他面试的公司大都在国贸附近。每天早早起床,地铁13号线换2号线,单程就要在地下穿行近两个小时。“生命都浪费在路上了!”在老家本溪,他习惯傍晚在街上溜达。可在北京,公交站牌上两站之间的距离,没有半个小时根本到不了,“走路能累死人。”
胡深明到了沈阳,他首选的目标是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历史久、牌子硬,而且曾在其下属企业工作,渊源深。他如愿以偿。
他被分到一个科研项目组,负责制作潜水器。这是军工项目,工作强度大,而且常要出海试验。工作几个月后,胡深明开始了海上生活,“短的两个月,长的大半年。”吃住都在船上,他晕船,那也得咬牙挺住。
辛苦尚在其次,船上作业还伴着危险:潜水器由吊车放到海面,科研人员从几十米高的大船爬上橡皮艇,把吊扣解开后潜水器才能正常入水。这上船下船中,风起浪涌、潮湿打滑,稍有意外就会落海。“那后果不敢想!”
这份令很多年轻人渴求的体制内工作,背后也有难言的辛酸付出。
风景在远方
工作一年多后,胡深明提出了辞职。并非是怕吃苦,他始终希望自己研发的作品能便民利民,而不是制造武器。“跟我的价值观有差别。”
接到他的辞职申请,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很不理解,“多少人都进不来的单位,你咋想的?”胡深明含糊说不适应,对方瞪了他一眼,“死也要死在体制内,懂吗?”他差点乐出声来。
胡深明不想死在体制内,他觉得,青春还有更多令人向往的方向。
2013年秋天,他进入沈阳何氏眼科工作,负责医疗器械研发。选择这家民营医院,胡深明有自己的考虑。“在大企业,你只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如果放低一个层次,对未来发展也许会更好。”他笑着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一切从零开始。成立新部门、装饰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分配工作助手,胡深明看着部门一点点成形,“特别有感觉”。让他感到自豪的还有何氏眼科的理念,“一年有一半的手术是公益项目,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
何氏眼科有自己的大学。眼下,全民创业是热潮,而早几年前何氏就提出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胡深明一边做研发,一边给学生代课,还要带着学生搞创业,忙得不亦乐乎。
何氏的教学传统,课堂上提出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解决方案。很多关于产品的新点子,就此产生。“90后的孩子脑子快、点子多,老师主要是帮他们把想法落到实处。”
短短两年时间,胡深明已经带着学生做出了3个产品:手持式(眼镜)蓝光滤出检测仪,粘贴式蓝牙体温贴,和治疗干眼症的润眼仪。其中,蓝牙式体温贴在辽宁省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斩获金奖,蓝光滤出检测仪获得辽宁省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特等奖。“这可是高手如云的大赛,特别不容易!”胡深明笑起来,一脸的满足。
他告诉我,这些产品陆续会量产投入市场,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会让我觉得很骄傲。”他说,如果还在体制内造武器,这种喜悦一辈子也体会不到。
至今,还有亲戚对他当年的辞职举动耿耿于怀,胡深明笑着说:“也许他们不理解,我觉得正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