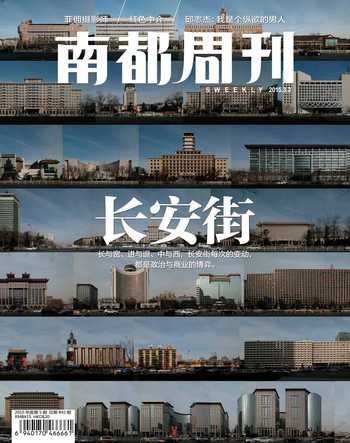地水南音,如花邂逅十二少
谢秋如

地水南音,据说从清末开始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粤调说唱。演唱者多为失明艺人,时至今日,地水南音已几成绝唱。
“这里以前整条街有五六间曲艺茶楼,我就是在这里一边摸着路一边听,穿过小巷又响起别家的收音机。”77岁的莫若文靠老伴梁姨搀扶着前行,一边带着我穿街绕巷。这里是广州的惠福西路,如今已是成行成市的电子电器批发市场,人声鼎沸。
或许因为4岁就开始失明,莫若文口中的惠福老街都是听觉的世界:榕树下“讲古”(说书)、街边自行车的“叮叮”铃声、卖花生卖蚊香的吆喝声、茶楼上纷扰的人声,还有茶楼上传来的琴弦声和南音唱曲。
地水南音,据说从清末开始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粤调说唱。演唱者多为失明艺人,又称瞽师或瞽姬,广州尚存地水南音宗师何世荣的“荣腔”的传人莫若文,58年来坚守在越秀区光明曲艺队。
“现在还有多少间茶楼有唱粤曲的?”我问。
“没了,剩下一间是维也纳大酒店,三楼才有粤曲团在唱。以前我卖唱的茶楼就剩下一间得心茶楼,都没有唱曲了”。他说完还一直重复那两个字:“没了,没了。”
《胭脂扣》里的南音往事

“你睇下夕阳照住个对双飞燕,我独倚在篷窗我重思悄然。耳畔听得秋声桐叶落,又见平桥衰柳锁寒烟……”香港电影《胭脂扣》里,如花和十二少在烟花巷里邂逅,唱的便是“南音”的名曲《客途秋恨》。此南音有别于《左传》中的楚声南音和《古今乐录》中的吴歌南音,而是特指产生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珠江流域的歌乐。
地水南音是南音曲种中极具特色的一种,“地水”本是卦名。因乡间一般的瞽者,都操卜卦业,故把卦名作为对盲者的别称,人们把由失明艺人演唱的南音称为“地水南音”,演唱者被称为瞽师或瞽姬。莫若文,是地水南音宗师何世荣的“荣腔”的传人。他今年77岁,经常身穿着白色衬衫和西裤,头发花白,身体健朗,戴着墨镜,声音低沉沙哑,但铿锵有力。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惠福路、海珠路、西关那些凉茶铺和茶楼,不仅有茶喝,还有曲听。五分钱一盅茶,有曲听的时候就售一角,他们喜欢称之为“叹茶”。那时何世荣是惠福路茶楼上的明星。他从澳门归来,身穿西装,一张口,唱腔丰富,低音雄浑厚重,风格柔中带刚,《祭潇湘》《韩江悼六娘》等是他的名曲,红极一时,往往表演时间一打出,票就售罄。莫若文也是在这时听到了何世荣的名字,当时他才十来岁。只要何世荣来,他就风雨不改地蹲在凉茶铺外听曲,也暗暗下决心:“我也要学艺傍身,总好过像其他盲人那样上街卖花生、卖蚊香吧。”
拜师之路并不容易,这是艺人们维系生计的“饭碗”。莫若文便到处听曲,听收音机里的唱曲。那时收音机还很珍贵,一条街只有一两户人家有,莫若文就这样,每当传出曲声,他搬张板凳坐在人家门口外听,摸索着缪莲仙与麦秋娟的《客途秋恨》、男客祭奠妓女的《男烧衣》的唱腔。莫家家境并不好,刚向刘剑青师傅学了三个月就只能作罢,后来他在三轮车工会上认识了著名瞽师杨炳昆。杨炳昆家境富裕,人热心,教授了莫若文不少唱曲的腔调和琴艺上的经验。莫若文没有读过书,只能加倍努力自学,清早起床,还未漱口洗脸就开始念曲白、口簧。盲人学琴艺需要老師手把手摸着弦来教,节拍则用手指尖敲击琴身作响。曲白跟着念要念熟上百次,曲句熟了再学唱腔,腔调的变化很多,他通常根据曲词的情感琢磨了好几种腔调。刚学新曲那段日子里,他有时半夜睡不着觉,就起来关门窗练习,“我本来是卖歌人出身,其中的凄惨身世会融到里面。初初唱《失明卖歌人》想到自己还会默默掉泪。”

机会来临。1958年前后,他通过考试,被安排到何世荣的失明曲艺一队。何是队长,他发觉莫若文的潜质,于是倾囊相授:“荣腔的唱法,关键是怎么去运腔,有些拉腔干脆有力收住反而更好。”还有何世荣最为人称道的“四线秦琴”技艺,是在琴弦靠近底部的“线脚”位置能弹出模仿各种打击乐器的声音。弹唱者既要拨着琴弦弹奏,又要兼顾着用琴打节拍,这对盲艺人的技艺更是一大挑战。说罢,他随即唱着作曲家刘荫慈为何世荣作曲的《今昔歌坛》。只见莫老正襟危坐,左手熟练地来回拨弦,右手抚椰胡,双脚夹紧椰胡的圆筒身,左脚跟着曲子打着节拍。“最怕年华渐老容色不美,受那包家冷落无能献歌声。捱饥、捱苦、捱冻!想起往事有恨说不清,常自叹,一身好似逐浪浮萍。”椰胡低缓,伴着他低沉浑厚却又沙哑的声线,不时用苦喉哭腔一声叹,抑扬跌宕,如泣如诉。
搭着肩膀上船的夜晚

第一次上茶楼卖唱,年仅14岁的莫若文,站在茶楼一角,献唱何非凡的“凡腔”《虎啸毒龙潭》和《红花开遍凯旋门》。唱完了,明眼人会帮忙牵着他,拿着碟子到每张茶桌去领钱,往往仅仅挣得一角几分,百般滋味上心头。少不了的,还有茶楼的驱赶和听众的嘘声,甚至恶言相对。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次数多了之后他学会看淡,练就了属于他们与“开眼世界”打交道的人情世故:“忍让点,懂得礼貌,不用理会那些闲话,就不易吃亏。”他小心翼翼地在桌上摸索着茶杯,喝了杯茶,“毕竟还是好人多,同情我们的人多。”
后来,曲艺队演出的盛况让莫若文他们初次尝到了甜头,何世荣带领着他们到处演出,“几十间戏院曲艺场轮着上台,新华戏院、河南戏院啊……每周表演一次,月收入少则也有四五十块。”除了固定演出,逢“七姐诞”、中秋等节日还要去到南海、番禺、顺德等珠三角的下乡演出。当时在珠三角交通不便,水路小艇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为了赶场,起早摸黑是常事,还要半夜两三点赶着上船,码头却没有灯,一两个明眼人领着他们六七个盲人,挨个排着队搭着肩,顺着窄长的船板一步步挪到船上,一个稍不留神就会连累全部人掉进海里。
“这么多年都没有掉进海里,真是求得华光师傅保佑啊!”莫老家里供奉的神灵是华光师傅,即“戏神”马天君。据说初时广东人作戏不避忌讳,得罪上天,天神就命马天君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戏台烧毁。马天君不舍,于是就托梦,教广东各戏班如何祭祀,不要触怒神灵,从此各梨园平安。
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开始,曲艺队被迫解散,何世荣屡屡受到批斗,莫若文和队友们被安排下厂做工。但也有禁不住的欲望,“那时只给唱刘胡兰、唱雷锋,有人偷偷请我到他家里唱古曲,紧闭上门窗,生怕被人举报。”那段时间,莫若文和老伴梁姨生活困苦,一个月只有26块,还有一个女儿需要供养。下了班,他就去卖唱卖花生,帮补家庭。梁阿姨一路跟随,如今不知不觉已经度过了51个年头。

怨、忆、苦,逃离了就不是南音
“文革”过后,何世荣因病逝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曲的涌入冲淡了人们对粤曲南音的热情。重组的“越秀失明曲艺队”从专业演出变成了业余私伙局聚会的性质,近年已经到了将近绝唱的境地。2012年,越秀区政府将这特殊的曲艺队挽救了回来,保证他们的退休金和残疾人补助,并改名“光明曲艺队”。2014年又将“荣腔”推荐为越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线索。
莫若文接过了队长的接力棒。现今队员里剩下七人,全都是视障人士,其中称得上瞽师的,还有李广生、郑建明、刘志光三人。年龄最大是80岁的李广生,去年突发心衰竭入院;郑建明最年轻,60岁,是“荣腔”的第三代传人,最近糖尿病住院了;刘志光也68岁了。莫若文并没有停下来,这些年他培养了不少学生,“有视障人士也有明眼人,大多数是退休人士”。
每逢周二下午都会有三两个学生去他家开“私伙局”,和他鼓捣起乐器,唱唱粤曲。“起板啦!这首叫做《初遇诉请》。”“嘀”一声用脚打着节拍起板,莫若文便熟练地弹起手中的班卓,身边的盲学生邝炳光端坐着,手中高胡伴奏起,女学生黄玉玲边弹着月琴边唱:“我感怀身世不觉暗自凄然,那风筝,可叹佢摆布由人。”莫若文停止了伴奏,说:“这句腔口不大好,你试试这样停顿,这样拉腔。”然后他示范了一遍,再重新开始。他总是强调抓好节拍,“心中有节拍,就能够边弹边打,这才是我们地水南音的本事。”黄玉玲跟了莫老学习11年,听得师傅教导,一次次重来。
“他骂了学生后自己也难受,但他说不骂学生又學不精。不过看到现在有些人只是学来玩,也渐渐收敛起来了,还劝退一些想拜师求生的学生。”梁姨说。
香港东莞等地不时还会邀请他登台表演或是授课,他基本上都回绝了。“年老了,很多不记得了,表演得不好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尽管如此,他仍习惯每天早上五点钟开着收音机听新闻和粤曲,有什么新人新曲,他比学生们更加清楚。“他一听就知道什么是好的,有多少年的功底,什么是应该学的,好像心里有个秤在度量那样。”黄玉玲说。
“大家还是喜欢听经典的多,怨、忆、苦,逃离了这些就不是南音了。但现在粤曲都越来越少人听,更别说南音了,现在更多盲人靠按摩就能解决生计,业余的‘私伙局’是永远不会散场的。但要说‘地水南音’,我们之前是以它谋生的,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了。”莫若文谈起传承问题,爽朗的他也变得有些忧虑。“地水南音需要真正有所经历的失明人才能唱出曲情,还需要花上十年八年心思去研究传承,才能成为地水南音的瞽师,现今要去哪里找人来继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