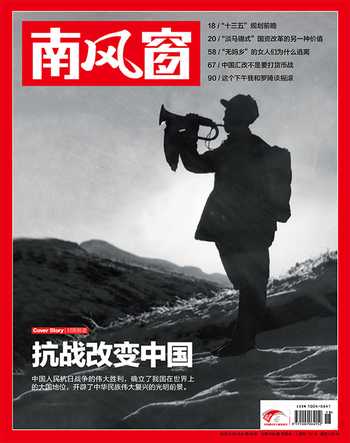处理中日关系需要大智慧
刘怡
8月15日,中国北海舰队的7艘舰艇驶离青岛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军事演习。尽管本次军演的日程年初即已商定,但由于前一天“安倍谈话”不合时宜地宣扬了1905年日本打败沙俄之于亚洲历史的正面影响,北京首度联袂派遣水面舰艇、两栖战部队和固定翼战机赴日本海海空域参与联合军演一事,就更具象征意义。在中日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接触”常态化的背景下,这也是对5月中国新国防白皮书中“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方针的呼应。
无独有偶,日本自卫队8月下旬~9月上旬将在美国加州与美军联合演练“夺回离岛”。而在东京7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出现了“中国公务船进入尖阁诸岛(钓鱼岛)周边已呈常态化倾向”等字句,日方据此认为“(中国)持续采取可称为高压的举措,令人对其今后的方向性感到担忧”。7月15日,日本众议院特委会通过了对11项现行法案进行修订的新《安保法案》,为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显然,继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风波和2013年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之后,中日安全关系在2015年再度多云转阴。从7月中旬日本国家安保局长谷内正太郎访华的效果看,尽管两国领导人对继续强化政治沟通和外交接触并无异议,但过去“制热”效果显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已逐渐无法抵消安全领域的压力。日本争当“正常国家”的长期目标与安倍巩固自身权位的操作相结合,已在防务政策上找到了“输出终端”。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

中国国力上升的巨大幅厦,终会使日万“拆东墙补西墙”的军力重整因跟不上节奏而主动放弃无望的竞逐。
应该说,中日关系的纠葛使普通中国人、甚至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放大日本的意义。在警惕日本和借重日本的自我心理暗示下,一些日方政策的影响被显著放大,并产生复杂的涟漪效应;同时,中日之间的互动(如拟于今夏签署旨在避免东海偶发性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协议)又被视为旨在牵制美国的亚洲政策调整,而使得形势愈发微妙。
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国力上升的巨大幅度,终会使日方“拆东墙补西墙”的军力重整因跟不上节奏而主动放弃无望的竞逐,转而寻求新的战略框架设定;届时中日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意愿和力度,不仅取决于外部因素(1970年代以降长约20年的中日蜜月期,诱因之一是苏联这一共同对手,之二则是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对日本的刺激),还与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引导和形塑能力有关。仅就当前而言,中日关系正呈现外交缓和与安全对垒“双轨化”的趋势,亟需以高级别的接触来控制分歧。
新安保法案在众议院“过堂”后,前日本驻华海军武官小原凡司对香港媒体表示:“和平宪法某种意义上也是孤立宪法,导致国人什么都不想……日本现在试图修改安保法制,并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敌人,而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相应的法制。”这类解释尽管较为委婉,但都指向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具备与经济规模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和安全行动能力的全球大国—的愿景。
自1990年代以来,“正常国家化”成为日本自民党的长期目标,具体构成包括:更充分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主动性,以及谋求在国际组织内的更大话语权;手段则以对内扩充和修正安保体制、对外输出经济和文化资源为重心。安倍在8·14纪念谈话中公开宣称,日本愿“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即是上述目标的反映。
然而从构成要件上看,日本政治家对“正常国家”的理解明显失于偏狭。就物质力量而言,日本与安理会五常之间的确已不存在差距,但它严重缺乏积累世界性权势所需的区域政治根基。从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判断,成长为“正常国家”的日本必须首先在亚洲树立旗帜,但在东北亚与日本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中韩两国,恰恰和东京存在严重的情感疏离及政治分歧。即使不论反省历史的态度,日本在地区经济和安全一体化、防务政策、修宪倾向等问题上,与中韩的沟通和协调也相当不足。这使得中韩很难确信日本的意图是可靠的、建设性的。缺少了中韩两国的信任和支持,日本即使能依靠经济援助在东南亚获得一定影响力,基础仍是不稳固的。就此而言,东京在“入常”之争中的优势远不及德国和印度来得明显。而在全球层面,日本在气候问题、粮食安全等较新的议题上表现平淡,却汲汲于伸张军事权利和安保诉求,显然无助于迅速建立正面、积极的形象。
另一方面,美国的亚洲战略对东京外交政策的捆绑,也使得日本的制度设计和能力养成受到局限。如小原凡司所言,在着手修正安保体制之前,日本对真正定位于自身的安全需求考虑甚少。东京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流程长期以来饱受诟病,但由于美国的存在,日本对内改革的决心不足,在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时依旧只能对华盛顿亦步亦趋。甚至连新安保体制最倚仗的自卫队,也因为美国的诱导和限制,发展极不均衡—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的设计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职能是充当美国第七舰队的反潜和水雷战分队,并参与美军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空中自卫队则要协助保卫在日本的美军基地。1980年代末,美方正是以“缺乏必要性”为由,否决了日本购买固定翼舰载机的申请。今日的海上自卫队尽管以精良的装备和优秀的训练水平闻名于世,但在远程投送、水面攻击和对地支援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后3项能力上的优势恰恰是美国希望继续确保的。在缺少美军指导和支援的情况下,海上自卫队几乎不可能单独介入一场大规模海上冲突。
由此看来,近年来日本以伸张军事权利作为“正常国家化”的努力方向,并非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更像是情急之下的应激反应。经历了“失去的20年”之后,东京引以为傲的经济优势在体量巨大的中国面前已相形见绌;再加上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则使日本愈发怀疑华盛顿安保承诺的可靠性。在此情况下,追求防务政策的自主性和自卫能力的提升,无疑能使政治家乃至普通国民获得莫大的心理慰藉。是故尽管安倍内阁在政策的争议性上远大过其几位前任,却仍能赢得相对较高的支持率:这是过去几年里中日国际权势此消彼长的后果。
以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风波为起点,中日两国在海洋权益争端方面大致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中方一改上世纪末韬光养晦的作风,频繁派出舰艇和飞机宣示主权,并在硬实力支撑下单独实施经济开发。日方则在巩固既有控制区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大搞舆论攻势,搬弄法条,营造出“中国恃强凌弱”的氛围。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拒斥对海洋权益争端的国际仲裁和调停,以避免区域外势力公开介入,故日方的说辞一度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同情与认可。最终,双方各自取得一定成效,但皆未能掌控全局,只是使两国关系周期性地出现紧张。
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被中国政府视作仅次于美俄(苏)的双边关系伙伴;这种特殊的重视与日本在冷战后期给予中国的战略惠利相结合,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两种貌似对立、实则有暗合之处的思维倾向。乐观者认为,日本依附强者的历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中国重整亚洲秩序的基石,北京应当支持日本争当“正常国家”,扩大美日矛盾,最终以中日一致为基础建立亚洲新秩序。悲观者则认为,日本以伸张安保权利作为“正常国家化”先导的冒险迟早会引发中日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能否击败日本、并迫使美国接受既成事实,将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领导者。换言之,两种倾向都认定处理好日本问题对中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这恰恰都属于夸张。日本的地理位置、人口和资源规模,决定了它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资质,尽管其威胁仍没有彻底解除。
今天的中日关系大致呈现这样的形态:由于日本的自身问题和美国在政策指导上的制约,它不可能入侵中国,中国也绝无必要对日本实施大规模武力打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东京仍将满足于“专守防卫”的国策,而将政策修订的目标设定为联合国框架内的充分安全权利。而中国从外部影响日本国民和政府的心理、并阻止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努力,大体已达到效率瓶颈,现在需要争取的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终极目标—不管导向的是结盟还是对抗—而是使日本的“正常化”尽可能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并借助两国高层的沟通不断调整和完善本方的政策。
应当承认,尽管安倍在70周年谈话中所称的“二战后出生的人占现在(日本)人口的八成以上。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子孙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不甚中听,但似乎代表了多数当代日本人的心理:他们对承认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的认知,远不及对中国“硬实力”和大众民族主义的疑惧来得直接。从外部促进日本民众对历史问题的正视,必须、也只能以长期的渐进方式进行;在此过程中,没有必要由于历史心结,就置经济合作、区域稳定(如朝核问题)等议题于停滞状态。我们相信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大智慧和战略恒心。
2010年8月,刚卸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在题为《日本的新出路》的论文中提出了“日美中关系正三角形论”。所谓“正三角形”,指的是3国中的任意两者都处在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之中,且每个国家都乐见另外两国发生矛盾,以为本方争取盟友,并获得收益。但在建立同盟时,较弱的一方必须提防强势盟友的支配能力和影响力持续上升,最终由三角关系转变为二元博弈,增加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尽管这一提议至今尚未获得实践的空间,但它的确显示了一种趋势:日本“正常化”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独立于美国的政治空间,以实现政策自由性。
换言之,尽管到目前为止,日本更多的是借重美国的对华防范心理和“再平衡”的需要,获取防务自主的空间,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正常国家化”对中国构成的冲击将会递减,美日之间的分歧则会愈发凸显,这就为中国的外交操作提供了更灵活的选项。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安倍晋三并不满足于华盛顿划定的政策界限,从尝试恢复对朝接触、力图邀请普京访日等举动看,安倍正在小心地试探美国的政策弹性,并尝试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推行外交政策。近日,有日本媒体曝出安倍有意在9月3日或稍晚时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尽管日本首相官邸随后称尚未经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若安倍在习近平访美之前,率先与中方就双边关系达成某种共识,尤其是就东海油气田开发等突出矛盾做好协调,无疑是一种相当大胆的“跳跃”。
对中国而言,顺应和利用这种新变化是有裨益的:当日本表露出激进的修宪倾向和在历史问题上的彻底倒退时,需要利用美国的战略戒心,争取华盛顿(尤其是2016年选出的美国新领导人)采取不那么偏袒日本的立场;当美国继续坚持其“权势傲慢”,拒绝以平等的姿态面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时,则要借重日本的“正常化”倾向,以和平的方式劝服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汲汲于在现阶段孤立或联合日本,眼界都太过狭小,中国最终是要对中日关系的终极形态做出回答:中国所能接受的是一个怎样的“正常”的日本,日本又将和怎样一个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