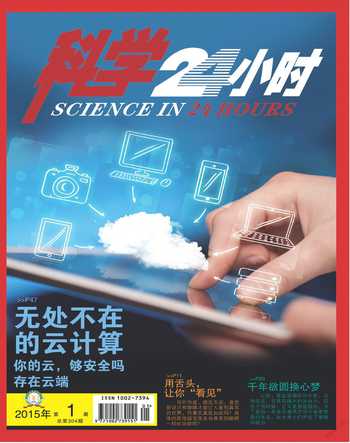浪漫诗人的科学情怀
隗斌贤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不仅是20世纪初新文学史上“新月社的巨擘”、“新月诗派的祭酒”,在新文学创作上所散发的光芒如日中天、久而不晦,而且他风流浪漫的人生同样传奇瑰丽,富有诗情画意。无庸讳言,徐志摩一生最受社会责难的莫过于他所追求与实践的“不是罪”的“浪漫真爱”,但人们却常常忽略了他为把各类具有不同价值的西方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引入到封闭已久的中国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非常重视科学文化交流的人,他不仅介绍文学艺术,还向国人介绍了许多国外哲学、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甚至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对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产生巨大的影响。在1922年,《民铎》刊登了徐志摩撰写的长篇大论《爱因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面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中阐述的是不是时间也绝对了、空间也绝对了、地心引力也绝对了等观点,他用了许多事实和比喻做了别开生面的论述。而实际上早在1921年4月15日出版的《改造·相对论号》上,徐志摩的文章就与夏元瑮、王崇植等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以及爱因斯坦撰写的文章一起被刊登出来。徐志摩为了写好那篇文章,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了,他收集并列出了1920年出版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狭义与广义的理论》、埃丁坦的《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广义相对论纲要》、哈罗的《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弗莱德利克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功能》、哈夫·埃里奥特的《相对论法则》和维尔登·凯尔的《相对论法则的哲学和历史层面》等相关著作。可见,他是真正下了功夫去研究的,以至于林徽因说他“疯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在《悼志摩》中风趣地写道:“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知识还是我从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文章才懂了。”
徐志摩并不局限于“迷恋”相对论,他在《猛虎集序》里就明确地说:“在24岁以前,我对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这不仅源于他“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的观念,而且也与他所接受的早期的科学教育有关。他11岁入学海宁开智学堂,除修英文、国文、算术外,还学自然、修身、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13岁升入杭州府中学(后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后,除前述课程外,格致、地理等新课程也使他感到新奇,尔后他又对天文学甚感兴趣。他不仅经常观察夜象,而且购买了不少有关天文知识的书刊,孜孜不倦地研读,还记了不少笔记,甚至打算写一本关于天文的小册子。与他同班同宿舍的同学郁达夫在《志摩的回忆里》一书中回忆道:他是同学里最顽皮的孩子,可是考试起来门门功课得第一。这包括在自然科学方面。徐志摩17岁时发表在校刊《友声》上的《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中就多次提到科学,如“若科学、社会……等诸小说,概有裨益于社会,请备言之;科学小学,发明新奇,足长科学知识”等。次年,他又用文言文撰写的科学论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发表在《友声》上。他对自然科学的这种钟情一直未变,正如张奚若在《我所认识的志摩》中所说:“他的聪明、他的天才,当然也不限于美术方面,他对于科学有时也感很大的兴趣,我1921年和他在伦敦重聚时,他因分手半年,一见面就很得意地向我说他近来作了一篇文章,料我无论如何也猜不着……我笑谓大概不是自由恋爱,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说都不是。原来他作了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林徽因撰文也提到:“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都认得很多,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用徐志摩自己的话说:“宇宙间的玄妙并非自然科学的人的专利,凡是诚心求实真确知识的人,都应该养育一种不怕难、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头头是道。”
徐志摩不仅对科学有兴趣有研究,而且他在诗的创作与研究中也嵌入了科学元素,他认为:“合理的人生,应有几种原素——自然的幸福、友谊的情感、爱美与创作的奖励,纯粹知识——科学的——寻求……”在他所留世的200多首诗中,涉及星、月、光等自然环境描述的内容就占了四分之一,不仅表达了诗人有关社会、人生与艺术的观点,诗的意境与抒情的色彩,而且流露出他对自然的敬仰。正如他在《染记(二)坏诗,假诗,形似诗》中所说的:“真好人是人格和谐了自然流露的品性;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自然流露的产物。”所以他认为“诗是人天间基本现象之一”。他在《鬼话》中更加明确,“我只是自然崇拜者,我生平教育之校择者,都从眷爱自然得来”。他在描述了月的圣洁、幽秘、慈悲、美妙以及自然崇拜心境后,以“慧”字来概括宇宙的奥秘。如“慧,然汝喜科学,问言天文者月何似”,“向之神秘,向之美,今变为科学之事实,幻象消而美秘俱逝”,“慧,设汝有择于真灵之间,汝将焉取?虽然科学何足以知月,量镜何足以知月,惟见事物之灵者,乃见其真,故讶月之秘之美,而月真之”。他在《坏诗,假诗,形似诗》中对“有人想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诗”时,认为“就是研究比量诗的尺度,音节,字句,想归纳出做好诗的定律,揭破历代诗人家传的秘密”,这“犹之有人也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恋爱,记载在恋中人早晚的热度,心搏的缓急,他的私语,他的梦话等,想戡破恋爱现象的真相”,“所以研究做诗的人,尽让他从字句尺度间去寻秘密”,并认为“这都是有剩余能耐时有趣味的尝试”。
在社会问题研究中,徐志摩也不忘与科学相关,并分析如何正确区分与运用。1923年12月,他分别发表在《东方杂志》、《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中分析道:“工业主义的一个大目标是成功(Success),本质是竞争,竞争所要求的是捷效(Efficiency)。成功、竞争、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观,便是造成工业主义……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他进一步分析道,“我们常以为科学与工业文明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科学,就没有现代的文明”,“但科学有两种意义,我们应得认明:一是纯粹的科学,例如自然现象的研究,这是人类凭著智力与耐心积累所得的,罗素所谓The most gool-like thing that men can do;一是科学的应用,这才是工业文明的主因。真纯的科学家,只有纯粹的知识是他的对象,但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绝对不问他寻求与人生有何实际的关系。孟德尔(Mendel)当初在他清静的寺院培养他的豆苗,何尝想到今日农畜资本家会利用他的发明?法拉第(Faraday)与麦克斯韦(Maxwell)亦何尝想到现代的电气事业?”因而,他认为“功利主义的倾向,最是不利于少数的聪明才智,寻求纯粹智识的努力”。他在谈到“近来很讨论科学是否人生的福音,一般人竟有误科学为实际的工商业,以为我们若然反抗工业主义,即是反对科学本体,这是错误的”时,明确“科学无非是有系统的学术与思想,这如何可以排斥,至于反抗机械主义与提高精神生活,却又是一件事了”。显然,徐志摩在那个时代已经对科学价值、科学精神以及科技伦理有自己的见解了。
可见,徐志摩不仅是中国新诗坛上一颗闪烁的巨星,而他的自然天性与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统一,使之作为中西学术联络人为东西方科学文化与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从对科学有“兴味”到“疯过”,以及他对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学精神与科技伦理的认识,成就了浪漫诗人的科学情怀,这是我们不能忽视,也是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