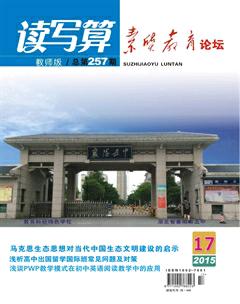漂泊孤零的个体、追寻与自我拯救
陶果 孙涛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7-0025-02
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讲述了一个不算爱情的爱情故事,小说中主人公背后的身份确认、追寻指向和倾城之后的某种程度上正常人性的回归,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成为我所思考的焦点。本文正是试图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方法,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受索绪尔和雅可布逊的二元对立原则影响极大的格雷马斯力图按照语言范例来描述叙述的结构。例如黑暗与光明、上与下、男与女等等,正如格雷马斯所言,“我们感觉到差异,正是由于这种感觉,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人们对这些对立物的感觉构成了符号学指示的基本结构的基础,于是就有了构造结构的知觉的最基本公式:A和B的对立等于-A与-B的对立,展开后即为如下的矩形图:
格雷马斯把普罗普的七种行为范围(即:1.反面角色; 2.施与者 ;3.助手;4.被寻者和她的父亲;5.送信者;6.英雄; 7.假英雄。)重新调整,产生了三组二元对立的关系,即:
1.主体对客体。英雄(主体)和被寻者(客体)划为一组,构成以寻求或希望为主题的故事;
2.送信者对受信者。构成“交流”的故事。
上述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就可以构成只有两个最主要角色的平庸的爱情故事
他 主体和送信者
她 客体和受信者
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即是
范柳原 主体和送信者
白流苏 客体和受信者
第三个二元对立关系是助手与敌手。这对范畴包括普罗普的施与者、助手以及反面角色甚至假英雄,主要起辅助作用。如文本中那场“成就”了流苏爱情的战争、徐太太和白公馆白流苏的家人等,就使这样一个简单平庸的故事更复杂化和更具戏剧性。
在分析《倾城之恋》的整体结构之前,首先有必要来整理阅读一下文本经便分析一下有关白流苏和范柳原的两个子故事。通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分析来确定主人公的自身定位与取向,从而有利于对整个故事文本的理解。
通过对《倾城之恋》和《金锁让》文本的阅读,让我们对文中的主人公的身份指认和人性取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那么这种追寻与自我拯救的道路与结果又是如何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倾城之恋》整个文本的叙述结构。
通过对《倾城之恋》和《金锁让》两个子故事的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白流苏和范柳原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有着相似的被集体“驱逐”的背景和孤零漂泊的身份,也有着在一种失落与失望后的自我追寻的拯救与挣扎。“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失望不等于绝望,在亲情与爱情的失望,要么绝望到底陷入一种虚无,要么在将信将疑中重新追寻,从而获得一种自我的拯救。但同样有着对亲情、爱情追寻与对归属感的渴望的两个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没有被划归为一类,而是处于一种对立的位置之上呢?这是源于两个人都太过于心计,爱情本来是两个傻瓜的游戏(这里“傻瓜”和“游戏”均是褒义),或者爱情从心理学上讲是让人智商下降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把原本美好甜蜜的爱情演变成了两个人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于是,在这场原本有着共同追寻与相互拯救的爱情故事里,两人却一时充当了对立的角色。这个故事的第三个因素便是与范、白个体身份与价值观念相反的一类,他们看重的更多的是金钱、地位,没有人情,勾心斗角,如白家的人等等。可以说这种家庭和人表现了一种缺乏美好人性的一类,可以称作“反人”,与此相对立的就是这个结构中的第四个因素,也就是正常美好的人性了。这第四个因素,之所以也和范、白也构成一种对立就在于,两人虽然有着一种对美好人性的追寻,但追寻与拯救的本省就说明主体的身上这种东西的缺失,至少是不完善。因此与完美的人性也同样形成一种对立和追求。
然而追寻的过程并不平坦,范柳原“我要你懂得我!”的内心袒露的人性不过是昙花一现,之后又“恢复原状,又开始他的上等的情调——顶文雅的一种。”白流苏也同样给自己穿了一件防范的“外衣”——“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耍心眼儿,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儿,人家还拿我当傻子呢,准得找着我欺侮!”追寻之路眼看又走向歧路,拯救的过程也似乎走向美好人性的反面。作者让一个类似命运之手提供了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让一场倾城的战争促使两个追寻的人由一种对立转化成相互偎依。“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两个人重新找到了追寻的爱情,个体孤寂与漂泊的灵魂也暂时得到了安慰,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得以复苏和回归。战争刚开始,他们开始相互惦念和对对方着想了:“柳原用另外的一只手托住她的头,急促地道:‘受了惊吓罢?别着急,别着急…”“本来昨天就要来接你的,叫不到汽车,公共汽车又挤不上”;到了浅水湾后战事依然不断,“隔着棕榈树与喷水池子,子弹穿梭般来往。”“炮子儿朝这儿射去,他们便奔到那边;朝那边射去,便奔到这边。到后来一间敞厅打得千疮百孔,墙也坍了一面,逃无可逃了,只得坐下地来,听天由命。”“别的她不知道,在那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他。”停战后的初期,这种相互偎依更是又进一步,两个人“偶然有一句话,说了一半,对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没有往下说的必要。”自古人们所追求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妙感竟在这里重现。当然,这种拯救只是暂时的,虽然“仅仅是那一刹那的彻底地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但是,接下来,我们却看到非战争状态下的平常的生活,“范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给旁的女人听。”
“胡琴咿咿哑哑来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故事的叙述到此结束,但是生活的故事却依然在继续。漂泊孤寂的个体,在一个荒诞的战争后得到暂时的归依,但个体人性最终的自我拯救之路又在哪里?没有答案!
(责任编辑 楚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