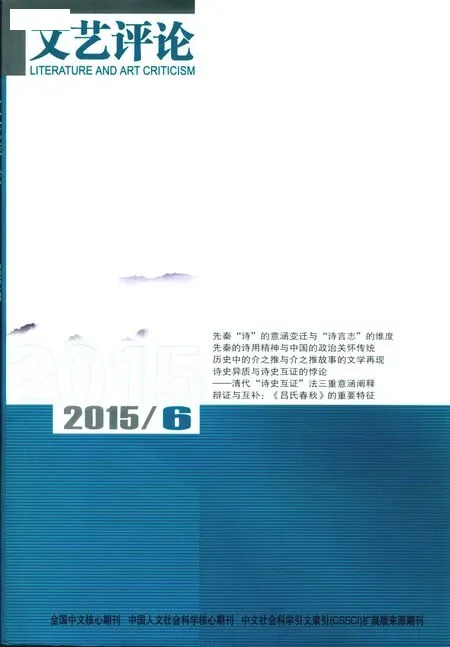先秦的诗用精神与中国的政治关怀传统
谢炳军
先秦的诗用精神与中国的政治关怀传统
谢炳军
一、先秦诗用精神
中国的经学文化,是实用型的文化,其始终以积极的人文情怀关注“国计民生”和“世道人心”两大亘古不变的时代主题。就《诗》而言,则为诗用。诗用,是通过创作诗或诠释诗的意义或引诗,而达到用诗者表述情志的功能。诗用由来已久。据刘勰认定为黄帝时的《弹歌》①“断竹,续竹,飞土,逐害”②就是诗用的很好体现,它至少蕴含两层基本意思:一是向人们讲述制作弹器的情况;二是运用弹器,伴随着歌唱驱逐鸟兽,表达孝子保护父母尸骸的心志。诗用与现实需要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诗用与政教相联系。对王官诗学最早的正史记载是《尚书·舜典》,其说:“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③此明指诗是乐的组成部分,即是乐的“乐语”,歌、乐器演奏、舞蹈等艺术形式是为“陶心畅志”而设,以最好地展露诗所承载的教育意义,以达到“以乐洗心”的教化效果;是为“防欲”而作④,其“不役耳目,百度惟贞”⑤以防玩物丧志。正如《乐记》所言“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⑥,歌、乐器演奏、舞蹈等是表现诗的形式。诗的意义是艺术形式的根本,艺术形式是诗的枝叶。辅广说:“教之本末,犹舜之意,本在德性,末谓声音。”⑦即声教、舞教等教务皆为“象德”的德教服务,王官的话语权即通过编造诗篇、改制礼仪、约定歌曲舞蹈等事件表现出来。有无德行成为衡量一个政权兴衰的标尺,成为估算君王寿命长短的原则。诗歌之旨趣与教化、德行绑定,展现施行教化的政治功效、德行的优劣的静态图景,本身提出了对君王的道德期待,并由此形成对君权的制约,完成了上古帝王自我完善到中古君王“因王官约定的道德期待”之制约的过渡。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劝谏周穆王废弃周行天下的决心,其诗说:“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⑧是祭公采取以退为进的进谏方式,赞述明王言行有德度,利用民力珍惜如贵玉如重金,而不贪游恋逸的怀抱;同时,暗示昏君则反其道而行之。作诗谏王是王官深具政治才能的体现,它比其他文体更具感召力。
两周王朝的诗用,是王官之诗教,是教官、礼官组成的教化系统的重要环节;而春秋私学的兴起,打破了王官之学独尊的诗教格局,《诗》学的湖面吹起清新的涟漪。诗用除了被普遍用于升歌、吟咏、断章等聘问礼仪程序,成为“读者之意”的表述形式,还成为了私学之教本。《孔子诗论》是《诗》教学的一种记录,是孔门诗教的接受与传播的展示,其未必是孔子诗教的历史图景的实录,或经孔子后学的损益,但无伤且无碍于我们对诗用精神的研究。诗用,直接表现之一是阐明《诗》之诗的“读者之意”。
清儒姜炳璋说称《诗》之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⑨,从广义而言,“编诗之意”是“读者之意”。诗教是为激发“读者之意”而造设。“诗言志”,可指诗人的情志,如《魏风·葛屦》说“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⑩”诗人之意是指出“好人(富家)”的吝啬,薄待女工,她寒天也未能添置暖鞋,由此讽刺富家“体虽富,心不贵”;“诗言志”,也可指读者之情志,《葛屦序》说“刺褊也。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⑪,此以小见大,以富家薄待女工之小事,而升华至魏国贵族阶层的品性,从而刷新了诗的归趣,诗也因此有了明切的讽刺对象,即魏君为代表的贵族集团。提升诗歌的旨趣,是编《诗》的王官因材施教的需要。因诗教的对象是太子、国子等贵族继承者,故诗的旨意括而大之才更具现实意义。站在“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善天下”⑫的思想高度,王官对太子、世子等贵族继承人提出了道德期待,此与将有杀父放弟嫌疑的舜塑造成孝悌模范的《书》教归旨统一,此种王官的“诗用”精神,在中国《诗经》学史与经学文化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汉代诗用承担着建设汉代政治伦理的重要角色,王式以《诗经》为谏书⑬是此之显证,由此可追溯中国“诗导志”与诗教的政治审美观的渊薮。
二、“诗导志”与诗教的政治审美观
有学者称“与身为古之圣君而被后人崇仰的英雄虞舜相比,作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孝梯标杆而被后人效法的孝子虞舜,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更为深远的影响”⑭,同理,较之作为个体层面的“诗人之意”,融入国家政治层面的政治伦理因子的“编者之意”,使《诗》的精审面貌焕然一新。简言之,“诗言志”的“诗人之意”过渡至王官“诗导志”的“编(读)者之意”,使《诗》文本的哲学意味发生了质的飞跃。孔安国说:“诗言志以导之”,孔颖达说:“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⑮诗如启迪引导读者的明灯,使读者情志绽放,可以藉之起兴,“诗可以兴”正言及此,太师教国子“兴诗”的创作之法,乐师教国子“兴”诗之道,皆是疏导国子心智,传授其表述情志之办法,以让其在政治情景中作诗言志,如周公“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⑯,钱钟书先生说“‘触物起情’为‘兴’之旨欤”⑰,清华简《耆夜》载周公旦睹蟋蟀而作诗⑱为此一证;或恰如其分地引诗述志,如《左传》《国语》使臣、诸侯等的赋诗明志,例证甚多。诗用与贵族阶层的文化修养乃至前程命运联结,“正德、利用”是诗用的约束力量,“厚生”是诗用的终极目标。礼义文化关怀下的诗用饱含着中国文化“正德、利用、厚生”⑲的情怀,孔安国说:“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⑳,于诗用而言,吸纳《诗》的养分,修正德行;又可用《诗》而利于教化,展示政治才华,完成国家使命;诗以抒发人们情志的艺术形式,与歌、舞、乐器等汇成表露各国人们生活的流动场景,再现天下苍生的心灵地图与时代的缩影,警示王族居安思危、敬天保民,以达长治久安。《诗》尤以《雅》《周颂》彰显诗用精神,其所具政治伦理用意和实用意义更为突出。赵辉先生以独创的“限定时空言说”理论阐述先秦文学的发生机制及本质㉑,此理论对王官的诗用实践言行也有启发作用,因主体“言说场合、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身份及其构成言说关系存在差异性”㉒,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内,诗用因时空而异。王官诗用实质地绘勒出理想的帝王将相的图示,构成了对帝王将相的道德约束,“顺美,刺过,讥失”㉓成为王官言说诗义的政治审美观。
王官的诗用精神在春秋私学勃兴的场域中易轨,孔子树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读《诗》新风,以礼义为旗帜的诗教,崇尚学《诗》以明礼,推重引《诗》以述志,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思想端正地体悟《诗》之诗之意义”。在礼义的限定条件下,诗的意旨是大集合中的子集,而子集因人而异。因此,“诗导志”走向了“和而不同”的广阔园地,思想的火花各显本色。清儒陆奎勋称“孔门言诗则维零章双句而有无穷之义焉”㉔,此言不诬,恰道出孔门诗用常态,与孔子引导弟子习《诗》的初心相切合。苏轼说:“孔子之叙《书》也举其所为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非不能详,以为详之则隘,是以常举其略,以待学者自推之……《诗》之叙未尝详也。”㉕苏氏之言可谓精审,恰好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孔子论诗归趣相印证。融入了孔子“读《诗》之意”的《诗论》,将“情、爱”,“忠、义”表而出之,并将个体对《诗》的体悟置于理想的礼义语境之中,力图打破礼义一去不返的现实生活,引导出知礼识义的心灵力量,重塑时代的文化丽质。
战国之际的王官诗用,伴随着古乐的僵化与活力的每况愈下,新乐的勃发与流行,《诗》教本的义教系统的重要性愈显突出。“教国子六诗”的教学内容也随之调整,被时代赋予新的使命。如何作诗言志与如何断章取义,成为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教导国子作诗,《周礼·大师》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说:“教,教瞽矇也。”㉖实际上,大师除了教瞽矇现成的诗,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国子作诗之法。为了规范和简化作诗的方法,诗歌用语的齐整化、成语成分的约定俗成及可代入化,是王官编制教本的重要原则。李辉先生说:“‘套语’或‘比兴’在诗乐中运用,是乐官出于‘歌唱’之便利而做的巧妙适应。”㉗此同适用于教官、礼官组成的教育体系培育国子与造就士人的情况。随着《诗》《书》等成为典型的教本,它们便是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常常被视作两个整体加以称引,《左传》中“《诗》曰”“《书》曰”是其显证。学《诗》者从《诗》与“六诗”之法的教学中,领悟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场景中,从“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㉘的《诗》《书》中抽离恰如其分的因子,学会在各种情景中以“赋比兴”的作诗之法去作诗,用以展示才能,用以传导心志,舒展怀抱,完成各种使命,这是诗用精神的一种典型表现。另一种表现则是私门的诗用实践。《孔子诗论》是私学诗用的实践案例。
陈桐生先生说:“以《孔子诗论》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㉙此为精审之论。《孔子诗论》意味着诗用从王官过渡到了私学,王官一家独尊的诗用局面被瓦解,百家争鸣的诗用实践升起其实用的旗帜,以兼容并包的文化情怀共同指向中国文化“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期待,这种人文之光穿越时空,成为人类文明温暖的归宿。方铭先生说:“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幸福的,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当然也是文学的目的。”㉚《诗》的阐释活动,本身也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活与获得人们互相的关怀。换言之,由《诗》的阐释活动而生成了《诗》解说文体,是为了引导读者更好地观察与理解人心,以在公共场景、私人生活中得到心灵的指引,而作出恰当的言行。这种文章以解说为特征,最先是由王官所制撰,如解说三兆、三易、三梦的“赞”体文㉛,此种文体在春秋战国时期也走向了私学的场域,其内容有所损益,韩高年先生认为“春秋时代的解兆说卦之文的模式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因事命龟、据颂释象的僵化的礼仪写作模式,促使新解说文的生成”㉜,又说“发为言辞与撰制文章是春秋时期人的能动性得以发挥的重要手段,所以重视言辞、语、说、命、论等篇章的功能、并进而探讨其言说与撰制的规律,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气”㉝,沿袭此种风气,战国的说《诗》走向“碎片化”。所谓《诗》论的“碎片化”,是指诸子百家及秦汉后的说《诗》家站在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文化立场上,以各自的方式阐释《诗》的意趣,使《诗》说呈现出见仁见智的多样化局面。尤值得表而出之者是《孔子诗论》,其沿波孔门学脉,彰显孔门《诗》学光芒,将普遍的人性之情形置入论诗之中,使诗论闪烁着人文之光,展现着人性之美。
《孔子诗论》载“孔子曰”计6次(分别系第一、第三、第七、第十六、第二十一、第二十七简),所表述的内容是《诗论》的核心,它承继了孔子“以诗导志”的说诗风格。孔子的“以诗导志”理念即是他以《诗》之诗引导弟子的思想观念,使其树起正确的健康的人生价值观。这种诗教理念种在启蒙与引导,而不是生硬地、简单地提供“标准答案”,它不是一步到位、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而是循循善诱、顺阶而上的教育图式。如《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㉞
《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㉟
此两处皆说“始可与言《诗》”意味着弟子可从诵诗阶段进入讨论《诗》之义理的阶段。孔子这种诗教理念与他自身学习经历一脉相连,《孔子世家》载:
孔子学鼔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㊱
是孔子学秦重视循序渐进、各个击破,从熟悉琴曲到体会弹奏的技巧,再至体悟琴曲表达的情志,最后认识升华到对琴曲所传递的人性之美善的高度。而《诗》之诗归趣也是千姿百态的世风民情、复杂多样的政情人性,“志、情、言”是孔门诗教阐释诗意的主题,《孔子诗论》说:“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无离言(意)。”㊲对这句话的解读,我们不宜将三者独立看待,割舍彼此关系,志、情、言是统一共存于志、乐、文当中,只不过表现的方式各异而已。孙少华先生说:“‘情’与古人常说的‘志’有某种内在关联。这个‘志’,就与‘意’有关。”㊳此为确论。《孔子诗论·诗序》反映出战国时代人们崇尚坦荡、真诚的胸怀,无论是作诗或阐释《诗》,无论是制乐或阐释《乐》,无论是撰文或阐释文,不无流露出推重真实的心志、真诚的性情、饱实的意义。此种情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诚信”精神实质一致,表示在不破坏社会公德、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遵纪守法的大前提下,国民有抒发内心真实情志的自由。《孔子诗论》第七简说:“‘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裕也,得乎?此命也。’”㊴人性之美,首先是表里如一的真诚,其被《诗论》升华至王者风范的必备素质,真诚是形成王者政治公信力坚固的生命线。
总而言之,《诗》学从来就是洋溢着政治关怀的学术,具有双重性,既有学识的成分,又具治世之策略的因子。诗之意旨的政治关怀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情怀,是诗意的情怀,是沉淀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诗意文化。如果《诗经》学无有此种美、刺政情的人文光芒,《诗》学的魅力将大为黯淡。《诗》学以诗意的情怀和诗意的目光引导读者诗意地认识世道、人心,这个“诗意”与“温柔敦厚”相连,使归结到政治关怀的诗旨显得温情脉脉。有人说文学是人学,笔者则认为经学也是人学,《诗》学的人学色彩尤为显著,它与《易》学一起成为描绘中国人诗性心灵的动态轨迹和地图。傅道彬先生称《周易》体现出中国文化诗思同源的诗性哲学品格㊵,六经皆有诗性思维的舞动,诗性参与了先秦哲学的书写,所以“‘六经皆文’与‘六经皆诗’是解读周代经典文献诗学精神的理论支撑”㊶。而诗学精神落脚点终归是诗用精神,它关注现实人生,它始终与“正德、利用、厚生”的教育和文化理想血脉相连,不同的时代诗用精神各添新的内容,但这种文化基因从未消失或弱化,体现着经学“因变而通”、“因通而变”的学用一体的实践性品格。
三、先秦诗用高扬中国的政治关怀传统
政治是人类发现、表达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方式㊷,是政教得失的总和,它关乎国计民生,关乎世道人心。政治关怀即是政治对“国计民生”和“世道人心”两大社会主题的关注、批评和道德实践。先秦的《诗》《书》等书籍是历时性与共时性通融的经典教本,其对政教关怀提出了道德期待,即政治的基本原则。就《诗》而言,“采诗观政”与“听音知政”被理想地设置在一起,《诗大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㊸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在此所揭示,而作为音乐的思想文本的诗所承载的政教功能便甚为明了,《诗大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㊹诗与教化、祭祀的关系,是代言与被代言的关系,而教化、祭祀本身就是检验先秦政治良莠的重要环节。《诗》,作为古典学的其中一个重镇,作为导引读者心志的正典,其旨在使读者“广显德以耀明其志”㊺,《诗》从王官的诗用精神到私学的诗用精神,展示出《诗》作为文化宝典的生命张力,而诠释《诗》作为诗用的一个实践活动,是承载《诗》生命力的坚船利器,宣扬着中国文化中永不褪色的德义本性。无疑,诗用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经学品质的表现,在经学的天空下,高扬着每个时代和而不同的旗帜。如《孔子诗论》作为战国中期的《诗》学著作,以厚积薄发的姿态,重审中国政治情性,重读人的性情,为今人敞开一扇观察战国楚地学人教学《诗》的心灵地图,它具备“扬弃旧义,创立新知”㊻的学术品性,与经学“求变、求新”的经术要求相呼应,使《诗》焕发出时代的新义,对现代《诗经》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裘锡圭先生说:“很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㊼中国的经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术,其以深远阔广的人文情怀撑开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怀抱,其与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业精神的实用主义㊽有着显著的区别。经学以厚重的姿态积累起中国文化英华的力量,体现着中国政教关怀传统。
赵剑英先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横空出世的‘异质文化’,而是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㊾所以如何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优秀的古典文化精神的桥梁,成为我们的时代使命。经学推尚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的、人文的情怀,应当被我们的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社会主义的建设所关注。就诗用文化而言,它侧重引导人们情志的宣泄,“诗可以兴”,既是作诗技巧,以《诗》为取材的素材;也是疏导表述心志的渠道,是撰文、说话取材共享的智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生活、政治场合的赋诗言志、断章取义是其明证。诗用注重观察人的内心世界,“《诗》可以观”,是从“乡乐唯欲”㊿中观察人心的美、丑,《孔子诗论》第三简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物”指人,具体即指人情,《国风》容纳人情,可用以观察各国人情世态,可以作为诗歌素材,其用语有文采,其声音和善。进而言之,《诗》作为言说政治生态的思想资源,其诗用实践是对政治审美的注脚。政治与审美在这里密不可分地结合,共同地指向政治关怀的维度。而如果丧失此意义,中华文化的“光明与厚重”将流失,是对我们由来已久的政治关怀传统无原则的抛弃。伊格尔顿先生说:“如果美学繁荣,那也只能是通过政治转变;政治支撑着一种与美学的元语言学的关系。”指出政治与审美并无内在的矛盾关系,而就中国文化而言,撇开《诗》学与政教的紧密关系,而寻求一种纯文学的审美,是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行为,因为作为中国文学理论之祖的“诗言志”就与政教血肉不分,所以“诗言志”具有“政教与审美的二重性能”。
伊格尔顿先生说:“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对于文学理论,不应因其具有政治性而横加责备。”此不无道理,可以说,从文化建设与政治文明史的角度而言,《诗经》作为经表现出的政治关怀的品格超越了其作为纯文学的审美的高度,所以刘毓庆先生说:“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上,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诗》的经学实践赋予了它政治关怀的学术活力,此种活力恰不应被剥夺,而随着经学地位的沦陷,经学的大旗的下落,经学身上流动的政治关怀的血液也日渐凝结,有学者甚至认为其政治说教充满功利,已是明日黄花。这是对经学精神的误读。在我看来,政治说教恰是《诗》学政治关怀的直接表现,彰显出其阐释的德义的光辉。当然,并不是说《诗》学所表的内容皆是精华,但其主流精神应被重视,“如果对传统《诗》学予以彻底否定,那么否定掉的不只是一种诊释观点,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与儒者道济天下的担当精神。”此种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政治关怀,对当下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依然意义重大,其诗意情怀尤值得关注。
四、中国的政治关怀传统的诗意特质
中国的政治关怀传统流动着审美与诗意的清泉,其光明而甜美,至当下也未为枯竭,也不当干涸,而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怀一道建设起中国政治人文的靓丽风景线。政治关怀作为王官、诸子对君臣提出的执政的道德期待。这种道德期待荡漾着诗意的涟漪,由来甚为久远。《尚书·尧典》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其中所涉中国诗意的政治关怀之义尤值得表而出之,其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稽古”表明溯源两周的政治关怀的文化源头,从而树立“内圣外王”的明君施政模范。《尧典》作为生成于西周中期的文献,是我国传统美政教育思想的渊薮,是王官阶层制定的“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的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其给国子、士等受教育者灌输“立政者当有政治关怀的德行”的思想观念,以形成“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理想的政治关怀的场景。这种政教合一的教育与进谏体系,阐明了王官阶层、平民舆论参政议政的合法性与权利,“以德为法”成为圣君贤臣必具的素质,以彰显施政者人性之美。孔子说:“《帝典》可以观美。”宋咸注:“谓君圣臣贤,称让、礼乐之美。”这几种“美”皆出自执政者的人性之美,而此又必然与治政相联系,并通过治政表现出来,如《大禹谟》载: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榖,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郑玄注:“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则所善政……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劝之,使政勿坏。”
可见,诗用情怀与政教思想共融,诗歌以表演的形式抒写着王官们设定的古帝的政治关怀图景:一切的真、善、美皆与善政养民相连,美政是人性之美的终极体现;而歌乐是人性之美流动的画面,是人性之美跳动的鲜活的心灵轨迹。政治的兴衰,君臣的德行的美丑,可察见于世风民情,故采诗制度应运而生,《诗经·国风》是典型,赵逵夫先生认为采诗、献诗制度的形成与贵族阶层音乐需求紧密相联,是从诗乐娱乐功能阐述采诗制度的发生。而王官制定的政教制度,诗乐是与政治联结。《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巡守作为帝王祭祀山川神灵,博览各地风土人情,流播帝王惠泽,宣扬帝王权威的出行制度,其起源甚早。《舜典》载舜时“五载一巡守”,郑玄说:“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则十二岁一巡守。”据此,舜之时已有一套成熟的巡守制度。赵世超先生称尧时巡守制度已经生成,此言甚确。而采诗是巡守制度的文化产物,诗歌被当成考察地方政绩的标尺。孔颖达说:“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以诗观政使帝王政治具有了诗意的审美意义。诗歌表现着人们的心志和感情,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寄托着人们的愿望与理想。而三代星罗棋布的国家面积小是常态,人们“以国为家”的观念甚强烈,施政者治政的得失直接强烈地关系到平民的利益,甚至生命的安危。从这个角度而言,诗歌本然地与政治生活牵连并非不根之论。进而言之,政治关怀的诗意性正表现在它流露出的真诚的人文大情怀之中。此为王官制作教本时特地用心所书写和刻画,呈现出教本德义的理想化特征,如《大禹谟》载舜“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于此《大禹谟》所载未必为信史,但并不害于其作为教义的意义,其是作为诗意性的政治情怀而被书写,展现着和谐的政治伦理观念。郑玄《诗谱序》说: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迩及商王……
“诗之道”即是歌颂世道人心之美,讽刺伤害国计民生之丑。此正是中国政治关怀传统的应有之义。诗歌因为具有这种政治美刺的功能,而成为王官制礼作乐的内容,而阐释《诗经》成为后世文人关注政治和世道人心的重要方式。戴琏璋先生称“《诗经》中表达基本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代表性作品,勾勒出先民生计与情爱方面的意趣与憾恨”,《诗经》作为经典教本,宣扬着它不同于其他经典的政治情怀。无论是作为文学范本的《诗》,还是作为阐述政治教本的《诗经》,皆意欲抹去或许看起来复杂的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暗影,以光明的形象展示诗人或读者内心的灿烂。《尚书·金縢》载:“周公居东两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周公受管、蔡等流言所伤,避居于东,特地作诗表露其政治处境,言明其内心之凄苦,以展示其心路之光明,从而化解了成王和周公之间的政治危机。周公这种寓政与诗的方式,本身是先秦诗用精神的体现,也反映出作为一个贤者应有的政治情怀及政治才能。总之,这种诗意的政治关怀传统成为经学的一种生命活力,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厚重的遗产。
综上所述,先秦的诗用精神以诗意的方式延续并书写着中国的政治关怀。这种政治关怀,流动着“正德、利用、厚生”的血液,昭示执政者要“善政养民”。此等诗意的政治情怀,在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在关注国计民生与世道人心的主题中,多一份诗意的政治情怀,或许可以让我们栖息的大地多一份明媚的诗意。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510632)】
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9页。
②赵晔《吴越春秋》,四部丛刊初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6页。
④㊱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62、2320页。
⑥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1页。
⑦辅广《诗童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卷首。
⑧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64页。
⑨姜炳璋《诗序补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页。
⑫赵岐注、孙奭疏、焦循正义《孟子正义》、《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91页。
⑬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0页。
⑭尚永亮《英雄·孝子·准弃子——虞舜被害故事的文化解读》,《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
⑰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7页。
⑱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0页。
㉑赵辉《先秦文学发生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㉒郑杰文《言说先秦文学——评〈先秦文学研究发生〉》,《光明日报》2013年8月18日。
㉔陆奎勋《陆堂诗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㉕苏辙《苏氏诗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5页。
㉖㉛郑玄注,孔颖达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96、803页。
㉗李辉《论〈诗经〉“比兴”的兴起及其诗乐功能》,《文艺评论》2015年第1期。
㉙陈桐生《〈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
㉚方铭《〈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文艺评论》2002年第2期。
㉜韩高年《春秋卜、筮制度与解说文的生成》,《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
㉝韩高年《春秋时代的文章本体观念及其奠基意义》,《文学评论》2012第4期。
㉞㉟刘宝难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33、89-90页。
㊳孙少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研究的探索——〈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4期。
㊵傅道彬《〈周易〉的诗体结构形式与诗性智慧》,《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㊶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文学遗产》2010第5期。
㊷刘学坤、戴锐《政治、政治教育与公民的意义生活》,《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㊻裘锡圭《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7日。
㊼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4日。
㊽赵敦华《实用主义与中国文化精神》,《哲学研究》2014年1期。
㊾赵剑英《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㊿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