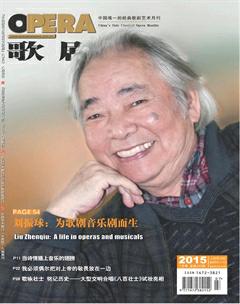当诗情插上音乐的翅膀
卜大炜



2015年5月28日晚,翁贝托·焦尔达诺谱曲的传世歌剧《安德烈·谢尼埃》由国家大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和美国旧金山歌剧院联合制作,在国家大剧院歌剧厅隆重举行了在中国的首演(A组)。这是一部高度艺术化的精品歌剧,它不以高音论英雄,而以诗意飨听众。
这部意大利歌剧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爱情故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焦尔达诺为这部爱情传奇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感人至深。
因人撬动矛盾发展的角色
安德烈一谢尼埃史上确有其人,是法机地推进,而引入了杰拉尔德一下子风生水起。这位与诗人同属“第三等级”的人物使歌剧构成了三角恋,但这里用“三角恋”不妥,准确地说应该是撬动矛盾发展的第三方。他并不鄙俗,力主“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这正是雨果对那个年代社会精神的总结。
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1896年2月1日在都灵皇家歌剧院上演,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谢尼埃》于同年3月28日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上演,几乎是在同时,真实主义歌剧中一下子出现了两部以诗人为男主角的歌剧,而剧本又都由路易吉-伊利卡参与编写(《波希米亚人》是贾科萨与伊利卡合作)。《波希米亚人》中的爱情是市井中的爱情,而《谢尼埃》演绎的爱情是动荡年代的一种理想主义爱情。谢尼埃不是拉丁区的文艺青年,与鲁道夫相比要更复杂些,也更“高大上”些,他当过兵,投身革命,有着更丰富的经历,对爱情有着哲学和政治思考的崇高定义,这在第一幕中他的第一首咏叹调“某日,眺望着碧蓝天空”就唱出了——“爱是一种精神,她在宇宙中运行”,这是一曲人间大爱的宣言。在《安德烈-谢尼埃》中,女主人公为拯救心中的偶像而不惜委身于权贵,这又与1800年6月在罗马上演的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情节相仿,而《托斯卡》的剧本也是伊利卡与贾科萨合作。但玛达莱娜不是托斯卡那种为爱发狂的艺术家,而是在社会动荡中阅尽人生又视爱情为真理的女性。而杰拉尔德更不是《托斯卡》中的警察局长,而是让歌剧绽放人性光辉的关键人物。因此,这三个人物都为作曲家提供了深厚的创作沃土。我认为,被列入真实主义歌剧的《谢尼埃》有着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元素,并且将一般意义上的儿女情长上升为人间大爱。
焦尔达诺高度艺术的音乐
我十分喜爱焦尔达诺的音乐,这次较为全面地在现场感受了他音乐的魅力。
诗情是什么?诗人如何塑造?这是个极具挑战的命题。焦尔达诺以极具诗情的音乐完成了命题。首先是这部歌剧的音乐优美抒情,既声乐化又戏剧化,典雅而又能打动心扉。焦尔达诺与普契尼属同一时期的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作曲家,咏叹调与宣叙调熔为一炉是他们这一支作曲家的共同点,但我认为焦尔达诺在心理描绘方面更为细腻。
宣叙调时他让乐队做交响性的推进,咏叹调与宣叙调以音乐色彩的变换来交替,这些音乐色彩的变换都是随着歌词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以一种心理变化的轨迹呈现。抒情与叙事做到天衣无缝,有些咏叹调包围在宣叙调之中,甚至是以“咏叹句”来呈现,这些“咏叹句”在调式、调性或和声的微妙一转之瞬,犹如云开雾散时投射到亚平宁半岛的一缕阳光,是诗中佳句的到来。他为人物设计的音乐没有普契尼《波希米亚人》那样晌遏行云的大线条咏叹,但不时到来的佳句或极富特色的音程代表了意大利歌剧的古典美。安德烈·谢尼埃的诗情就是这样抒发出来的,心有灵犀的听者不时会被打动。玛达莱娜和杰拉尔德的音乐也是如此写成。而杰拉尔德的“祖国的敌人?”虽基本上是一首大宣叙调,却因为是以色彩变换来呈现复合性格的载体而成为当今流传最广的音乐会曲目之一。
焦尔达诺在剧中设计了几个音乐“形象”,这些“形象”在剧中多次再现。第一幕启幕不久就出现“金粉世家”的动机,并按场景的需要而产生和声的变异体,而动机的原型是后面贵族们跳的一个加沃特舞曲的“垫步”。如果说这是源自瓦格纳的“主导动机”,真实主义歌剧作曲家如普契尼等都有所借鉴,那么焦尔达诺则将这一手法的意大利化做到了极致——咏叹句的多次再现。例如,谢尼埃第一幕的咏叹调“某日,眺望着碧蓝天空”中“这是生命真正的美丽!”一句旋律,在其后几次他的咏叹调时再现,并在第二幕与玛达莱娜的二重唱中成为崇高爱情的赞歌,还在玛达莱娜第三幕咏叹调“我的母亲被杀了”作为大段引子由独奏大提琴再现。杰拉尔德第一幕中“你已年过六十”的咏叹旋律也在“祖国的敌人”等处中再现生发(以显著性格特征的音列组成核心音调)。
在管弦乐配器上,焦尔达诺写得非常精妙,不是新奇,而是继承了多尼采蒂的精髓,和声严整,配器灵动,构成一种透明而又绚丽的音响织体。比比皆是的戏剧性交响细节是对剧中人物的心理解析和歌词的回声,而大线条的“托腔”永远赋予小提琴声部在最靓丽的音域上尽情挥洒,这就是意大利歌剧的浪漫传统。在这一晚,我们还听到了洛可可风的加沃特舞曲,这是海顿、莫扎特时期的宫廷音乐:还听到了牧歌,文艺复兴的复古:还听到巴黎大革命时街头的群众歌曲,似乎预示着后来的苏维埃歌曲。当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终场二重唱结束,你就体会到焦尔达诺是多么天才地用音乐完成了命题。这可谓是一部高度艺术化的精品歌剧。
诗人比英雄更难演
诗人要比英雄更难演。我认为,谢尼埃应该有浪漫激情,要有股英气,否则唱不出“某日,眺望着碧蓝天空”中的愤世嫉俗:或许不需有幽默,但要有一丝忧郁,这几样缺一不可。过去,在国内歌剧音乐会上能听到剧中男中音角色杰拉尔德的咏叹调“国家的敌人?”,或许还有女高音主人公玛达莱娜的“我的母亲被杀了”一段,但男高音主人公安德烈-谢尼埃那些最能体现作曲家灵感和才华的咏叹调罕有听到,原因在于这些咏叹调不是靠歌唱家对高音的冲击就能一蹴而就,更难的是要对音乐深层挖掘,并集合台上台下多元系统同时“在场”的条件而幻化出一种诗人气质。
因此,对于诗人的演绎在国内歌剧舞台上无从对比,仅可参考几个国外版本的视频。巴黎歌剧院版的马切罗·阿尔瓦雷兹,演唱情绪非常饱满,声音贯通,质量非常好。但他是偏戏剧的大号抒情,高音区充满英雄性,革命者的味道大于诗人的气质。卡雷拉斯与卡巴耶的巴塞罗那里西欧歌剧院版,觉得卡雷拉斯尽管演唱技巧天衣无缝,但英气不足,小生气太多,甚至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之虞,缺乏人物性格的立体刻画,较为平面化,如同戴了面具。或许与歌剧女神同台,卡雷拉斯的“诗情”也被抑制了。大都会版(傅海静饰诗人鲁谢尔),《波希米亚人》中饰演鲁道夫出神入化的帕瓦罗蒂在这里虽然技术游刃有余,但音乐冷漠,与角色貌合神离。直到看过这个制作今年1月英皇首演阵容的考夫曼版本,觉得还是考夫曼最传神。他在各个声区都有靓丽磁性的音色,不仅以清晰的“喷口”一展英雄傲视群雄的气概,还有轻声技术的运用让爱情桥段愁肠寸断。他对于作曲家悉心安排的音色变化都能捕捉到,演唱的音色也随之变化,从而令人物形象丰满真实。优秀的歌剧和优秀的歌剧演唱当以心理描写为重,这方面的成功就奠定了一部歌剧或一次演绎成功的基础,考夫曼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深,从而艺术效果也最为出色。当然,每一位歌唱家的固有艺术风格、气质和技术条件也影响着对角色的感悟。
在国家大剧院演唱诗人的大号抒情男高音卡曼·查涅夫出生在保加利亚,曾获瑞典的毕约林奖,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慕尼黑歌剧院等世界一线歌剧院担任主演,不久前在华盛顿国家歌剧院出演了《玛侬·莱斯科》的格里欧。从资料看他曾于2009年随意大利凤凰歌剧院前来国家大剧院出演过《蝴蝶夫人》中的B组平克尔顿。当晚的演出,查涅夫在发声技术上并没拥有高位置,这样在中低音区的音色非常坚实,从而使那些宣叙调段落得到了“真实主义”的表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高音区以宽厚明亮的另一种音色示人,且无缝衔接,有丰厚的胸音。第一幕的“某日,眺望着碧蓝天空”、第二幕的“我从未爱过”、第三幕的“我以前是名军人”及第四幕“像五月晴丽的日子”,都是如此以一腔诗人的豪情唱出。“我以前是名军人”一段中两处哭腔的运用很具诗人气质,其悲愤之情很出彩。
扮演杰拉尔德的阿尔贝托·卡扎雷同样是一名频频在欧美一线歌剧院登台的男中音歌唱家。声音位置非常稳定,在名段“祖国的敌人?”中能将作曲家匠心安排的音色对比悉心做出,这是这位当年“第三等级”人物——曾经的玛达莱娜家仆在三角情爱进程中的心理折射。演唱玛达莱娜的意大利女高音阿玛丽莉-尼扎以演巧巧桑出道,曾获巴蒂斯蒂尼奖,自2001年以来在欧美一线歌剧院和音乐节频频担纲主演。她在当晚的演唱音色统一,讲究技巧,聚焦出色,圆润委婉,带有一丝弗蕾妮那样的音色。同时饰演伯爵夫人和盲人祖母玛德隆的女中音郭燕愉也传神地刻画了人物。郭燕愉在第三幕玛德隆送孙子参军时唱的“我是老玛德隆”音乐上处理得非常细腻,使这个仅出场一次的人物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饰演贝尔茜的女中音朱慧玲同样寥寥几笔就为人物画下了“速写肖像”。第一幕芭蕾舞场景的牧歌合唱,大剧院合唱团女声的音色很清纯柔美。
虽然此轮A组演唱一号、二号角色的演员比起英皇首演的考夫曼和女高音伊娃一玛利亚-维斯特布洛克(Eva-Maria Westbroek)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但为另一组华人歌唱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平台。能在现场观赏这部歌剧是一种享受。
交响化的管弦乐演奏
绘制成法国国旗的幕布一拉开,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便是动力十足,指挥吕嘉带领大剧院管弦乐团同样使焦尔达诺的交响性光泽频频闪现,全剧包括的音乐四季风情都有体现,其中包括与合唱团共同营造了那个狂热年代的群众场面。小提琴声部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张力,听他们拉的“过门”、“托腔”非常过瘾,真是一支意大利化的歌剧乐队。第三幕玛达莱娜咏叹调独奏大提琴引子,极佳的句式感和醇厚的音色令人难忘。管乐各个独奏声部都能以灵巧的手法将全剧众多的管弦乐细节逐一完成,乐队合奏(Tutti)经过句非常流畅干净。如果将一些画龙点睛的和弦演奏得再果敢一些,就会显得更老到一些。大剧院乐团还是一支年轻的乐团,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绩非常可喜。
交响性的舞台调度
本次制作的导演是擅长传统制作的大卫·麦克维卡,他的风格与大都会歌剧院和英皇这样的深具传统并实力雄厚的歌剧中心相吻合。歌剧的舞台调度时常纠结于戏剧需要和音乐需要,而该剧的调度首先完全服从声乐演唱的规律,并做到动静结合。第一幕牧羊男女芭蕾双人舞让伯爵庄园成为革命时期的一个世外桃源。而审判一场的群众场面每个人都在慵懒地忙着自己手中的“活计”,与雨果《九三年》对当时巴黎市井众生相的描述如出一辙。麦克维卡打造了一个狂热的时代背景,让剧中人物在其中展现其性格发展。在独唱场面,独唱者平稳地保持处于视觉中心,其他人物在舞台走位都是出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对歌词的即时内心反响,例如谢尼埃第一幕咏叹调“某日,眺望着碧蓝天空”,触及到封建统治阶层的虚伪,满台的“第一等级”人物都处于不安之中,尤其是那位从巴黎来的神父。而有些场面如第三幕审判场面,合唱团集中站位,似乎像近来很流行的情景合唱音乐会的做法。真实主义歌剧的音乐,一个和弦就是一个眼神,一个收束就是一个亮相,导演构思都在大总谱内。当晚,剧中人物的举手投足、眉目传情都在音乐里完成,音乐成为戏剧动作的回声。在群众场面,每个人物或每组人物都是一部小品在表演。
没有任性的真实舞美
这部歌剧在制作上凸显了真实,舞台上路易十六年代的服饰与古典家具细节的一丝不苟,让人赏心悦目。舞台装置布局有前后左右功能区的划分,但都有透漏处理,能有所呼应,画面浑然一体,没有硬性切割。舞台后区顶光和侧光的使用产生室外自然光的效果,但没有过度的动态追光。罗伯特·约翰斯设计的布景、装置与詹妮·蒂拉曼妮设计的服装始终保持色系的统一,第一幕伯爵庄园客厅的明黄色系,寓意“金粉世家”。而第三幕审判和第四幕圣拉扎尔监狱则呈冷色调。
演出后我联想到一系列的歌剧舞美制作。许多歌剧在舞美上不可谓没有创意,但太多的概念堆砌让人感到喧宾夺主甚至画蛇添足。还有的制作创意不可谓不新颖,但细节上不是粗糙便是失真。还有的设计考究、奢华,但与音乐和文本的风格不搭界。以上这些制作思路都花了大笔经费,却干扰了戏剧和音乐的呈现,引起观众的失望。而此次英皇在舞美上完全舍弃抽象、象征、先锋等手法,甚至是什么噱头都没有,就是真实,当年大都会版就已经很写实了,而这次英皇版更写实,处处是复古的细节,却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创新的概念和定义似应重新考量了。什么叫创新?都在追“新、奇、特”,但是不追的、诚实的制作反倒抢了眼。我并不主张都像英皇那样真实到用金线刺绣,但设计风格与音乐风格的统一是美的基础。巴黎歌剧院的版本为降低成本,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府邸中一些上层人物夸张而象征性地戴上假发,画了脸谱,但仍然真实地呈现了路易十六的艺术风尚。
舞美耗资不菲,烘托音乐的意境为其宗旨,尤为初涉歌剧的观众带来美感是其目的,而一味任性的实验是应规避的。回想到前不久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阿依达》同样在舞美制作方面有精彩的表现,说明大剧院在制作上开始将舞美与戏剧、音乐同等重视。
更多艺术化的歌剧
国家大剧院成立以来,西洋歌剧中的男高音戏、男中音戏、女高音戏、女中音戏、文戏、武戏、唱功戏、场面戏在舞台上异彩纷呈,填补空白的阶段已经过去。“缪斯女神是很羞涩的”,像这次《安德烈-谢尼埃》这样一部高度艺术化的歌剧,引进版也需要眼光。去年由阿尔瓦雷兹领衔的大都会版《安德烈·谢尼埃》,同样是真实主义制作,却遭遇了滑铁卢,如引进这样的版本,我们的艺术期望值就会大打折扣。引进英皇歌剧院的制作是一个十分成功的选择。联想到不久前国家大剧院推出的另一部高度艺术化歌剧——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来看,新的深度开拓似已到来。不仅也想到,我们民族歌剧的创作能否更多地从艺术化开拓考虑,少些实验与概念化呢?
——寒窑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