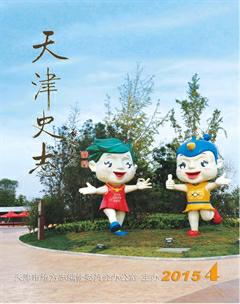方志学与民族学(下)
时培磊 史雪
三、方志学与民族学的合作与交流
独木不成林,一花不成春。一门学科的充实发展不可能代表全部学术界,要想实现整个学术界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加强各学科间的合作与交流。但要进行学科间的互助合作也并非随意几门学科就可以的,而是要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因此,就要找寻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和融合点。通过以上对方志学与民族学关系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可合作性很强,故促成方志学与民族学的合作交流势在必行且前景广阔。
(一)方志学与民族学撰述原则和研究方法的互相借鉴
首先,在撰述原则和工作者素养上,无论进行何种学科的研究,扎实地掌握该学科的理论撰述原则,具备高素质的研究工作者品质都是首要前提。
1.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方志学和民族学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特色思想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学科系统。具体而言,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民族政策是民族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各项中央和地方方针也是方志学研究要注意的方面。党和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制度都是从实际出发,最终落脚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因此,在进行学科理论和实践研究过程中,方志学和民族学都要考虑到地方、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情况,尤其在二者的交叉研究领域。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方志学研究要注意国家民族政策和当地民族自治状况,民族学研究也要联系到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地方政策和民族自治差别。总之,就是要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客观、真实地展现地方和民族的全貌,深化学科理论体系。
2.培养高素质、多元化的研究工作者
历史学作为方志学和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纽带,也使二者拥有许多共同的学科素养要求:推陈出新、大胆实践、求真务实、不畏艰苦、专业基础扎实等等,这些对于每一个研究工作者而言都是最起码的品质。归结到具体学科,有一些独特的学科素养是值得两门学科互相学习的。民族学在田野调查中主要就是与人打交道,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的特殊风俗习惯必须要了解清楚,做到“入乡随俗”,因此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是民族学工作者的必备要求。正如美国人类学家P.K.博克所言:“野外工作者还必须使自己及其研究技术适应当地情况,因为无论谁也无法保证其准备是完全的,哪怕他预先充分地做了准备。对于一个优秀的野外工作者来说,灵活性是最基本的因素,尤其要保持清醒,不过分拘泥于既定的研究方案。”[1] 诚然,无论是方志学还是民族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人沟通和善于应变都是研究者值得学习的一类能力。另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落后而生活艰苦的,同时还有浓厚的民族风俗氛围,民族学工作者就要做到入境问俗和坦诚以待。你只有接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让对方了解调查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少数民族人民才会接受你并乐于配合。同样,方志学在各个地区进行研究工作过程中,也要秉承遵循地方文化和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甚至获取许多意想不到的研究资料。
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我国丰厚的历史资源为方志学和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尤其在研究少数民族聚居区领域上,方志学和民族学各自搜集整理的资料可以相互借鉴和使用,两门学科的工作者也可以相互交流、配合推进学科研究。对于方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笔者在前面分析二者关系时已经提到,在实际应用中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例如,观察与参与观察法,“民族学工作特别注重观察,并以此为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的方法……作为民族学调查……是有目的地细致观察,当地的自然地理、人工建筑等都要尽收眼底,这是对静态的物的观察。另一方面,对当地的日常活动、生活礼仪、人际交往等更要留心,这是对动态的人的观察……通常称为‘现场观察、‘直接观察……民族学调查更强调‘参与观察。这种方法,又被称为‘局内观察法或‘居住体验法。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观察法,其先决条件是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去,至少要一年时间……民族学发展史上许多重大的成果,都是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2] 方志学研究也可以倡导这种观察法,尤其是参与式观察,一味埋首书卷是不可能得到真知、探寻规律的,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而如何深入地方生活实践,学会观察则是方志学要向民族学学习的方面。还有定点跟踪调查法,又称“历史溯源法”,是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进行有间隔性的长期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在总体或局部上发生的演变,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3] 就是一个研究者或研究单位在一个地区设置一两个固定的调查点,每过一段时间就去调查一次,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对研究资料和成果进行对比分析。费孝通的“五访江村”、林耀华的“三上凉山”就是该方法的有力实践,并形成了优秀的学术理论成果。同样,方志学也可以采用这种定点跟踪方式,在所研究的地区设置固定调查点,进行长期跟踪分析,这样的研究成果更具准确性,动态效果更好。
(二)方志学与民族学的相互作用
1.方志学对于民族学
(1)从方志研究中寻找民族的存在感
历代方志文献虽然是从一个侧面或某一角度展现各民族的风貌,但却可以从中深入挖掘出许多汉化程度较高、民族史料匮乏或者已亡佚的相关民族资料,甚至获得一些意料不到或与现实理论相反的史料。这不仅有助于补充民族学研究资料,核实民族学研究理论,还能够找寻已消逝民族或小群体民族的历史存在感,尤其是提升小群体民族的历史主体意识,对于发展本民族文化和生活质量大有裨益。具体而言,就是在方志尤其是民族志文献资料中搜寻以往未发觉的民族研究点,在该民族聚居区进行深入实践探究,将文字材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梳理线索、撰述成文,编订成册,肯定该民族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2)指导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民族
发挥“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作用。例如,在民族学研究中,可以借鉴方志尤其是民族志研究的相关资料,整理出各民族发展演变历程中“汉化”的过程,总结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过程以及规律,从而使民族学在充分认识各民族实际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和方法,有效指导现代民族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方向,使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这样,学科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推进规范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形成过程,同时使民族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形成社会主义社会下健康发展的新型民族。
(3)促进民族融合和多元化发展,建设优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
方志学对民族学研究的协助作用还体现在,它打破了民族学单纯对某一整体民族的全面研究,使得民族学研究的全面性扩大化,拓宽学术视野,将眼光拓展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以往民族学研究有提到民族间关系问题,但落实并不彻底。在方志、民族志研究中可以更宏观地把握和建立对该问题的认识并进行有效解决,甚至将视野放到各民族与周边海外民族的关系发展,这在历史上都是有迹可循的。民族学全面性和整体性的加强,则有利于各民族文化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促进民族融合和多元化发展,将各个“小民族精神”熔融为统一的“大民族文化”,形成多元的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
2.民族学对于方志学
(1)树立正确的民族史观
通过与民族学的合作交流,可以使方志学工作者深刻准确地了解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历程、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而在方志撰述和学科研究中树立正确的民族史观,对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地位有一个正确合理的定位和认识。在古代社会,着重体现在官方史籍和历代政策中,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表现十分明显。一些歧视、贬低少数民族,过分提高汉族地位的文字材料有所存在。在汉族统治者时代存在这种现象,在以元、清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亦然,实际上民族歧视现象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更为明显。众所周知,元朝统治者将社会成员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等级,这种民族等级政策便是最显著的民族歧视表现。金代也有过类似民族等级的划分,赵子砥《燕云录》记载:“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金代虽不像元代的四等人制具有明确的法制性规定,但亦体现出当时民族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实际上,受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的限制,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但其间也存在较为客观公正的民族史观,例如,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过程中也编排了民族列传,而且始终秉承如实记史的记述原则和平等客观的史家态度,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生活方式无丝毫排斥与歧视,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采用庄蹁入滇之事来叙述中原人民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平等往来,深层次也表明了司马迁本人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在现代方志学研究和方志撰述过程中就要秉承这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正确的民族史观,在研究成果表述上采取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民族学研究则为方志学工作者正确民族史观的树立提供了可靠保证。
(2)查漏补缺,核实理论准确性
学科研究工作者作为学科认识的主体,不可避免会受主观意识、知识结构、认知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就需要不断的实践活动和丰富资料的补充核实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这里,学科间的跨学科研究与合作就为查漏补缺,核实研究结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方志学工作中,面对涉及各民族研究,如考订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时间断限的划分等相关史料的真实性问题时,民族学就可以给予很大帮助。同理,在该方面,方志学对于民族学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3)对历代民族政策解读
对于方志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些民族性问题,毫无疑问需要借鉴民族学的帮助。着重体现在对于历代民族政策的解读,历代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映了当时各民族关系,尤其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与融合,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的时代发展状况。这些问题单纯凭借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容易出现观点片面、材料缺失等失误,通过与民族学的交流合作,则可以尽量弥补这方面的缺漏。
总之,强化方志学与民族学的合作与交流,不仅有助于促进整个学术界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其他学科间的跨学科研究树立表率,而且还有利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历史认同感,增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巩固和发展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民族和国家进步都有着深刻而非凡的意义。
四、方志学与民族学的“大数据”时代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有着显著不同,它不再发源于技术工作者之手或者被动地应对社会生产需求而开展,而是积极前进,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由被“生产力”牵着鼻子走转变为与“生产力”携手并进。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化世界,科学技术的主动性愈发增强,不管任何领域,如果想要站在时代巅峰,就必然要学会与科技“携手”。无论是出于时代要求,还是研究需要,当下学术界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持。而在双学科合作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难题无疑便是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何为“大数据”
2013年5月10日的淘宝十周年晚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卸任阿里集团CEO演讲中提到:“大家还没搞清PC时代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来了,还没搞清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大数据时代来了。”“大数据”时代实际上是伴随着人类的网络行为而产生的,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大量的数据信息充斥着世界各个现实和虚拟的角落,传统的数据分析库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信息时代正向数据信息的高效分析处理演进。然而,“大数据”并非一个完全创新的词汇和科技模式,早在1980年,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将大数据称赞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但直至2009年左右,“163数据”才在网络信息技术行业流行开来。已故图灵奖获得者、美国资讯工程学家、数据库专家詹姆斯·尼古拉·格雷提出将大数据科研从第三范式(计算机科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单独的科研范式,即“第四范式”,因为其研究方式已不同于传统方式,其实质已由以计算为中心转变为以数据处理为中心,即数据思维。目前,“大数据”日益受到各行各业人士的关注,但在我国目前主要应用于商业领域。放眼世界,“大数据”发展已然受到国外许多国家政府的关注。“2012年3月,美国公布了‘大数据研发计划。该计划旨在提高和改进人们从海量和复杂的数据中获取知识的能力,进而加速美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发明的步伐,增强国家安全……欧盟方面也有类似的举措。过去几年欧盟已对科学数据基础设施投资1亿多欧元,并将数据信息化基础设施作为Horizon 2020计划的优先领域之一。2012年1月截止的预算为5000万欧元的FP7Call8专门征集针对大数据的研究项目,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4] 因此,“大数据”同各种战略资源一样,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实际意义。在“大数据”时代,国家竞争力也体现在对数据的灵活应用,对科技的重视与发展。
“大数据”现在之所以如此火爆,就在于它依托着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储存、虚拟化技术。简单说,就是一个实用的大型数据集分析与云计算联系在一起,可以将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台电脑同时运作,并伴随不同的工作分配,实现最高效、最优化的工作成果。“大数据”最重要的价值不是掌握最充分的数据信息,而是将这些信息进行专业化处理,以最短的时间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大数据”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目前出现的各种定义多是从特征出发,而数据量的庞大并不能显现出“大数据”同“海量数据”“超大规模数据”等传统概念的区别,因此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3V定义,即认为大数据需满足3个特点: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和高速性(velocity)。除此之外,还有提出4V定义的,即尝试在3V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特性。关于第4个V的说法并不统一,国际数据公司认为大数据还应具有价值性(value),大数据的价值往往呈现出稀疏性的特点。而IBM认为大数据必然具有真实性(veracity)。维基百科对大数据的定义则简单明了:大数据是指利用常用软件工具捕获、管理和处理数据所耗时间超过可容忍时间的数据集。”[5] 可以看出,同传统数据库分析相比,“大数据”具有信息量庞大、数据类型繁多、处理速度快和高价值回报等四个优势,当然,这是建立在合理利用数据信息,并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高效高质量的最佳成果。因此,在多学科合作交流过程中,面对传统研究难以解决的庞杂资料信息分析等问题时,则可以利用“大数据”得以有效处理。
(二)双学科合作研究中应用“大数据”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的应用为方志学和民族学的合作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仅可以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还对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大有裨益。
首先,在政治政策和地方发展上,利用大数据集分析系统,一方面可以整合从古至今的各地方政策和民族政策,并整理出现代各民族尤其是民族聚居区的生活生产现状等信息,从而使党和各级政府在制定地方及民族政策时从实际出发,同时充分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思想,做到有的放矢,宏观调控与微观自主相结合。例如,我国最基本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具体实施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应结合当地本民族的人口构成、知识水平、历史发展特点和实际生活状况等因素来制定实施,协调好国家和地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另外,利用大数据还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正在实行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地区性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就是为了实现地区间的平衡高速发展,使先进地区带动待发展和落后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大数据系统对各地区、各民族信息的分析整合,一方面可以找寻发达地区与被扶助地区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最有效的产业对接;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找出具体工作实施过程中的纰漏,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从而高效高质地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大数据系统具有很强的动态性,能够将近数十年以来的地方各领域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专业化分析,虽然是针对某一方面得出的结果,却可以考虑到所有相关方面的影响效果,使得分析数据更加全面准确,这就有助于帮助少数民族和待发展地区快速找寻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独特优势,形成本民族或本地区特色,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对于地方和民族思想文化的系统分析,也有利于形成健康和谐的地方文化氛围,使民族语言、文字和传统风俗习惯得以完整保留,增进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认同感,进而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建设与弘扬。
第三,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帮助。通过大数据系统对方志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整合分析,对其他学科建设也有很大帮助,例如,在医学方面,针对一些地区性或民族性疾病,可以追溯历史源头,查询相关文献史料,通过研究地方或民族的历史发展历程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状况找寻原因,从而有效破解地区性或民族性疑杂病症难题;在语言学方面,对于研究各地区、各民族共同语系等问题上也可以利用大数据系统得以迅速解决,以最充分的民族语系信息,研究相邻地区的不同民族,发现相似语系特征,或许可以发掘出一些已亡佚的民族语言或文字,实现学科新突破。同时,还能进一步实现民族学和方志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跨学科合作研究,使各学科关系愈加紧密,形成一个整体,完善学科体系。
(三)“大数据”应用的不足与解决措施
“大数据”虽然是数据分析的前沿技术,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同时针对不同的学科需求,仍会存在许多不足与问题,这在学科研究和应用中需引起注意。对此,笔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以供参考和指正。
第一,语言文字问题。大数据使用的前提是数据信息的丰富化和相对完整性,然而在民族学实际研究中,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或是存留文字却没有合适的输入法输入到电子数据库中去。或许有人提议,可以用汉字代替,但在一些学术研究中,有些少数民族文字是汉字无法诠释和形容的。而且,如若所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都以汉字来演化,长此以往,将会有更多珍贵的民族史料和文化无声地消逝,这也将是民族学研究的一大损失。另外,在许多以往的民族史料记载里,有许多类似于一人二传的情况出现,如《元史》中的速不台和雪不台、完者都和完者拔都、石抹也先和石抹阿辛等,其实两两之间都是一个人。这多是由于汉人翻译和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时的不严谨和不统一导致的。而面对这种问题,“大数据”只能机械抉择,而缺乏变通的“思维”,这就为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麻烦。这在方志学研究中虽不明显,但也存在方志文献的个别方言化记载以及同一地方事例不同典籍表述方式留有差异等问题,从而容易造成研究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纰漏和失误。
针对该类问题,尤其在民族学研究中,虽无法彻底解决,但还是可以尽量弥补的。譬如,民族学工作者可以整理出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在计算机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一个专业的输入法或汉化翻译器,然后再利用“大数据”系统进行信息配置和整合。此外,针对同人异名、同一地方事例不同表述等问题,可以建立一个配对库,结合信息数据库自动联系上下文的资料表述,筛选出可能具有一致性的信息名词,再由人工进行判断和抉择,减少研究工作的贻误。
第二,数据完整性和实时性。虽然科技的使用极大便利了研究工作的进行,但所有科技工具和手段都是由人类发明创造,所有数据信息也都是由人来发现和输入的。因此,在民族学和方志学的研究及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利用的“大数据”信息是众可皆知的,既缺乏新的发现,又极易限制研究的视野和角度。同时,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数据信息的实时性也难以保证。
因此,徘徊于文本信息间是难以开拓广阔的学术范围和把握整体的研究脉络的,“大数据”仅是一个信息工具,不可过分依赖。对此,民族学应充分发挥其研究特色——田野调查法。深入田野作业,才能保证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完整性、实时性,同时还可获取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发现学术生长点。
第三,数据泛滥的困扰。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使地球幻化为一个小小的村庄,更使每一个小小的人类个体犹如屹立在宇宙之巅,放眼望去,几乎可以掌握各类信息。甚至每个早晨,只要一睁开眼,无论你愿意与否,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信息都会涌遍你的眼球。民族学和方志学在利用“大数据”搜集、分析信息时也会面临这样的状况,即数据信息的泛滥性造成研究过程的费时费力,使本应高效完成的工作演变为低效低质的结果。这便需要与相关专业人员合作,更新“大数据”系统,甚至制订专门适用于本学科研究的数据库,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方志学和民族学作为两门各自独立的社会科学,既有显著区别,又存在深厚联系,二者的合作交流是一个良性互动关系。在当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环境下,通过采用“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可及时借鉴对方最新研究成果,掌握本学科研究所需有效资料,进而规范和完善学科理论,积极推进国家、地方和民族的繁荣富强和长足发展。同时,也对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树立了典范,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注释:
[1]〔美〕P.K.博克著 余兴安等译:《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4页。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7-168页。
[3]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
[4]李国杰、程学旗:《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年第6期,第649页。
[5]孟小峰、慈祥:《大数据管理:概念、技术与挑战》,《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年第1期,第147页。
参考文献:
[1]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杨群:《民族学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4]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5]王建民:《学术规范化与学科本土化——中国民族学学科百年回眸》,《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6]〔美〕C.恩伯、M.恩伯著 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7]〔美〕P.K.博克著 余兴安等译:《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8]李国杰、程学旗:《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年第6期。
[9]孟小峰、慈祥:《大数据管理:概念、技术与挑战》,《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