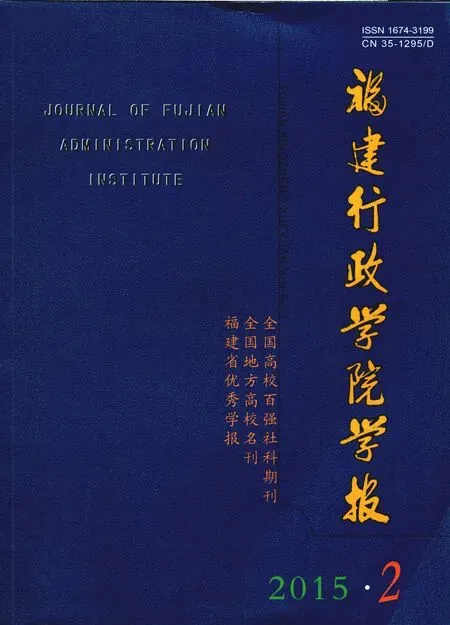论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及行政法展开
徐庭祥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重庆401120)
政治与法律
论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及行政法展开
徐庭祥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重庆401120)
合作国家所内含的指导理念即是改变传统行政管制模式下政府与私人间的对抗关系,通过合作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管制困境,即以合作理念作为国家治理新的规范性理念。按照合作国家的要求,行政将更多地采用公私合作治理的方式进行。规范行政的行政法也就需要有所应对,为实现合作国家建构规范公私合作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保障合作关系建立的行政法制度,以及规制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制度。这些制度拓展了行政法的疆域,属于合作行政法的范畴。
公私合作;合作国家;合作行政法
在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经过“政府放松管制”与“加强社会自治”的阶段,近来又出现了“公私合作”的新治理模式。公私合作处于以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两个极端光谱的中间地带,既可以是私人部门参与国家治理,也可以是政府采用私人部门的组织形态履行治理职能。这些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公私合作治理形态,是否代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是否蕴含可以普遍指导和适用于整个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是否能够作为应当优先选择的国家治理模式,此即公私合作治理理念的规范性问题。
本文利用合作国家模型,在理论阐释上指出公私合作现象内含的合作理念,进而论证将合作理念作为国家治理理念的规范性主张,即合作国家不仅只是存在公私合作现象的国家,更应是以促进公私合作为目标的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应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合作,提升社会合作的水平”。[1]合作国家既具规范性,则需要建构实施合作理念的规范性结构。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在制度层面如何具体展开,如何建构制度以保障公私合作关系的建立,维护公私合作治理的良性运行,是本文要研讨的问题。
一、公私合作的基本类型与合作国家的界定
面对复杂多样的公私合作现象,我们从公私合作在国家治理中不同的法律地位入手,对公私合作进行类型化把握,将公私合作分为“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和“非独立的公私合作”。
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是指参与国家治理的公私合作组织被授予了行政职权,取得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我国存在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实例:《邮政法》第25条授予邮政企业属于典型警察职权的检查权,使邮政企业有权检视邮件,《邮政法》第26条第1款授予邮政企业处理违禁品的权力,《重庆市轨道交通条例》第4条第4款授予采用公司制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行政处罚职权。这些属于私人部门的公私合作组织被纳入国家人格,被视为行政主体,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同时应当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是指公私合作组织虽未被授予行政职权,但仍以其自主意志参与国家治理。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常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因私人具备专业技能而在具体执行环节替代行政机关履行。例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由民营汽车检验公司代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机动车安全检验的行政任务。由于机动车的大量增加,国家通过引入民营汽车检验公司的方式,替代行政机关履行检验任务,减小自身的人力和财力负担。此时民营汽车检验公司自主执行检验事务,但检验是否合格的行政职权仍由公安机关享有和行使。第二类是国家将本来由依行政职权进行管制的行政任务,转而采取非权力手段进行治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设立私法组织,亦容许纯粹的私人参与。这一类在我国的典型事例即是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47号)设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电力、能源、供水等其他的公用事业的民营化,亦产生了大量的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
非独立的公私合作,是指公私合作组织不仅没有别授予行政职权,而且在国家治理中根据行政机关的命令和指示活动,不享有自主意志,被行政机关作为自己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加以利用。例如:《重庆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操作规程》规定由银行发放养老保险,《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由家电销售企业向购买人垫付政府补贴。上述两例中的商业银行和家电销售企业,均属于行政助手。类似的事例还有,商业银行代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收取罚款,商业银行此时只相当于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财务机构,在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完全指令下参与行政处罚的执行。[2]
上述三类公私合作中,相较于被纳入国家人格的职权独立公私合作,以及被纳入政府官僚体制的非独立公私合作,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最具有开创意义。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中,改变了政府直接管制的传统行政方式,转而由私人部门中的组织,运用非权力的手段进行国家治理,开创了新的国家治理模式。除前述事例外,再以粮食安全和粮食流通秩序治理为例,我国不由农业行政部门直接予以管制,而是依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的规定,由承担临时存储粮竞价销售的粮食批发市场、负责提供交易标的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及负责成交粮食的货款结算和贷款回收工作的农业发展银行,这三方私部门主体综合采用市场的手段开展粮价治理,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满足市场需要,保持粮食市场稳定。这些私部门主体不属于传统的国家领域,却参与了应由国家负责的粮食安全治理,这创造了新的国家活动方式,需要新的国家模型才能予以归纳。
德国学者海特(Ernst-Hasso Ritter)首先提出了合作国家(cooperative Staat):“合作国家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社会主体和经济行为经过转化服务于国家目的,它的公共任务正是利用这些行为主体的社会化加以完成。”[3]合作国家抓住了国家治理模式革新的要点,即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的社会化变迁,准确的描述了以公私合作为典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从国家学的视角考察,使合作国家作为一个分工的、专业的和多元的统治组织和行政组织得以理解”。[4]本文以海特的合作国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公私合作内含的规范性理念。
二、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建构
德国学者海特的合作国家,只是描述了合作国家这一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外在特征,即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私部门化(Privatisierung),但没有深入挖掘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私部门化变迁给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和理念性变革,从而无法揭示合作国家模型内含的规范性。也即是说,海特的合作国家,只是对实践中大量公私合作现象外在特征的一种归纳,并未考量这些出现在个别行政领域的外在特征中,是否蕴含可以普遍指导和适用于整个国家治理的规范性目标。
国家模型并非通过对国家现象的外在特征进行描摹就能够建立。“国家理论也不能仅被理解为是一门纯粹的‘事实学科’,‘国家现实’同样包含规范要素,因为国家共同体更应当被视作有意义导向的,尤其是有规范导向的行为构造。”[5]4合作国家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上区别于传统国家模型下的官僚制政府管制行为,意味着合作国家在对国家目的的认识上,或者在对国家目的的实现方式上,区别于传统的国家模型。因此,有必要阐释合作国家的规范性理念,建构合作国家的规范性,以实现合作国家模型的规范指导功能。
(一)合作国家的规范性理念
德国学者海特描述的合作国家现象,其所内含的指导理念即是改变传统行政管制模式下政府与私人间的对抗关系,通过合作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管制困境,即以合作理念作为国家治理新的规范性理念。
合作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人类的历史,合作理念古已有之[6],但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作为指导国家权力行使的优先理念,是近来的现象和趋势,尤其以20世纪末“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论的提出为标志。普遍认为,“善治”是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非洲国家治理的危机所提出的评价性概念[7],“‘善治’可以被看做是治理的衡量标准和目标取向,所谓‘善治’即是结果和目标意义上的‘良好的治理’”。[8]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被认为是善治的典型特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就指出:“善治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形成公共事务中相互作用”。[9]我国学者俞可平也指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0]
但合作理念的规范性并非来源于善治理论,合作理念对国家治理的规范性根植于人类社会应对国家管制失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面对仅以管制为手段的官僚制政府,出现公共物品供应短缺、行政决策无法应对复杂的风险社会、官僚主义日趋严重等政府失灵现象,通过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合作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日益成为共识,“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11]因此,善治理论只是对人类普遍共识的正确概括而已,而人类共同体基于公私合作的善治效果,对国家角色和政府目标进行再认识,才是合作理念规范性的思想基础,对公私合作的普遍选择,才是合作理念规范性的社会基础。将人类共同体在国家治理中选择公私合作的共识予以规范化,使其具有普遍指导和适用于整个国家治理的效力,合作理念即具有了规范性。
我们应当在理论阐释上指出公私合作现象所内含的合作理念,指出合作国家所具有的规范性,即合作国家不仅只是存在公私合作现象的国家,更应是以促进公私合作为目标的国家,公私合作应当成为国家治理实践中优先选择的治理模式,此时合作国家即成为具有规范性的国家模型,其包含为了实现善治而优先采用公私合作治理的规范性要求。
(二)合作国家与传统国家模型关系的再认识
但公私合作受到与传统“国家社会二元论”国家模型相冲突的批评,“合作虽有其正面评价,但其缺点亦不容忽视。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距离乃是法治国与民主的价值。合作可能会导致此一距离消失、造成个人特权、官商勾结甚至于腐化”。[12]31如果这些批评成立,公私合作即可能导致破坏民主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结果。因此,有必要深入检讨公私合作内含的规范性理念与传统国家模式的政治安排之间的关系,澄清公私合作是先进的国家治理模式此一主张的规范性来源,以此为实践中公私合作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理论支撑。
故要证立合作国家的规范性,还需要探讨合作国家模型与传统“国家社会二元论”模型的关系。合作国家允许采用私人部门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履行国家治理职责,这被有的学者认为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论”模型相冲突,后者要求只有国家官僚层级机构才有资格行使行政权力,私人部门则没有资格,否则将导致国家与社会二分架构的破坏,“在‘合作国家’中,国家机关与诸社会势力间的距离已被消弭”[12]31,“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公私协力带来的国家与私人关系的演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基本命题。”[13]本文不赞成这些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社会二元论”模型并未禁止私人部门参与国家治理。国家社会二元论所要求的,是行使强制权力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官僚机构,非行使强制权力的其他国家活动不受此限。因为只有在公民基本权利可能受到国家侵犯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行使才在事前通过社会契约取得全体公民的授权,而只有国家官僚机构才凭借其权限位阶结构(Stufenbau der Kompetenzen)享有“法定的机构化的政治权力”[5]82,从而保证强制权力的行使与民主授权之间存在“不断的正当性链条”(ununterbrochene Legitimationskette)[14],因此,强制权力才要求只能有国家官僚机构行使。但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现代行政出现了许多不需要采取强制手段的行政任务,更有传统需要政府管制的行政领域转而采用非强制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这些现象并不与国家社会二元论的要求相冲突,德国学者Roman Herzog就正确的指出:“国家独占物理上强制力所涉及的是权限形式的问题,非关任务领域的转移”。[15]
第二,通过基本权利保障社会自主性的机制并未受合作国家破坏。通过基本权利保障社会自主性,是国家与社会二分模型的重要政治机制,传统认为只有保持私人部门和国家的绝对二分,才能保障私人享有基本权利,并在受到国家侵害时能够获得法律保障和救济,而当私人部门进入国家领域活动时,由于其并非国家机构,其基本权利就无法对抗公私合作中的侵害行为了。其实并非如此,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模式,是一种功能结构,而非用于区分私人与国家的主体理论,基本权利所对抗的是全部从事国家活动的主体,而不论其组织结构是政府官僚机构或其他。“当部分学说将上述基本权理念过度简约成‘私人对抗国家’(Privatpersonen gegen den Staat)之模式时,实际上已误导性地将基本权之本质重心从‘功能面向’转移至‘主体面向’上。实则,基本权之核心价值理念应在于抵抗‘公权力行为’不法侵害‘基本权所保障之自由领域’。质言之,凡立于基本权所保障之自由领域,这皆为基本权主体;反之,凡行使公权力者,则应受到自由基本权之拘束。”[16]因此,公私合作同样受基本权利的约束,通过基本权利保障社会自主性的机制并未受合作国家破坏。
综上所述,合作国家并未否定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政治安排,合作国家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分前提下,对国家治理模式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提出的优化要求,是对传统国家模型的完善和补充。导致错误认识合作国家与传统“国家社会二元论”模型关系的原因,是形式化的理解国家与社会二分,认为只有国家机构和社会主体的绝对分离才是符合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制度设计。这一错误没有认识到国家与社会二分所要求的,是在实质功能上能够保障民主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因此,当出现公私合作等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时,不应当用形式化的错误观点去否定革新,而是应当综合新治理模式的规范性目标与传统国家模式的政治安排,考量如何改进法律制度,使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民主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的约束下得以成功建构和有效运行。因此,合作国家并不与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安排相冲突,合作国家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在法律层面的,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符的现行制度与理论该如何改变以适应合作国家的问题。
三、合作国家的行政法展开
“行政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与当时流行的国家主导理论直接相关的”[17],按照合作国家的要求,行政将更多的采用公私合作治理的方式进行,那么规范行政的行政法也就需要有所应对。行政法不能再将视线局限在传统的政府管制,而需要为实现合作国家建构规范公私合作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保障合作关系建立的行政法制度,以及规制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制度。
(一)建构保障合作关系建立的行政法制度
按照前述公私合作的基本类型,建立公私合作关系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授权、订立行政契约和设立组织。
通过授权建立的是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我国现行法中存在授予私人部门行政职权的实例,但没有从行政法整体的角度建构相关理论制度。我国台湾学习德国,建立了所谓“委托行使公权力”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委托行使公权力之人或团体成为行政组织法上重要的制度,并且可能在所有现代国家的任务领域出现。从传统典型的机长及船长执行警察权、私立学校颁授学位,一直到现代秩序法及各种安全法规领域,例如民营汽车制造厂或修理厂代办汽车检验*参见:我国台湾《公路法》第63条第3项、我国台湾《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7条。、商品检验、录像带节目审查及合格证明文件之核发,乃至于财政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例如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防治费之征收或公路及附属停车场之兴建及收取费用,甚至罚锾之处罚。”[18]授予私人部门行政职权的制度,属于保障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行政法制度,除包括授权的前提条件,授权的形式和程序,被授权人的选择等,其制度核心为授权的法律效力,即授权后作为被授权人的私人部门、授权的政府、以及行政相对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是合作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通过建构授权制度来保障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关系得以建立。
订立行政契约是建立公私合作关系的重要方式,传统行政契约理论并未包括建立公私合作关系的事项,故行政契约有必要应公私合作进行扩充,“行政契约法制必须作适当的扩充以便容纳公私协力关系中公部门与私部门的互动。”[19]德国率先对此采取修法举措,联邦政府于1999年12月1日在内阁会议中通过“现代国家—现代行政”(Modere Staat-Mordere Verwaltung)的行动纲领,提出:“联邦政府将致力于建构合作契约的法律规范,对于公私协力行为以现行的行政契约法制而言,并不足以彰显合作国家的积极意义及创造新的责任分担模式。因此应于行政程序法中规范(公私协力)合作关系适当之契约类型及契约条款。”[20]联邦内政部为践行此纲领之要求,于1997年12月9日设立由学者、法官、律师、官员组成的“行政程序法咨询委员会”(Beirat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负责初拟应对私人行政的行政程序法修改方案,并委托柏林洪堡大学休培特(G. F. Schuppert)教授和史拜尔高等行政学院齐科夫(Jan Ziekow)教授对其方案进行学术鉴定,最终作成两份鉴定意见书。两份意见书虽在具体细节上不完全一致,但对于在《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增设“合作契约”(Kooperationsverträge)类型和相关规定意见一致。[21]27其中齐科夫教授的意见书中建议在《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增订第62a条,对合作契约做出规定:“官署得于履行公共任务时,透过契约与私人为下列之合意(行政合作)而共同协力完成:将公共任务的履行责任转嫁于私人,官署则必须采取实际上履行任务的措施;将从事公共任务的工作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私人,官署则保留任务履行的责任;不以成立公私混合的私法人型态而与私人以伙伴的合作形式共同完成公共任务。”[21]27可见,除通过授权和设立组织建立的公私合作外,通过在合作契约中约定公共任务在公私两方之间的责任分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构多样的公私合作形态。通过合作契约建立公私合作,将可根据国家治理和公共任务的具体情况,更为灵活的应用私人部门在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我国尚未建立行政契约制度,或可利用此一后发优势,建构我国的合作契约制度,从而我国实践中常见的公共服务外包、公共事业特许经营、基础设施的BOT营建等公私合作形态,其合作关系的建立均应受合作契约制度的规范。
政府与私人部门设立公私混合的私法人型态,而与私人以伙伴的合作形式共同完成公共任务,此即以设立组织方式建立的公私合作关系。通过设立公私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建立公私合作,能够使政府利用公司治理结构直接影响和监督合作治理,相较于订立行政契约往往只有在事后对是否违约展开监督,设计组织使政府能够在事中更直接的将公共利益输入公私合作组织。但设立公私合作组织如果仅凭借私法,按照出资多少决定对组织的影响,则在国家资本少时就无法保障公共利益对公私合作组织的有效输入,故德国行政法学提出了“行政公司法”(Verwaltungsgesellschaftsrecht)的主张,“当公行政早已走向组织私法化之途,渐渐以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态出现时,那么行政法也必须开始研究公司法制”。[22]131我国同样存在大量以设计组织方式建立的公私合作,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除可以通过订立行政契约建立外,设计组织亦是重要的建立方式。因此,我国亦应考虑区别于私法的行政公司法制。
(二)建构规制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制度
行政法除落实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建构保障公私合作的制度外,还应出于保障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建构规制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制度。除职权独立的公私合作因被纳入国家人格而受传统行政法规制外,对于组织独立的公私合作和非独立的公私合作,由于并不涉及行政职权的行使,故往往不受传统行政法的约束,但如果仅依靠以保障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私法对其进行规范,又使公私合作治理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提高国家活动的灵活性和合作性的努力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关系人权益保护,这种努力必须谨慎”[23],因此有必要建构规制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制度。
1.建构规制公私合作组织的监督影响义务。通过公私合作开展国家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公共任务不再负有责任,国家仍应对公私合作组织发布指令与进行监督。德国行政法学提出国家对公私合作的“履行监督影响义务”(Kontroll- und Einwirkungspflicht),来避免国家成为“甩手掌柜”,确保其对公私合作组织的监管,使公私合作不致偏离公共任务的目标。
监督影响义务的意义不只在于明确了行政机关监督私人的义务,更在于明确了行政机关监督私人的方式。行政法允许采取公私合作治理,意味着行政法认可公私合作的优越性,如果仍然以政府机关通过层级命令来管控公私合作组织,将使公私合作的灵活性被层级指令意志压制,“将公营企业法纳入行政组织法并不代表要公式化地套用行政机关及公法社会团的组织原则。认为以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的形式设置公营企业乃是行政‘逃入’私法,从而必须尽可能地回到行政执行法制内的观念,对此处或他处也一样,帮助并不大”。[22]252因此,监督影响义务明确了行政机关不以层级命令的方式监督私人,而是可以一方面透过对事业经营负决策责任之重要人员(如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等)的指派,另一方面规定在董事会、监事会等私法组织的意思机关中发挥主导作用等方式确保行政的监督影响以及业务执行的公共目的,而不通过层级命令直接干预公私合作治理的具体运行,“如果认为有必要强加拘束,而政府部门又想获取额外的影响力,则必须回头采取类似自营事业或营造所的组织形式”。[22]254
德国《联邦与州财政预算基准法》(Gesetzüber die Grundsätze des Haushaltsrechts des Bundes und der Länder)第53条第1款即是规定监督影响义务的实例,其规定了地方政府对其参组的私法企业的权利(Rechte):“若一个私法形式企业的股份,大多数属于地方自治团体,或者至少四分之一属于地方自治团体,并且此地方自治团体和其他地方自治团体一起合法拥有了该公司大多数的份额,那么它有权要求公司:(1)在年度结算审查的框架下,运营的规章制度也列入审查范围。(2)委托年度结算审查员,在他们的报告中要报告以下内容:公司资产和收益情况,以及公司流动资金和经济效益状况;报告亏损项目和亏损原因,当这些经营项目和原因对公司的资产和盈利举足轻重的时候;报告在盈亏计算中出现的亏空额的原因。(3)向地方自治团体报告审查员的结算审查报告,当公司要进行集团结算时,集团结算审查员也要不延迟地上交呈报集团审查报告。”
我国也存在规定监督影响义务的实例。我国政府通过设立国有担保公司履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共任务,财政部2001年发布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对国家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做出了具体规定,该办法第5条即禁止行政机关通过层级命令方式监督担保公司:“担保机构应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照规定程序对担保项目自主进行评估和做出决策。担保机构有权不接受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为具体项目提供担保的指令。”故该办法在后面的规定中均以规定担保公司的经营指标的方式,间接来实现行政机关对担保公司的监督。
虽然我国实践中已经存在属于公私合作中政府对私部门监督影响义务范畴的制度,但由于尚未建立基础的学理,监督影响义务并未能在公私合作中得以普遍落实。更为重要的是,监督影响义务的内在法理在于寻求保障公私合作的灵活性与监管之间的平衡,如果此法理未得以澄清,则难免会出现以直接干预代替间接监管,或者单纯用盈利指标来监管公私合作的两类极端情况。因此,有必要在学理和制度上明确行政机关对公私合作进行监管的平衡目的,确保监督影响义务以正确的方式履行。
2.建构规制公私合作行为的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仅从组织法制的角度间接监督公私合作必然存在不足,还应完善对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规制。我们反对行政机关对公私合作的直接干预,但这与公私合作受法律的直接约束是两回事。就对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规制而言,应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
就实体规范而言,核心的是对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给付公共产品的行为予以约束。公私合作涉及面广,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形态多样,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繁多,给付职责的履行不再限于金钱给付,还包括劳务给付、物品给付、信息给付等。因此,根据具体情况详细规定给付的质量要求是公私合作中公共利益和相对人权益保障的核心内容。前述德国休培特教授在建议《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增设合作契约的鉴定意见书中,认为通过签订合作契约建立的公私合作,应当在契约中约定质量保证条款,即公私双方必须就公私合作所提供之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品质达成合意,并且应当详细约定给付的内容、范围、品质、价报以及对品质之评价基本原则与基准。[21]27我国亦有必要将规定公私合作给付质量的内容作为公私合作的强制规范,即不论何种形式的公私合作,均应明确给付质量的详细情况,如果是通过设立组织建立的公私合作,则应当在公司章程等公私合作基础性规范中,约定质量保证条款。总之,不论公私合作采取何种形态,都应以保证公私合作给付质量为核心,落实对公私合作的实体规范。
就程序规范而言,则应重点完善公私合作的建立程序。公私合作虽然是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但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因此,在建立公私合作关系、选择私方合作者时,就需要配置相应的程序规范,以保障公共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故公私合作的建立程序属于分配程序,“分配程序(Verteilungsverfahren)在于提供有限资源之分配”。[22]343政府采购法即是典型的分配程序,2014年12月31日由我国财政部发布实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即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程序的约束之下,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程序机制,保障合作人选择的公正性,保证建立权利义务平衡、物有所值的公私合作关系,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保证参与人都能受到公正的对待,维护公私合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该办法适用范围有限,我国目前还仍主要从资本合作的狭义视角来看待公私合作,主要的公私合作事项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更多的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履行公共任务,即政府借助私人部门的专业能力而非资本,则没有被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视野。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程序的适用范围,将全部的公私合作事项纳入政府采购法的约束范围,为公私合作的建立提供程序保障。
四、余论:建构合作行政法
合作国家倡导的公私合作治理,必将引发行政法变革。随着国家治理更多的采用公私合作形态,合作理念应当作为行政法的规范性目标,如何促进合作应当成为行政法的目的之一。我国行政法学重视研究行政法的目的,行政法的目的是控权、是服务、还是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已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即使在理论上就行政法目的达成了一致,指导行政法具体建构的规范性目标,仍需结合各行政任务领域不同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具体化才能得出,才能对行政法的建构和适用产生更具实践意义的影响。以我国《宪法》为例,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这并不是《宪法》对法律与行政关系的唯一决定,《宪法》第14条至第26条还规定了国家需要积极创造而非消极执行法律才能完成的诸多公共任务,法律对行政的规制亦需将法治目标与这些宪法目标相结合,建构机制保障行政对这些任务的履行。
公私合作实践的善治效果正是对多元宪法目标的回应,面对合作国家的合作理念在各行政任务领域与各宪法目标的有效结合,行政法自应当建构相应的规范性结构,以保障合作理念的实施。这即公私合作带给我们的行政法问题意识,我们需要为公私合作建构不同于仅以落实法治原则为目标的传统行政法的规制模式。本文研讨的“合作契约”“行政公司法”“监督影响义务”等,区别于传统行政法为政府管制所配置的“法定权限”“层级组织”“法定程序”等规范性要素,以促进公私合作的建立,维护公私合作的良性运行为目标,为公私合作建构了新的行政法规制模式,“法律并未向合作国家投降。毋宁‘将新的行政效力注入行政法’。”[22]166这些制度拓展了行政法的疆域,属于合作行政法的范畴。合作行政法区别于传统行政法的控权目标,兼顾合作目标和对合作的监管,以使对公私合作的监督既能有效的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又不致对私人部门的灵活性造成损害。
合作行政法拓展了行政法的适用范围,将原本不受传统行政法规制的公私合作,纳入了行政法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合作行政法采用了不同于传统行政法的规制模式,对行政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开拓了思路。但对合作行政法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合作行政法自身体系的完善,其与传统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理清。
[1] 王学辉,张治宇.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以“诸神之争”为背景的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14:(4):54-62.
[2] 徐庭祥.缴罚款为何挂钩银行卡[N].法制日报,2012-08-22(7).
[3] Ernst-Hasso Ritter.Der cooperative Staat, in: AöR 104 Jhrg./1979[M]//Guido Pöllmann, Kooperativer Staat und Parteiendemokratie.Berlin: Galda+Wilch 2006.
[4] Guido Pöllmann.Kooperativer Staat und Parteiendemokratie[M].Berlin: Galda+Wilch 2006.
[5] [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M].赵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6] 王学辉,张治宇.迈向可接受性的中国行政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3):97-106.
[7] 张康之.公共行政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8] 魏治勋.“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J].法学论坛,2014(2):32-45.
[9] [美]G. 沙布尔·吉玛,丹尼斯·A.荣迪内利.分权化治理:新概念与新实践[M].唐贤兴,张进军,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10]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 [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31-46.
[12] 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J].月旦法学杂志,2005(5).
[13] 邹焕聪.论公私协力中私人主体的基本权利能力——以公私合作公司为中心[J].天津法学,2013(2):25-30.
[14] Utz Schliesky.Souveränität und Legitimität von Herrschaftsgewalt[M].Täbingen: Mohr Siebeck 2004.
[15] Roman Herzog.Vorbehalte und Grenzen der Staatstätigkeit[M]//J. Isensee/Paul Kirchhof(H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Band Ⅲ, 1988.
[16] 詹镇荣.从民营化观点论公民合资公司之基本权能力[J].高大法学论丛,2008(1):20.
[17] [美]Alfredc·Aman.面向新世纪的行政法(上)[J].袁曙宏,译.行政法学研究,2000(3):84-91.
[18] 胡建淼.公共行政组织及其法律规制暨行政征收与权利保护[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9] 陈爱娥.行政法学的方法——传统行政法释义学的续造[J].月旦法学教室,2011( 2):35.
[20] 吴志光.ETC判决与行政契约——兼论德国行政法契约法制之变革方向[J].月旦法学杂志,2006(8):26-27.
[21] 程明修.公私协力行为对建构“行政合作法”之影响[J].月旦法学杂志,2006(8).
[22] [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林明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3] [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郑继汤]
On Normaliz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State and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XU Ting-xiang
(School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The guiding idea embedded in the cooperative state is to change the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ividuals in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ministration and to come out of the plight of the market failure and the government failure, i.e. the cooperative idea is taken as the normative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operative state, mor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done in the way of cooperative management by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together, thu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which regulates administration, need change accordingly. The legal system must be constructed to regulate the public and private cooperation for the cooperative state,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ve law systems of ensuring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nd regulat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cooperation, which expands the ran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can be referred as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public and private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state;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2015-02-10
2014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4BS052);2014年度西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青年项目(2014XZQN-04)
徐庭祥(1983-),男,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讲师。
D912.1
A
1674-3199(2015)02-004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