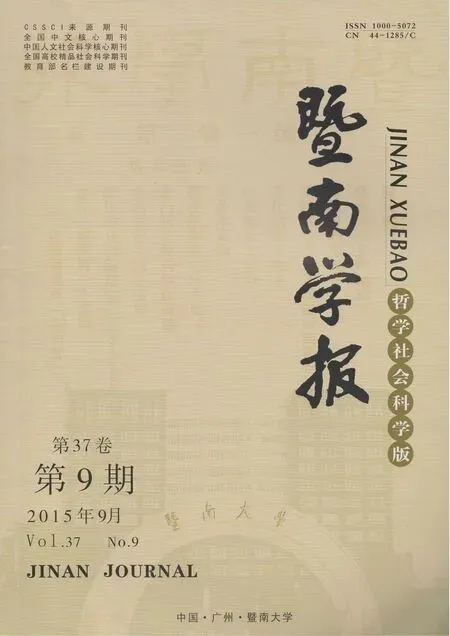中唐礼官的精神品格与文学思潮的兴起
于俊利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传媒系,陕西 西安 710068)
文学思潮的形成,自有文学传统与审美观念等方面内在因素的化育作用,但是,特定的时代环境却往往成为最为直接的促成机因。就唐代文学思潮而言,如果说,开元天宝时代的理想主义恰是强盛高朗的时代气象对文人心理强烈感召的结果,那么,贞元、元和时代权德舆、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礼官文人关注现实风格的形成,则显然与时代革新图变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社会痼疾,在贞元、元和年间更趋于激化,并出现新的矛盾。社会危机促发思想危机。这时,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礼官文士,坚守儒家化的政治人格,以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走向历史前台,直接参与中唐的思想与文化重建。他们重新确立儒家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来匡正时弊,解决新的时代课题。
对此,葛兆光先生谈到:“在贞元年间国家渐渐恢复元气。外患略略平定后,一批由礼官出身的文士渐渐替代了财政出身的官吏,朝廷中的议论话题也渐渐由理想的秩序重建取代了策略的现实管理。这种变化促使‘折中定议,损益仪法’,即朝纲重整的想象越来越成为士人舆论,并影响到实际的政治操作。”蒋寅先生在《大历诗人研究》中也指出,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这批文人“有共同的礼学或史学的背景”,“贞元后期,烽火稍歇,矛盾的焦点就转移到典礼方面来。如果说大历至贞元前期,是由刘晏盐铁转运府中的人才充任政治、文学舞台上的主角,那么贞元后期则是由权德舆周围的由礼官出身的人才充任政治、文学舞台上的主角了。”这些论断都明确地指出了礼官出身的文人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和政治作用,但是,均未作为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贞元、元和之际的礼官,大多兼有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身份,这使得他们可以用特有的文人视角来看政治,也可以从政治的角度,从经世致用出发来对待文学。本文通过分析贞元、元和之际礼官文人思想文化的精神品格,试图考察礼官文人及其职事活动在中唐文学思潮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唐代历史上这一转型时期文学的生成、发展规律进行解读。
一、中唐思想文化秩序的重建与礼官主体地位的确立
安史之乱后,中唐政权已难续昔日之辉煌,李唐王朝在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权的内外交困中风雨飘摇。中央集权统治一蹶不振,地方藩镇叛乱此起彼伏,时时威胁着唐王朝的存在。德宗建中三年(782 年),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同时称王,自称孤或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中国自古“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种更改届下配置和名称的做法,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僭越,更是肆无忌惮的挑衅。
对国家政治权威与强大而有效的皇权的诉求,在文人士大夫这里,主要表达为对思想文化秩序的诉求。儒家传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向心力,成为唐王朝维系人心、巩固王权的精神支柱。《礼记》开篇即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立”。礼不仅“节民心”,防止“悖逆诈伪之心”,杜绝“淫佚作乱之事”,而且教导人们恪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常纲纪,协调人际关系,维护宗法秩序。长于经史的礼官士人群体这一时期被前所未有地推向政治舞台的前台。从至德、乾元至永贞、元和时期,颜真卿、李泌、梁肃、柳冕、陆贽、权德舆、李绛、高郢、陆质、崔元翰、郑余庆、杨於陵、韦渠牟、王绍、崔从质、仲子陵、王仲舒、许孟容、陈京、唐次、齐抗、冯伉、张荐、徐岱、蒋乂、崔邠、令狐楚等一批由经史出身的礼官文士渐渐相继主持或参与朝政。作为朝廷中的儒者重臣,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表现出对社会道德提升的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他们企图用道统来维护政统。礼官文士以儒家道统的卫道者自居,坐镇朝廷,不仅以深厚的儒学素养及对典章故事的熟知,正君臣,别名分,以仪式规则来清理社会秩序,而且重构文化理念,推原“礼制”之本源,以其内在根据的诚、忠、义、情等来重新衡量、裁断具体的“礼制”,发掘儒家思想的思想实质及现实功能,从而以重新确立儒“道”在学术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
贞元之前的礼官,为中唐儒家政治伦理的重建拉开了序幕,表现出这一精神上升时的最初动向与文化意义。宝应元年,礼部侍郎杨绾认为对文辞章句之学的好尚有损于人们对儒家经典思想道德的关注,对个人道德品行的关注,而提出废除科举制建议,引起了科举制度重经义务实的改革;建中元年,颜真卿为礼仪使整顿山陵陵寝之礼,初步恢复祭祀礼制规模;德宗奉天之难中,陆贽依经立义,为德宗作“罪己诏”颁布与天下,在兴废存亡的关键时刻,更以儒家道德精神的感染力维系人心、振奋士气,民心军心为之大振,局势因而大变。不久,动乱即告平息。韩愈《顺宗实录》卷四记述了当时的情形:“行在制诏始下,闻者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议者咸以为德宗克平寇难,旋复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盖以文德广被,腹心有助焉。”礼官儒者的改革的努力充分显示了儒家文化“文德广被”的现实功能与价值意义。他们着眼政治改革倡扬儒家经学的思想和做法得到了贞元礼官的继承和发扬。
这时期的低品秩礼官中,太常博士发挥古学,弥纶礼制,职事活动尤其频繁。《旧唐书·柳冕传》载:“(贞元)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柳)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新唐书·张荐传》载:“贞元元年,帝亲郊。时更兵乱,礼物残替,用荐为太常博士,参缀典仪,略如旧章。”除了张荐、柳冕、徐岱、陆质,翻翻《旧唐书·仪礼志》、《新唐书·陈京传》及诸位作者的传记,我们会看到,陈京、权德舆、仲子陵、蒋乂等人也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经历。德宗朝几次重大的典礼争议,他们都卷入其中,仕宦并不显达的仲子陵就是因议礼而著名的。《新唐书》卷一二五《儒学传下》载:“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皆自名其学”,明确指出“士匄、子陵最卓异”。
太常博士在制礼、议礼中,表现活跃,其在唐代中后期政治地位逐渐升高。我们只要检索一下《唐代礼官表》便可以发现,唐代中后期的太常博士如权德舆、令狐楚、李吉甫(贞元中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白敏中、崔龟从,后均升任宰相,其他的多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措施层面,太常博士、礼部侍郎等这些掌握着行政资源、且文明颇盛的礼官文人,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把复兴儒学、修复礼教秩序、重建国家政治权威的思想逐步落实到政治活动与社会文化活动中。
二、经学复兴与礼官的用世务实思想
贞元、元和时期,不仅盛唐时期张说、张九龄启用旧有礼法以应付新问题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而且杨绾作为士大夫文化精神的象征性领袖所提出的完全复古倒退的取士观显然也已经不能适应改变的时代背景,传统无法对新的社会变动给以解释与批评的时候,仅仅用原有的知识与思想已经无力回天。基于巩固王权、中兴唐朝统治之共同目的,经学重新受到中唐礼官文人的重视与倡扬。但是,所不同的是,盛唐偏重复古,中唐重在革新;盛唐停留在章句之学的表面,中唐则深入到了礼乐经义精神的内在。中唐时期的经学已经由唐初的“统一时代”走向分化革新的时代。中唐从政治上提高经学的地位,而经学自身也开始了自振与变异,从而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改革与重建运动的理论支点。
中唐礼官从传统儒学汲取思想资源,尤其重视当时具有变革意味的经学学派——《春秋》学派。礼官文士倡复儒道的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及对现实政治批判的勇气,与《春秋》学派以经立义与通经致用的政治立场,重振纲纪、务实图强的革新导向都有相通之处。
出于复兴和发展儒学的需要,大历以后,一批“异儒”开始批判“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古文经学传统,而直接从“六经”中探求“圣人之微旨”、“王道之根源”。“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淳《春秋》,施士匄《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中,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成为这一股新经学思潮中最卓异者。而他们所理解和阐发的“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突出地显示了儒学探求伦理道德之内在本源的思想转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礼学的态度上。啖助说,“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实在于“救时之蔽,革礼之薄”。《新唐书·儒林传》认为,啖助、赵匡所理解的“《春秋》大义”,乃是指孔子“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这虽是从具体的“礼制”层面阐发《春秋》大义,而事实上,啖、赵所明“《春秋》大义”,其重大意义在于已向内深入到“礼制”之本源的层面上了。啖助的这样一段话其实更值得注意:“是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这就是说,孔子在《春秋》中推原“礼制”之本源,以作为“礼”之内在根据的“诚”、“忠道”、“情”来重新衡量、裁断具体的“礼制”。啖助所言“《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表面上同于旧说,而实际上则是从具体的礼乐之“文”深入到根本的礼乐之“质”,从外在的“名位”达于内在的“性情”。对此,赵匡阐述得更为明白:“然则圣人当机发断,以定厥中,辨惑质疑,为后王法。”所以,在他看来,《春秋谷梁传》所说:“《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诫,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孔子《春秋》推原礼义,穷究性理,要弄清楚的是所以褒贬之“本”要确立的是终极性的、根本性的价值原则,并据以推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价值体系:“齐心极虑,于此得端本澄源之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匡说:“《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啖助说:“(《春秋》)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两人都特别强调了《春秋》作为“经”的性质,关键在于其重心在“义”、“道”。他们认为礼学的意义不只是为帝王制定礼乐制度与礼仪规范,而是在于阐发其中的维系人心的道德力量。他们已不再把经文礼制的外在形式作为经学的主体,他们关注的是它内在的道德生命,他们的视角已由形而下的礼器转向形而上的儒道,并以此来“从宜救乱,因时黜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通过解读经书,依经取义,发挥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作用的思想可见一斑。可以说,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这时期的文化建构,它使儒学逐渐走上了由谨守章句训诂向追求精神义理的转换之路。同时,也为中唐士人以时代的精神来追求儒家的先王之道,联系社会现实来重新确立儒学传统的价值观念开辟了道路。
这些与中唐礼官文士思想文化重建的出发点与指向都不谋而合。作为《春秋》学派的主要人物,陆质本人曾长期担任礼官。陆质初以精于儒术而知名。《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修传始终记”末言:“淳,字伯冲,吴人也,世以儒学著,时又为陈公荐,诏授太常寺奉礼郎。”《旧唐书》:“转太常博士……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据考证,其大历十年至建中二年左右任奉礼郎六年,建中四年至贞元四年为太常博士,先后十余年在礼官任上。陆质亦精通礼制,《旧唐书》本传记其曾作《类礼》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也著录此书。此书与《郊祀仪注》同类,可能就作与他任礼官时。贞元十九年,陆质还与柳冕以及当时的礼部侍郎权德舆以文论取士之道,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春秋》学派的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赵匡虽未担任礼官,但是其在建中二年前后所作的一系列论及选举的文章如《举选议》、《举人条例》、《选人条例》、《举选后论》,指出“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於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以致出现士林鲜体国之论、当代寡人师之学、当官少称职之吏、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等科举弊端,并提出“立身入仕,莫先於礼,尚书明王道,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等改革措施。这些建议对中唐掌贡举礼官重经义文章的科举改革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他礼官,或直接受业于《春秋》学派,或与其主要人物互为师友,多有交往。如宝应(762 年)前后,张荐、崔造等在江南与《春秋》学派的主要人物赵匡有交往。《全唐文》卷四四五张荐《答权载之书》中云:“宝应中……荐家於邗沟,耕於谢湖。每岁春艺秋获,途由漕浦……与……赵洋州、户部兄弟同客是邑,或承馀眷,留欢浃日,无旷再时者数焉。”据考证,此“赵洋州、户部兄弟”当指赵匡与其弟赵赞。张荐是张鷟之孙,“少精史传,颜真卿一见叹赏之。”权德舆为其所作的《墓志》中也称其“代名儒学,至君彰大。七岁善属诗,十岁通《太史公书》。未弱冠有声于江湖间。”后来任太常博士,参典礼仪。此外,柳冕、徐岱、张荐等人还与陆质同时为太常博士。《旧唐书·柳冕传》载:“(贞元)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柳)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并且,权德舆与陆质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权氏有诗《送陆拾遗祗召赴行在》,此处陆拾遗即指陆质。永贞曾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为《春秋》学派一重要传人。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柳宗元明确言道:“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柳宗元是受陆质影响颇深的一位代表人物,对陆质《春秋微旨》“纪侯大去其国”三例特别称赞,说:“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武、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其《非〈国语〉》一书“非左氏尤甚”,“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可视为是啖助、赵匡、陆质之后的又一继作。
因为礼官士人群与陆质、赵匡亦师亦友的频繁交往,贞元礼官接受了《春秋》学派的变通复古、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不泥于汉儒的注疏,而是直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深入到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探求本源性的价值原则,为道德伦理寻找新的形式依据,从而回归到儒家“礼”之内在根据,以“礼”之义、理、忠、信等本质来统摄一切,强调经义的道德力量。中唐礼官弘扬儒教,鼓吹圣人之道,其内涵为仁义道德,其制度为礼乐刑政,开始实践到中唐的思想文化秩序重建中。
三、礼官承继道统的努力及其对中唐文人的重要影响
贞元礼官以“礼”的本质和内在精神为价值原则,强调其作为道德准则的特有价值,着手现实思想文化秩序的改革与重建。其职事活动,彰显其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着经世致用,礼官直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接受变异的经学思想,推动儒学复兴,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新建立思想文化秩序。
依经立意是儒学的基本范式。从深层次的文化意蕴看,中唐经学的自振与新变不只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儒学精神振作的表现。中唐礼官文士立足于经文中所贯穿的圣人之志,依经议政,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相对的独立性与批判性。
权德舆在《两汉辨亡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汉之所以衰亡,不在于王莽、董卓的篡逆,而在于张禹、胡广姑息养奸所致:“向若东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庶乎无灵、献之乱。”张禹、胡广系汉代名儒重臣,权氏批评了汉儒泥于礼制而不重现实功用的倾向,认为这是释事忘义。处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代,权德舆曾身居宰辅之位,对安史之乱的起因,自然深有探求。他认为唐朝的衰乱,表面上始于安史之乱,实际上与唐玄宗时奸相当权及儒学落魄大有关系,这同两汉覆亡的原因有某些相似之处。权德舆以此文借古讽今,其立意高而“持义正大,可为小人儒下一针砭”,颇具思想性和现实意义。他认为汉儒只是将儒家经典作为一般经学史书对待,却丢弃了其最根本的政治精神,而被丢弃的政治精神才是经典的重要价值所在。正是在此意义上,葛晓音先生在《汉唐文学的嬗变》中高度评价了权德舆的地位及影响:“儒学由专习章句转为精求义理的这一变化,便是‘文以载道’说的先声,也是早期古文运动的主要背景……在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到韩愈、柳宗元之间,权氏是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韩愈重新整合了儒学文化体系,进而形成了儒家的道统理论。韩愈所著的《原道》一文对“仁”、“义”、“道”、“德”范畴的内涵作了儒家精神的限定,“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韩愈还从国家和文化的起源发展等方面论述了儒家“道”“德”的表现,力图证明儒家的“道”“德”乃是人类文化的根本原则。“仁”、“义”的根源涉及“性”的问题。他进一步发扬儒家的心性之学,希望以建设儒家化的人生哲学,在人的心性本体之中使道统学说的道德主体得到落实。他在《原性》一文中同样为“性”下了儒家意义的界说和定义:“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他还特别强调仁义之道德的“无待于外”的特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原道》)这一段话充分体现了其强调主观心性的修养、以内在的道德为本,通过将礼制经文的解读转向对道统的推崇,进而将之落实到人心人性之中的思想。
第二,注重选士活动的导向作用,增加经义内容,改革贡举考试。因为中唐礼官秉着学政合一的经学观与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所以他们的文学思想不象天宝儒士群的独孤及、李华等人一般空言明道,而是带有实践性的品格。
陆贽以文学、识见、治才见知于德宗,为翰林学士时号称内相,爱奖掖饱学儒士。贞元八年(792)知贡举,他认为士子应举应“帖经为本,本实在才,才不由经,文自谬矣。由经之才,文自见矣”。其所选拔之人,多为崇儒好学之士,这一年,欧阳詹、李观、冯宿、王涯、韩愈、李绛、崔群等二十三人登第,几乎网罗了当时天下的名士,后来多为朝中重臣。
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权德舆以礼部侍郎之职三年连掌贡举(贞元二十年诏停),他把改革科举的主张付诸实践,希望能选出“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的人才。他在《答柳福州书》中深感“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不言理道、仅以诗赋取士的考试制度的弊端,批评时下进士只会“甲赋律诗,俪偶对属”,明经只会“幸中所记者”,若令其释经通义,只会“墙面木偶”,因此,他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在试题中加重了经义的分量,所出进士、明经、崇文生等各种策问,均以通经义为主,自称“半年以来,参考对策,不访名物,不征隐奥,求通理而已,求辩惑而已”。权德舆“元和以来,贞元而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三掌贡士,号为得人”。权德舆在务实改革的经学影响不断扩大的时期,将经义引入科举考试,制策问卷中多带有学术政治化的思想倾向,明确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导向。
第三,奖掖选拔后学,培养思想文化革新的后续人才。礼官文士这批中唐最有影响力的儒士学者,他们的学术活动不仅给文化重建带来新的思想支持,促进了诗文学风的务实变革,而且他们以礼官身份下的职事活动影响并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经世致用、务实革新的士人精英,这些文人成为后来元和诗文革新思潮的中坚力量。
人才的培养,在于它所依存的文化环境。“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盛于德宗之世”。元和文坛的文学家正是在贞元礼官的奖掖提拔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对文士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主盟二十余年的权德舆。大作家中有案可稽的,刘、柳登第必有权德舆的揄扬之力。柳宗元,贞元八年应进士试,曾拜谒权德舆并行卷,几天后又向其温卷问讯,冀其援引,有《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补阙执事,……今鸳鹭充朝而独干执事者,特以顾下念旧,收接儒素,异乎他人耳。……愚不敏,以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为色取象恭,大贤所饫;朝造夕谒,大贤所倦。性颇疏野,窃又不能,是以有今兹之问,仰惟览其鄙心而去就之。”又陈故人言曰:“补阙权君,著名逾纪,行为人高,言为人信,力学掞文,朋侪称雄,子亟拜之,足以发扬。……曷不举驰声之资,挈成名之基,授之权君,然后退行守常,执中之道,斯可也。”权德舆的答复及为之通榜的具体情况现在虽已无史料可查,但柳宗元举进士权德舆予以提携则是无疑的,因为柳宗元的期冀没有落空,翌年春终于进士及第。刘禹锡,贞元十一年登制科,权德舆有《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称其自幼“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及长“居易以逊业,立诚以待问,秉是嗛悫,退然若虚”。这不用说是在为年轻的刘禹锡题拂延誉。显然,柳宗元、刘禹锡这两位中唐大家锐步登上政坛、文坛,与权德舆的援引奖掖是有很大关系的。
元、白等人的入仕同样与礼官权氏的奖掖有关。贞元十七年(801)冬,权德舆奉命以中书舍人典礼部贡举,翌年正拜礼部侍郎,接着连掌三年贡举(贞元二十年曾停贡举),共取进士七十二名。元、白俱于贞元十九年中书判拔萃科,是年知贡举即为权德舆。元稹元和十一年(816)在兴元治病,有《上兴元权尚书启》(《元稹集》外集卷二),称:“元和以来,贞元而下,阁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矣。某亦盗语言于经籍,卒未能效互乡之进,甚自羞之。”并随启封上诗五十首,文四篇。这不只是属吏对上司的恭维,更应该说是新进对先达的尊敬。权德舆等礼官这段时期奖掖提携的元、白、刘、柳这批文人,组成了元和文学革新的主力。
总之,中唐礼官的政治与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他们的人格理想设计时,常将自己放在一种动荡的社会背景中,借以规定自己的政治目标,使自我价值通过参加为国家振兴等政治活动而得以实现。这批礼官文人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他们以“辅时及物”为己任,以“力挽狂澜”相期许,而且还以倡复儒道的实践情怀、敢于直谏的淑世风范形成一代文士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思想与精神风貌影响了一批元和时期的重要作家,正是他们所培养提携的文人担当了元和时期的诗文革新,继续了他们重建文化秩序的愿望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