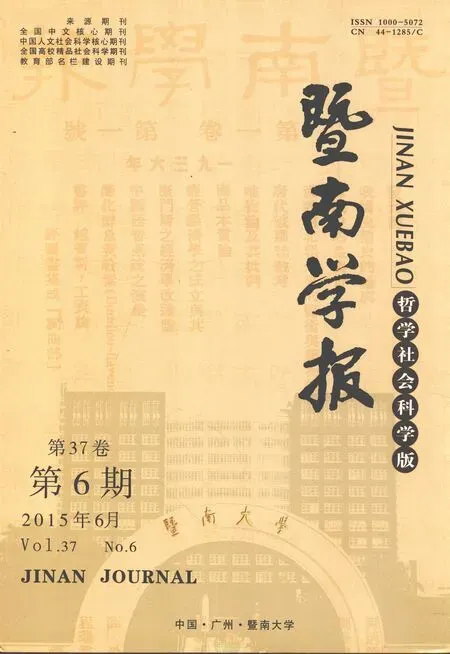预言、命运以及反抗的悖论
——《奥狄浦斯王》与“褒姒亡国”之叙事比较
陈 琛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预言、命运以及反抗的悖论——《奥狄浦斯王》与“褒姒亡国”之叙事比较
陈 琛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故事在中国与古希腊各自的文化背景中都有深远影响。后世文学史家、批评家分别对它们进行过多次的批评与阐释,但少有人从比较的角度对两个故事进行研究。客观地说,两篇故事就其叙事方法和潜含的无意识心理等方面有较强的可比性。通过探究《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叙事模式、人物设置和矛盾冲突等方面,发现两个故事具备极为近似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并基于此,探讨出东西方民族对命运及其反抗的共同心理态度和其他相通的文化信息。
叙事;预言;命运;文化
人类作为一特殊而广泛的生物种群,自诞生以来就分布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之中。不同民族由于积累了不同的原初经验和历史记忆,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形态,尽管如此,异质民族在其各自的历史进程中仍会形成一些相近、相通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内容。这种共通性往往可能就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各种文艺作品中。通过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相似结构、相似表现手法、相似叙述模式或相似审美风格的文艺作品,我们会发现作品背后隐藏着某些人类整体共通的文化信息以及文化结构,传递着人类心灵中某些共有的惊惧、疑虑、希望、期待、爱和恨等普遍性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依据这种认识,本文将出现在公元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故事——《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进行比较。
一、《奥狄浦斯王》与“褒姒亡国”故事梗概
(一)《奥狄浦斯王》内容简述
奥狄浦斯王的故事出自古希腊神话,后经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取材加工而成,《奥狄浦斯王》(以下简称《奥》剧),其被亚里士多德誉为古代悲剧的典范。
故事起因是特拜城国王拉伊奥斯年轻时诱拐了美少年克律西波斯,致使后者自杀身亡。克律西波斯的父亲佩洛普斯在天神宙斯像前诅咒拉伊奥斯将被自己的亲子所杀。王后伊奥卡斯特担心预言成真,将刚出生的儿子奥狄浦斯弃于基泰戎山中。丢弃奥狄浦斯的牧人可怜婴儿,将他送给了科任托斯的牧人,该牧人又将婴儿送给了科任托斯国王波吕博斯。
在波吕博斯的抚养下长大后的奥狄浦斯,偷听到德尔斐神殿关于他将杀父娶母的神谕,不知身世真相的奥狄浦斯为避免神谕成真离开了科任托斯。奥狄浦斯流浪至特拜城附近时,误杀了生父拉伊奥斯,随后又因答出了女妖斯芬克斯的谜题拯救了特拜城,被拥为国王,并娶了生母伊奥卡斯特。十六年后特拜城闹瘟疫,在阿波罗的神示和先知特瑞西阿斯的揭示下,奥狄浦斯知晓了真相——他最终没有逃脱杀父娶母的命运。
(二)“褒姒亡国”故事简述
关于褒姒的故事,中国古代几部文献都有所记载。最早是春秋末期的史书《国语·郑语》,其次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本文选取《史记·周本纪第四》中的记载作为考察对象。因“褒姒王国”不像《奥狄浦斯王》是独立成篇的故事文本,它是《史记·周本纪第四》中的一个小故事,因此不使用书名号。但因其故事的完整性,故不影响比较的可行性。
故事从旧时两条神龙降落在夏帝宫廷中说起。神龙自称是敌国褒国之先君,夏帝为避免灾祸,占卜得知须留下龙涎。然而,盛装龙涎的匣子在周厉王时代竟被打开。龙涎化为鼋鼍爬进周(宣)王后宫,为一个小宫女撞见。后小宫女无夫却生下一名女婴,宫女恐惧,将女婴丢弃道旁。
正当此时,民间流传一则“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童女谣传。而镐京中又有一对售卖山桑弓具(鳿弧)和箕木箭袋(箕服)夫妇,宣王害怕童谣成真,于是下令捕杀二人。夫妻俩在逃往褒国的路上,发现了宫女丢弃的女婴,心生可怜收养了她,并取名为褒姒。褒姒长大后,被褒国国君献给周王,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掉了申后和太子,改立褒姒为后,并以烽火戏诸侯的游戏来博其欢笑。后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缯国、犬戎攻打周幽王。幽王燃烽呼救,却无人再派出救兵。幽王被杀死于骊山脚下,终致西周亡——“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预言由此而得到印证。
二、两个故事的可比性分析
必须承认,两个故事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表达的主题也各有侧重,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故事差异背后叙述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相通之处。
(一)类似的故事叙述结构
就两个故事的叙述结构即情节安排而言,它们的相似处和可比性是最明显的。如果将两个故事的情节进行压缩,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遵循同一个基本叙事模式,即预言(神谕):前置预设人物的命运及终局—人物的理性反抗—人物因反抗而坠入偶然性处境—人物因偶然性处境而促成最终命运(印证预言)。考察前文简述可知,奥狄浦斯王的故事中,德尔菲的阿波罗神殿神谕作为一种强大预言是一种前提性预置,整个故事的叙述都在这个预置的前提下展开。奥狄浦斯弑父的结局早在其降生之前就已预置起来。而后无论是其父母的行动(弃子),还是奥狄浦斯本人的行为(离家出走),都可将其视为人物的一种理性反抗与主动选择。然而正是因为人物的这种理性反抗,反而坠入偶然性的命运处境(误杀生父、战胜斯芬克斯获取国王宝座、迎娶其母),由此印证了“弑父娶母”的预言。
同样,“褒姒亡国”的故事里,“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预言虽表面上指售卖“鳿弧箕服”的夫妇,实则所指为夫妇所拯救并收养的弃婴褒姒。有了这种前置性预言的流布,周宣王(幽王父)也就有了其主观的努力和理性行动欲图破除这一预言,他命令捕杀售卖“鳿弧箕服”者。而此同时后宫宫女弃下女婴(人物的理性决定)。在这“追捕—逃离”和丢弃之间,“鳿弧箕服”者宿命性地遭遇并挽救了被丢弃的女婴。女婴长大后因貌美而被褒国送给周王,又因得宠而发生废太子皇后、烽火戏诸侯等事件,终至亡国。人物的积极、理性反抗反而导致了人物落入偶然性处境,继而又因为偶然事件的合理延续而印证预言。“预言—反抗预言—坠入预言”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方式,在两个故事中共同展现出一种“正—反—合”的内在逻辑张力,人物命运由此最终完成了一种封闭式的循环,最终宣告了神启或天命不可违逆的绝对威严。
(二)类似的人物角色设定
人物是任何故事在其进展中的灵魂。人物的性格决定故事和情节推进的方向,而性格又往往取决于不同社会结构、环境中各自扮演的身份和角色。因此,叙述者为了叙述故事,就需要设定不同的人物角色,并赋予其不同的社会性格、情感色彩及其生命轨迹。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奥》剧与“褒姒”故事里,都共同存在着几类关键的人物角色。这些人物对故事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由于相互冲突而形成了故事的内在张力。这些人物包括:第一,核心主角,即命运的体现者,预言的承受者和遭际者。《奥》剧里体现为主角奥狄浦斯,“褒姒”故事里则是褒姒,他们都无疑有过一个共同的身份(弃婴)以及被人收养长大的经历;第二,命运的主动反抗者,即对预言所示必然性命运进行能动、理性反抗的角色。《奥》剧体现为奥狄浦斯的父母拉伊奥斯和伊奥卡斯特,也体现在奥狄浦斯本人身上。“褒姒”故事里则体现在周宣王及其臣下相关的人众系列;第三,主角生命的拯救者,同时也是人物命运的反转者和偶然性处境的推进者。《奥》剧为特拜城与科任托斯国的两位牧人以及科任托斯国的国王夫妇,“褒姒”故事里则为逃到褒国的售“鳿弧箕服”夫妇。这三种身份角色构成了故事构架中基本的三角关系。
除此以外,两个故事中还各自存在一个隐性但极为重要的身份角色——如同全知的上帝一样,它以一种超越的、俯视众生的高度来设计和拟构着故事的一切要素,那就是预言的制定者、主角命运的决断者。它们在故事中并没有直接现身,而是通过某种代言显现。在《奥》剧里,预言的设计者是天神宙斯,其预言的传递者和宣示者是阿波罗神和人间先知。在“褒姒亡国”的故事里,预言的制定者与国家命运的决定者则显得更加的隐秘,我们可以把它设想为某种神秘的天命,也可以把它和夏后氏时代出现在夏庭中的神龙联系起来,但不管是谁,它都被暗示为某种隐藏的神秘力量。而其代言与宣示者则是国都里闾间的女童,采用的形式则是歌谣。
(三)偶然性事件对于情节的推动以及对于人物命运的生成
福柯认为,历史是偶然性的领域,充满了冲突。从解构线性历史和历史的连续性出发,偶然性在福柯那里被理解为一种断裂,一种破碎,一种对于线性历史之必然性的突破与反叛。而文学叙述中的偶然性事件也有如此意味,它是为了打破叙述之惯常,打破命运之必然,是为了制造出人意料的冲突。“一个东西被称为偶性,(是指它)既非出于必然,也非经常发生。”(《形而上学》)“机遇或偶性是没有确定的原因的碰巧,即不确定。……偶性或机遇确在发生着和存在着,不过不是作为自身而是作为他物。”(《形而上学》)因此,偶然性事件就是,由某种不确定原因引起的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基于某种确定的因果联系,事件打破了主体命运的惯常和可预见性,将主体命运的无主体性、无常性,甚至是无皈依性的“被抛”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文学叙事永远离不开偶然性事件。在《奥》剧和“褒姒”故事里,偶然事件并不仅仅只是故事叙述中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相反它是决定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必不可少的内在成分,是故事结构中的关键环节;这种偶然性蕴含着丰富的心理文化信息,暗藏着人物最终命运的密码,它潜在指向于人物命运无可抗拒的必然结局。正是偶然事件的出现,实现了对预言的最终印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偶然性事件体现了故事叙述的某种方法性策略:偶然性事件,是“神”或者“天命”用以驱使人物角色,使其最终抵达预言结局的赶马鞭,是决定人物命运的手段和依凭,是故事得以推进的内在机枢,是叙述者对故事情节、场景的主观上的“故意为之”,即故意的安排、制作与设定。这是一种衍生性叙述行为。换言之,偶然事件并非是由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的内在必然逻辑决定的,它更多的是叙述者出于特定叙述目的所采取的某种看似具备合理性的偶然性情节设计。它作为故事的特定内容表达和结构要素对于叙述来说举足轻重,但从偶然性事件自身的内容、形式上讲,它又完全是任意的。它可以以这样一种情形出现,也可以由那样一种情形出现,一切全取决于叙述者的叙述。
那么,在这两个故事中,哪些算是偶然性事件?通过阅读文本可知,在叙述中叙述者设定了比较多的这类事件。举例言之,伊奥卡斯特出于对神谕的恐惧而抛弃儿子,这可以视为人物的必然性选择,然而牧人却偏偏把奥狄浦斯交予另一个牧人,并最终由科任托斯国王夫妇抚养,这便是偶然。长大后的奥狄浦斯出于对神谕的恐惧离开养父母也可以视为人物角色的必然选择,然而却偏偏又以流浪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出身之国而不是其他地方,恰恰正是在这时候“岔口”上的相遇和争斗等,这同样都是一种极端的偶然性事件。同样,褒姒故事中“鳿弧箕服”者的恰好出现,以及褒姒长大后的“貌美”,“不好笑”等等,也同样都是“偶然”的体现。这些偶然性事件我们其实完全可视之为叙述者的某种“故意制作”,是叙述者为了特定的叙述目的(为了让结局印证预言)而有意的安排。在特定的故事情境之下,我们可以将这些偶然性事件直接理解为“神”的“制作”,“天命”的“故意设定”。换句话说,也就是理解为叙述者所主观认为的“神意”的安排,“天命”的安排。
三、探寻故事背后的深层文化信息
(一)对命运反思的再反思
对于命运的思考,永远是人得以为人的一种根本性好奇。毫无疑问,东西方民族对命运的追问都悠远而深刻。通过考察《奥》剧和“褒姒”故事的叙述过程,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不管是中国早期还是古希腊对于人类生存的未知命运都同样包含着一种俯首的膜拜、一种恐惧的虔诚、一种神秘的敬畏。《论语·颜渊》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中的生死观体现的正是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庄子·人间世》中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考。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在《阿尔刻提斯》中也借赫拉克勒斯说出:“命运隐秘莫测,我们无法知道它怎样运行,即使凭借巧妙的技术,也捕捉不住它的踪影。”那么命运究竟是什么?从存在论者角度分析,命运可以泛指有特定时间限制的存在者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存在过程和延续轨迹。这里面包含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命”,即生命,即有特定时间限制的存在者;另一个是“运”,指时运或运势,亦即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存在过程和延续轨迹。“命”和“运”构成了命运。广义的命运可泛指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过程,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种族、民族等,只有狭义的命运概念才专指作为有独立意识与反思能力的个体特定性的生命轨迹和人生过程。
命运植根于已然和当下,同时又隐含指向尚未发生的将然,即潜在指向于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不确定性趋向和结局。任何存在者,小到个人、家庭,大到一个社会、国家、民族、种族的存在与发展,总是处在不同的关系,以及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而在这不断地运动与变化中,偶然与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遭际。这是人们难以预料和把握的,是人的主观努力以及任何理性力量都很难有效决定和掌控的(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人尚不能很好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霍尔巴赫说的:“人类的命运和每个人的命运,任何时刻都依赖于那些感觉不到的直至它们的活动自行表现出来时一直隐藏在自然之内的种种原因。”“一个最有德行的人,由于种种意外环境之奇怪的巧合,顷刻之间能变为极大的罪人。”在霍尔巴赫看来,周围环境的原因系列——种种原因之结合的系列、意外环境之奇怪的巧合,即偶然性,造成了各种命运。这些种种原因中,必然性可以预见;因为可预见与可把握,人类对必然性充满信心。偶然性却因其变数和不确定性而使人坠入于一种生存的恐慌与不安之中。
人因为对自身安全感的缺失而失去了对当下和未来的信心,人沦入悲观绝望、荒诞无助的境地。由此人进一步对生命不可预料之偶然性充满恐惧与敬畏、惶惑与忧疑,人于是最终将自身命运交付给神秘的上天或神谕。它不得不让人相信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外在力量,仿佛一切都是早已前定的,一切都必将这样发生。正是这样一种心理认知观念的前在预设,才真正构成了《奥狄浦斯王》以及“褒姒”故事中极具神秘色彩和悲观主义特质的宿命论心理基础与逻辑机理。是命运,前定的命运、上天或神注定的命运,决定了奥狄浦斯王和褒姒故事中人物的最终结局,决定了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最终遭际。命运不是掌握在主体自我的自由意志中,而是决定于某种外在的、偶然的、他性的神秘力量手中。人的自我理性和主观努力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听由摆布、随命所化,个体的人与整个王朝都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处境中走向预言所设定的最终之结局。
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不论是奥狄浦斯王,抑或褒姒、西周王朝,真正决定其终极命运的,仅仅是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这些偶然性事件折射出了生命处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无能为力感。正是这种存在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对命运的无能为力,才使得故事创造者和叙述人不得不采取“如此”的安排,不得不让人物的命运以“必然如此”的方式向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事”场域中的任一个人,创作者、叙述者、表演者、观众,每一个人都是预言的真正制定者、宣示者,他们才最终诠释了故事中的人物以及故事中的王朝最终的必然命运。
(二)对抗命运的悖论:理性还是非理性?
一直以来,理性自觉或觉醒都是被当作古希腊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高扬人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一直是古希腊哲学、艺术所追求的崇高价值。到近代,理性主义更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一种主要形态。在中国,以儒家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为主导的社会思想也一直占据着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如果用最简略的一句话来描述理性其本质的话,那就是自主性——人依据规律进行自由自主的决断,并且完全独立地承受这种决断。这种决断建基于康德理性批判意义上的认识能力:“我们可以把出自先天原则(Prinzipien)的认识能力称之为纯粹理性”,同时,也强调人对于这种认识、决断及其结果的坚决承受。与此对应,当人不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进行自主决断并独立承受时,我们就可以说,人的命运便陷入非理性的荒谬之途。在《奥》剧与“褒姒”故事之中,相关人物对于预言所宣示的命运都有主动甚至极端的反抗,例如拉伊奥斯夫妇将新生婴儿丢弃山野,周宣王下令捕杀售卖“鳿弧萁服”的人。可以说,这种反抗体现的确实是人的理性抉择,它直接对抗的就是那神秘的神谕,它所表明的也确实是人的自主感以及对天命、神明的怀疑与抗拒。正是如此,在中西方各自文化背景下,人们两个故事所体现的人的理性反抗精神都被赋予了正面积极的评价。黑格尔就曾经把《俄狄浦斯王》理解成人的自觉、清醒的意志与神意的决定之间的冲突。同样,周宣王在历史上也被认作了中兴之主,“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第四》)从司马迁的评价里,也显然包含着对周宣王在对待“鳿弧萁服”者行为做法上较多的理性肯定。
然而,确也正是故事中相关人物的主动、积极、理性反抗,导致了事件终局走向了初始预言所宣示的结果。在故事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反抗者之所以展开其“理性”反抗,是基于各自心中的某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寓言之可敬畏——预言乃是神定,是上天安排好的,所以必须慎重对待,必须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寓言的成真。这种心理机制和思维逻辑首先是建立在对天命、神谕的绝对信任与虔诚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知,人物对命运的理性反抗实际包含了一种前提上的极大被动,包含了人的主体意志的断然缺位,和对自我信心和理智判断、自我独立性与个体自由的显在犹疑。总之,在这一系列看似决然的理性行为中,无可置疑地蕴藏着某种非理性的惶惑:人首先是被处处笼罩在神谕之阴影下,人始终匍匐在外力掌控之下。人为神与天命所预设,人最终由非我的外力所“设定”和“处决”,因此人无法真正做到认清自我,了解自我,决定自我;人无法与神相对抗,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人的理性精神与理性力量在“神”面前不堪一击,人似乎只能放弃自己的理性,臣服于理性认知世界之外的神性力量的处置,安然于性命,沉沦于现实。这是一个明显的理性悖论。我们在两个故事里,看到了人物命运共同陷入了黑格尔的“理性机巧”意义上的尴尬境地。我们对所谓的理性,以及与之对立的非理性本身不得不产生进一步的怀疑:对于“神谕”、“预言”的“理性”反抗本身,是否真正具备启蒙主义的理性意义?它自身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反理性的?
(三)预言与语言:对故事所涉预言的语言分析
预言由语言构成,预言通过语言得以表达和传递,这一简单事实暗示出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神奇力量。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着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对于人类精神领域所具有的奠基性意义亦成为20世纪后哲学与人文学科思考的重点。“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语言之本质就在道说之中,道说就是显示:既澄明着又遮蔽着之际开放亦即端呈出我们所谓的世界。”(《语言的本质》)这些独特论断成为当代存在论语言哲学的标志性话语,它道说出的是语言与存在的本质性关联:语言即是存在,语言乃存在的显现与本源。语言不仅开启了存在之过去,这种过去乃是世界历史之铺展也不仅仅只是揭示出存在之当下,这种当下乃是作为人的此在自由绽开之处所,语言之于存在的根本性力量在于:语言能召唤世界之未来。语言将未知世界之命运带到当下,置放于凝视者的眼前。就这一点而言,语言成为了世界神秘本质的寄寓之所,语言具备了超越时间、空间,具备了显现世界之神秘本质的神性力量。我们可从人类历史中普遍出现的宗教与神话中关于神谕、寓言、谶语以及巫术语言的道说中获得确切的证明。《圣经·旧约·创世纪》开篇即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黑格尔谈到,在这里,上帝创造世界的方式是凭借言词(语言),语言成为世界之源。同样,在中西方的文化起源阶段,为了展现神秘世界的神秘力量,所有的图腾崇拜、习俗禁忌、原始巫术等,都无不与语言发生隐秘的关联。巫师在扮演着通灵角色时,必须借助于“咒语”的神力;祭司在祭天祭神时,必须要借助于语言的呼求与祷告;在中国哲学思想源头之一的《周易》那里,卦辞、爻辞的语言性本质同样展示出了语言对未知世界的召唤与预测的巨大功能。在这样一些早期人类半宗教半巫术性质的神秘活动中,语言本身无不具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借助于语言,彼岸世界、神话世界才得以建构起来,禁忌、灾变、报应、显灵、命运、救赎等这一切的心理观念和心理内容才得以呈现。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看到,《奥》剧里阿波罗神殿的预言正是以语言的形式宣示出来;“褒姒”故事中,“鳿弧萁服,实亡周国”的神谕也是通过语言(童女谣)的形式传递出来。语言不仅传递着预言的暗示信息,甚至还成为了设定故事人物命运的绝对手段和唯一工具;语言不仅被用于言述,而且被赋予一种权威地位和本体功能,被赋予了决定性的强力。从这种程度上讲,“弑父娶母”以及“鳿弧萁服,实亡周国”的预言,借助于神秘的言说,以寥寥数词的语言形式,带给读者的震慑几乎远远超出了奥狄浦斯弑父娶母的行为本身,也超出了“烽火戏诸侯”,“犬戎攻镐京”等历史事件带给读者的内心冲击。在这里,预言—预言的发布者、预言的毁灭性内容指向、预言的符号性能指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关联在一起,共同演绎了故事的内容,并造就了人物的最终命运。
(四)预言与权力表达:对预言的信息学考察
最后,对两个故事中所涉及的预言分析我们还可以作信息传播学上的考察。故事中,预言的传播更倾向于单向传播模式,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即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表达了这样一种传播过程:信源(信息发出者)—媒介或信道(信息传递材质)—信宿(信息接收者)。它首先确立了信息发布者的独断地位。这种信息传递结构潜在暗示着某种专制的权力模式以及意识形态观念。无论是《奥》剧里阿波罗神殿的神谕,还是里闾坊间盛传的童谣,我们都看到预言作为信息,从某个隐秘而权威的信源处发出。阿波罗神殿因其代神宣言,神在古希腊人的生命中本就具备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由他所发出的信息自然也就成为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这种信息源于神,它自上而下,凡人庸众作为信宿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容许任何怀疑与反抗(即使反抗都是徒劳),人不得不屈从于该权力形态的束缚、统治之下。而童谣的信息传播则体现出另一种不同的文化信息:童谣流传于民间,虽不具有阿波罗神那般的权威性和绝对性,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童谣并不是预言信息的最初发出者,它只是传递信息预言的一个信道、一种媒介途径,在这里真正的信息源、真正的预言制定者,在童谣传唱之中渐渐消隐不见。看不见且不可捉摸的东西才是最恐怖神秘的,我们只能推测它隐隐指向于背后的某种神秘所在(天命、神权)。天命不可违,因为天命不可见,而天命又通过一种神秘的信息渠道进一步加深其神秘与恐怖,最终预言、天命、神权在这一信息学的操作、流转过程中最终获得足够的统治力量。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传播的“塑造社会的力量。”
总之,在这两个故事里,关于情节结构的设置、关于人物命运的安排,叙述者无不体现出一种神秘主义的思维观照。预言、天命作为一种权力信息,借助于语言的外壳,凭借一种自上而下的威权化传播渠道,最终作用于人物的意识形态,并且以人物的自觉但却又无效的反抗形式,使得天命、神权的强大意志性力量得以巩固。语言、预言、权力信息,作为人物命运的本质性隐喻,作为君—臣、帝王—百姓、神权—民众的统治关系的曲折表达,最终在故事的叙述以及叙述者的意识形态里逐一显露出来。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106
A
1000-5072(2015)06-0149-07
2015-01-30
陈 琛(1985—),女,湖北荆门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诗学、文艺与传媒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