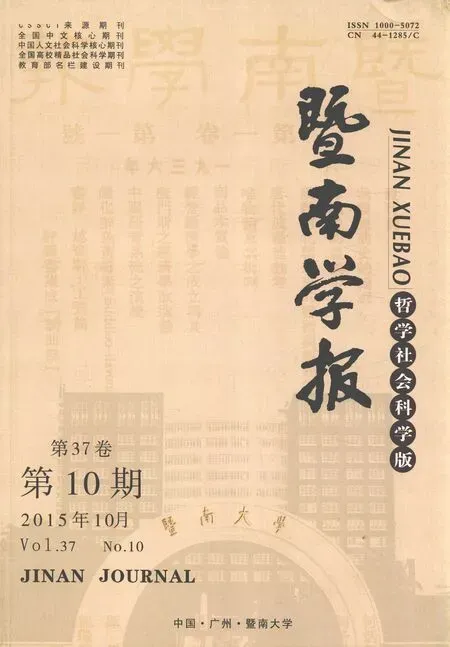灵魂之根的追寻与隐喻——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綦 珊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陆犯焉识》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在反思一段极左的历史,展示个人遭受历史意志强行挤压之后的无奈和悲凉。但是,渗透在故事深处的,却并非仅仅是历史的强权意志对个体命运的伤害,还有创作主体对生命之根的执着追寻。因为主人公陆焉识的命运之所以频频出现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对人生的理解和选择,也就是说,陆焉识并没有丧失主体意识,并非随波逐流,而是在面对残酷的历史挤压时,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生存环境时,他仍然在追寻自己的信仰,只不过,他的信仰出现了错位。
在《陆犯焉识》中,陆焉识一直在和时间赛跑,试图执着地追赶自己的人生,去实现他那总是显得有些滞后的理想——他年轻时所极力逃避的家庭生活,却成为他晚年的终极梦想。从挣脱家庭的束缚,逃离婚姻的安排,抛开恩娘与妻子之间的挤压,到寻求各种浪漫却不踏实、昙花一现的婚外情,再到不合时宜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追求公正,最后以越狱的极端方式,想回到妻子面前表白并忏悔、苟延生存……这些情节所勾勒出来的陆焉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才情四溢却找不到“用场”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陷入世俗生活之中后知后觉的可怜人形象。他总是膺服于自己的内心愿意,从来不关注个体的存在与社会、家庭之间的群体关系,而等到他明白了这一切,岁月又不再给他更多的机会。
对一个想要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陆焉识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灵魂的解脱,追求所谓的浪漫和理想,这一追求正是他逐渐内化而成的生存信仰。这个信仰让他积极地适应自己无法抗拒的生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无论人生经历怎样的苦难或得意,甚至政治与人生碰撞出残酷和荒谬,都未曾动摇。因此,这个信仰虽错位却坚定不移,更因命运坎坷形成他心中不停的追问:“何处是家”“如何存在”;这种探索与追询流露出对释放内心、获得自由的渴望,这便是作家精心铺设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底布”上“最讲究的艺术性”:深刻地展现出也存在于作家心中对于实现写作自由、追梦和探寻人生的创作意图。
一
在《陆犯焉识》中,到处晃动着“出走”的光芒和“回归”的背影。“出走”和“回归”,常常以二元对立的形式,构成了严歌苓很多小说中内在的张力密码,成为解读其作品的重要意象。作家非常擅长设置这对内蕴丰富的意象,并以此展示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情思或意念。通过这种隐秘的叙事策略,严歌苓总是顺利而又巧妙地建构起一个个关于“家”与“爱”的寓言,并使之成为严歌苓小说中非常突出的主题。事实上,在她的很多小说中,这一主题都会以人物各自的个性气质和人生际遇表现出来。比如《寄居者》中女主人公任性的爱情,《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愚钝的孝义,《扶桑》中扶桑那蒙昧的母性等等,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最终叩问了“爱”与“家”对于生命的意义。《陆犯焉识》也不例外。无论是“出走”还是“回归”,陆焉识以其奔波的一生,折射了其人生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追爱”和“寻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因命运的错位而造成的永劫不复的遗憾,既有历史的内在规约,也有陆焉识自身的性格因素。它所产生的内在张力,直接指向人性中“叛逆”与“依恋”这两种情结。
这些是通过陆焉识三次出走、三次回归表现的,这三次出走与回归相辅相成,划定了他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出走,是因为“那个跟冯婉喻结婚的是另一个陆焉识,没有自由,不配享受恋爱”,陆焉识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彻底逃离”去美国,他针对的就是那个“帮着长辈一块来断你一生唯一的择偶机会,灭掉你无数的相爱可能”的妻子和家庭。此时,关于爱情的自由选择与掌控让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归——自我的回归。这一次回归遂其本心意愿,表面上让他尝到自主选择的甜头,实际上却误导他忽视了自己逃避生活的本质,这使他盲目自信而不审时度势,继而出现了连锁错位。当他结束与旺达的荒唐的自由恋爱,完成学业回到上海,就不得不回到他那“想叛逃的家室和中国大部分男人的生活格局”。回国后的生活,大学、图书馆、咖啡厅等可以代替家而存在,这是第二次出走:他在另外一条平行空间里生存,那便是科研与写作。他在那里肆意发挥着个性与不羁,即便存在与社会的摩擦,甚至出现陷阱,他于其中也是乐此不疲,不管这过程多么漂泊、孤独、无助、虚幻,都因为能够和他不喜欢的家庭隔离而充满吸引力。此时,他虽然在家,但实际上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实质接触,直到“身不由己。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陆焉识坠入被动的论战中,他无处可逃的时候木然地回到家,才有了与妻子和家庭的真正接触。这是他的第二次回归。这一次是被动的,这一段生活让他无意间对妻子注意起来,并由此生出了对妻子的怜爱,虽然这一切都还是模糊的,但点滴积累起来,促使陆焉识后来悟出自己对这个家和妻子的爱。
这种爱爆发的时候就是在陆焉识彻底失去自由的时候。顶着政治犯的帽子身陷囹圄,他所有的追求成为一场闹剧,在他根本不想收场的时候并不美好地收场。在死亡边缘的几番打转,让已经变成老几的陆焉识越发沉浸在对妻子的爱与对家的眷恋中,此时发生了第三次出走与回归,并一直延续到结尾。这一次,“出走”与“回归”紧扣在一起:逃是为了回来,挣脱是为了顾念,回归是彻底推翻自我的出走。这个时期的陆焉识仍然执着,只是这份执着曾经是为了寻求爱而离家,现在却彻底灌注在他想要回家的愿望中,他要保全妻子和家,要站在婉喻面前忏悔、补偿、相爱。他的人生追寻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此时的“家”与“爱”终于同步,却与命运错位。
故事呈现出“家”与“爱”的合一以及错失的遗憾,却并未结束,而是将这个对比更鲜明地表现出来,尽致地展现出主人公如何面对这种错位。在陆焉识将生死完全交由命运安排的时候,却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回家通行证。他的释放并不是妻子走动人情的结果,儿女也并不期待他的归来,原本以为可以回家与妻儿团聚,尽享天伦,却面对着抱怨、鄙夷、猜忌,尤其是妻子的失忆让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结局充满了戏剧性,家不成为家,爱也不成为爱,失形失意的生活、生命主题,让人无所适从。然而,正是这样非常态的结局为人物开辟出一个空间,陆焉识表面上放弃了自我,选择了一个迎合生存而停止追求的方式,实际上他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主体意识,他并未在这种遗憾或错位中沉沦,反而对此忽略不计,心无旁骛地为这个家付出,他的改变与适应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成为老佣,随和,却也时不时地发表意见,表达对现世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陆焉识,却又是一个从未改变的陆焉识,或者说改变他的貌似是命运,实际上是他认清了自己真正渴求和希望的,这就是他此时真正的生活目标——家与爱,是为了它们陆焉识才选择了“新”的生存方式。最后,陆焉识带着婉喻的骨灰回到大草漠,像一个浪子享受随处可见的自由,不可思议又不出所料。它将“家”与“爱”变成一个理想模子,打破了凡尘意义和个人局限,化成一种力量支撑起一个人的生命。这种以流浪作为外在形式的生存选择是放逐还是皈依天然,是享受还是赎罪,是无奈还是释然,这种力量是负担还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是命运的烙印还是自我套牢的枷锁……这些问题都是小说叙事的留白,引人深思,关于这点,在作家对末章题目从《浪子》改为《无期》,再改回《浪子》的雕琢中可见一斑。
三次“出走”“回归”勾描了小说的整体轮廓,将“家”与“爱”牢牢地镶嵌在人物理想与追寻的血肉之中。而这些理想不仅仅是陆焉识一个人的向往,他的妻子、儿女无一不对之充满期待、始终追寻,只是因他个人选择而造成的错位辐射了他人的人生,由此产生的非常情况磨损了原本该有的正常。因此,“家”与“爱”作为有着特定含义的实体,不是作家笔下的人性表达,而是人性使然的原因,不是明示而是隐喻,不是表现人性的系列动作,而是人性构成的要素。它们接近并塑造了小说和人物的共同灵魂,是引人追寻的原因,更成为人活下去的意志。
二
在展示“家”与“爱”的计划中,严歌苓找到了自由这个重要的意象作为承上启下的设计,同时,这也使得小说拥有了张力。自由不仅连接了主人公陆焉识前半生的出走与后半生的回家,也是许多事情如此发展的一个原因,是主人公特有的、执着的,甚至迷恋至深的追求,却在追寻中失却了。通过对自由的追寻,他领悟到“家”“爱”对他的重要性,待到他明确了自己对“家”“爱”的追寻,便抵达到真正的内心自由。
“自由”形成了叙事框架的基础。这不仅仅在于整个故事就是围绕追寻自由展开的,还有一层意思即适合人终极愿望的是获得自由的家、自由的爱与自由的生活,而不是由体制或者权力安排的,也不是依照社会或者家长的意愿扮演的。“自由”的这份灵魂特性,是通过非常规的叙事方式揭露出来的。从开篇动物与生俱来的千古自由到篇末主人公终于体悟到草地上将会有无限自由,小说中出现“自由”63处,分别代表了人和物于自然中对“自由”与“生命”的体验。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事物、自然更迭或人畜相争等多元对比,其实是作家设置的一种多元对比,也是对人类情感自困的隐喻。
小说的第一句就提到“自由”,接下来是人与畜的对比。《引子》提到自然中原本天然划分的强弱群体因为生存而出现了反逆的现象,动物的自由自在因为人群的到来而被打破,甚至被迫迁移,人充当了严肃并凶猛的角色以致“谈人色变”;在《场部》中又出现了“严寒和缺氧的大荒草漠,自由和不自由都一样”。这个叙述通过“逆转”现象,和人类脱离了社会属性回归自然界的物种平等,获得一个信息:什么都有可能逆转,而逆转的可能是源于不同种群在自然、生命面前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一切预示着即将出现的是一个非常环境。故事将在这个非常环境中发生、发展、结局,它要的也正是这种“非常”性,因为这是一种全面、整体的喻示——这部小说的颠覆性,不仅是人物命运的颠覆,更是写作目的的颠覆——深触人性已经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提醒书内外的人去询问人性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和人性深处渴望和寻找的目的,小说对于这个目的的阐释就是围绕“家”与“爱”展开的。所以,陆焉识为“爱”要自由、要出走,又为“家”要自由、要回来,而最终获得了真正的“爱”,“家”与“自由”又合而为一,甚至再与“爱”达成了三位一体,出走即是回归。
当“自由”介入到“家—爱”的框架后,便打破了原本应有的稳定,因为这个“自由”是陆焉识个人理解中的自由,有着非常主观的想象和解读,虽然他也追求跟深具传统观念的家庭明确成为对立,对社会产生非常态的依赖,但这既不是深刻的革命,也并不与追求真理相连,在陆焉识的身上,自由只是不受牵绊或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被牵绊,没有反抗,没有痛斥,成为简单无意义的“出走”行为。所以,本该更加丰富而稳定的框架摇摆不定,因失去方向而尖锐、敏感,刺伤了人生。
这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陆焉识与冯婉喻之间的爱,从不知不觉到后知后觉,随着陆焉识追获自由和丧失自由,发生了反差极大的变化。是自由的存在影响了他们的相处,也正是自由反射出他信仰的盲目与人生中不断的错位。“自由”第一次进入他和妻子的共同视野,源于他和妻子谈起失去自由的恐惧,对于他的这个恐惧,冯婉喻的眼神刺穿了这个伪命题“你不自由吗?!你还不自由吗?”这让他恍然明白“他到底有过自由”,而按照他的标准,面前的妻子是从来不曾拥有过这种奢望的。这是第一次一个“自由”却自认“无自由”的人和“无自由”却“内心无比自由”的人的初次碰撞,并引起了他的思考,引领他进入到两个人的空间里去看待问题。这让陆焉识萌生了带给妻子自由的想法,似乎也是在满足自己潜在的欲望,几乎是在抗争中,妻子获得了与他同去赴会的机会。“婉喻那两天的自由是他硬给她的,那风景恬淡、有山有水的自由”,然而却成了“没有比这间旅店的卧房更能剥夺婉喻自由的地方”。反而确定了马上回上海的归期,一切都自然畅快起来,这便有了两个人第二次因“自由”而“自由”的碰撞。从第一次到第二次,是谈话到自由、从自由到爱的深层剥离。“自由”从谈话的主题中剥离出来,成为思考的中心,从“谈自由”到拷问“你自由或不自由”,隐喻着人内心的某种欲望和生活内心的真实:一个给一个扔,一个让一个逃,其实他们之间没有合力,却产生了合力的背离效果。第二次,由第一次引发的“自由”实践,暴露了潜在的“爱”,两个人都在“爱”中,只是陆焉识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妻子的爱,冯婉喻也不知道丈夫的真实内心而依旧活在一厢情愿的情态里。二者均迷惑在自己表达爱的方式当中,却没有交集,换来了各自收获的假象。
这个假象是错位的隐喻,贯穿在陆焉识矛盾的一生中;也正是这个假象披露了“家”与“爱”就是陆焉识的生命之本,所以他可以大胆、不遗余力地追求自由,它解释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肆意流浪,是因为有一个能等他回得去的、叫家的地方;“回归”则是彻底将爱还原给人性本初,变成能够应对沧桑变幻的强大内心,此时的自由是外在追求的人生理想,更是属于内心的自由。如果说“家—爱”是全文及人物的灵魂,那么以一种自由的姿态对这两者不尽追寻,并将这份期许与渴望深藏在内心深处,时时襄助命运破除万难,就是支撑这灵魂的根源。也许,这正是作家的创作理想。
三
从“家—自由—爱”这条线索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在这部小说中“新颖中的熟识”,因为作家始终努力地进行专属自我的叙事建构,力求在人们业已成熟的既定观念之外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作家特有的叙写方式和审美意味。其实在“家—自由—爱”这个架构中,作家将自由置入打破了原有的完美模式,除了达到丰富叙事的效果,还让阅读的过程出现了一种转折,让接受也具有了一股张力。这个目标的实现,源于一种新架构的形成,由于“自由”的介入,作家便将“家—爱”转向“家—自由”的模式上,在新的模式里,人们自然地忽略了对“家—爱”的仰慕与感叹,转向对“家—自由”的担忧与制衡。因为“家”与“自由”正是一对矛盾体,追寻家的安稳与释放内心的自由,都是人的欲求,成为力的两极,将人放置在了撕扯与争夺的强力之间,人于其中必定要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所以,在这两极中挣扎的人通过“爱”找到两极间的平衡点,获得了人生与内心的稳妥与安宁。
这种通过一个途径获得缓解矛盾的可能,并达到平衡的状况,也是严歌苓等新移民女作家自身的一种写照,身在多重文化之间,既受到中国母根文化的牵扯,又受到西方新质文化的冲击,她们在这种惊涛骇浪中体尝着被颠覆、被重塑,也具有了挥之不去的流散性与混杂性,这种流散的意味流溢在她们的文字当中,体现了她们身为新移民作家无论如何也抛不开的思想与情感根源,和她们无时无刻不向往新生与新变的渴望,这就是她们精神欲求中实实在在的两极,需要通过一种方式、一个点为这两极寻得平衡。因此,她们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体系,去置放和支持灵魂,这是她们需要的新的“根”,在原来的“母根”之上嫁接而成的新的“灵魂之根”。
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歌苓的创作总是希望并努力地进行自己的叙事建构,超越已有的意识形态或既定的因果,书写自己的看法与理解,正是因为她要通过写不同的人生和人,揭示类似的人性,从而表达其忠于自我和亟须的强大内心,即灵魂之根。这种内心关乎作家追求的写作自由,也就是心之所向,一种自然生发的生存情态;这也源于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要澄清、证明、捋顺或辨认的东西:在离散的状态下,始终怀有一种“寻根”的情怀。对于新移民作家来说,“‘离’是一种主动的‘离’,是一种距离的放弃;‘散’则是一种甘居在‘边缘化’的超然心态。”离散这种状态涵盖了作家笔下流露出的写作理想,它不是被书写的目的,而是写作性格。“寻根”也不仅仅是对文化之根或民族文化心理的追寻、挖掘,而是作家追寻灵魂之根与文化依赖的尝试。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用眺望的方式去梳理这样的特点,不是写现在的生存环境里的人,也不是身边移民世界中触手可及的事件,而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人物,遥远又贴近的出现,是作家用一个符合生命规律、历史规则和人物命运的想象提出的一种可能。这也是近些年来,海外华文女性作家创作的一个精神特征,即如陈瑞琳所言:“勇于在远隔本土文化的‘离心’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并能够在自觉的双重‘突围’中重新辨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寻找自己新的创作理想。”
所以,这种寻根情怀实际上显露着该作家群体一直具有的独特心理情结:对故土的期待与深沉而强烈的家园意识。“黄万华教授曾经指出:北美崛起的海外新移民作家,他们有意识保持了‘边缘’与‘中心’的心理距离,从而构成了一个极有张力的空间。他们迅即消解着‘原乡’的概念,以一种文化自信的实力企图寻找自己新的精神依托。”但这种家园意识却又非完全的故土情结,而是超越局限的个体情感,寻求集体的精神皈依,这体现在创作中就是追求自由与梦想。
正是这样,严歌苓在《陆犯焉识》的创作中,所关注的不再是缓解焦虑的身份书写,也不是生存策略的简单呈现,她所望见的是更深度的矛盾,那是一种在身份转换后,越过眼前的安宁平淡,而依旧排除不了的惶惑或孤独,这种“孤独已从相对外在的怀乡,发展成为对生命的一种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内视”,“孤独不再是对往昔的牵挂,喧喧大千,孤独是对世界既排拒又渗入的一种认知和态度。”“孤独”就是陆焉识,由于他的错位、误解和种种不合时宜造成了他的孤独,并内化成他内心的孤独,从而造成了无奈与悲凉,而驱散孤独的尝试就是重建正确的信仰。这个信仰在《陆犯焉识》中,以“家—爱”的形象被建构,回答着作家通过人物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我”存在的意义与方式?这也正是新移民作家群体逐渐转变的思路,超越了对政治权力和知识话语权力的争取和向往,转向对生存的关注,开始思考华人移民群体充满存在主义浓重意味的生存哲学。
在《陆犯焉识》中,“家”“爱”与“自由”是全文的核心关键词,也是作家重点推崇的价值观念,不管人生境遇怎样悲惨,这样的追求目标是引人入胜的,是值得人们为之付出的,所以,从目标出发进而回溯,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作家由此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和评判历史的方式,就像陆焉识最终选择的那样,以“救赎”宽待“历史”,因为这一切并未改变人心,反而擦拭了真正的赤子之心,激活了那份曾经蒙昧的情感。这远比控诉或憎恨更有价值和意义。因此说,这部小说是作家在经历了丰富的人生并积累了深厚的创作经验后,以一个“合适”的身份叙写这样一个新鲜奇异的故事,表达一种敏感执着的情感。而这个合适的身份不仅指作家具有双重性的移民身份,也指她作为一个建立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之个体,在这个精神家园里,陆焉识追寻的就是作家期盼的,陆焉识失却的正是作家想找回和守护的。这是作家通过文学获得的灵魂依托,它依赖着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家与爱,去实现个体生命的继续和孜孜以求的精神追寻。这才能更好地诠释、烘托出作家潜在的表现意图:关于“家”与“爱”的潜在依赖与终极追求的巨大隐喻,而这正是生命与心灵获取的最大的“自由”。
总而言之,《陆犯焉识》通过展示一种个体性的“自由”,重塑了作家一直以来坚持书写的人性,为的便是直接探讨心灵深处的隐喻家园,这便回答了“作家创作究竟为何”的问题,也指引了我们去理解创新与这一创作群体继续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