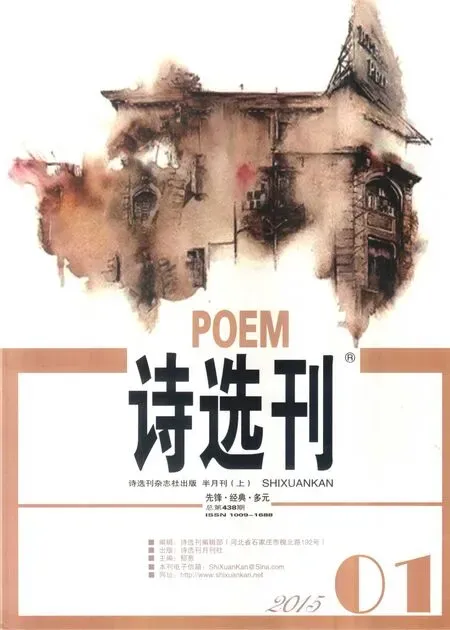李琦诗歌的抒情方式
罗振亚
本栏主持人:李洁夫
进入20 世纪的大门之后,黑格尔那句老话“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愈发被时间证实为真理性存在。 虽然它未得到所有文学家的一致认可与赞同,但感性显现却的的确确成了艺术的精髓特征,反对情感滥用的物化追求成了诗歌不可遏止的艺术趋势。
在这方面,李琦不像许多诗人那样有洋洋洒洒的创作谈作佐证,而是以大量不事张扬的文本说明她是以感性暗合世界艺术潮流脉动,走向胜利的。 作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抒情诗人,她的诗总是向读者敞开心扉,真诚坦率地流泻细微的灵魂隐秘,表现出一种挚朴深切、丰富动人的情思;只是她深知裸露的情思如同裸露的人一样苍白无力,情思的躯体只有穿上质感的衣裳才能直立,所以从不喜欢在逻辑思考与推演中品味人生,而是以恰适隐显的抒情度的寻找,控制调节情思运行,从而呈现出一派迷人的具象化抒情景观。
思想知觉化
许多人错误地主张,浪漫主义诗歌要直抒胸臆,以明朗为佳。 其实任何诗歌都不该沦为情感或意志的传声筒。 尤其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日趋繁杂的内心世界,一览无余的情绪喷射显然已显出肤浅,仅求诸稀疏形象也难再完美地表现具体的感觉;所以铸造心灵与外物契合的意象,并以之作为感觉思考的直接运行方式,愈来愈成为世界化艺术趋势,其结果是在直抒的浪漫主义那里只居于附属装饰地位的意象,开始大量密集地涌现于现代诗中。
李琦是本土化特征显在的浪漫歌者,但开放的艺术观使她认识到“许多优秀的外域诗歌让我们懂得了,如果想飞翔,什么才是羽毛”,①从不拒绝阿赫玛妥娃、里尔克、狄金森等现代或浪漫诗人艺术技巧层面的援助。 同时流动于她诗歌空间的朦胧美妙的纯个人化视境,也呼唤着一种间接曲折的形式寄托。 于是渴望在追求新的表现手法和捕捉意象的过程中,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艺术)小路的她,把诗歌魅力来源之一的充满感情色彩与理性光辉的意象凝定、抒放心灵,纳为方向性追求,建立起一种索物以托情的内聚性言说方式。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李琦的诗歌基本上避开了大喊大叫、低语倾诉的直抒窠臼,它常携着灵动的爱心与直觉式的诗感经验,来往穿梭于心灵与世界之间,寻找自然万物的灵性与人类精神物质对应的相通点,采用“思想知觉化”方式进行抒情,即把思想还原为知觉,像感知玫瑰花的香味一样去感知思想,通过意象这一情思的客观对应物加以暗示,实现心灵与外物的全息共振。如“吻着你美丽洁净的小小脚趾/想着它就要去踩的那条长路/孩子,我多么心疼/那条路上如果有树/每一片叶子/都是妈妈闭不上的眼睛”(“女儿你睡着了”), 母亲对即将步入坎坷漫长人生之路的女儿那份忧虑不安的抽象情思, 借助脚趾、长路、路上的树、树上的叶子、眼睛等实有或虚拟酌对应物表现,获得了具体的实物化依托。 再如“郊外有风/吹我裙裾轻飘/想忽然遇见李白/院子里却只有/傻头傻脑的假山”,“月也没家/风也没家/今夜,我也没有家”(“成都第一夜”),它明明在写一种情绪,但它不直接抒发,而是转向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从中融入心灵的隐秘;所以由寥寥蛙声、风、假山向慵慵的月、点点滴滴的夜露、家的弹跳转换,即可视为诗人由渴望到念远惆怅情续的流动,不同的物象因子在诗人心灵的地平线上,无不昭示着内在的情思。“两片叶子”也许尤为典型:
两片叶子
自我的身上悠然飘落
那是一个动人的名词
青春
青春是一个果断的手垫
对于女人,
她更像
一粒抛向湖面的石子
刚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就再无踪影
从祖母少女时的笑声
到我女儿的笑声
从母亲从前的红晕
(注:①李琦:“21 世纪诗人纵横谈”,载《诗林》,2000 年第1 期。 )
到我眼角的第一道细纹
一个漂亮的女人端坐在黄昏
她的身后
正次第亮起夜晚的灯
走过摇篮
走过曾经妩媚的草地
女人在做女人的过程中
懂得了女人……
这首纯粹的意象诗,以青春、果断的手势、石子、红晕、细纹、黄昏、夜晚的灯等意象的顺接跳跃与交互撞击,展现了女人青春流逝的感伤、走向成熟的满足、温柔力量唤起的价值实现感复合的心理状态,但这复合的心理意绪再不是清晰语义导致的结果, 而完全是靠意象的生成与转化构成。 李琦的诗歌这种“思想知觉化”方式,不仅具备化抽象为具象、化虚为实的神奇功力,避免了浅薄空洞的失控状态,同时意象的直接呈现,也节制了抒情成分,以不说出来的方式达到了说不出来的飘逸朦胧的效应,而物象成了心象外化的“人化的自然”,无形中增加了镜花水月之美。
如果李琦的意象艺术仅仅停浮于此,便显得一般化。因为它在新诗历史上众多诗人那里都有似曾相识之感, 更不用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 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提出的诗歌应为意象组合的情绪方程式理论了。 李琦诗歌意象艺术的独特是在对现代诗“客观对应物”起用的基础上,通过主体意象的渗入,强化了意象的鲜活性、整合美与知性化。
鲜活性。 黑格尔说“东方人在运用意象比譬方面特别大胆。 他们常把彼此各自独立的事物结合成错综复杂的意象”。①凭借悟性才气走近诗神的李琦并不十分在意修辞学上的理论阐释,她一心致力的是要把意象经营得新奇活脱,更具个性化风采,所以不论新的旧的雅的俗的意象一经她的梳理都变得熨帖自然,沾染上诗人的灵性,生机盎然,即便是别人用了一千次的意象,她不经意地一调弄也会充满令人折服的情趣。如风、月这样称得上老掉牙的意象,几成创新意识强烈者厌弃的存在,可诗人信手拈来的将之安置在友情诗“别”中,仍旧风情万种、妙不可言。“从此我们各自有许多地方/每一个远方都相互瞩望/友情是风/吹身前也吹身后/友情是月/照南方也照北方”,笃实浓厚的友情以风、月意象出之,转化为泡沫般轻点软绵的语言,诗意缠绵。 再有“你的爱你的睿智是壁炉之火/在这北国冬夜/从此我们有了去处//美好的老人是一座深山密林/长满奇花异草/吸引你直想迷路”(“你的家”),壁炉之火、冬夜、深山密林、奇花异草,不能再普通不能再生活化的意象,可是进入人的阅读视野后仍会造成一种审美的震颤,不是么?一个充满爱意的睿智老人无异于一本深刻的大书,恰似一座生长奇珍异宝的山林,引你前行,诱你深入,同时也让你提升,给你愉悦。
李琦从不去生僻的领域里捕捉怪诞的意象。她进行诗意抚摸的常常是习焉不察的质朴平凡的事物,但实际上日常生活和事物并非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和事物, 常常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和事物遮蔽了其本身应该自然敞开的生活和事物。 那么她是如何“点石成金”地“去蔽”,化平凡为神奇,使它们饱具新颖鲜活的冲击力的呢?我想不外乎有两点:一、她决不彻底地沉入无意义的琐碎芜杂的现象中,而是强调
(注:①[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34 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对事物现成的先在意义的反抗和拒绝,凭借自身经验思考的参与创造,使其生成并呈现出与自我相关的意义来。这样她笔下的意象大多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与摆设,貌似信手拈来实则都内涵着人生的彻悟与情思的体验,独到的思索与发现,所以能在人们熟稔的事物中标示出人们一直忽视的东西。 二是注意在意象之间或意象与前后左右的词汇组合时设置特殊别致的语境,使朴拙的意象爆发出葱郁的诗趣。可以想见“别”若只有友情是风是月的意象,充其量不过是枯燥平板的比喻而已,可与“吹身前也吹身后”、“照南方也照北方”结合后,干瘪的比喻则被激活为油画般的画面情境。 “你的家”正因有了美好的老人为深山密林的出人意料的“远取譬”,才有了袅袅余响与潜在的刺激性。
整合美。 除却小诗以单个意象承载意向外,一般诗的建构都要铸造众多意象使之转换、组合以完成情思运动过程。它的意象分子间有着严格的和谐度,有时一个不安分因子的误用即可造成意象间的散乱无序、完整画面情境的支离破碎,因此中国传统诗歌十分注意意境的创造,追求艺术情境的整体性。或者说,运用饱含主观内涵的感性物象,烘托暗示人类心灵情思的意境审美范畴,恰恰是中国诗美的核心与精髓。 可悲的是近些年的新潮诗人对这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大多不屑一顾。 李琦吸收西方诗思想知觉化与意象理论营养,但她反对食洋不化。 受骨子里镌刻的传统意识烛照,她的意象选择自然传递出了古典音响;尤其在意象之间的组合上,她少在陌生的联想轴上撷取意象,搞突兀奇崛的转换,而是以感触较深的事物意象铺展联想,讲究和谐一致,力求使众多意象以群落状态朝诗的灵魂——情思统摄定点发展敛聚。即意象的组合给人一种张弛有致的流动美感,而流动的便是氛围,这种情调氛围的统一、整合所造成的情境合一、心物相融,获得了一种类乎古典意境的审美特质。 这类意象与诗情浑然的诗在李琦那里出现的频率极高。 如“从前的脸盆”:
从前的脸盆
一声不响
静望岁月
从物质成为精神
洗过祖父的汗水
洗过祖母的胭脂
水声清亮
那双男人的手修长有力
那双女人的手秀丽白皙
岁月从指缝间滴落
两张年轻生动的面庞
一遍遍洗过
脸盆和脸
在每一个清晨对视
直到有一天,它们彼此分离
早已陈旧的脸盆
依旧滴水不漏
它侧立一隅
如一则寓言
我没有想到
世事苍茫
命运的暗示,有时
只需半盆清水
这首意象诗,抽去了语义上前后密切的因果关联,以一连串意象的重叠、弹跳直接表现意绪。初看起来,综合视觉、听觉、幻觉类型的意象脸盆、汗水、胭脂、手、面庞、寓言、清亮的水声等,是处于零碎随意状态的存在;但透过驳杂的外表就会发现它各意象分子间内在的一致性了,它们不但都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意象,笼罩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而且内涵与情调也都具有同一指向,即它们都是飘忽逝去温馨而渺远、苍茫又感伤的,它们在任何温馨美好的时光、事物都必然消逝的惆怅情调那里,又都熨帖和谐地统一一处,形断意连,意与象浑,构成了一个幽深隐约的情思意境。再有“月光梳理着你额角上的黑发”,“梳理我如烟如缕的歌声/墙壁和天棚都突然有了光华/天使的脚步在窸窣走动/我们的床变成了一只古帆船/在如梦的深海上远航/这一刻我们肯定去了远方/那是世界的尽头/一座最安静最优美的渔村”,幻觉模糊的心理转换成一幅立体的印象派画面,月光、歌声、古帆船、渔村等几个散乱铺展的标准的国产意象,从不同的方向向诗人与丈夫相依相握的夜晚是温暖宁静的家园港湾这一情思定点敛聚靠拢,织就了完整和谐的情思共享空间,形象的画面中隐寓着诗人对尘世嘈杂、人间冷风的厌倦,与丈夫相依相握的幸福感。至于像“读你从前的信”、“麦秸女孩”等诗则或以文字酿成的酒、词语的丝棉、语言树上的蜜桔同满足又感激的情思合一,或以乡间的路上、清风拂过的原野、粗糙温暖的手同麦秸女孩的美好灵魂洁净本性的联系谐调,使诗浑成为团块的整体生命迹象。
李琦为诗寻找感性寄托的意象化抒情方式,沟通了精神与物质两个视界,抒发心灵同时又节制了心灵,外简内厚张力无穷。意象组合的整体化,保证了诗点的才气与面的功力的双向获得,强化了诗的东方美学意蕴,难怪她的诗能唤醒一些读者蛰伏在心底的情绪审美记忆了。
意象的知性化,也是李琦诗歌意象艺术新变的内涵之一,只要重温一下“打开智慧的魔瓶”一章,这一倾向就会不宣自明。
象征与个人私设
李琦的创作愈到后来愈趋智性化。这种倾向来源于多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诗人注意寻找意象与象征的联系,靠象征性想象飞升建构智性空间,铸成丰盈的理趣与主题内蕴的多义多重性。
众所周知,意象作为一种心灵载体,一定情境下它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品格,有种借有限表无限、借刹那表永恒的意义。 作为女性基本修辞抒情方式的隐喻、象征则突破了单纯比喻的樊篱,基本上隐去了喻本,凭借象征性想象对客观事物进行观照便能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使之既是自身又具有自身以外的许多内涵,成为情知一统的载体。 而意象与象征合成的象征性意象对文本的介入贯穿,自然常常提供两个互相融汇的信息源——写实与象征,在写实的底层上有超写实的象征光影,这种高维复合结构在走向具象的同时又超越了具象,深层意蕴寄居在结构的第二层、第三层虚实隐露的形象间,引你去探寻、捕捉、品味诗歌有限尺幅内丰富的审美指归。
李琦的 “婆婆丁”、“泰山”、“雪的赞歌”、“干不死”、“海与我之一”、“飞天”、“死羽”、“草药”、“瓷盘”、“白菊”等大量诗篇都闪烁着象征意识的光芒。 如“雪山”:“你雍容于远方/远方明哲而温柔了/那少妇静卧的曲线呵——美丽的乳胸下/软蠕美丽的腰腹/每个小小的起伏都如此销魂/你辉煌得曲高和寡/你高洁得让我绝望……望着你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你这额如白岩石的/仪表堂堂的哲人啊//千呼万唤我的雪山啊/一言不发我的雪山啊。”诗人观照的只是自然的雪山吗?诗歌承载的只是诗人对自然雪山的瞻望与感叹吗? 显然不是。 在它第一视象背后隐藏的深层意味又是什么? 是赞叹造物主的巧夺天工,还是感叹于雪山的高洁辉煌? 是写精神雪山对人类灵魂的净化,还是写精神雪山对诗人人生境界的启迪? 似乎都对,似乎又都不完全对,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它可以悟出不同的“解”。 象征意识的深入使自然界的雪山完全成了精神隐秘的象征对应物,上升为形上的理性凝聚与抽象。美丽与圣洁代表着一种无法企及的精神高度,它不仅令人感动赞叹,更需人们的仰望与心的顿悟,人生旅途中能获得它的启迪是天赐的福分。寥寥数句,旨趣深远,精警深刻。还有“西北风”,那“不声不响/却常让你/石破天惊”的西北风,显然也不是自然之风,更是纯朴民风,热情民风。想想西北女人每人两朵胭脂红,想想西北卖瓜汉子与买卖无关的热诚话语,就不难发现西北风不只对应着世界的表象,更深指西北人类的精神品格,标题与关键词的隐喻使全诗众多的意象无形中成了象征的森林,有了飘渺不定、空灵迷蒙的一种言外之旨,有种“文似看山喜不平”的妙处。
李琦以整体的象征性贯穿抒情空间的诗歌覆盖面已较广泛,至于象征的局部镶嵌更不胜枚举。 “每个人最初的天空/都是母亲一片奶香的前胸/夕阳睡一夜就是朝阳了”(“豫北小村速写”),“我发觉我们站过的地方/正长出新草来”(“一个人在江畔”),那夕阳、朝阳、新草可以清晰把捉其替代涵义,但其指称功能恐怕已远远超出了语象词汇之外。
意象与象征联姻,使诗情在写实与象征间飞动,统一了人间烟火与形而上学,强化了情思力度、厚度;同时,赋予了诗歌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难以捉摸的隐性朦胧美,一种梦与真交错的情调。
李琦的象征世界是丰富、幽深、优美的,其意象构成中裹挟着一些个性鲜明、高度私人化的“主题语象”,这些语象是走进李琦诗歌艺术王国的理想通道。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认为,比喻性语象只有靠复现才能成为象征性语象;西方的新批评派更断言“一个语象在同一作品中再三重复(例如艾略特“荒原”中水的语象),或在一个诗人先后的作品中再三重复(例如叶芝笔下的拜占庭)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分量”①,成为积淀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象征。 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发现李琦二十几年诗路中以本貌或变体方式,高频率、大剂量地跳动的中心符码是纯净的雪、冰、月、水、茶,柔丽的云、花、风、微笑,坚贞与理想化的远方、帆、桅杆、灯等等,这些执着的人文取象,凝聚着她主要的人生经验与深度情绪细节。这些高度个人化的私设象征,几成她不可重复的专利语码与戛然创造,它们在形上的本质意义上规定着诗人的情思走向与风格构成。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对其主题语象一一展开解剖,这里只对其中几个最主要者进行抽样透析。
雪。 也许是生于北国长于北国的缘故,李琦似乎对雪情有独钟。 “茫茫的雪野”是她“诗歌的阔大背景”(“写诗的岁月”)。据不完全统计,她迄今为止的诗作中,雪意象出现不下几十次;并且呈现出逐渐递增之势。 雪在她那里显然既是自然风景,又是人生与心灵风景——纯洁、美丽的隐喻,80年代的诗中,她这样写雪:“如果明年你还化作雪花,/那么, 请在他的面前降临……//当他伸手接住了你,/也就捧起了我这颗心”(“雪上的字”);白雪春天“溶尽自己那小小的躯体,/为春花褪下心爱的白色”,“当融化的雪山汇
(注:①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第15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 )进小溪,/我听见了你一路笑得咯咯”(“雪的赞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该是一场大雪呵”(“大雪的启示”);“你晴朗的呼唤/是百合在我心谷柔曼地摇曳/是香雪在我头顶芬芳地飞洒”(“听你叫妈妈”……雪对于李琦决非北方严酷可怕的背景存在,而是象征着纯真的爱情,隐喻着奉献的欢乐,是圣洁磊落的代名词,甚至有种甜美的味道。 其精神意指多为与雪之色彩相联的色彩象征,象征本体与喻体的联系尚嫌直接浮面,过于单纯明朗。
进入90年代,诗人咏叹的雪,内涵的拓展更侧重潜入其审美、精神意蕴层面,手法上象征意识的渗透出神入化,本体喻体妙合无垠不落痕迹,指归也更为内在与抽象,“人类的良知飞扬起来/变成那一年/俄罗斯的大雪”(“托尔斯泰的阳光”);“多么白的雪/是神的微笑散落了/凛冽硬朗的北方/一下子伏动起/温柔而忧郁的气蕴”(“我的冬天”);“雪花”“宁愿融化/它坚守自己的完美”,“落在我额上/变成清澈的水/洗掉我脸上的尘垢/是一缕清凉的/暗示”,“美就像窗外的雪/不肯久留尘世/惊鸿一瞥/来去轻盈”(“雪中听歌”),色调象征之外又强化了情调与精神象征,主体日趋凸显的雪意象更成了一种灵魂品格的代指标志。她不但美丽轻盈洁白,而且一尘不染,宁肯消失也要坚守完美。那坚贞倔强、美丽又悲凉的灵魂,那份圣洁之美,对人生不是清凉的暗示吗?它不正是一种人格的隐喻么?它洗去的岂止是脸上的尘土,更有灵魂的污垢,它真的是一场“精神的大雪”啊! 当然,不论前期还是后期诗中,雪纯洁美丽的隐喻之意都是一以贯之的。
远方。 这一他人稔熟得难再引起注意的词汇频繁走进李琦的诗中,构成了独创性的主题语象。 在一篇同题散文中,诗人坦告“远方是我们的未来,远方是人生的境界,远方是魂牵梦绕的家园,远方是希望的象征”①,这一诠释为人们解读诗人的远方取象提供了一把钥匙。李琦诗中的远方大都摆脱了地理方位的原本指向,而借喻着人们憧憬向往追求的美好的未来、理想、希望所在,所以“江水/你却无旁顾之心/急急切切向远方”(“过岷江索桥”);诗人眼里的丈夫则“你是为远方出生的/那异乡的道路与天空/总向你打着神秘的手势”(“两种难过”),“我们为远方而生存/远方有古老的家园”(“唱俄罗斯民歌‘小路’”)。 每个生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的地平线,那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那是神秘的伊甸园,每个人都是为生命中的远方而生活的;正是因其神秘才更具有诱惑力,正是因神秘的远方诱惑才使平凡而普通的岁月光彩勃发,充满力量与乐趣,人类正是凭借一次次对远方的进发的支撑推动历史进程的。 所以诗人才自诩为“一只原野的赤狐/魂魄系在神秘的远方”(“我”);三只小麻雀的遗体“三只小头颅/向着苍茫的远方”(“死羽”),只是“远方却从来迷茫”(“过岷江索桥”),“远方永不可及/远方让我们把这支歌/反反复复/唱成了永久的悬念”(“唱俄罗斯民歌‘小路’”)。 远方一定是迷人的,但抵达远方必须付出代价,人必须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走好足下的每一步;远方难以企及,它永远在你能够看见之处诱你前行,可一旦你到达追求的目标,视野中又会出现一个新的远方。 如果说在李琦诗中“雪”昭示一种精神品性,那么远方则是精神追求的同义语。
灯。 李琦诗中常常隐现的月亮,写得轻柔妩媚、皎洁空灵,甚是招人喜爱,但将其置于中外古今的月亮诗海中就不十分稀罕了,倒是90年代以来对灯的青睐更引人注目。在李琦的笔下,灯随生存的语境不同变化呈现出的内涵也姚黄魏紫色调纷呈,“纸笔之间/我心灵的木屋/它是一盏灯/我住在一盏灯里/靠光取暖”(“写诗的岁月”),那是给人以温暖慰藉与快乐的智慧之灯;“你的家在条名字美丽的街上/你的家是一盏温柔的灯/在这喧闹的沉沦的城市/独自放着清凉柔和的光”(“你的家”), 那是在喧闹之外放出宁静温柔光辉的理想之灯,“一盏如豆的灯光/也会让我体悟温暖”(“我”),那是给跋涉于冷漠虚伪的黑夜中的人以力量与勇气的希望之灯;“一九六二年/一个六岁的孩子深怀忧伤/满目纯洁的白色/那张失去了
(注:①李琦:《从前的布拉吉·远方》,第118 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年版。 )祖父的空床/使我注定要成为诗人/一盏灯 轻轻熄灭了/另一盏小灯 正悄悄点亮”(“回忆祖父的葬礼”), 那是一代代绵延不绝的诗性生命之灯;“写下你名字的时候/手指下亮起/一盏雪夜里的风灯”(“寄”),那是令人感动、回忆、渴盼的明净的真情之灯。 李琦对灯的执意趋赴与被誉为诗坛夸父的艾青对太阳的追逐不谋而合。 只是她表现得不如艾青那般热烈而已。 在宗教神学的体系里,光乃神灵或圣化的生命的象征,李琦对灯的喜好既是其重视人格精神提升的表现,又是生命创造力的象征。试想,在象征着死亡与停滞的黑夜背景中,灯光微弱而顽韧地燃烧闪烁着,响亮冲动的金属般的光调质感,甚至可以让人忘却周边的停滞与黑暗,带给人以光明温暖、信心和力量,这盏灯不正是生机、希望的象征吗? 但愿每个人生黑夜中的过客都拥有这样一盏灯。
茶,在李琦诗中也有原型意义,诗人有意而又无意地常常提及它,“碧绿的叶子带着神性/一种高雅素洁的气质/让你想到汉语里/人们正逐渐淡忘的一个名词——君子”(“望茶”),“阿里山夜色苍茫/我们手执香茶/像坐在一片云上”(“阿里山的茶”),显然“茶”已经成为诗人崇尚的境界的一种心灵抽象。 类似的意象还有水、月、花、风……
李琦创造的私人化的主题语象诱导读者联想或想象, 这正应合了语言论美学所关注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它们不断复现的弥漫性常会延宕读者阅读的心理时间,强化情思氛围的浓郁,在弘扬创造力的同时,达到了化抽象意念为具体质感的效果,既新鲜又防止了浪漫诗的滥情。 那些柔媚、雅丽、清纯的国产型语象复现,也可视为诗人情趣个性的间接外化。
向事态扩张
李琦极具人间情怀,对芸芸众生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平凡琐屑基于平常心的关爱,注定了她无法不走进生活与心理细节中间;对这些流动繁富、瞬息万变的外在世界与完整浑然的动态情绪流、意识流,仅仅靠追逐意象弹跳与暗示象征,势必泛出传达的无力性,背离生活的可感性特质。 受不得憋闷的情感希望自由淌动,诗人的生命需要寄托,社会生活与心理的日趋明朗丰富也渴盼诗从沉滞的意象象征中走脱。面对种种呼唤,诗人为拓展情绪的容量与宽度,与起用思想知觉化与私人象征手法并行不悖,又积极向叙事性文学扩张、借鉴,巧施事态艺术技巧,使诗歌的抒情本质融入了新机。
动作(生理与心理动作)的强化与凸现。李琦的某些诗意象相当疏淡,动作细节倒跃为结构主角。它常常以人的意绪张力为主轴,联络带动若干或连续或颠倒的具事(子情节、动作)链条,把诗演绎成一种行为一个片断一段过程,从而使诗获得了整体性情趣和流变飞动之美,获得了一定的叙事性。 但是这种“过程”的叙述,这种词意象向行为意象或句意象的转换背后,诗的生命支柱仍是生活与情感并重。如“偶遇”这样写道:
你没有眼睛看不见
二十年这条马路
被嘈杂的热闹挤瘦了许多
你却依旧玄色衣服
无意间和你的世界
保持统一的颜色
扶着你我说自己眼睛也不好
说谎话第一次这么坦然……
诗中马路、衣服、眼睛等几个稀稀疏疏的意象已不大为人注意,而普通的生活细节却占据了读者的兴趣热点。在嘈杂热闹的马路背景下,失明的“你”依旧衣着朴素,“我”扶着你说自己眼睛也不好,两种生理事态开始交叉,“听说我住过那一带/你向我打听一个姑娘/说那时她天天送你上班”; 又是单向的心理、语言动作运行,“我说不认识真不认识/我不敢说那就是我”,两种事态继续渗透交叉,结尾延宕出诗人的心理感受:“人长大了有许多事再做不到从长大了其实并不快活”,平淡的事件升发出一种清新的诗意美人性美,在过去与现在两种事态的叠印碰撞中,闪烁出善良人性的诗意光辉,诗人又找到了往日那种送盲人上班的快乐体验。这种散点式的叙述并不完整,跨度很大的事件运动细节组接与细节中回忆片断的穿插,造成了大面积的“净线空白”,并使诗充满了强烈的动作推进感。
再如“想起了许多年前/一个雨季/无意中伤害了/那个多情的少年//如今你早是父亲了吧/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愿此刻也下起雨来/是我轻轻地道歉了”(“我知道这雨是因我而下的”), 诗捕捉的是内心情绪中展开的抒情情节,因一场雨唤起一段人生往事的回忆与心理感受碎片,以想象和心理的行动代替了外在故事情节的推衍,情节行动与感悟交织,虽是来自生命的体验,仍有强烈的事态流动性。“头发”、“异乡的雨”、“老宅”、“那天”、“泰山”、“现在是午夜”、“新年快乐”等诗都走进了生活的细节与感受中,它们不再注重词语意识而转向注重语句意识,所以词意象逐渐向句意象(心理意象转向行为动作结)转化了。
动作的强化凸现甚至使人物的性格要素也以多种姿态走进宽阔的空间,如“老祖父”、“哑童”、“那个人”、“川江老渔夫”、“托尔斯泰的阳光”等把观照镜头瞄准人的诗比比皆是,这也是诗走向生活与芸芸众生后必然留下的痕迹。 但它决不以人的一生当描述对象,沿续小说戏剧的完整谨严的叙述原则,往往只选择几件典型的场面或事件细节,从某个角度刻写人,并常常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情感意向,使所描绘的生活与细节成为“隋绪事件”。 如酷似戴望舒的“我的记忆”的“很旧的人,很远的事情”,以拟人化手法创造的记忆中的朋友与“我”的对话拼贴,映现出了诗人形象;可它只截取了诗人童年的“各种大胆”“浪漫的举止”,“四十年住在一座城市/二十年经历一场爱情/十年不变发型/朋友愈来愈少/世界阔步前进/你几乎原地不动”,在木桌上用老文字写新感受,几个典型人生细节片断,凸现出诗人外在的生活历史与心灵脉动潮汐,那是一位远离流行的欲望虚荣,坚持精神操守,内心世界高洁丰富以独特方式关注世界的人,她在以艺术与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构筑自己的“外面”,以对抗“拥挤热闹”、“欲望缭绕”的现实的“外面”。“住在青海的诗人”也只是以“他每天用很长时间/读书、冥想/或者痴迷地从早到晚/练习书法”,“做着/很慢的事情”等两三个细节的描述性再现,凸现了这位西部诗人的豁达与悲怆、坚忍与快乐,深入到了西部诗人悲壮的心理内核;并且掺合了诗人抒情主体的情感倾向与评价,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那位“悲怆独语”诗人的一片钦敬与怜悯,这种诗绝非仅仅为写人而写人,情感仍是它的生命支柱。
这个特征表明:随着观照视角的变异,李琦的部分作品已形成了诗的小说戏剧化、述实同序志的平分秋色甚至大于序志的倾向。 它依靠内世界与想象的铺展,表现心灵与外世界的流动变幻,而非浅层次的客观描述性再现。这种事态的强化使诗时时弥漫着或浓或淡的生活趣味与生气,有了稳定又通脱的真实亲切感,情绪氛围的渲染获得了沉实的依托;并且诗境疏淡清静,多得大音稀声之妙。这种向叙事文学的扩张,是事态的但更是诗的。从形态上看,它具有叙事文学的一些要素——人物、情节、地点乃至性格,仿佛诗的特征在淡化,但本质上它仍是诗,它只是合理吸收了小说散文的笔法,在戏剧性情节构架或细节画面中仍注意情趣情绪对事件的强渗透,因此叙事也是情绪化叙事。这种事态以亲切平实的语调叙述出来,更真实更自由地接近了读者;事态本身的具体单纯也加强了诗歌联想再造的限定性,即便有象征意识思想的介入也不至于太过空泛与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