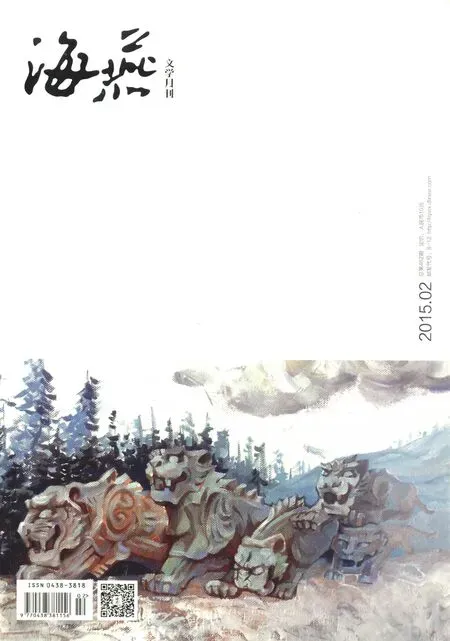编钟
□沈秋寒
邓明达看着窗外。晨曦的第一缕白从东面的暗青色的山坡上缓缓燃起,没有多久就突破了城市的桎梏,把树和街道,圆顶的伊斯兰教堂,以及坐落在护城河边的破败钟楼都染成了刺目的银色。
河水似乎稍微停顿了一刻。不是幻觉,那条自战国开始就一再被毁,毁掉后又一再重修的孱弱的河流,在晨曦的微光里确实停顿了,然后又继续流淌,沟通着这座城的前世与今生,明与暗,生与死。
在邓明达眼中,晨曦并不会带来幸福。相反,有一些事物沉坠在黑暗中,永远见不到阳光。和太阳是否明艳无关,也不会因为心里隐藏的苍凉而显露悲悯,所有无法亮起的世界都隐含不可说的故事,有些像他一样明知荒谬却无力改变,有些永远也不能摆脱愧疚和恐惧。
这大概就是活着的含义。不能屈服,不可抗争,不被包容,也无法逃离。
爸爸。当邓明达凌乱的思绪被早晨这个词语缓缓点燃时,一个稚嫩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女儿起床了。邓明达随着这一声呼唤,身体顿了一顿,好像时间逆流,眼前的世界也倏忽变化,潮水一样退去。
晨曦,明暗,河流,都向后退去。
深吸了一口气,邓明达转过身,露出和煦的笑容。女儿小雨正扶着漂亮的水族箱站在客厅边,眼神有点迷茫。
小雨从不美丽。甚至邓明达也从未幻想过女儿有朝一日会变得美丽。美丽是个太奢侈的梦。如果女儿有一天能像其他同龄的女孩那样跑那样跳,那样开心地缠着他玩耍,缠着他要喜羊羊要芭比娃娃,邓明达就很知足了。
邓明达恨自己。当女儿在幼小中表现得与众不同,当女儿在幼小中比其他孩子更迟缓,爬得更慢,表达更迟钝的时候,他在忙着。他在阅读战国的音律,他在寻找战国的乐器,他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他不停地走,不停地寻觅,寻觅让他魂牵梦绕的战国,寻觅让他魂牵梦绕的编钟。
邓明达恨自己。是他耽误了女儿,当妻子提及女儿的情况时,他只是觉得女儿发育得太慢,他自己幼年的时候发育也很慢。他以为那是来自遗传基因的共通性,以为过一段时间女儿就会一切正常,可他从未想过女儿有病。
邓明达转过身,把女儿拉近自己。小雨因为身体的限制,并没有显出喜悦的笑容,相反她的整个身体都有些不稳,几乎被邓明达拉倒。但小雨还是微侧着头,撞进邓明达怀里。
爸爸,我已经能自己穿衣服了。小雨似乎是想安慰邓明达,可抱着女儿的邓明达却差点没有忍住眼圈里的泪珠。在最能给小雨帮助,并且最应该给小雨帮助的那段时间,邓明达却从来没有好好陪过她。
那时候邓明达在一次外出鉴宝的商业活动中,无意发现了一只细小的丁字形铜锤和一块印刻着精美龙纹的青铜碎片。岁月的磨砺使那两件残缺的青铜器藏起了光芒,只留下斑驳的锈迹和泥土。
没有人在意那两件小物品。毕竟民国时期的仿制工艺空前绝后,短短数十年制造的赝品达到几十万件之多。凡是听过名字的古董,古玩玉器茶具青铜几乎都在民国时被大量地仿制过。所以一次普通的商业活动,出现几件假货确实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邓明达抓住了一个细节,一个在过去出土的文物中所没有的细节。就是那个细节使邓明达大胆地推测,考古界所知的编钟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比预知的早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他立刻收购了那两枚青铜小件,并带着它们去了北京。也正是那天,妻子第一次打电话说,小雨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太正常。可是妻子的警告却被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邓明达轻易忽略了,那时候没有任何事能比发现了疑似商代制造的编钟更重要。
邓明达甚至能够确信,那两件青铜器残件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编钟,是后来巨型编钟的模板。他需要最权威的机构做出最权威的认定。然后他需要追查两件国宝的来历,追查那段早已埋进尘埃的历史。邓明达甚至生出一种意愿,他要找到编钟的设计者。
隐隐地,有一个模糊的面孔正被勾勒出来。
邓明达是那种忙起来就是废寝忘食的人。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可以几个月不回家,也不和任何人联系。邓明达那时所想的事情只有两件:第一,保护国宝;第二,尽早还原发现疑似编钟部件的现场,寻找其他部件的下落。
那段时间,妻子一次又一次给他打电话,诉说着小雨的特殊,都被他简单地忽略了。直到上级部门确认了青铜残件的年代,就像邓明达料想的那样,它们来自一个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的时代。
怀揣着兴奋,邓明达把这个无比重要的消息告诉给电话另一端的妻子听,想要和她分享自己的喜悦。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妻子声嘶力竭的哭喊。
小雨患上的是脑瘫。并且,孩子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将来,他的女儿,可能要面对终身残疾。
脑瘫这个词,邓明达以前从未听过。他对如此专业的医学用词,陌生得很。
从结婚前10年算起,邓明达就很少看电视了。他不关心政治,也不懂经济,从来不看新闻,无论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邓明达从不在意。在学术领域,邓明达是专家,他向来只看最权威的论述,也只参加最权威的讨论。在非学术领域,邓明达则可以用白痴来形容,就连方便面,他都只知道华丰一个牌子。
于是当妻子在电话另一端哭得跟泪人一样的时候,邓明达竟很不合时宜地问了一句,脑瘫是什么意思,发高烧吗?
现在,邓明达已经彻底明白了那两个字当时给妻子造成的的惊恐。可是为时已晚。
妻子恨他。母亲恨他。他自己也恨不能时间倒流,把所有的苦难都重新来过。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一定会放下所有,放下战国,放下编钟,只关心女儿。
是的,邓明达恨不能有一天早晨,阳光会突然倒退。岁月重来。他甚至希望患上了脑瘫的人是自己,那样就再也不用面对无助的女儿,也不用面对内心的愧疚。
可命运就是这样,那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着他,不肯松开,也不肯让他有一丝的欣喜。他拼命寻找的编钟不过是一场梦。那两枚青铜残件经鉴定出具体年代之后,科研部门紧急讨论,磋商,最终根据种种迹象,排除了商代编钟的可能。会议除了决定将邓明达带回的青铜器高价收购,就再无议题。
邓明达所建议的新研究部门,所建议的对编钟诞生年代的重新定义,所建议的寻找其他编钟部件的计划,都被全盘否定,再也无人问津。
通知他结论的部门领导态度和蔼,但是语气不容置疑,国家研究经费非常紧张,科学研究必须谨慎,要拿出真凭实据,不能仅以发现两件商代青铜器疑似编钟部件,就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进行重大修订。
也就是说,相关部门领导严肃地否定了那两件青铜残件是编钟部件的可能性。邓明达为之付出的重大牺牲,为之付出女儿的编钟研究,走到了尽头。
现在,女儿的身体正在缓慢地接受治疗,康复进度堪忧,如果不是邓明达变卖家产,从大宅搬进了远在市郊的小房子里,女儿的治疗费用早已捉襟见肘。事实上,为了给女儿治病,邓明达已经辞去了工作,如果不是为了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妻子早已和他离婚。但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两人多年分居的事实。
爱情早已死去。
邓明达也不敢奢望什么。母亲是站在妻子那边的。因为女儿的事,他和母亲已经多年没有交流。亲情这个温暖的字眼,却使折磨的含义更多了一层。
却是女儿从未记恨过父亲。无论情势多么恶劣,无论身体多么不堪,小雨每天早晨都来给邓明达问好,都要让父亲抱抱自己。
爸爸,这是我自己选的衣服,好看吗?小雨笑着问邓明达。
可邓明达完全看不懂这是女儿的笑容还是痛苦的表情。女儿略偏着头,因为她想正过头来,要付出无比艰巨的代价。首先,她要努力地摆正自己的左肩,要和右肩平衡,这个过程很可能会令她身体倾斜,狠狠地摔倒在地。然后,即使她拼着疼痛达到了这种艰难的平衡,还要直起脖子,忍受剧烈的头晕,忍受从指尖带来的撕扯感。
但小雨正在克服这些。邓明达显然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但他知道,孩子很要强,比他期望的,比他想象的,都要强出太多太多。
邓明达强忍着流泪的冲动,给女儿整理好衣服,然后才问,乖女儿今天有什么打算?
小雨偏着头,仔细地想了想才说,丹丹去年就上学了,浩浩今年也上学了,爸爸我也想去上学。
邓明达怔怔地站在那儿,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事实。女儿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但是怎么告诉女儿呢,她的心智并不残缺,智力也不太差,只是语言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使她与健康孩子差别太大。把女儿送到专门的学校吗?邓明达想过,但是被妻子否定了。因为那无疑在告诉女儿,她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普通的学校,对女儿的心理是巨大的打击,对她后面的康复计划不利。而且妻子认为,自己在家里也能很好地教女儿文化知识,等将来有机会,或者女儿的康复足够成功,再把女儿送进学校,才是对女儿最负责的办法。
邓明达也算勉强同意这个建议。可是今天,女儿终于主动提出,自己该上学了。邓明达抱着女儿,使劲忍住了没有哭。乖女儿,你不喜欢在家里,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吗?
可是,别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小雨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邓明达深深叹了一口气。他想说你现在还不能上学,可是终究没有说出口。房间里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妻子又一次精神崩溃了。她的嗓子已经完全沙哑,虽然已经控制过音量,但仍旧震得邓明达皱了皱眉。
人生的无奈莫过于此。那种清晰可见的绝望,那种因过分压抑而生出的恐惧,邓明达实在不能强求妻子更多。尽管他一直也在挣扎也在承受,可是这个世界对他和女儿来说,真的太过狭窄,阴影也太过浓重。
爸爸。小雨伸手,使劲伸手,够到邓明达的脸,抹去了他眼角的泪水。
胡凯恩已经七年没见老同学。他当初只是隐约听说邓明达家里出了点事,还没有来得及细问,邓明达就不辞而去,把一大堆烂摊子留给了他。再找这个人,就电话关机,搬家,差不多是彻底失联了。虽然后来从其他人那里也打听到一些邓明达的情况,但是胡凯恩一直没有主动联系邓同志。
说实话,胡凯恩生气。当年那叫什么事啊,邓明达千里迢迢地把他从湖南召到北京,又从北京跑到陕西,胡凯恩没说半个不字,为了商代编钟,吃再多苦他都认了,哪怕就是个疑似,不也说来就来了。他老胡自认没有别的长处,就是讲义气,一条路走到黑。可结果真就走进了黑洞洞里。老同学连个招呼都没打,说撒手就撒手了,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没了,楼空了,就留下一大堆半吊子资料。
胡凯恩发过誓,这辈子,邓明达你爱咋咋地,跟我没半毛钱关系了。
一晃就是七年。胡凯恩过得不容易,他没有邓明达底子好,钱不多,没房子,经常是今天挪个窝每天换个巢,有了上顿就没了下顿。这年头谁都知道钱不好赚,可谁又知道没有钱还要搞研究搞调查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人能过的?
胡凯恩不求人。他豁不出去那张脸,也没有求人的志气。可是这一次,胡凯恩非见邓明达一面不可。
编钟的事情有眉目了,很可能不是疑似了。这么大的事,胡凯恩必须和邓明达说个清楚。当年你可以不仁,但我胡凯恩不能不义。
事情的转机其实也不算是转机,为了生计,胡凯恩一直在到处跑,做生意,倒腾字画,鼓秋瓷器,鉴定古董。说到鉴定古董,那才是胡凯恩的本行,赚钱虽然不多,但总归他是专业人士,看好看坏都能弄点生活费。
还是三年前,胡凯恩经人介绍去河南给一个老板看古旧家具,几个来回就混熟了,老爷子只要划拉着什么东西就把胡凯恩叫过去瞅瞅,东西值钱就包吃包住包飞机,多给辛苦费,东西要是赝品就直接送给他玩,算是交朋友了。
胡凯恩收钱收得手软,自然尽心尽力,帮着老爷子做了几次大生意,也帮着他挽回过不小的损失。老爷子没有儿女,玩古董就是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颐养天年。日后这些老东西说不准都得跟他一起埋回地底下。
胡凯恩看着就心疼,多次劝老爷子别玩了。烧了那么多钱,就为将来陪葬,不值。
老爷子听了就火了,谁说我要陪葬的!将来我走了,这些东西有一半是你的,捡捡那些你喜欢的留下,其余的就交给国家了。胡凯恩看看满屋子的陶器、瓷器,还有字画,一件也没勾住他的心思。
老爷子我跟你说实话,这些年我什么都不在乎,就是在找一件青铜器。就一件。一旦有了它,我什么都不要。
哦?老爷子也被勾起了好奇,上下打量着胡凯恩,良久才说,我这也有几件青铜器,从来没给外人看过,都是真正的宝贝,你刚才说的要是真心话,我就领你看看。
跟着老爷子去中信银行打开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是一个厚厚的油布包裹,打开以后,只有三四件碎铜片,蒙着历史的尘埃,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老爷子不无怜爱地将它们捡起,一件件捧在手上揣摩着,然后又递给胡凯恩。
得到这几件东西都是偶然,代价也不小。老爷子的口气有些沉重,说本来以为自己要带着它们入土了,但如果真有一天能让它们重见天日,也不枉当时付出的代价。胡凯恩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滞了。他接过几件青铜器,心脏开始扑通扑通地跳。
就是它们。七年了。几件青铜本是一体的,可以拼接成一个半圆的小钟,上面雕琢着细致的龙纹和早已失传的文字。只是这几件青铜拼接后并不完整,还缺少了一部分,所以很难认出它的本来面目。
老爷子知道它们的来历吗?胡凯恩谨慎地问。
年代鉴定过,很古老,可能在商代甚至更早,但是用途不详。老爷子似乎在回忆什么,但终究没有说。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开口,如果这真是你在找的东西,就拿走吧,留在我这儿也是徒增伤感。
胡凯恩没有再追问,也没有解释。他仔细地把青铜器重新包好,带在了身上,然后对老爷子郑重地鞠了一躬,说老人家,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老爷子连忙止住了他,摇了摇头,也没有再说什么。
过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拿到了?邓明达接过胡凯恩递来的青铜碎片,心情无比复杂,问出的话却简单到可笑。
简单吗?胡凯恩反问。我吃了七年的苦。整整七年。
邓明达重重地拍了拍老同学的肩,反身去书架的最高处取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卷图纸和几张照片。他拿出放大镜,详细地和青铜碎片比照着,十几分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胡凯恩就站在旁边,一言未发。
这时小雨推开了房门。爸爸。她喊。
胡凯恩回过头,看见孩子,几乎是立刻,七年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抑郁,所有的不甘,甚至是所有的愤懑,都过去了。
天空的颜色似乎在那时也暗了一暗。七年了,你是为了孩子?胡凯恩问。
邓明达点头。眼泪转了两转,虽然止住了,但他的嗓音却难以平静,这些年,一事无成啊。七年前他见到孩子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七年了,他才终于能够面对这么残酷的事,可是当着老同学,愧疚和痛悔又一次占据了他的心灵。
那天晚上,邓明达喝了很多酒。七年来他第一次喝酒。胡凯恩说,今晚我不醉不归。然后拧开一瓶二锅头,使劲往嗓子里灌,怎么都劝不住。
两个人都醉了。邓明达说咱们得马上去北京,这么大的事,得尽快和领导报告,如果还能找到那处遗址,要马上进行抢救性挖掘。时间不等人。
那孩子呢?胡凯恩问。
带上她一起,正好去北京看病。邓明达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却伸向窗外无边的黑色中,似乎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正在盯紧了他,盯紧了他身后凌乱的房间。
夜悄悄蔓延,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邓明达和胡凯恩在北京一住就是三个月。他们白天带着孩子,或奔走,或求医,晚上回来就整理新发掘的资料。几乎到了不休不眠的程度。
三个月后,小雨的病情略微有了进展,已经能完整地读写和走路了。邓明达几乎难以表达自己的快乐,这么多年的恐惧和阴影终于有了散去的可能。哪怕只是可能,对于邓明达,也是天大的喜讯。
胡凯恩那边也传来消息,他们带回的青铜碎片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初步肯定,关于商代编钟的研究计划有望在近期开启。但是考古研究方面却有不同的声音,虽然他们带回的碎片相对完整,而且已经与原有的碎片对接,却依旧不能认同整套编钟在商代已经诞生的思路,假设仍是假设。
没关系,只要研究计划能够开启就是好事,这些年就没有浪费。邓明达安慰着胡凯恩,并且提出不想参加研究小组的想法,毕竟他现在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小雨的病上,假如小雨的病真能有重大转机,那么就是再离家几年,他也不会犹豫,现在肯定不行。
胡凯恩长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不参加这个研究计划,真是损失太大了,再说没有你怎么会有这个研究啊!邓明达笑了,说研究嘛谁做不是做,况且考古这个领域的专家还是很多的,我都离开那么久了,落后啦,思想落后了,知识也落后了。
我还举荐你做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呢!胡凯恩悄悄地说。
哎,没必要。邓明达一口回绝了,我这拖家带口的,小雨的病还不知何年何月,我去做组长,那不耽误正事吗?
说到这儿,胡凯恩乐了,说你真当这个组长,那我就去争了。邓明达也乐了,说你就扯吧,这个研究组都未必有,你去当组长,小心一幌子,跟以前似的,计划又搁浅了。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这个研究组真能成立,邓明达从内心还是希望胡凯恩去争一争。一个是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而且也确实搜集了很多资料,论经验肯定没有人比他丰富;另一个是胡凯恩这人够坚持,有恒心有毅力,研究嘛,需要这样的人带头。但是论资历,胡凯恩却显然不够,所以他也就提了个醒,告诉胡凯恩,这件事顺势而为的好。
胡凯恩也同意这说法。
接下来几天,心情大好的两个人除了继续带孩子看病,也抽空领着小雨去北京的名胜古迹转了转,天坛地坛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香山北大,差不多能带孩子去看的地方都去了,毕竟来北京这么久了,天天都在奔忙,也该放松一些。
再过两个星期,准确的消息传来,上级已经同意了重启对疑似商代编钟的研究计划,课题组的组长是一个对历史和人文都颇有建树且在国内威望很高的老教授。对于此,邓明达和胡凯恩也算服气。
胡凯恩是肯定要加入研究组。邓明达却不愿继续留在北京,毕竟小雨的治疗暂时不会再有大的进展,该回家了。胡凯恩不好阻拦,于是买了不少东西,送他们去火车站。
可是邓明达的返乡计划却在临走的前一天搁浅了。因为小雨丢了。其实就是一转身的事,邓明达带着女儿买点吃的,然后有个人过来问路,邓明达其实也不熟悉,但见那个人急得火烧火燎,就帮忙打听了一下,前后就一两分钟的事,孩子就不见了。
找了三天。也报警了,也登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汽车站,火车站,飞机场,小旅店,能藏人的地方邓明达都去找,可是北京太大了,找一个患有脑瘫的9岁女孩,比大海捞针都难。
邓明达一下子苍老了几十岁,四十出头的人,突然间白发苍苍。胡凯恩看着都想哭,可邓明达却没有。他连哭的勇气都没有了,就那么天天在街上乱转。他拿着小雨的照片,几乎是逢人就问,你见过这个女孩吗?她是我女儿,我找不到她了,我找不到她了。
起初还有人表示关怀,和他打听情况,一个月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有个疯老头在街上找女儿,留言也四处传播,有人说他可怜,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这就是个骗子。胡凯恩每天都要出门找邓明达,找已经疯了的邓明达。
后来邓明达的妻子来了,就看了一眼,转头就走。她说活该。
邓明达像个乞丐似的,破破烂烂地依旧拿着小雨的照片,在街上逢人就说,你见过这个女孩吗?她是我女儿,我找不到她了,我找不到她了。
再后来,邓明达失踪了。没人关心他去哪儿了,也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唯一在找他的人就是胡凯恩。他也老了很多,并且离开了研究组。
同样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有人在河南见过他,有人在陕西见过他。有人说他一直在找商代编钟的下落,有人说他在找失散多年的老友邓明达。
真正最后见过胡凯恩的人,其实是老爷子。看着眼前的胡凯恩,憔悴苍老到和自己相仿,老爷子终于一声长叹,眼泪忍不住落下来,说当年我也是这么找我儿子的,我也是这么找的。
但是不久,老爷子就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跟我讲这个故事的人,是老爷子的律师,年纪和老爷子相当,两个人走过了半辈子,患难与共。我问他,真的再也没有胡凯恩的消息吗?
他摇摇头,说胡凯恩是走胡同的人,自己一个人找编钟就找了七年,何况找一个人。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有一轮明月,照耀着马路边新栽的小树。很直。很硬。也很瘦弱。但总有一天,它们会长起来,长成大树,长成遮挡马路的树荫阴,长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