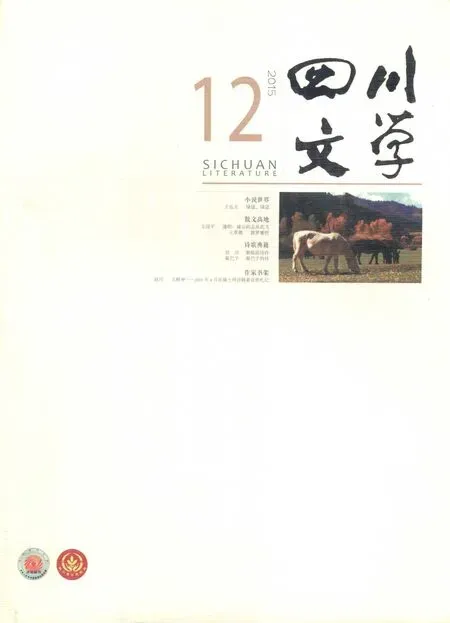白玉烟嘴
○ 程相崧
一轮圆滚滚的黄日头已经掉到土城那头去了,楼群林立的西天上,溅起的晚霞血红一片。这个时节,按照平常习惯,老石街上人家昏黄的电灯都该已经拉亮,饭菜也都该摆上桌了。老石街是土城最古旧的一条街,家家一个四合院,青色的院墙,常年都有些潮湿,墙边长着玫瑰,月季和蔷薇,香气塞满了院落。这街上有花家堂楼、二贤祠、文峰塔、奎星阁这些老建筑,上头知道拆迁阻力大,就搁置下了。从土城走出去的人,逢年过节回来,爱到老石街找记忆。他们惊讶着说,以为土城从这世界上丢了,她偷偷藏这里嘛。
这时,花荣老汉家里才收拾停当。这里所谓的“停当”,并不是指家里比往日整洁多少,规矩多少,若论那样,是比平时还更不堪:杂乱的衣物、肮脏的鞋子、破旧的被褥散落一地,让进来的人简直没有一个插脚的地方。这“停当”指的单是花荣老汉这个人儿。那件黄布滚边的深蓝色衣裳,是穿在老人身上了;那顶莲花瓣儿样的镶边蓝布帽,也在老人头上周整戴着。老人嘴巴里噙着一枚铜钱,软软地躺在那里,看上去舒舒服服,清瘦的脸庞像是安详地睡着。老人身子下面的被褥是新的,床单是新的,全身上下的衣服也是新的。这崭新的一切让人感觉简直跟这几间青砖红瓦的小屋有些不搭调。这副模样让街上许多老人都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这老家伙穿着一身借来的卡其布衣裤,在这小屋里当新郎官时那副拘谨可笑的傻样儿。
刘小兵老汉这时才有空闲把那个白玉烟嘴衔在了嘴上,那玉通体透亮,白得可以跟冬天的雪花相比。他盯着亡人,目光停留在这张脸上,他知道,等会儿,再搭一张草纸,这张脸就轻易看不上了。在两天三夜葬礼的过程中,除非来了重要亲戚,做儿女的才会爬着过去揭开草纸,让人瞻仰上一回;让人盯着那平静的脸庞,说些在老人生前没赶上说的体己话。这会儿,老人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以及几个孙子辈儿,都已穿上了白色的孝服,在床下跪着。老汉的大儿子花援朝领头的几个男丁,手里还都拿着柳木丧棍。那棍子粗细不一,都是刚刚从护城河边的柳树上砍下来的,两端还湿湿的,让空气中带着些微苦的气味儿。地上,已经在稍早时候,铺上了一层麦草,黄黄一片。那麦草是从城郊农户家买来,带着阳光的颜色和味道,给悲伤的人许多温暖。人跪在上面,软软的,跪久了盘腿儿坐一会儿也可以。
“刘伯,谢谢您哩,俺爹这辈子没白交你这个朋友。”花荣的大儿子花援朝在招商局工作,四十多岁,感激地抓着刘小兵的手。
“你们放心,谁让我是咱老石街的百事通(街上红白事的总操办人,其他地方也叫大拿、大知佬或问事人等)哩?”刘小兵老人安慰着他。
“在咱土城其他地方,住楼房,家里一旦老人亡故,都把灵堂设到殡仪馆,”花荣的大女婿说,“还是咱老石街好,平房小院,就还守着以前的传统,在家里设灵堂。”
“这倒让年轻人手足无措了,俺这些做晚辈的,虽也见识过无数次别人家老人的死亡,参加过无数次别人家老人的葬礼,但这种事儿摊到自己身上,还是一下慌得手足无措。”花荣二女儿接过去说,“别的不说吧,在参加别人丧礼时,是看到孝子都要穿白,但哪些人重孝,哪些人轻孝;重孝里哪些人须要穿上白大褂、白鞋,哪些人只须缠头、缠腰,还都安排不清。”
“是啊,稍不注意出了差错,又怕惹人笑话。”花荣小儿子说。
今天,从花荣老人倒头那一刻,穿衣、梳头、搬床、以及布置灵堂,都是在刘小兵老汉操持下进行的。刘小兵是街上百事通,他嘴上的白玉烟嘴,就是个信物,像武侠小说上丐帮的龙头拐杖,一代代传下来,不知道传了多少代。有懂玉的人说,那是一块清代玉,产于和田,羊脂白玉级。刚才,街上的人已经来吊唁过了。在丧礼上需要帮忙的人,也于几个小时前,在一起碰了头,分得了各自的任务。负责孝布的人,已经到集市上扯来孝布;负责请响器班儿的人,也赶去找揽头(响器班的领班)商量坐棚的事宜了;第二天负责去跟丧事人家亲戚朋友报丧的年轻人,也已经明确了自己须要去哪条街道,哪个小区,找哪个人,第二天一早就可以骑上车子,或搭上公交,奔赴目的地了。这一切,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不用说,都是刘小兵老汉的功劳。刘小兵老汉在老石街做百事通三十多年,这些事儿前后套路都在他肚子里装着。他闭着眼睛就能说清该先干啥后干啥,干哪件事儿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他在,大家心里就有了底。不会因漏了哪道程序让主家操心,也不会违背了哪道礼节让外人笑话。
人们都散去之后,刘小兵老汉吸了两窝烟,望着花荣老人的脸,望了老一阵儿,心里才确信眼前的老人的确仙去了。老人小他五岁,七十二了。他有些怅然,有些犯迷瞪,这种情况在他这一辈子里还从没有遇到过。让刘小兵感到奇怪的是,这几天不知为啥,街上一连仙去好几个老人。有老头,也有老太太,像商量好了一块儿上路。这一阵,可真忙坏了他。昨晚上,他是半夜才回到家。四天前,白老鸹女人故去了,昨天发的大丧。他前前后后照应了许多天。发送了老人,那家晚辈过意不去,非得留下他多喝几杯。他就喝了几杯,第二天半上午才爬起,头还有些昏沉。没想到刚过中午头儿,花荣老人的大儿子花援朝又到家里去找他了。
“伯,伯,我爹怕不行了哩。”
刘小兵扔了饭碗,急匆匆赶过来,老人已经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
“娃儿,先给你爹叫上几声!”他朝花援朝喊。
“大呀,大呀!”儿女们就趴在床边,呼天号地。
刘小兵望着这老伙计的脸,情不自禁低声说,你听到没,你娃儿叫你哩,你不要心带遗憾,孤单冷清上路哇。他等年轻人喊完后,情不自禁扑过去抓住老人的手,想再跟老人说两句话,可看看花荣老人,他分明连自己的儿子也认不得了。刘小兵老人缓缓站起来,接着,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你们给老人预备寿衣没?”他问。
“预备下了,俺爹住院时,就让俺们给他预备下了。”花荣大女儿说。
刘小兵趁老人身子还没有僵硬,跟家属一起把老衣给他顺顺利利穿上,然后,召集了老石街的老住户,把该做的事儿在天黑前都安排停当了,忙得满头大汗。
这个时候,街上人才忽然发现,这些日子,刘小兵老汉身边少了一个搭档。
在大家记忆里,从前老石街每逢老人去世,在葬礼上,小兵老汉身边总是还有另一个忙前忙后的老人的身影。许多容易疏漏的地方,他们总是在一起互相提醒;许多重要事体,他们也总是会凑在一块儿商量。大家想,如果有搭档在,小兵老汉今天也许就不会热得这样满头大汗了。
“刘伯伯,你往日搭档哪里去了哩?这些日子为什么都没有来给你帮忙呢?”开卡车跑运输的王文革说,“如果来了,别的不说,仅仅帮你把分配给大家的任务记在纸上,也省去很多头绪。”
“我的搭档?你说哩?”刘小兵反问了一句。
王文革让他问得愣了一下,其他人也想了一会儿,都哑然失笑了。他们这时候才想起来,原来从前那个总是跟小兵老汉一起为别人操持红白事儿的,正是今天仙去的花荣老人。
“花荣老人不是这大半年都病下了吗?他不是从那回住院后,就走不动路了吗?他怎么再跟小兵老人一起操持街上的白事儿哩?”菊仙拿着十字绣,穿针引线,跟人说。
“是啊,这些年在咱老石街,一到红白事儿上,总是离不开两位老人——刘小兵老汉跟花荣老人哩。”王宝贵的老婆拍拍菊仙的胳膊,“自从花荣伯病倒之后,为街上老去的人料理后事的重任,就都落在刘伯伯一个人身上了。”
今天,也许正因这位从前老伙伴的仙去,刘小兵老汉显得比平日更为伤感。他安排好一切,又默默到了灵堂,将明天亲友来吊唁时,孝子如何回礼,如何作揖磕头,种种细节安排一遍。这话他刚才其实已经叮咛许多遍了。他最后临走前不知是忘了刚才那茬儿还是不放心,又让领头的花援朝模拟丧礼上的种种场景,在他面前原样不动做了一遍,才放下心来。
在回家路上,刘小兵觉得自己真是一下老了。虽然,他早已知道自己步入晚年,可还从没有意识到已经这么大岁数,已经七十七了。常言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几年前没当回事儿,轻松过了七十三的坎儿。没想到今天,这坎儿却把这老伙计给绊住了。他从前觉得,自己还活早哩,自己这老伙计也还年轻着哩。
按说,人到了这个岁数,早不该再做街上的百事通。他早该赶紧“退休”,让年轻人来“接班”了。他嘴上那个祖传下来的白玉烟嘴,也早该交到年轻人手上了。其实,“退休”和找“接班人”的事儿他在头些年也都想过,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百事通虽然算不上什么官儿,可也不是平常人能担任的。他们除了主持红白事儿,一般还要负责处理老石街上的事儿。两口子闹矛盾啦,年轻人不孝顺啦,都可以来找他。他们处理老石街上的事情,先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在不行,训斥加恫吓,年轻人也没人敢不接受。所以,做百事通的,一般年龄要大些,资格要老些,得有一定威望。不然,说话没有分量,也就压不住场。另外,除了威信,还要有办事儿能力,做事要有条理,不能出乱子。
当然,街上也并不是没有合格的人选,但有能力者多在忙自己的事业,或做生意赚了钱,在高档小区里买了房子,或常年在外工作很少回来。他们没有时间干这份差事。前几年呢,街上倒有几个中年人跃跃欲试,可他们要么说话不利索,要么做事虎头蛇尾,总让人不放心。老石街的青年小伙子呢,资历又没哪个够。常言说“嘴上没毛,办事儿不牢”,大家不相信他们,他们发号施令也不会有人听。
他回到家,儿子爱忠已经给他花荣叔请好响器班子回来了。这让他松了口气,心里也舒服了许多。女人孩子们都已吃了饭,碗筷也已收拾干净,小饭桌上只摆着两副碗筷,一副是他的,一副是儿子的。小兵老汉洗了手脸,朝儿子瞥了一眼。他看出来,花荣老人的死给儿子带来的冲击也不小。
“爹,回来了。”
儿子在灯下坐着,一脸土灰,吸着烟,朝他招呼一声,又将脑袋埋下,不知心里念想着啥。
“嗯,嗯。”
他答应着走过来,想劝劝儿子,又没有劝,因为,他觉得劝也是白劝。
“你把响器班给你花荣叔找下了哩?”他拿起筷子问。
“你放心吧爹,我咋会不上心?”儿子抬起头说。
他想,儿子到了这个年龄,四十多岁的人,是该明白一个人的仙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了。他点点头,吸一口面条儿,粗大的喉结滚动着,贪婪地吞咽。
“你注意到没?咱老石街上最近这几次丧礼,我都有意给你安排下一两桩重要的事项。要么去请响器班儿,要么去裁孝布,要么领几个壮年劳力,去林上打坟启坑,为啥?”他埋着头问儿子。
“我咋会不知道,我傻哩?”儿子不屑于回答他。
“这一切虽看上去也没啥,可千万不要小看,每一项想要办好,既需要口才,又需要统筹安排能力和协调能力。哪一方面稍有闪失,不用心或者用心却出了纰漏,就办不圆满。”他把一大碗面条喝完,额头上渗出明晃晃的汗粒儿。
这些年,刘小兵都在有意培养儿子这方面的办事能力,他是有意要把那个白玉烟嘴在将来传给儿子刘爱忠的。刘小兵老汉觉得,这并不能算是私心,古人不也说过“举贤不避亲”的话吗?他觉得,现在如果从街上给自己谋划个接班人的话,自己的儿子刘爱忠是再合适不过了。论岁数,爱忠已经四十挂零,有了应有的威信和阅历;论能力,刘小兵老汉觉得儿子的脑瓜比自己还要好使。从这几次丧礼上他安排的活计来看,儿子完成得都还圆满。当然,儿子的本事还远远没有达到能独立主持红白事儿上种种事务的程度。
刘小兵老人通过自己这几十年从事这行当的经验觉得,其实,要做好这工作,光有威信和能力,还是不行;除此之外,还要真正喜欢它。
“人家怎么看你不要管,你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份活计看得重器些,不能自轻自贱,不能妄自菲薄。要不然,做下去还有啥意思哩?”他拿出一根烟,安在白玉烟嘴里,也扔给儿子一根,“比方说葬礼吧,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对于亡人家属来说,它就是把一个没有知觉的人送到一个没有知觉的世界。但,对百事通呢?却不是这样。你要把它从心里当成搭救亡人的一种神圣方式。这样一来,你从事的就是一份跟灵魂最为接近的工作了。”
“爹,这样的话你说了多少次了哩?”儿子也把烟点上,“我不懂这个道理,能跟着你?”
刘小兵朝儿子望了一眼,点点头,心想,儿子变了,年过四十的人,就是跟小年轻不一样。刘小兵老汉常常口中这样喃喃着,心里这样盘算:一个鲜嫩的孩娃儿落地的时候,人们是多么重器,多么欢欣哪;一个劳碌终生的老人故去时,又怎能那样潦草哩?想想,那些亡人,大部分是都活了长长一辈子的。又多是努力了一辈子挣扎了一辈子都没有改变命运,甚至没有脱离贫寒,这样草芥一样一辈子被轻贱着,踩踏着。到了仙去这天,长长的一辈子都干了些啥,几句话就概括完了。生在何时,死在何时,供养了几个儿女,诸如此类。如果是鳏夫,省略中间成家和抚养儿女的内容,就更简单些。
是啊,街上这些老人,有谁干过啥辉煌的事迹哩?有过辉煌事迹,也就不用再在街上呆着了。一辈子这样简单,这样寡淡稀松,一旦仙去之后,如果再草草埋了,草草入土,那就真是一件庄重的事儿也没经历过了。这样一来,这一辈子过得也太没滋没味了,这一辈子也就几乎不能算活了一回人,几乎要跟个啥动物没甚分别了。
“我看电视时留意过,人家外国人亡故时,都要有牧师在场,都是要请牧师祷告;我们土城的那一条清镇街,住着的都是穆斯林,死后也要请阿訇诵《古兰经》,入殓的程序独特、繁琐而讲究。”刘小兵今天看着儿子的变化,由衷欢喜,话也就变得多起来,“你瞅瞅,咱这老石街上,住着的都是汉人。我们汉人原本就重生轻死,在对待亡人问题上,一向不甚庄重;这些年移风易俗,就越发应付而草率。这怎能行呢?这怎能行呢?”
“爹,在丧礼仪式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我一个帮忙的人不能眼泪巴嚓,但我每回从仪式上回来,心里都难受得吃不下饭。”儿子瞅着爹,接过去说,“好在,街上还有人记着祖辈们传下来的这些规矩,还有人专门儿操持着这些事儿。”
“你是这样想的吗?你是真的这样想吗?”刘小兵惊讶地望着儿子,一连声问道。
“爹,你没瞧见咱土城其他那些街上,老人是咋走的吗?在那鸽子窝一样的楼上住着,病下了,住院了。病得不行之后,蹬腿死了。人死了往哪儿送哩?回家吗?回家设灵堂吗?一个楼道里嫌哩,一个小区里嫌哩。不要说设灵堂,就是门上贴个草纸剪成的符,一个楼里的人看见,也说害怕呀,膈应呀啥的。爹,你再看我们老石街,在你的主持下,轰轰烈烈地举行一场葬礼,好歹让这些几乎让人忘记了许久的老人都还算体面地去了,还算带着尊严地走了。老石街人好福气哩!爹,我真想不到,如果没有了这些规矩,没有了你这样的人,往殡仪馆一送,那些吝啬的、不孝的、图省事儿的子孙,将会如何把仙去的老人的骨殖草草处置呢?”儿子动情地说。
“你成了,孩儿啊,你成了。”爹说,“你这四十多年的饭,没有白吃。”
这天晚饭,刘小兵老汉是只喝了一碗面条儿。也许是心事重重的缘故,儿子在他面前坐着,只吃了一块饼,连粥也没喝。刘小兵高兴地放下饭碗,不由多看了儿子几眼,不能不说,儿子今天的话让刘小兵老汉由衷欢喜。看那样子,儿子到现在,总算真正理解了百事通这个行当。刘小兵不禁心想,早知如此,前几年就该让儿子渐渐参与这项工作,如果从那时开始学,到现在也许已经能够接过他肩上的担子,接过那个白玉烟嘴,胜任这项工作;至少应该能够独当一面了。
这事儿也后悔不得。
他记得,前几年呢,一方面是自己疏忽,另一方面也是儿子爱忠自己不愿学。那时,儿子还年轻,孙子孙女也小。为了可以放开手脚干这个,小兵老汉跟他们分了家。他当时说,老母鸡该撇窝了。这些年,儿子的两个孩子都是他们自己带大的,家里所有家当也都是他们小两口自己挣的。想想这些,小兵老汉还真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们。当面显不出啥,背后,他也曾听到过儿媳的抱怨。诸如:“人家的爹,都帮着自家儿子看孩子,我们这个爹倒好,什么也不管不问。”
那些年,他有几次也曾暗示要把这行当传给儿子,儿媳却说:
“土城土城,你还以为要这样一直土下去哩?老石街早晚拆迁,到时,都住了楼,谁家老了人,会去请百事通?再说,干那有啥好啊?耽误自家事不说,有时候还出力不讨好。”
刘小兵老汉刚想分辩,儿子又接过去说:“你说破嘴唇,我不干哩,干那啥意思?安排安排迎来送往、茶水烟酒,在桌子前记记账,也就相当于个宫里的太监总管吧?”
那次,儿子一句话噎得小兵老汉愣了半天。
今天,儿子的变化,让刘小兵老汉心里很是欢喜。
第二天一早,雪白的引魂幡是在亡人家院里挂起来了。院墙外一处空地上,几个男人正在那里忙活。把地用铁锨铲平,再铺上一层金黄新土,用脚挨边儿踩,踩得结实平展。四个角里呢?各挖一个坑,栽上四根粗细长短相当的棍子,棍上绑横杆,上面再搭席子。不用说,这就是将来响器班儿里的响手们坐棚的场所了。这棚是儿子监视着搭好的,棚子搭好,小兵老汉走过去看了看。地上的土摊得平展,踩得结实;四根棍子不知从哪家找来,一般粗细,摸上去光滑顺溜,连个疤都没有;上头席子也崭新崭新,还散发着高粱秸秆的味道。刘小兵站在那里,将那白玉烟嘴从口袋里掏出,在手里摩挲着,再摸出一根烟,装上。儿子的细心让他颇满意。他吸着烟,望着正指挥着众人安放八仙桌子和椅子的儿子,暗暗点了点头。
这些收拾停当,接下来便单等响手进老石街了。
从前,土城的老规矩,老人仙去之后,是讲究热热闹闹吹打三天三夜,方可入土。这些年,其他地方都简化了,只有老石街还坚持,用许多人的说法,顽固不化哩。三天里,最重要的项目是第二天傍晚送盘缠和第三天大殓,中间便是守灵、跪拜及吃饭时的谢客、回礼。一般情况,响器班是当天下午或第二天一早便到。如果老人在夜间仙去,一般天亮之后当天下午响器班即到;如果老人是白天仙去的,响器班来的时间则是第二天早上。响器班在进家之前,一般是在街口张扬老号两到三声,算是给事东家报信儿。东家听到老号的声音,便会由百事通引领,到街口叩谢响手,然后将他们接迎家中。
这天,棚搭好没大会儿,老号便响了。刘小兵老汉手里拿一张草席,引众孝子到老石街口,准备接迎响手。远远地,老汉就看见几个响手带着家把事儿站在那里。让他吃惊的是,来的并不是从前常请的响器班子“福寿昌”,而是赵四的一伙人。刘小兵老汉若无其事,先朝响手们作个揖,然后,将草席铺地上,让众孝子给响手们行了三拜三叩大礼。赵四代表响器班回礼之后,端起大号又张扬三声,代表三天坐棚正式开始。
这样,礼数便尽到了。众人浩浩荡荡地领着响器班儿朝家里回,小兵老汉边走心里边犯起了嘀咕:“刘爱忠啊刘爱忠,你这是想干啥哩?你肚里装的啥心思哩?!”
响器班子是儿子爱忠昨天去定下的,回来之后,也并没有跟他交待定了哪家。其实,土城一共有两家响器班儿,福寿昌是一家老字号,赵四那帮人呢,则是最近几年才拉起来的。他们的差别,土城一般人却并不了解。在普通人眼里,反而是赵四这班人马显得更专业,更气派。他们都统一穿着镶着金边的白衣白裤,吹打的乐器哩,也不拘于唢呐锣鼓。他们啥乐器都有,什么电子琴、电吉他、萨克斯、架子鼓之类。如果事东家加钱,还可以增加歌舞表演,甚至脱衣舞表演。他们弄得热闹,动静大;再加上两家响器班儿收钱一样,都是一天七百,三天两千。所以,一般人家,倒是愿意请赵四。
别人看不出啥,不等于小兵老汉不明白里边的小九九。刘小兵老人知道,要说有板有眼,正规正统,还要数老字号“福寿昌”。从头几年看,整个土城,也都是“福寿昌”天下。后来,赵四成立了唢呐班,为了跟“福寿昌”抢生意,只要哪里百事通去找他们,他们一律给一百块钱提成。所以,他们的生意竟然也渐渐好起来。在这之前几个老人葬礼上,刘小兵老汉也曾安排儿子干过这个活计,儿子都是老老实实请了“福寿昌”师傅们。这次儿子咋会自作主张,忽然换了赵四那帮人呢?不用说,是贪图人家给的那一百块钱。这一下,刘小兵老汉才算弄明白儿子昨天晚饭时说话讨好他的真正含义了。当时,老汉还以为他是为亡人的故去而伤心,还以为他活明白了哩,原来是偷偷做了亏心事儿啊。
刘小兵老汉引领着响器班儿到了事东家里,把一切都安排停当,在账房找着儿子刘爱忠。他朝儿子招招手,让他出来,接着转身在前头走,把他领到一个僻静处,开口问:
“你花荣叔做了一辈子百事通,仙去之后却让你这个猴儿给耍了!你说说,你咋能欺哄你花荣叔哩?”
“爹,有些话我昨晚其实就想说,只是忍着。人家都跟我说,百事通,那可是个肥缺,权力大得很!红白事儿上,用哪家喇叭,用哪家布,用哪家厨子,全是他说了算。其实,用谁不是用?要不给点儿回扣,干嘛要用你的?”儿子似乎早就料到爹会说这话,也没心虚的意思,直直望着他,“现在都兴这个,有的给钱,不给钱的话,多少也要送些东西。一条烟、一箱酒,多少都意思意思。爹,你做这些年百事通,都赚到了啥?别说钱,别说烟、酒,连包饼干也没见你往家给孩娃儿带回来过。”
刘小兵衔着白玉烟嘴,将烟一根接一根吸,从始至终没打断儿子。他听了儿子的话,一颗心掉进冰窖。昨天晚上还一心想把自己肩上的担子卸给儿子,那在当时看来已颇为成熟的计划,这一刻又如受潮的糖塔般,顷刻间坍塌在地。儿子话让他心里充满怒气。他心里说,我刘小兵咋就生出这样个不肖之子哩?奇怪得很,儿子的话又分明让他惭愧得要命,那感觉似乎自己真的做了对不起家人的事儿。他呆望着儿子,望着这个四十多岁、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再想想,儿子的话虽然也有道理,可是,老石街上的百事通一辈辈传下来,这洁白通透的白玉烟嘴一代代传下来,啥时候听说哪个百事通收过事东家一分一文?不管是料理红白喜事儿,还是为谁家调解纠纷,甚至分家清帐,从没听说过哪一辈的百事通克扣过人家的钱财,或者收过人家的调解费。如果那样,老石街还要你干啥哩?你还咋在人面前活人哩?
“别的地方的百事通,比如丧事上需要买菜吧,首先定好了厨子。用谁,谁就得稍有表示;不表示?对不起,换另一家。定好厨子呢?你领厨子去采购鱼、肉、蔬菜。这些东西用谁家的,还是你当家,还能再捞一层好处……”
刘小兵老汉听着儿子的话,额头上已涔出汗来。他干了一辈子百事通,这个行当里的所有猫腻,他了解得比谁都清。据他了解,儿子说的这种人的确有,可哪个行当里没几个败类呢?如果所有人都照那样去学,这个行当传下去还有啥意思?
“你别说了!”他训斥道。
“爹,你不捞,不等于别人不捞。每次红白事儿,厨子你都用王秀峰,买肉买菜都让他一人办。你不从中间捞好处,你能保证他不从中间捞好处?”
如果这时不是有一人恰巧过来问他供品摆放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小兵老汉真不知自己跟儿子还要吵到什么时候。小兵老汉赶过去时,供品摆好了,谢天谢地,位置顺序也恰合要求。可让人不安的是,分管这项工作的人却把一双筷子插在了猪肚子上。按照规矩,那双筷子应该交叉着从猪的嘴巴里穿过才对。小兵老汉赶紧调整过来,站在那里,不由嘟囔一句:“老哥哥,你早就看出来错了吧?”说完,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是啊,任谁的丧礼上出差错,也不该在花荣老人的葬礼上出差错。想想,还有谁比他对红白事儿上的每个程序、每个细节更了如指掌呢?
刘小兵想,如果在从前,如果有个帮手在身旁,供桌上就绝不会出现像刚才这样的闪失。这样想的时候,刘小兵老汉又有些想笑自己了。他问自己,你的帮手呢?眼下仙去的不就是你从前最好的搭档吗?眼下举行的这场葬礼,不就是为花荣老人布置的吗?
这些年,刘小兵老人心里明白,要说祖上传下来的礼数跟规矩,花荣老人其实比自己安排得还清。那么繁复驳杂,算起来也足有上百条吧,可随便问起哪一条,人家张口就来,就像说自己身上哪儿有个痦子,哪里有条疤痕一样。在无数次红白喜事儿上,什么样的亲戚吃饭时该用几个碟子几个碗儿,孝子谢客的时候响手们该吹奏哪个曲牌儿,花荣老人都事先安排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做百事通的小兵老汉亲自过问。再加上花荣老人心又细,礼金多少,花销多少,每项支出都在什么地方,他丢开账本儿都能说得清清楚楚。一场白事儿下来,小兵老汉绝不用担心因为账目不清落下主人的埋怨。
刘小兵老汉记得,花荣兄弟不止一次跟他暗示过,想把那个白玉烟嘴接过去,想接过他肩上的担子。我毕竟比你年轻几岁,花荣老汉说,能为这老石街多做几年。刘小兵知道,花荣兄弟是真正喜欢这个行当,真正喜欢。刘小兵想到这又叹口气,心里说,老人已殁了,还想这些干啥哩?再想也是过去的事儿了。再想,人也活不过来了。眼下最重要的,便是在这场葬礼上盯紧些,不要因为不合礼数让外人笑话;也不要因为糊里糊涂的账目让亡人的后辈们心里不痛快。
也许是儿子那一席话,让刘小兵老汉几乎要疑心今天葬礼上帮忙的所有人都是贼,都要耍奸偷滑。他首先到厨房,大厨王秀峰已经大致采买齐了几天需要的鱼、肉、蛋及各种蔬菜,正蹲那里给鸡鸭拔毛开膛。若从前,刘小兵老汉看看就算了,今天,他不但上前亲手验看鱼是否活着,肉是否新鲜,还要王秀峰拿过账本一一过目。询问东西都是买哪家的,人家要价多少,最后以什么价格成交等。等几个出门报丧的年轻人回来了,他又问人家到了报信那家,是否喝了人家的茶水,吸了人家的烟,吃了人家的饭。
这样事事亲力亲为,劳心劳力的地方比平日几乎多一倍。再加上亡人亲戚朋友来吊唁的多,年轻人处处都要向他询问,事事都要等他定夺。忙活到第二天傍晚,临着送盘缠烧纸马时,他已经累得有些气喘嘘嘘了。
土城风俗,在亡人仙去后第二天傍晚,要由亡人长子抱着灵位(或由老人的一件棉袄代替),呼唤着亡人,小声祷告着,去老石街和中后巷交叉路口焚烧纸钱,叫做“送盘缠”。送盘缠时,长子在前,后面还要跟着所有直属男丁。纸钱焚烧过后,画一个圆圈儿,表示财不外溢,接下来才是烧纸马或纸牛(马还是牛依亡人性别而定,男骑马,女骑牛)。
在这过程中,重孝男丁一律白衣、白鞋,儿子、孙子未结婚的,只需缠头。缠头是用一束白布缠裹在头上,然后挽个结儿。这过程虽简单,但在挽结上也有一定讲究。一般,如果去世的是男丁,就结左边;如果是女丁,就结右边。如果两个老人都已过世了呢,那就把结打在额头正中央。
在送完盘缠,孝子们都要回灵堂的时候,刘小兵老汉忽然发现,花荣老人的孙子竟在额前正中央挽了一个结。这就不对了,小兵老汉心里叫着,花荣老人老伴儿还在,老嫂子身体还硬朗得很哩,咋能打在正中间哩?天哩,天哩,忙活了两天,唯恐哪儿出现差错,最后还是在这细节上闹了个大笑话。刘小兵老汉脸上一热,汗就淌下来了。他知道,虽然当时也不一定会有人看到,看到也未必能看出毛病;但只要碰巧有一个懂行的在,日后传出就成了人家说笑的话柄儿。
刘小兵紧走几步,过去一把便把孩子头上的结扭了过来。在喧闹的队伍里,并没人注意到这个。可是因这差错,刘小兵老汉还是像被什么一下子击垮了。送了盘缠,烧了纸马,回去时,他的脚步几乎拖拉不动了。
百事通这个行当不好干啊!刘小兵老汉记得,花荣老人在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跟他说:“咱们这个行当,事情处理再好,也不能收人家一分钱;事情没处理好,事主背后还要说你没本事。”
这是花荣老人的心里话,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心声呢?
葬礼第三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繁忙、最紧张的。
这天,要大殓,要送殡,中间的摔盆子、起棺,礼数最为繁复,看热闹的人也最多,哪一项干得不利落都会让人笑话。
傍晚时,在土城郊外三十多里的那个墓园,花荣老人的骨殖终于埋入土里,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坟丘。刘小兵站在老伙计坟前,觉得有些眩晕,似乎腔子里的东西都被掏空了。这几天里,他觉得不只是把花荣老汉葬了,也把自己葬了一回。几天来的情景又像撕扯不断的碎片,在他脑中慢慢拼凑在一起。这几天的许多事情,让他觉着真是无法言说,也言说不清。
他叹口气,又想起这天的一件事儿来。在他为亡者大殓时,当着家属的面,他恭恭敬敬地在棺底铺了褥子,然后小心翼翼移金,即把老人的骨灰盒移入棺中,最后给老人骨灰盒盖了被子。他做完这些,略微愣了一愣,又从衣兜里掏出那个白玉烟嘴,双手捏着两端,恭恭敬敬地放在了老人的骨灰盒边。
“伯,你……”站在一旁的花援朝住了哭声,有些惊讶,泪眼吧嚓地望着他。
“这烟嘴我早打算好了传给你爹,可惜他走得早了。”
刘小兵说完用双手捂了脸,揉搓几下,不忍心看人钉钉子,踱到一旁。
他站在人群里,听着葬礼的尾声发出的杂乱声响。他看见身边的几个年轻人一边吸着烟,一边嬉皮笑脸地说着啥。这几个年轻娃,因为刚下学,刘小兵老汉还有些闹不清他们的爹是谁,爷爷又是谁。他想骂他们,想在人群里大吼一声,喝来他们的大人,把他们领回家去,好好地管教。可是,愣了一会儿,他却只是叹了口气,说了那样一句话:
“我们两个已走了一个,早晚我也得走,你们这些后生要跟着学啊!否则,以后老石街上事儿,谁来管哩?”
太阳黄黄地挂在西天,野地里风忽然大起来,吹得烧尽的纸灰黑蝴蝶一样在半空里飘。响器班的响手们是在棺材刚一入穴、亲人刚一爆发出撕心裂肺哭号的那一刻,就收起家把事儿,骑上摩托车离开了。花花绿绿的纸器燃尽,看热闹的女人跟孩子们也悻悻而去。林子里一下子静寂了许多。刘小兵老汉等在那里,他是在孝子们都走尽之后,最后一个离开的。他走的时候,风更大了。他从兜儿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用半块石头压在花荣老人坟头儿上。他拍打拍打身上的土,团了身子,弓着腰把头往风里扎。
刘小兵是半年之后老了的,也许几个月前,在花荣老汉故去的时候,他就预感到自己不行了。他得的是那种老石街人称为“孬病”的毛病,在市人民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后又转到省立医院。他死活不做手术,不让医生用刀划拉他肚子,坚持让儿子把个囫囵身子拉回老石街。他回到老石街两个月之后,走了。
在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的精神又忽然好起来,喘气也足,还喝了一碗南瓜粥。
“那个白玉烟嘴呢。”儿子刘爱忠接过碗来问他。
“你别做梦了,那东西还轮不上你!”刘小兵老汉道。
“我那天在街上走,正巧碰上花援朝站在街边跟人说话,咋仿佛看见他嘴上衔着个白玉的烟嘴哩?”刘爱忠说。
- 四川文学的其它文章
- 我的名字叫叶星河
- 蒲阳:凌云壮志从此飞
- 活在漫写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