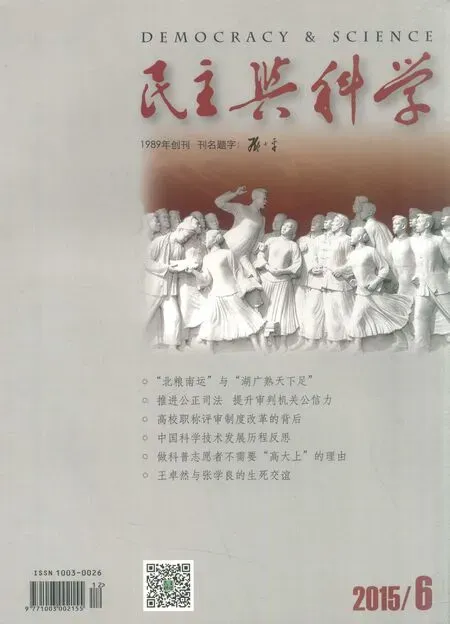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反思
■ 熊卫民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1949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教育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林可胜、吴宪离开了大陆,但大多数有选择机会的院士、所长、校长、名教授以及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大陆的科学家、教授留了下来。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人员,也在随后几年成百上千回到中国大陆。以这些人才为基础,在苏联帮助下,共产党发挥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迅速设计了新的科学发展道路,组建新的科研教育机构,改造、培养了不少人才,对科学技术研究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在短时间内从整体上得到较大提升,为国防、工业、农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建立大量科研机构,制定发展规划或目标,投入大量人员和资金,集中力量“向科学进军”之后,尽管有政治运动、长篇累牍的会议、下放劳动等干扰,尽管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造成很大浪费,但确实办了一些大事,主要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
第一,对自然资源的考察。摸清地形、水文、矿藏、土壤、气象、动植物、地震等基本资料,直接影响到城市、道路、水坝、工厂等的规划、选址、设计等,是全国各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前提。这项工作是民国时期基本资料收集工作的继续,但其规模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拿地质勘探来说,1949年前,“全国的地质工作人员总共不满200人,而到1955年,从事地质勘察的职工发展到17万人,其中高等学校毕业的地质工作者达6000余人”。(摘自许良英、范岱年《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地质部、冶金部、煤炭部、化工部、铁道部、交通部、石油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等多个机构均组织了自己的自然资源考察队伍。在这些队伍中,中国科学院的资源考察工作是比较突出的。它于1956年1月1日成立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下辖多支长期或临时考察队,包括“文革”时期在内,每年组织多支大型考察队,派出上千位科技人员到野外进行各种考察。“以1959年为例,中科院当年有近2500人参加工作,考察经费达600万元”。(摘自张九辰《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
巨大投入带来丰硕成果。考察队发现了克拉玛依、大庆、胜利等油田,使国家石油能够自给;在蒲魁堂、金银寨等地发现多个铀矿,为原子弹研究和原子能开发准备了材料;在海南、云南、广东等地找到三叶橡胶宜林地并提出开发方案,为从无到有发展橡胶产业打下良好基础。在煤、铁、锰、铜、钨、铅、锌、钒、钛、盐、稀土矿等方面也有重要发现,考察队绘制出全国不同比例的地层表、大地构造图、地质图、地形图、土壤图等;出版了《中国各断代地层总结》《中国各门类化石》《中国的黄土》等专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等的编撰也有重大进展。通过对考察资料进行研究,刘东生等人创立黄土学,黄汲清等人发展出多旋回构造运动说,施雅风等人发展出冰川学……
第二,国防军工研究。中国人历来好面子,长期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天朝大国”,可1840年以来,经历的却是长达百年的屈辱。如何迅速使国家强大起来,恢复汉唐时期的国际地位,是中国人尤其是领导人的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朝鲜战争,让人们看到先进武器对于现代战争和国家地位的关键作用。于是,发展国防军工研究,成为中国科研布局的重中之重。1956年前后,中央领导人部署了原子弹、导弹研制任务。在1956年夏天制定的十二年规划中,有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四大紧急措施”,主要是为了两弹研究而服务的。国防科委和中科院很快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并从其他机构抽调人才。在中央坚强领导下(先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抓两弹研究;1962年成立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其他成员为7名副总理和7名部长级干部为委员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1965年后,这个委员会还兼管导弹),借助苏联帮助,主要依靠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程开甲等一大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科学家的努力奋斗,经过几年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研发,终于在1964年6月和10月,导弹和原子弹分别获得初步成功,并在随后一些年取得更大进展。在部署原子弹、导弹研究之后几年,中国又部署人造地球卫星、氢弹的研制工作,在赵九章、姚桐斌、于敏等科学家主持下,这两项同样不计成本的研究,分别于1967年6月、1970年4月取得成功。后来,原子弹、氢弹这两种核弹和导弹、卫星的研制工作被统称为“两弹一星”。与此同时,在军用飞机、舰艇、坦克、火炮、死光等常规武器的研制方面,中国也部署很大力量并取得一定成效。
第三,工业、农业、医疗、交通、水利等相关研究。19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个比较先进的大型项目,之后,中国自行仿照建设了一些新项目,使得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尽管整条整条生产线都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但是,在工业原料制备(如矿物的勘探、选矿、冶炼、提纯)、生产技术改进、农业生产发展、医疗卫生提高等方面,还是给科学技术研究提出一些问题。于是,在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规划中,国家部署多项民用重大科研项目。可惜的是,不久之后,由于“大跃进”运动失败所导致的国家经济极端困难,除两弹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四大紧急措施”研究,其他项目都不得不紧缩。由于没有得到足够投资,这些民用项目完成情况不佳。其中一些又出现在1962年制定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第二个规划执行不久,又受到“四清”“文革”等运动严重冲击,致使其完成状况更差。
尽管投入不足、执行不力,遭遇许多不利因素影响,但由于成立了机构,安排了科技人员,经过二三十年时间,国家在这些民用领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譬如,袁隆平等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李振声等对杂交小麦的研究,曾呈奎等对海带栽培技术的研究,朱洗对家鱼人工繁殖的研究,马世骏等对东亚飞蝗生态生理的研究,屠呦呦等对抗疟药物青蒿素的研究,张亭栋等对白血病治疗药物三氧化二砷的研究,沈善炯等对金霉素生产技术的研究,汤飞凡等对沙眼衣原体的研究,葛庭燧对金属内耗的研究,叶渚沛等对氧气吹炼转炉炼钢铁技术的研究,徐光宪等对稀土冶炼技术的研究,周望岳等对顺丁橡胶工业生产新技术的研究,沈鸿等对万吨水压机的研制,成就都相当突出。此外,科技专家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刘家峡水电站建设、高压输电线路研制、汽车制造、民用飞机制造、化肥生产、血吸虫防治等方面也取得了成果。
第四,基础研究。由于新政权批判“为科学而科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研究地位相当尴尬,在政治运动中不时受到冲击。但真正的科学家对于认识自然、发展基础研究总会有一定兴趣,而国家领导人也并不是那么短视(譬如周恩来是了解基础研究价值的,1956年组织制定十二年规划时他提出要增加对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1972年给周培源、朱光亚等写信时,他又要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把基础研究抓起来),主管意识形态、强调政治挂帅的领导人有时会重视某些基础研究的宣传意义,所以,基础研究还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在所取得的著名成果中,由国家组织多个机构大批科技人员协作攻关的有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等,由科学家个人主导而完成的有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吴文俊的示性类及示嵌类研究,秦仁昌的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研究,邹承鲁的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邹冈的吗啡镇痛作用部位及镇痛机制研究,叶笃正、顾震潮的东亚大气环流研究等。
有了不错开局,一度让科技工作者十分振奋并确实缩小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就形势陡转,科学家普遍受到肉体或精神折磨,中国科学和国际水平的差距又被迅速拉大。
实际领导各科学技术单位的大部分人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外行,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更正确,敢于对不懂的科学技术工作指手画脚。在1958年中央强调党对科学技术的绝对领导后,这些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更是一竿子插到底,罔顾科学规律,大搞所谓科技大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导致极大的浪费和破坏。
中央制定过一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策,但是,政治运动和一些错误政策又压制前一类政策发挥其效能。邹承鲁曾回忆说:
那时候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说我国研究所中的人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努力工作、有成果的人;一类是混混时间,没什么成果,但至少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人;第三类是自己不做事,专门给做事的人捣乱的人。第一类和第三类抵消,第二类不起作用,所以研究所没有前途。
……
我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只有大约1/3的时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而且,能工作的时间也是不连续的。你刚开始做一个工作,又搞了一个运动,工作又得都停下来,后来又只得重新开始。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摘自熊卫民《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访邹承鲁院士》)
在科学家中,邹承鲁的经历是比较典型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业务工作,中国科学家当然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在所有错误科技路线、方针、政策中,影响最坏的是“大跃进”期间颁布的“我国科学工作的道路”以及“文革”初期得到阐述的“毛主席的革命科研路线”。其核心是边缘化专家,直接发动群众破除对外国、对专家、对书本的“迷信”,“土洋”并举,“海阔天空的想,势如破竹的干”,大搞所谓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全党全民办科学”,把执行主体换成科学素养不够的普通群众。在大轰大嗡气氛之中,这些“研究”很快就变成不顾或不知道客观规律的空想、妄想、胡干、蛮干。例如,在大炼钢铁浪潮中,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提出用土法炼铝,全国有200多个单位前来学习并纷纷推广。但事实上那个方法根本就行不通,早在50多年前就已从科学上证明了那一点。邹元燨等专家知道那个常识,他们也私下向相关管理者说明过情况,但他们已被边缘化,他们的意见没人听。(摘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大炼钢铁”本身也是不顾客观规律的蛮干。不说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矿对生态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只论发动群众所建立起来的那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就非常不科学,在那样非常简陋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炼出合格的钢来。(摘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如1960年推广的“超声波”技术。发动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推广,从养猪、建澡堂到合成胰岛素,什么领域都要求实现“超声波化”。没有那么多的超声波设备,就用土办法来搞超声波。轰轰烈烈搞了几个月,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只能不了了之。(摘自熊卫民《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
科技体制强调党的领导、中央集权。这种体制效率很高,做出规划和决策之后,能够迅速建立机构、购买设备、组织人员集中力量向某个方向进军。如果决策正确,领导尊重和信任科学家,给科学家一定自由,放手让他们去主持,也能干出一些成绩,譬如“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可问题是,没有经过专家论证、民主决策,很容易有考虑不周之处。而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出于无知或私心,各级领导很难完全杜绝瞎指挥或打击报复现象,因而未必能让科技工作者心情愉快。在不能满足其独立、自由、自主的要求,不能给予承认、尊严和成就感的环境中,他们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毛泽东时代,中国确实集中力量完成了一些目标明确、基本手段具备的工程性科研工作,但也应当注意到,更多花了巨量资金的大协作项目、攻关项目是失败或没有显著成果的。而陈景润、邹承鲁等人获得国际赞誉的理论研究,是热爱科学的人士在设法获得一定自由空间后私下探索的结果。二战后出国留学的人,很多曾追随诺贝尔奖得主在国际一流实验室学习,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做出国际一流或接近国际一流的工作。回国之后,这些接近国际一流的人才被集中起来办大事,在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情况下,却并未做出多少国际一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