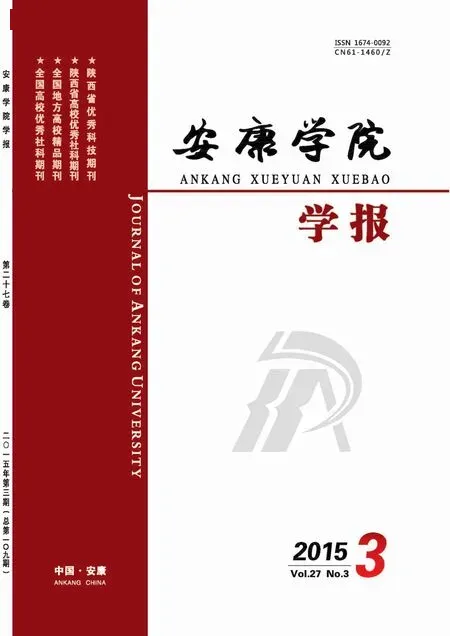从“碧瓦初寒外”看宇文所安解读《原诗》之不足
潘伟利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美国汉学研究专家宇文所安先生所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自2003年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著名学者乐黛云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该书也并非尽善尽美,如在第十一章《原诗》中,关于杜诗“碧瓦初寒外”一句的分析和解读,似有不妥之处。
关于诗歌创作的对象,叶燮认为“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颐,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1]20。“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1]23。此后,叶燮便设置了一个对话者,对自己的理论提出不同意见,对话者称“而语于诗,则情之一言,义故不义,而理与事,似与诗之义未为切要也”[1]29,“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见诸事者;若夫诗,则理尚不可执,又焉能一一征之实事者乎!而先生断断焉必以理事二者与情同律乎诗,不使有毫发之或离,愚窃惑焉!此何也?”[1]30该对话者认为叶燮的理论不适用于诗歌,认为“理”不是诗歌本质的一部分。叶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子之言诚是也。子所以称诗者,深有得乎诗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1]23为此,他举杜甫的四句诗为例。其中,《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中“碧瓦初寒外”一句着力最多。宇文所安在其书中用了较大篇幅对此句进行解读。本文对作者解读此句时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旨在促成共同探讨。
一、对诘问之语的误读
叶燮举杜诗为例进行说理:“今试举杜甫集中一二名句,为子晰之而剖之,以见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1]30
此段之后,宇文所安解读称“对该诗我们没有任何固定看法,正如叶燮所说,我们不知道它是近还是远。”[2]593宇文所安并没有充分理解叶燮的意思,这里叶燮是以问句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叶燮认为提出此类问题的人不懂得审美,不懂得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试举一例,如“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杜甫“碧瓦初寒外”的误解,因为杜甫是说碧瓦没有受到初寒的影响,而提问者却是问碧瓦之外为何没有初寒。关于这一点,张文勋先生有过专门论述。他说“这些都是叶燮以设问的方式归纳的一些诘问。他认为如果照这样‘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懂得文学的艺术特征,所以才会提出这些问题。”[3]即叶燮认为这些问题是外行话,是“俗儒”之谈,更不屑于去回答。接下来的“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固非庸凡人可摹拟而得也”,才是叶燮本人观点的正面表达。
因宇文先生没能充分理解叶燮以问句表达出的观点,做出了其书中关于“写近乎,写远乎”的不当解读。即宇文所安认为是叶燮观点的语句,其实不是,它是叶燮以问句的形式所列出的反面观点。
二、对诗歌指代的忽视
汉语诗歌作为数千年中华文化孕育出的精华,具有许多其他民族诗歌所不具备的特点。尤其是古典格律诗,其在描摹自然、表情达意、意境营造等艺术表现方面手法各异,需读者反复吟咏、细细揣摩方能体悟诗人用心,必要时还要参考他人评点。汉语语言,尤其是古代汉语语言,更以其词性多变、词序无常、修辞多样的特点,使得汉语诗歌更加耐人寻味。
关于杜诗中“碧瓦”一词,不管是叶燮还是宇文所安都没有对其具体意义和所指进行专门解释。在宇文先生的书中,尤其是第593页的行文论述中,可以发现,在宇文先生看来,此处的“碧瓦”就是实实在在的碧瓦,即瓦就是瓦,不包含其他物象在里面。同时,也没能在其书中找到有关“碧瓦”的其他解释。假如是这样的话,试问本诗并非“咏瓦诗”,杜甫为何在此处专门写瓦,其用意是什么?讲“瓦”在初寒外,那这庙中其他的东西都在“初寒”之内了吗?比如说下文提到的“金茎”、“绣户”。为何要单单强调这瓦的独特,而置庙中其他物象于不顾?且“瓦”仅限于房顶上一个面,其所占空间并不大,单就屋顶而言其下还有房梁、房椽,为何仅有“碧瓦”在初寒外。这与诗人去拜谒的老子庙比起来,似是喧宾夺主。
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此处的碧瓦是汉语修辞中的指代用法,在这里用来指代老子庙。这种修辞在古典诗歌中并不少见,即便在此诗中亦不止此一处。该诗首句“配极玄都閟,凭虚禁御长”中的“极”和“玄都”即属此用法,前者本为北极星之意,这里指代帝王,因其至尊之位相似;后者本为丹台仙真之所,神仙所居,此指玄元皇帝庙。诗人之所以选择以“碧瓦”代指老子庙,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碧瓦在庙之顶,是拜谒者最先看到的地方;其次,瓦处在庙的最外层,最先与外界接触,拦截着风雨,包括“初寒”,如果“初寒”无法渗透“碧瓦”,也就没有机会进入庙中;再则是这“碧瓦”为琉璃瓦,非一般平民住宅可以使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既突出其流光溢彩的一面,又兼带其华贵与尊严的一面。
当了解到诗人的这一用法之后,即可得出杜甫此处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整个老子庙都在“初寒”的外面,而非只有“碧瓦”独在“初寒”外。这种解释也是符合叶燮本意的,前引“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一句,如前所析,是诘问之语,是那些不懂得文学艺术特征的人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这里不是写瓦,不是写初寒,也不是写远或者写近,此句写的是老子庙,言其若处于“初寒”之外。只有清楚了“碧瓦”一词的具体所指,才能进一步挖掘“碧瓦初寒外”一句的理之所在,即叶燮所说的只有诗人才能发现的“不可言之理”。
对中国古典诗歌深有造诣的汉学研究专家宇文所安先生亦必深知此法,只是不知为何对“瓦”之所指有此误解。
三、未能揭示的文论之“理”
清楚了“碧瓦”一词的具体所指,现在来分析“碧瓦初寒外”一句的“理”之所在。
叶燮此段内容是为回答该对话者的提问,所以目的是为了说清楚除了“情”之外,“理”和“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此处重在说“理”),同时说明诗人之“理”,不是“人人可言”之理,而是诗人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思维所感到的“不可言之理”。具体到杜诗之中为什么会形成“碧瓦初寒外”的状况,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情况为什么存在?叶燮一句“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便是回答。叶燮这里谈到的是一种方法,姑且称其为“默会”之法。但是并没有解释这“碧瓦初寒外”的背后之“理”到底是什么。至于为何没有解释,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宇文所安先生此书作为介绍与评论中国文论的书,是这样解释的:“所有这些可能性共同创造了被寒冷包围的瓦的感觉;虽然被寒冷包围,可那些瓦,不知怎么回事,似乎在寒冷之外而不是之内。”[2]593用一句“不知怎么回事”来阐明,似有不妥,等于说没有解释。
关于“碧瓦初寒外”一句中所蕴含的“理”,目前国内学者似乎也并未达成一致。前人如清代黄生认为是其高所致,“‘山河’二句,形其高耸,金壁照耀,虽冬侯而气色华美,故曰‘初寒外’。”[4]谭容培先生则认为“初冬寒意袭人,只见那深山层林中隐约露出的庙宇碧瓦,流光溢彩,更显得超尘出世、庄严肃穆,却无孤寂冷漠之感,反而生出一丝融融暖意。”[5]如周振甫先生认为是庙内香火旺盛所致,“‘碧瓦初寒外’,极写老子庙内香火之盛,使人感到温暖,好像庙上的碧瓦在初寒之外,即排除了初寒的侵袭。”[6]袁济喜先生指出“老子庙也处在初冬的寒气笼罩之内,但为什么诗人却独独突出老子庙超离于初冬寒气之外呢?原因是诗人看到老子庙的碧瓦红墙,于初寒中给人以温暖之感,所以说‘碧瓦初寒外’,它传达出诗人对壮丽的老子庙的赞美之情。”[7]麦永雄在其书中指出“何故?为我周边之空气而非远于碧瓦处的空气直接使我感到寒意也。其谓初寒,亦因我方才感受到也。初寒骤然而至,故使人突然间错觉顿生,似乎近身处最为寒冷。进而问之,近身处何以‘最为寒冷’?不仅在于人为有生命之物而碧瓦为非生命之物,更在于人是有情之物,且其人正处于某种不无寒意的心境之中。”[8]
虽然学界就这一问题的解释可谓歧见纷纭,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然宇文所安在其书中既未能揭示其中缘由,又对中国学者的成果只字未提,仅以一句“不知怎么回事”结束了论述,似有不妥。
四、片言只语的不当引申
“碧瓦初寒外”是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中的一句,全诗如下“配极玄都閟,凭虚禁御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盘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9]关于此诗的主旨,目前存在两种看法:其一是讽刺说,认为杜甫是在讽刺李唐皇家的滑稽做法;其二为歌颂说,认为这是诗人杜甫歌颂玄元皇帝庙的华贵。
对诗歌的解读应该建立在对诗人及其创作背景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该诗写作于天宝八载(749)冬,此时诗人暂回东都洛阳。李唐王朝因其姓李,而老子李耳也姓李,故尊老子为始祖,乾封元年(666),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东都洛阳玄元皇帝庙在城北北邙山上,即是杜甫诗中所写之庙。
宇文所安在其书编写过程中不知是否翻阅过杜甫全诗,其在解释“碧瓦初寒外”时讲到:“叶燮看出,庙顶上的瓦对无处不在的天气的抵制或许只限于这个时刻,那些瓦只在‘初寒’时节才把形状强加给寒冷;当严寒降临时,这个内外界限大概就消失了。因此,它不仅仅是诗人所见的一个特殊空间,而且也是一个特殊时刻。”[2]593再读叶燮《原诗》相关内容,无法找出宇文所安此观点在《原诗》中以何为据。跳过《原诗》,在杜甫诗中没有这层意思,宇文所安此论述并未与该诗主旨发生关系,属断章取义。宇文所安未能深入理解杜甫全诗,而仅就叶燮《原诗》所引杜甫诗歌中的一句,从语言词汇角度做出的引申、发挥,与诗歌主旨无关,属不当引申。
综上所述,宇文所安先生虽然在汉学研究方面独具慧眼,取得了许多让国内学者钦佩的成就,但终因语言、文化等隔阂,使其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没能探骊得珠。但即便如此,亦是瑕不掩瑜,其汉学研究的方法的确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