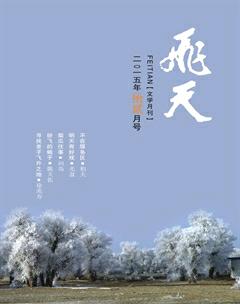城里的日子

蔡竹筠,男,本名蔡军, 1968年1月出生于甘肃省高台县。1995年在《飞天》发表小说处女作,之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作品近百篇(首)。出版作品集《故园》。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张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在高台县文联工作。
从县城西关十字向东走百来米,有一个巷子,叫羊头巷,巷口朝南。这巷口的西面是一家电器商厦,六层高的一幢大楼。当初修建时,城建上考虑,为了把巷口留宽,这幢大楼的设计,门口东面的墙并没跟巷子里毗邻的建筑墙面取齐,而是缩进去一进之地,这样一来,巷口西北角上便形成一个墙面呈7字形的空地。渐渐的,这空地被几个摆摊的占领。卖酿皮和凉粉的摊主是一个中年矮胖的女人,认识她的人都喊她李嫂。她有一辆改装的双轮手推车,车厢底板就是案板,上面罩了一个半人高的柜子,木头的框架,三面镶着玻璃,外面的玻璃面上贴着红油光纸刻的“酿皮”和“凉粉”字样。没镶玻璃的这面,挂着两片绿窗纱帘子,闲时对合着,操作时一左一右拉开来。车厢下,有一个隔层,放置一个白铁皮盆子,里面是一张一张黄亮亮的酿皮,不知有多少张,但摞起来有尺把厚。她的手推车车把很长,是木头的,车把下有两根鸡蛋粗细的撑柱也是木头的,撑在地上,能保持车厢水平,车把上能横放一张长方的矮桌和两条长凳。每天,李嫂将这些东西一车子拉来,摆上桌子和长凳,摊子就算摆出来了。来她摊上吃酿皮的很多,时不时会有三男两女,坐在那里,踢里吐噜,吃得非常可口。还有的不在摊子上吃,将酿皮和调料打包带走。吃客或买主中,有的嘱咐多放芥末,有的要求少放蒜泥,有的则让多放几块面筋,李嫂都一一照办。走时递上钱,如果要找零,有人的目光随着李嫂的手投向一个鞋盒子,会看见里面有半盒子钱。另一个是修自行车的,六十多岁,人虽坐在马扎上,但看起来个头不小,只是干瘦,有些皮包骨头的样子,头发花白着,也显得干枯。他的摊子上常有一辆自行车,龙头和车座子撑在地上,两个轮子朝天。他要么面前摆着一盆水,他在水盆中像开车司机转方向盘似的,转着充了气的内胎,在找漏气的气眼;要么,一下一下,用皮锉锉着内胎,锉干净一小块面来,补上疤子。闲着的时候,他就躺在一把躺椅上——他的摊上还有一把躺椅,供光顾的客人坐卧。倘若没有客人,他自个儿就躺上去——有时眯个盹儿,有时就躺在上面,睁着眼愣神。他脚前的路牙子上摆着两把打气筒,打一次气五毛钱。有时来人打过气,没有零钱,递上的是二十甚至五十的票子,他找不开,一挥手,算了。每天早上九点多,这两个摊子先就摆出来了。到了近午时分,还会来一个卖馒头的,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媳妇,三轮车上叠放着三层笼屉,笼屉上罩着厚厚的棉罩子,丝丝缕缕的热气袅袅地升腾着。三笼屉馒头,午时前后也就卖完了,巷口便消失了这年轻媳妇的身影。下午五时许,她的冒着热气的馒头车又出现了。除了这三个摊子,时不时的,巷口还会来一两辆卖菜或卖水果的流动电动三轮车。
这几年是多少年呢?也有五六个年头了吧。每年六月底七月初,这里还会来一个卖瓜的乡下汉子,开一辆兰驼牌四轮车,车厢上用钢筋条加高了有半米高的栏杆,载着满满一车瓜,有西瓜,也有甜瓜。他把瓜卸在巷口往里一点的地方,西瓜是墨绿的一大堆,甜瓜是黄澄澄的一小堆。瓜摊前面摆上一张小方桌,桌上放一把柳叶刀,桌两边摆四只尺把高的塑料矮凳。瓜摊后面是一面墙根,左面也是一面墙根,他在墙根拐角处打了一个地铺。他的车上,来时带了一块床板,床板是平放在车斗中的,把瓜卸下车,这块床板也就拿下来,用四块断砖,支在靠墙根的地方,然后从驾驶室里取下铺盖,一个睡觉的地方也就有了。他的四轮车一开始停放在巷子里,这一二年巷子里不让停车,被交警和城管抓住都要罚款,他便停在邻近的富地小区。小区也不让停,看门的老头来找他交涉,他跟那老头吵,说话是骂人的口气,面上却带着微笑。那老头也不生气,大概也是乡下来的,习惯了他这种声口,只要秉公办事。到了,事情却是私了,他抱两个西瓜,大步流星送到小区门房,就这么把老头打发了。过一段日子,他再主动送两个瓜,那老头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反在小区住户面前把这四轮车停放带来的不便全都担待下来。
羊头巷是一条窄巷,因在闹市区,又是两头通的一个巷子,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巷子两边都是居民聚居区,每天上班下班,这边的巷口和那边的巷口,私家车、电动车、自行车,更多的是行人,是要壅塞一时的,难免会有磕碰,甚至发生口角。在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巷里做生意的,不论是卖百货、卖粮油蔬菜的,还是开理发店、小诊所、茶园、服装店、小吃店的等等,只要是个店,气象都很兴隆。因此上,即便过了上下班关口,这巷子也难得有一时的宁静,除非是深夜。
照理,这样的巷口是不该摆摊设点的,城管先就不行。但多年过去,城管从未认为有什么不妥,也就从未来纠察过,因不是占道经营。那么,这块空地的主人、也就是那家电器商行应该不许,但事实上,商行不仅默许,心底里还是欢迎的态度。因这块空地曾经给商行带来过挠头的问题,是这几个摊主为商行解决了这个难题。
有一个流浪汉,蓬头垢面,一年四季穿一件油渍麻花的军棉大衣,脚上是一双穿没了后跟的皮鞋,整天在县城大街上四处乱转,身上背一个超大蛇皮袋,里面装着拣来的自以为用得着的垃圾,从人们身边走过,有时叼着一支烟,有时喝着半瓶矿泉水,还有时拎着半瓶烧酒,脚步趔趄,看样子已经半醺。他虽然四处觅食,但固定的歇处就是电器商行门口这块空地。许多时候,大白天的,他袒裸着脏臭的身体,躺在棉大衣上酣睡,路人无不掩鼻。一次,他掏出生殖器,猥亵一位刚走出电器商行的女子,被这女子身后的男友看见,上去一顿脚踢。商行得知此事,开始驱逐流浪汉。但撵他离开,时隔不久,他又悄没声息地返回。再撵,再返回,跟商行玩起躲猫猫。
后来,李嫂来这儿摆摊,流浪汉站在摊旁,眼巴巴地看客人吃酿皮,影响客人的食欲,也就影响了李嫂的生意,李嫂就撵流浪汉走开,如同替商行撵流浪汉。李嫂是温和的态度,不骂,只是一味地劝他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流浪汉有时听,大多数时候不听。再后来,修自行车的老头来了,看李嫂撵流浪汉走,流浪汉无动于衷,便也跟李嫂一块儿撵他。这老头的态度是粗暴的,他大声武气地让流浪汉滚,滚远点。流浪汉置若罔闻。老头一下子被激怒,他将一条自行车内胎,对折捋在手中,照流浪汉身上狠抽了几下,还将他拣来的东西几脚给踢得四散。流浪汉好像并不生气,他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东西捡拢在一起,有点不情愿地离开了,自此再没有来过。
流浪汉走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前面说过,这巷子里做生意的很多,巷道两边都是小门面,其中有十多家风味小餐馆,只管吃喝,不管拉撒。巷子里又没有公厕。有些人吃着喝着,突然内急,白天急了还能想方设法找到去处,深夜就不一样了,本是想走出巷子去找解处,走到电器商行这里,看到有一处拐角,虽是在巷口,且有路灯照着,但路灯是隔着槐树照来,斑驳之下,看得不甚分明,便在这半明不明的地方就地解决起来。商行的人早起上班,总看到门口一侧有尿迹或是秽物,捂口掩鼻而过。有一个负责人气愤不过,在墙上刷了警告的标语:“此地禁止大小便!”后来又加上:“违者罚款二十元。”又改成:“此处大小便的是驴。”照样不能禁止。李嫂或修自行车的老头每天来摆摊,还得先打扫卫生。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卖西瓜的乡下汉子来了,把瓜摊摆在这里,日里夜里固守。恼人的问题自此根除。
卖西瓜的汉子,有四十多岁,紫红脸膛,有这样脸色的人一般都有着豪爽的性格。来一个买主,问一句:瓜熟不熟?他是十拿九稳的口气:不熟包退。又问:甜不甜?他随手掂起一个瓜来,放在小桌上,用那把柳叶刀切下带瓜蒂的一块来,捏着瓜蒂,用这块瓜皮来来回回把刀抹几下,两面都抹过,算是洁了刀,然后把瓜四分五裂,让那人尝尝甜不甜。那人接过他递来的瓜,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吃过后没说瓜甜,也没说不甜,目光在西瓜堆上扫来扫去,看样子是要买瓜了,挑拣了半天,终于选定一个不大不小的成交。这一个瓜上的赚头,还不够抵这人吃掉的那一块瓜,但遇上这样的买主,他也并不觉得多么不值。
他们那村子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沙质的土地,充足的光照,能种出好瓜来。虽是地处偏远,但市场经济的浪潮也波及到那里。村里种瓜的十来户人家成立了合作社。曾经,合作社负责人来邀他入伙——合作社在酒泉、嘉峪关有客户,销路不发愁,给的价钱比他在县城卖的还要高,可他断然拒绝,不知心里是咋想的。每年到了瓜上市,他把瓜拉到城里来卖,卖光一车再去拉来一车,一直要卖到十月底瓜彻底败了秧的时节。
在城里,因是一个人,没媳妇管着,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凡事就随心些。在村里,他抽三块多钱一盒的烟,可到了城里,他的烟就上了档次,抽七块钱的“紫兰州”。他卖着瓜,口渴了却不喜欢吃瓜,喜欢喝饮料。巷口斜对过有一家小百货店,他每天去买饮料喝,今天喝矿泉水,明天喝雪碧,后天是可乐,下一天成了果粒橙,一天一个口味,一天一个牌子。小百货店的店主是一个已经做了奶奶的中年妇女,一边照管孙子,一边打理生意,见他掀帘子走进店门,便笑着问:今天喝个啥牌子?他往货架上睃一圈,抬手一指:那个黄的吧。店主按他指的拿给他。他从随身带的一个过时的公文包中,抽出一张钱付款。趁店主找钱的当儿,他拧开瓶盖,咕嘟咕嘟几口把饮料喝个底朝天,随手把空瓶扔在柜台上,接过找零的钱,一掀门帘,走了。
他吃饭,一天三顿都是下馆子,也是这样,经常换地方。早晨,大多时候吃牛肉拉面。这时,李嫂和老徐——时间久了,知道修自行车的老头叫老徐——还没来摆摊,他把瓜摊撂下,也不怕有人偷瓜,去巷子里一家牛肉面馆吃早餐。一碗牛肉面,又热又辣,不够他呼啦几嘴的。转眼之间,人已经坐在摊子上抽烟。有时去来,时间上要长一些,那是他吃厌了牛肉面,到邻近的街区——“宾馆对外餐厅”吃臊面,或是去“再回头”吃刀削面,有时要到更远处,去汽车东站门口的“东来顺”吃猪血包子。此去一时三刻,好像是不在意自己的瓜摊,其实能看出行色匆匆,心里是惦着的。午饭和晚饭便没这么匆迫。他去时会给李嫂或是老徐或是卖馒头的小媳妇打声招呼,时间或长或短。他回来了,李嫂或是老徐或是卖馒头的小媳妇会问一句:吃的啥?他有时吃炒面,有时是炸酱面,有时是干拌面。还有时出去好一阵子,没找到可吃的,回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塑料食品袋,里面是一斤半斤卤肉或是酱牛肉,放在小方桌上,抻开袋口,让李嫂拿来几双筷子,招呼李嫂、老徐、卖馒头的小媳妇过来一块儿吃。他们当然是推辞,他再三再四地邀请,仨人被邀不过,只得坐过来。最后的场面是,老徐去小百货店买来一瓶烧酒,有时是几瓶啤酒;李嫂又切来面筋和酿皮;卖馒头的小媳妇拿几个暄腾腾的馒头过来,大家来次小小的聚餐。他走开的这阵子,要是有人来买瓜,他们几个——大多时候是老徐,会替他照看买卖。
这几年,他在城里也相熟了好些人,李嫂、老徐、卖馒头的小王自不必说;百货店的女老板、富地小区看门房的老头、电器商厦的刘经理和张会计,也都熟到见了面非得搭讪两句不可的地步。另外,这巷子里的许多生意人时常来买瓜,虽然彼此叫不上名字,但脸面是熟的;还有小区的许多住户,也常来买瓜,脸面也是熟的。这样的人,他在心里都是看作熟人的。在众多的熟人当中有两个女人,表面上看起来他跟她俩来往的是西瓜,其实,私底下还发生了些别的。
第一个女人住在这巷子里的荣华小区。这女人第一次买瓜时开着一辆红色小轿车从巷口路过,她泊住车,人未下车,摇下车窗,隔着巷道招呼他,让称一个西瓜,连价格也不问。他拣了个个头大的,称过斤两送过来,这女人用遥控启开后备厢,他把瓜放进去,后厢自动闭合。女人付过钱,车子像一条红色的鱼一样滑进巷子,拐进了富地对过的荣华小区。这女人长得白净,一头卷发染成栗子黄,披在肩上。仅隔了一天,她又来了,这一次她是走着来的,一身的珠光宝气,金耳坠、白金项链、钻戒,两只手腕上各戴着一只银的玉的镯子,引得巷口的人无不注目。最夺目的是她的穿着,是一件低胸无袖的银白色旗袍,不知是啥质地,上面鱼鳞一样星星闪闪的,乍一看,让人目眩,再看,这女人是好吃喝养出来的,富态得有点过了。转侧之间,能看出她的乳房,像两只大白瓜。她的屁股像两只大西瓜,因为个儿高,并不显得臃肿,反显得壮美。她称了两个瓜,拎了拎有点沉,问他:你能给送一送吗?我就在旁边住着。他没有推辞,干脆道:行。女人在前引路,他跟在后面,一手拎一只瓜,像个勇武的跟班。
那一次,他见识了什么是有钱人家。他跟着这女人进了家门,踏进她家客厅的一刹那,感觉像是进了宫殿,他脑海中蹦出四个字:金碧辉煌。他是念过中学的,这个词语还是能想到的。他看到,偌大的客厅,时尚家具和高档电器应有尽有,但还是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从沙发上斜着横着的靠垫、茶几上敞着盖着的杯盏上,看得出这女人的慵懒和无聊。他把西瓜放在指定的地方,转身要走,女人招呼他,让他歇歇再走,话音未了他已出了门口。女人到门口来送他,他已经三五步跨到楼梯拐弯处。等这女人磕门的声音传来时,他已经到了楼下。他轻轻舒了一口气,才觉出刚才是压抑和憋闷的。
不几天,这女人又来买瓜,买了一个西瓜、两个甜瓜,又要让送回家。这一次,他显得不像上次那么匆迫。女人让他坐坐歇口气再走,他还真就坐下来了,很欣赏地看着房里的摆设。女人让他抽烟,她是见过他抽烟的。他摆手说不抽。女人看出他是不好意思,抽出一根烟递给他。他把烟接在手,没有点火。女人让他点,他说出门再抽吧,这么好的房子让烟熏的。女人说:没关系的。他这才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这一次,他跟这女人还聊了些别的。女人问他:你叫啥名字?他说他叫李伟。顿一顿,女人又问:你有手机吗?他不明白这女人问他有手机干吗,他是有个手机的,就揣在裤口袋里,是那种推盖的老式手机,还是他女儿上大学时用过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外地打工,换了新手机,这手机就归他了。于是就说:有。女人又问:你能留个号吗?他随口说了手机号。女人一边拨号,一边说:我的你也存下……话刚落音,他的手机响了,他从裤口袋里掏出手机,还没推开盖,手机又断了。女人说:这是我的号。稍顷,女人又说:我叫白玉玲。
有了这一次,他跟白玉玲算是熟络了。熟络之后,白玉玲再没到瓜摊上来买过瓜,都是打电话让他送过去。一次,临出门时白玉玲递给他一条烟,让他拿去抽。他推辞不受。白玉玲硬塞到他手中,他也就不无歉意地接下了。有了这一条烟的交情,除了送瓜,白玉玲还让他买过一次大米,给她送上楼;有一天,她家楼上停水,还让他买过一桶纯净水。
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已经黑下来,他吃过晚饭,躺在地铺上抽烟,突然电话响了,他一看,是白玉玲打来的,让他送两个瓜过去。黑灯瞎火的,他也没称斤两,挑了两个瓜,就拎着去了。到了单元门口,按响门铃,转眼间,门咔叭一声开了。他上了楼,房门开着,推门进去,客厅里亮着灯,却不见人在,偌大的客厅显得有点冷清。正纳闷,白玉玲从卫生间迤逦歪斜地走出来,她穿着睡衣,头发有点蓬乱,看房门开着,她趔趄过去,把房门推上,不待招呼他坐,自个儿先跌坐在拐头的沙发上,又把身子歪在沙发扶手上。他看出今天的情形有点不一般,心里多少起了一点疑。白玉玲这时强撑起身子来,看他还站着,这才招呼他:你坐呀。这时,他看出白玉玲喝了酒,人还醉着。果然,白玉玲迷蒙着眼说:我喝醉了……又笑着说:你不会笑话我吧?他说:能喝酒的女人多的是,喝醉的也有,这有啥呢!他的口气是宽慰的。白玉玲听了这话,又笑了一下。接下来是一会儿沉默,沉默过后,白玉玲问他:你吃过饭了吧?他说:这会子了,早吃过了。白玉玲又问:你把瓜摊撂下,不会有事吧?他说:几个瓜蛋子,放在那里能有啥事呢?又是沉默,沉默过后,白玉玲说:我这几天心里憋闷,想找个人说说话……咱们说点啥吧。想了半天,他不知说啥好,觉得大晚上的,待在一个女人家里有些不妥,但又不好即刻就走,只好默坐着,显得有点心神不宁。白玉玲看出他急着要走的样子,说: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来人?他未置可否。白玉玲笑了笑说:我家里不会来人的。白玉玲这句话倒引起了他的话头,他问:我来你家也不知多少趟了,咋没碰到过你家里人?白玉玲笑了笑说:他在外面……唉,就当他死了吧。他听出话里有话,便没敢再往下问。默了默,白玉玲像突然想起啥似的说:唉,你看,半天了,也没给你倒个水。说过,摇摇晃晃站起身走到净水器前,要给他沏水。杯子已经拿在手,又突然道:你喝啤酒吧。不待他应允,一转身,从酒柜里拿出两听啤酒,走过来放在他面前。白玉玲就势坐在他旁边。不知是沙发弹性使然还是有意,白玉玲坐下的当儿,他的身了稍稍倾侧了一下,似乎是要保持应有的距离。白玉玲看他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说:你打开喝呀!他好像拿不定主意似地说:不喝了吧?白玉玲说:喝,不喝干啥!说过,打开啤酒,给他手里递。他赶忙伸手去接,接住的当儿,他明显感觉到,白玉玲的手指有意地触了触他的掌心。他双手捧着一罐啤酒,像捧着一杯滚开水,喝也不是,放下也不是,在手中摩挲了一会儿,末了,还是一口没喝就放下了。接下来,他显得无所适从,不知该说点啥,静默一时,他想抽根烟,在裤口袋摩挲了一下,才想起自个儿的烟没带来。茶几上有烟,但白玉玲没让,他不好意思抽,只好干坐着。白玉玲也不知道再说点啥,只好干坐着。他们这时的情形,看起来就像一对赌气的夫妻,谁也不理谁。冷场半天,还是白玉玲打破了这难堪的沉默,问他:你待在城里,不想家里人吗?这次,他低头笑了笑,说:有啥想头哩,想也是白想。说过这话,他抬起头来,看了白玉玲一眼,目光碰撞的一霎,他看到白玉玲的眼里包含着某种情意。他的心怦怦跳荡,一时难以平静。这时他意识到,白玉玲让他送西瓜来,并不是为了西瓜,而是还有别的;白玉玲说想找个人说说话,也不是为了说话,而是还有别的。这别的,如果再待下去,真有可能发生。同时意识到,这别的,真要发生起来,他没那个胆量。事情不仅突然,还有些不可思议。当意识到这些,他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就要告辞离开。任凭白玉玲如何挽留,他坚持要走。临出门时觉得不忍,想说几句宽解她的话,又不知怎么说,就说了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时候不早了,你早点睡吧。然后,落荒而逃。
回到瓜摊上,他转辗反侧,难以入睡,将适才的一幕在脑子里过电影似地过了几遍,一时间觉得是自己多想了,一个城里的漂亮女人,又那么有钱,跟一个乡下来的卖西瓜的,怎么可能啊?他做梦都不敢想,当故事讲出来人都不信。一时间又觉得白玉玲真有那个心思,不然她不会喝醉酒,大晚上的让他去陪她说话。要真是这样,白玉玲看中了他的啥呢?她哪里找不到人,非要跟他呢?想想又觉得不可能,还是自己多想了。就这样,一个念头压倒另一个念头,翻来覆去,想得他云里雾里,像是做了一场梦。
但后来的迹象表明,白玉玲对他,还是有想法的。她没再打电话让他送过瓜,也没到瓜摊上来买过瓜,对他,还是有了隔膜。这时,他觉得有点对不起人。想打个电话,又不知道说啥好,也就只是想了想。
一天,白玉玲开着她的红色保时捷出了巷口。他们几个摆摊的都看见了。李嫂感叹说:唉,都是个女人,你看人家!老徐躺在躺椅上,双手支着后脑勺,说:咋了,羡慕有钱人了?过一会,又说:你羡慕人家,人家说不定还羡慕你哩!李嫂说:我一个卖酿皮子的,还能让人家羡慕?老徐说:有钱人有有钱人难念的经哩。接着,老徐给他们讲起白玉玲的事来。
时间久了,李伟知道,老徐是一个包打听,家长里短的事知道得多。他说,白玉玲的男人是一个煤老板,本是个退伍军人,在煤矿上当工人,后来,一步一步发达起来,如今,在祁连山里开着两个矿,在市上还有产业,家里的资产过亿。一双儿女,一个在美国念大学,一个送到英国读高中。她男人在外面有几个情人,听说,有一个还为他生了个儿子。白玉玲知道后,跟她男人闹过,都闹到离婚的地步了,但没闹出个结果。白玉玲家兄弟姊妹多,她家原本是乡下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兄弟,都是靠她男人成家立业。他两个哥,一个在矿上,一个在市上,给这煤老板打理生意。这婚要是真离了,他两个哥就没着落了。娘家人都劝她,算了,将就着过下去算了。白玉玲想到一大家子人都要靠她,也就不好一意孤行。只是男人回到家来,她没有好声气,也没有好脸色。时间一长,她男人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回来了……
李伟听了这些,暗自为白玉玲叹息了一回,心中歉疚了好些日子。但这份歉疚,日子一久也就淡了。
第二个女人叫邢兰芳。一眼看过去,她跟白玉玲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黑瘦,再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朴实。她家在城郊,开着一个农家院。两年前,县上要从他们村子通一条到风景区的路,县上拿不出修路的钱,就招商引资,条件是,路两边低价划给一百亩土地让商家开发房地产。县上给商家征收地皮,邢兰芳家的房子和九亩地都在征收范围。田地和房子被征走,村里人并没落下征地款和房款,被商家通过县上置换成了住宅楼和农家院,有的还补了差价。他们村子紧邻的那条街,一边一溜儿有二十多家农家院。邢兰芳的农家院刚开张时,一天还能有一两拨吃饭的顾客,但时隔不久,因为农家院多,也因为她请的大厨手艺平常没有特色菜,人就不来了,眼看就要关张。但如今,有闲又有两个钱的人,吃过喝过,还要打打麻将、诈诈金花、斗斗地主,赌两把消磨时光。热闹的农家院,客人一拨一拨的,没这个时间和场地。邢兰芳的农家院没人催着,可以一待大半天,甚至夜以继日。渐渐的,这些爱玩两把的人就摸索到邢兰芳的农家院来了。邢兰芳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茶水,按人头抽份子。她的农家院就这么着维持下来了。这些人玩起来没完没了,一泡一整天,甚至一天一夜,到了饭时也不回家,有时让邢兰芳给他们做点家常饭,有时让她上街去买。这天天热,有几个客人要吃西瓜,邢兰芳就骑着电摩,四处找着给买瓜来了。
午后,李伟躺在地铺上打盹,迷糊一阵,在这人来车往的巷口,他竟然进入梦乡。突然,修车的老徐大声喊道:“来人了!”虽是没有称呼,他也知道喊的是他,惊醒过来,睁眼看,见路沿下停着一辆枣红色电动摩托车,一个女人,就是邢兰芳,猫着腰,敲木鱼一样,用拇指和中指一弹一弹的,挨个儿敲他的西瓜。李伟走过来,邢兰芳问:西瓜多少钱?李伟报了价格。邢兰芳说:能不能便宜点?李伟问:你要多少?邢兰芳说:要十来个吧。李伟说:那行,给你少上两毛。邢兰芳又问:你的瓜甜吗?小方桌上有切开的半个瓜,瓤口又红又沙。李伟嚓嚓嚓几下,把瓜杀成牙子,递给邢兰芳一块。邢兰芳吃起瓜来,大口大口的,吃声很响,吃过一块,由衷地赞叹:哎呀,好瓜,再来一块!说着,自个儿从小方桌上拿起就吃。她这种见面熟的作派,让卖酿皮子的李嫂都笑了。
邢兰芳买了十来个瓜,装了两网袋,自己的电摩载不了,在路口等拉货的三轮车,等了好一阵子也没等来,手机响了,嗯嗯啊啊接听了半天,听得出啥人有事催她。这时老徐对李伟说:你干脆把你的兰拖开上给送一趟吧,人家买了你这么多瓜呢。邢兰芳一听这话,看着李伟,说:咦,你看你还装得像放了屁的亲戚似的,有车哩,还让人等了半天,也不早说给人送送!李伟啥也没说,只是觉得,这号女人男人没治,转头去开车,一会儿把兰拖开来,装上西瓜,邢兰芳骑电摩在前引路,一路给送到了农家院。
回来时李伟主动要了邢兰芳的手机号,他看邢兰芳是个大买主,想从她手里多走两个瓜。果然,十来个瓜,不够四五拨赌徒们吃几天的。邢兰芳一打电话,李伟就送两袋子过去。这样一来二去的,加上邢兰芳那种性格,一个月下来,李伟跟邢兰芳就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就像多少年的老熟人。
一次,李伟去送瓜,邢兰芳说:我使一下你和你的车。李伟问:干啥?邢兰芳说:去粮油店给我拉几袋面。两人一同把面拉来,一袋一袋往厨间抬。李伟抬了两袋,就抡胳膊甩膀子的。邢兰芳说他:一个大男人,咋啥球势都没有!李伟说:你放着自家男人不使,把别的男人当驴一样使唤哩。邢兰芳一听这话,突然间不高兴了,半天没跟李伟说话,干完活,连声谢都没说。后来,李伟才听邢兰芳说,她男人被判了刑。
原来那年征地的时候,她男人死活不愿意,先是不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来修路的时候又跟几个人在田地上搭帐篷睡在里面,不让开工。扒她家房子的时候,她男人坐在房檐下,让开发商动不了工。后来县上出动警察,强行把他带离。她男人发了疯似的,一铁锨把一个警察拍趴下,又在一个警察的小腿上铲了一锨。后来,她男人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家里公婆,还有两个儿女,如今都靠邢兰芳开农家院过活。
自从知道这事,李伟给邢兰芳送瓜时,看到能干的活儿就顺手给干干。遇到吃饭的时节,客人吃过还有剩的,邢兰芳让他吃,他也就吃了。李伟觉得,比起白玉玲来,他跟邢兰芳相处,言谈举止要自在得多。
这年深秋,李伟最后一车瓜卖得差不多的时候,有点急着回家,就一股脑儿把余下的瓜都送到了邢兰芳的农家院。
下一年,李伟上来得有点晚了。县城里别处的瓜已经卖过半个多月,他的瓜摊才摆出来。入夏时节,瓜秧扯条的日子,突然来了一场寒流,把瓜秧冻僵了,寒流过去,又紧着抢种,这瓜就熟得晚了。老徐和李嫂以为李伟今年没种瓜,或是到别处卖去了,还替他担心摊位被别的人占去。现在见他来了,热情地帮着卸瓜。一切归置停当,李伟杀了一个瓜犒劳他们。吃着瓜,闲聊间,老徐说:姓邢的媳妇子都来了好几趟了,没见着人,都以为你不来了……
消停下来,李伟给邢兰芳拨了电话。电话里顿时传来邢兰芳哒哒哒的声音:这么长时间了,没你鬼的音信,给你打了两次电话,都没打通,到你摊子上去,也扑了个空,问人,都说不知道。你不卖瓜了吗?到哪发大财去了?……前些日子,一个卖瓜的送货上门,瓤子是黄的,说是新品种,吃起来就跟葫芦似的。我又到市场上买了一回,客人一吃,也说恶水不叽的,说我蒙哄他们的钱哩……
半天了,李伟插不上嘴,待她说得歇了气,李伟才给她从头解释。一听李伟又来卖瓜,邢兰芳当下就让他送瓜过去。
两人见了面,李伟倒没怎么着,邢兰芳有一股热乎劲儿,把电话上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李伟没再解释。邢兰芳又说:你咋没多拉上些?……李伟以为给她拉得少了。只听邢兰芳又说:这条街上,好几个农家院都要瓜哩,上次那个送上门的,我看见好几家都买了。你也别有顾客没顾客就守着个瓜摊,你去走走,挨门儿问问。
离开邢兰芳,李伟照邢兰芳说的,顺便去问了问,还真有几家给吃饭的客人免费上瓜果盘的,天天少不了西瓜。于是隔三差五的,李伟到这边来送西瓜。送过西瓜,不管有事没事,他都要到邢兰芳的农家院逗留一刻。如此一来,他们差不多是天天见面,较之一般的熟人,关系又进了一层。
李伟四十出头,邢兰芳也是快四十的人了,但两人在一起,除了说笑,时常还打闹。一次,李伟新摘来一车瓜,顺路先到这边农家院来送瓜。给邢兰芳送瓜时,李伟告诉她,这是他今天起早摘的露水瓜,吃起来又水又甜,又爽口又解渴。邢兰芳就杀了一个吃起来,大口大口的,吃声很响。李伟见邢兰芳吃瓜不是第一次了,上次见她这吃相,人不熟没敢说啥,现在熟了,就说:你看你,饿母猪见了烂西瓜似的……邢兰芳一听,故作嗔怒,嘴里还鼓囊着一嘴西瓜,扬手把半块瓜甩在了李伟身上。一看甩了李伟一肩头的瓜水瓜瓤子,又回嗔作喜,撕了块纸给擦干净。邢兰芳擦着,李伟吩咐她:好好擦,来,嘴巴上也擦擦!一听这话,邢兰芳收起笑,一下子把脏纸又甩在了李伟脸上。又一次,还是邢兰芳的农家院,在邢兰芳的卧房里,邢兰芳问李伟:有客人吃剩下的鸡肉,你要不嫌弃,我给你端去。李伟没说啥。邢兰芳把肉端来,李伟拣着吃了几块。邢兰芳收拾碗筷去了厨间。李伟闲坐着,一转头,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像框,拿在手看,里面是邢兰芳姑娘时候的照片。邢兰芳进来时李伟还在端详。邢兰芳说:真人放在这儿你不看,把那么个照片嘛,有啥看头哩!李伟说:哎,你别说,你丫头时节长得还怪水灵的。说过又端详。邢兰芳说:你别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李伟端详了一会儿,看着邢兰芳,做了一个轻薄动作,把照片在嘴上对了一下。邢兰芳一见,扑过来抢照片。没提防脚下一滑,一下子扑倒在李伟怀里,就势从他手中夺过照片,起身的当儿照李伟小腿上踢了一脚,嗔道:坏鬼。
邢兰芳丈夫不在身边,在城里,李伟也是孤身一人,孤男寡女,他们之间除了说笑打闹,男女之心不能说是没有,但毕竟一个有丈夫,一个有妻子,心里的顾虑是有的。再一点,总有一层纸捅不开。后来,他们终于好上了,除了情意使然,可以说是老天作美。
那天子夜时分下起大雨。邢兰芳的农家院,天井上方用蛇皮袋编织布搭着雨棚,雨下在上面,声音格外响亮,先是像铁锅爆豆子,一会儿就跟放小鞭炮似的。棚布上积了水,整个儿往下兜着,顺着倾斜的一边,小瀑布一样往下流。雨下成这阵势,当下邢兰芳倒没担心自己的雨棚有什么闪失,突然想到李伟的瓜摊摆在露天地里,人也睡在露天地里,怎么过夜呢?当初搭雨棚时,还有剩下的小半卷编织布,立在储藏间墙旮旯,她取出来,又找了一团扯棚布的尼龙绳子,披上雨披,骑着电摩,冒雨给李伟送去。
到这儿一看,李伟已经在瓜摊上搭了一个帆布篷,人呢,被子蒙头都快睡着了。一听邢兰芳的来意,李伟觉得这个女人对他是上心的,不禁心中一热。他对邢兰芳说:防雨的东西,来时就预备着哩。
邢兰芳见李伟没淋在雨中,心中也起了一阵暖意。雨势有增无减,邢兰芳就想待会儿,雨停了或是下得小了再回。不待李伟招呼,她把被头往里拥了拥,坐在地铺上。两人看着路灯光下雨扯着条下着,街面上的积水四下里流着。呆看了一会儿,邢兰芳感到夜气凉浸浸的,一阵一阵袭人,看着两头儿透凉的雨棚说:哟,这个样子,就是雨停了也冷得睡不成。李伟说:睡不成也得睡,总不能把瓜摊撂下,住旅馆去吧!又说:再说,大夏天的,被子盖上,能有多冷呢?邢兰芳好像不信李伟说的,她说:我看被窝里有个热乎气吗?说罢,伸手去摸被窝,正好摸到李伟手上,赶忙缩回来。李伟这半天一直偎在被窝里,手暖乎乎的,而邢兰芳的手是凉的。她说:人家还怕你冻着哩,没想到狗爪还这么热乎!李伟这时说:你的手咋这么凉?来,我给你暖暖。说罢,一把抓住邢兰芳的手。邢兰芳似乎不愿让李伟给她暖手,下意识地挣了挣,李伟不让她挣脱,把邢兰芳抓得更紧,身子也就顺势挨到邢兰芳身边,然后,猛然间搂住邢兰芳,亲她的嘴,摸她的身……
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李伟白天守着瓜摊,盼着日头快快过去。天一黑下来,便坐卧不宁。夜再深一些,就给邢兰芳打电话。邢兰芳从未拒绝过,看得出来,她也是想着的。她的妆扮也有了改变,头发是用心洗过的,还挽了一个髻。她平时爱穿牛仔裤,但跟李伟约会时,她会换上裙子。一开始,李伟打电话她还接听,时日一久,也就心照不宣,摁断电话,过一阵人就来了。要是邢兰芳不方便过来,她会在电话上给李伟说明。李伟也就安然入睡。
两人在一起,除了亲热,他们还要说上半天话。说过,邢兰芳就起身走了,有时还要睡上一会儿再走。回到农家院,已是深夜,几个房里还是麻将声声,邢兰芳就在稀里哗啦的麻将声中接着再睡。
日子似乎也就这样一日一日地过下去了。
但到了这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李伟给邢兰芳打电话,邢兰芳没有摁断,也没接听,嘟嘟嘟响到头。电话里提示:你拨打的手机无人接听。过了会儿再打,还是无人接听。李伟想着邢兰芳生意忙,或是有别的啥事脱不开身。一直到深夜,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听。李伟就睡了。第二天,一起身想起这事,早早又打电话过去,还是没人接听。李伟这时想的,还是邢兰芳忙,没工夫接电话,但啥事能忙到这地步?又想,或许是电话没带在身上,或者是电话丢了。甚至想,邢兰芳是不是想跟他断了,不好直说,只好不接他的电话?一个一个疑窦存在心里,让李伟无法安心。到了下午,他耐不住性子,瓜摊上也没生意,就开着兰拖去了邢兰芳的农家院。邢兰芳的农家院,平日里门是大开着的,这天,到了门口,门关着,门上十字交叉贴着两张封条。近前一看,上面写着城关派出所封,还有年月日的字样。一看日子,正是昨天被封的。农家院被封了,邢兰芳她人呢?李伟当下没想到别的,只是意识到,邢兰芳出事了,事情还不小。能出啥事呢?他想不明白,就去旁边的农家院打听。那个肚皮晃晃荡荡的胖子,是这农家院的老板,李伟给他送过瓜,两人也算认识,他告诉李伟,邢兰芳被拘留了。
邢兰芳农家院赌博的事情被人告发,让派出所一锅给端了。赌徒们被罚了款,放人走了。邢兰芳被看成是组织赌博的,不仅被罚款,还被拘留了。李伟听了这事,当下脑海里一片空白,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不记得胖老板还给他说了些啥,也不记得接下来还干了些啥,等醒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开着车进入城区了。在一个路口,他突然想去一趟看守所,但又不知看守所在哪,便向一个老者打问。老者抬手给他向东一指,又向南一指,又向西一指。李伟只记住了大概方向,一路开车过来,又向路人打问,终于在县城南环路边找到了看守所。
李伟不知道自己来看守所干啥,他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目光先向看守所投过去,高大的围墙,紧闭的铁门,围墙一角有一座岗亭,上面站着一个值守的武警。再朝四下里看,看到看守所门前的马路对过是一大片庄稼地,庄稼已经收割,但能看出种的是包谷,包谷已经收走,秸秆也拉走了,只留下一地败叶。透过败叶,能看到一排排的秸秆茬子,在阳光下露出白森森的茬口。庄稼地和马路之间有两排白杨树,长得有些年成了,虽然稀落,但一棵棵挺拔高大。这时李伟意识到,他没头没脑地到这里来,是心里放不下邢兰芳,他急切地要找到她的下落。
找到又能怎样呢?接下来,李伟又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就在他踟躇的当儿,看守所门口来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上下来两个人,每人点了支烟,站在车旁抽着。一会儿,看守所大铁门上的小门开了,走出两个人,其中一个蔫头耷脑的,一看就是个犯了事刚放出来的,另一个是警察。抽烟的那个赶忙掏出烟来,给警察递上一支,警察摆手不抽;又递给放出来的那人,那人接住点上,猛吸几口,一大团烟雾在他头上升腾着。警察回身进了铁门。这三人上了车,一溜风走了。
见此情景,李伟突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把车开回了瓜摊。
下一天,摆摊的李嫂和老徐一到巷口,发现情形有异,李伟的瓜摊不见了,印象中,昨天傍黑,李伟的瓜还剩不小的一堆,不可能一夜间卖光,定是家里有事,急急回去了。
有几个买瓜的老主顾见瓜摊不在了,也都失望地走了。
县城南环路这条街是一条僻静的大街,但早晚时分也不冷清,许多人都把这里当作散步的好去处。近些日子,散步的人们看到,看守所对面的杨树下有人摆了一个瓜摊,卖瓜的是个红脸膛的乡下汉子,他把瓜摆在路边,在身后的杨树上扯着帆布搭了一个棚子,看样子晚上还在这儿过夜。时令已是深秋,冷风一阵一阵的,杨树叶子下雨一样沙沙沙落下来,落在路上,也落在他的瓜摊上。散步的人从他的瓜摊前经过,都禁不住要看上一眼。有人走过去,不免在心里笑他,偌大的县城,卖瓜都不会找地方。他们哪里知道,这个卖瓜的人,本意不在卖瓜,他在这秋风黄叶中,是在守候一分情义。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