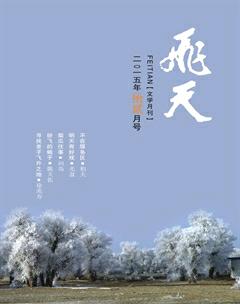寻找老子飞身之地
徐兆寿
引 子
出了兰州城,向南没走几步,就被一座座大山拦住。那就是七道梁。车在山上行走,我往山下看。山下的事物渺小若无。一辆正在作业的大卡车像小孩的玩具车。人如蝼蚁,慢慢蠕动。我不禁感叹,如此大山,古人是怎么翻越的?
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临洮。我们一行四人要去临洮考察。四个人分别是牛爷、老李、姜风和我。牛爷已经退休多年,他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曾与很多历史学家在报端争鸣,但他其实是个不大喜欢写文章的人。他说,他写文章就是看不惯那些人胡说八道。他退休时虽是个副教授,但比我们学校大部分教授都知名。牛爷很牛,人人都敬佩。老李也快退休了,博览群书,爱下棋,爱打牌,也爱喝酒,就是不爱写文章。他说,天底下没有他没看过的书。牛爷不信,老李说,那你可问我什么书我没看过。牛爷偏偏不问,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孔子那时候书少,就那一点点,他就以为都看过了,但他为什么去向老子问礼?说明老子比他看过的多些。老李张着嘴笑着说,也对,也对。姜风是我们新入职的老师,因其父亲是省上的某位高官,临洮的这个项目是她请我们去的。之前我只听闻牛爷的大名,却很少与他交流过。老李则是老朋友了,常常无话不谈。姜风找老李,老李便拉了我和牛爷。
关于临洮,我很早的时候就想去看看。著名的马家窑彩陶就出土自那里。据说,彩陶产于一万多年前。第一个制陶的模具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但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也发现了同时期的彩陶,甚至中国的彩陶工艺在后期更为成熟,其美轮美奂之灿烂,使发现者瑞典的安特生难以置信。后来在古希腊的爱琴岛上也发现了彩陶的碎片。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看上去充满着巫术思想的泥器因为火的亲吻,成为了那个时期文明的象征。这个被称为彩陶的器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为全球所共享。
从彩陶的传播和使用,就可以看到那个时期已经在进行全球化运动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抛弃那个充满了冰冷色彩的名字——新石器时代(晚期)——而重新将那个时代命名为彩陶时代?至少这个命名在我看来是充分地尊重了人类的创造,它一下将那个时代点亮了,有了华彩,不再蒙昧。新石器时代,这个命名在我看来,是将人类工具化了:它把我们人类的心灵活动视为乌有。事实上,在那个看似黑暗的时代,人类自身的灵性却是极为发达的。那个时期,山川大地之神都活着,与人类息息相通、水乳交融。从一切巫术与泛神化的萨满教等人类早期精神活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只是被我们想当然地否定了。这个否定是那样粗暴、愚昧。这个否定是基于今天人类自身器物的感受为中心,而不是知人论世、以心换心地触摸、交流、相和、微笑、通达。因此,我时常想以祖先的名义呼唤众人对11000年至4000年的这段历史命名为彩陶时代。
然而,何以那些用浓彩画着水波纹的彩陶、那些世界上工艺最发达的彩陶,竟然出现于中国的马家窑一带?
我曾经在甘肃省博物馆里看到那些像是青春女子的眉毛一样油亮的彩陶,也看见过它的衰落期——半山和马厂彩陶的色彩衰败,仿佛女子老了的样子。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叫马家窑的地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文明景观?于是,我总是想去看看现在的马家窑是一种什么样子。
我哪里想到,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临洮县的人来请我们去策划老子纪念活动。我问,临洮与老子又有什么关系?他说,老子的飞身之地就在我们的岳麓山上。
这令我大吃一惊。就在我身后100公里左右的地方,那个我以为很熟悉的地方,竟然藏着这样一个天大的历史之谜。
老子到底去了哪里
很多年之后,我想起那个秋天的下午,我们一行四人随着临洮文化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上岳麓山去看老子的飞身之地。牛爷走在最前面,背着手,什么话也不说。后面是老李,总是在说话。那位讲解人员似乎主要是为他在讲解。姜风跟在老李后面,不停地感叹。有时候,老李觉得讲解人员说得不合适,便要纠正几句,甚至禁不住自己当起了解说员。往往在这时,牛爷便说,你让人家给我们讲,你认真听。我们都笑。我记得我一直走在最后。我在不停地拍照。临洮上空不时飘来几片白云,使我总疑心有什么神仙前来观看。已是仲秋,天气已经开始凉爽,而岳麓山上的秋阳却是暖暖的。我还要不时地钻到柏树或松树下躲避秋阳。山上的亭台楼阁多是新造的建筑。据说,这是按宋时所建东岳泰山庙仿建的。介绍者说,老子就是在这里育化百姓的,于是,我便想象老子当时教授学生们的情形。有一超然亭,立于台上,遂见山下洮河从远处逶迤而来,又绕着临洮城缓缓而过,仿佛是活动的玉带。老李看了后对我说,这是最好的风水。我那时还不懂这些,只是听听。又有一凤台,说这就是老子飞身之地,所以凤台上建有一飞身阁。立于凤台前,有人告诉我们,老子当年看着对面之山或明或暗,便拿起笔在空中点了几下。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对面之山明暗分明,两山互衬,宛若太极图。
我站在那里,向远山看了一下,两座山确像阴阳互抱,酷似太极,于是拍了几张照片下得山来。
那次考察未能去了马家窑遗址,于是,找一机会又去。马家窑遗址上空空一片,踪迹全无。四面的风在静静地吹向那个小山丘,田野上唱着旷古的歌谣。但我们听不懂。那天傍晚,我又一次在岳麓山下徘徊良久。
我似乎想在那里听到一些玄妙之声。或许盼望冥冥中能与什么风云相会。但什么都没有。四野寂寂。我驱车而回。很多年之后,当我想起那两次去谒见岳麓山的情景时,我在内心中对着自己苦笑。老子之时,只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并未创教。东汉张氏创教,才奉老子为教宗。老子在那时何以能点太极?又何以能飞身?
以后人之需要来确定前人之行为,怕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吧?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在我数年后突然转过来的。临洮的人们大概还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个转变并不能否定老子在这里可能存在育化行为。同时,它使我进一步在想,甘肃和新疆其他地方还有老子的痕迹吗?
我们不得不回到太史公那些言简意赅的叙述了:
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今天来看,这短短的叙述简直就是一篇极好的微型小说,也是一篇非虚构写作。卡尔维诺若是看到,也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关于老子本人及老子的去向,自古都是谜。司马迁只说了三个人,还对他的年龄也说不准,一说是两百多岁,一说是一百六十岁。自庄子始,经司马迁,再经道教的创造,到了宋朝的《太平广记》中,老子就成了另一个形象:神仙,道教的宗师,随时可以存在人间。上面说,老子不同时期来到人间,以教化圣人,从而育化人间。老子在周文王时就任守藏吏,在周朝呆了三百年。所以,他出涵谷关时,随从徐甲就不大乐意了,想留在中国,不想跟老子去安息国,但是他又没有钱,于是,便写信给关尹喜告老子。状子是一位专门人士写的,那人一看状子上老子欠徐甲七百二十万钱的工钱,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徐甲。那人哪里知道此时的徐甲都已经200多岁。关尹子将此事告诉了老子,老子很生气,说你早就该跟你同时代的人一样死了,我当初官阶卑微家里也没钱,连个替我打杂的人都没有,就雇了你,同时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给了你,所以你才能活到今天。你得了长寿,这已经是别人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东西了,你为什么还要告我呢?我曾给你说过,到了安息国,我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全数还给你,你怎么现在就急不可待了呢?说完这番话,老子就让徐甲面向地下张开嘴,《太玄清生符》立刻被吐了出来,上面的字迹还像刚写时一样鲜艳,而徐甲则顿时变成了一具枯骨。关尹喜知道老子是不同凡响的神人,能使徐甲复生,就跪下磕头为徐甲求情,并自愿替他还债。老子就把那《太玄清生符》又扔给徐甲,徐甲立刻复活了。关尹喜给了徐甲二百万钱将其打发走后,又向老子执弟子之礼,得到了老子长生之道的秘方。他又向老子请求更进一步的教导训诫,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他将老子的话记录下来,形成了《道德经》。
这篇关于老子的记述简直就是司马迁对老子的那一段记述的详细叙述,并加入了玄幻色彩,使老子成为神仙。
因为这个原因,道家弟子对老子的想象就格外多了一些,这就出现了几部非常重要的道经,一部是《开天经》,另一部是《老子化胡经》。佛教被涉及了。于是,是非也就来了。从北魏到元代,以皇帝或朝廷的名义,道教和佛教进行了多达十五次的辩论,大多以道教失败而结束。民间的争论大概是日日皆有。
晋代道学家葛洪对老子的评价也可一观:“洪以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入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羲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
临洮岳麓山上的这个庙虽是道教庙宇,但与道教走了别样的路。它让老子有了一个确切的归处。这里的学者们经过考评,认为老子翻越陇山后,便进入“夷狄”地区的天水、武山、渭源、狄道,到达河西走廊的流沙、居延泽一带,旅游传道达十七年之久,然后原路返回狄道,最后在临洮逝世。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免不成道理。中国文化始于易,易由伏羲氏所创,而天水一带相传便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传说与地理学上的证据,比如有一座卦台山。天水一带还有尹喜庙,传说老子与尹喜在此传道。如果我们猜测,老子辞周,到西戎之地来便是要探访伏羲氏之遗迹。至于到安息国或昆仑之地则是另外的猜测,到底有多少根据则不知。
临洮本地的学者还从民间传说或节会中考证出老子飞升的日子正是农历三月廿八日。每年这一天,临洮全县各地的父老乡亲及道教信徒,都要在岳麓山举行盛大的纪念老子活动。民间传说这一活动始于三国之时,至今已经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
似乎是证据凿凿,难以辩驳,尤其是史书上对老子西去之后毫无记载的情况下,这些证据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下山的过程中,有人告诉我们,岳麓山下有好几个村子的人都是老子的后代,他们都姓李。我读《史记》,关于老子后代的记述总觉得别扭,因为既然不能确定老子是谁,怎么会有其明确的后代呢?史家在记述时应当再慎重些为好。
在那次考察之后的七八年间,我一直在关注临洮关于老子的研究有无新的发现,但毫无动静。在这七八年间,我也一直在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与佛教传播,想从其中找到蛛丝马迹,但得到的资料并不能准确地证明老子去了哪里。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因老子的思想与佛陀的思想相近而大胆猜测老子来自西域,所以他晚年一直想去西域,同时,老子受早期婆罗门教的影响,在晚年就必须隐遁山林。我对这些也进行过研究,发现中国在上古时期就已经通过玉石之路或草原之路与西域发生着密切的关联,文化上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大可先生过分强调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很少提及中国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他的这一猜测也很难说服我。我对北魏以来佛道两家关于《老子化胡经》而进行的十五场大辩论也逐一进行了研究,发现佛道两家确实存在着诸般因缘,但老子去西域教化佛陀一事则纯属道教弟子臆测并杜撰。我在《鸠摩罗什传》中有专门论述,在此就简而言之了。
黑格尔之后有一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写了一本《大哲学家》,第一次对东方的哲学家予以尊重。他考察出孔子约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前479年。他也考察出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560年,卒于前480年。孔子与佛陀去世的时间竟然那样相近,而他们出生的时间同样相近,如果他说的没错,佛陀比孔子早出生九年。也就是说,佛陀与孔子完全是同时代人。
然而,雅斯贝尔斯却无法知道老子的生卒年月。我们只能通过老子与孔子的交往来确认这件事。有人认为,《论语》中从未提及孔子拜见老子的事,所以孔子要比老子早。但在《礼记·曾子问》中孔子多次提到老聃,说明《史记》中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是确有其事。如此,我们就可以来推断他们的年龄。老子至少比孔子要大一辈多,甚至两辈。也就是说,老子比孔子要大至少二十岁甚至四十岁以上。庄子说,孔子见老子时已经五十一岁了。如此说来,那时的老子定然在六七十岁。
有人已经研究出周代官员七十岁退休。那么,老子是退休之后才去的西方,还是未退之前就去的西方?显然,应当是退休之后,否则一个那么大的官员莫名其妙地跑了,朝廷是不会轻易不查的。另外,按照老子的行为方式,也不会冒那样的险。他必然是从容不迫地去了西方。所以,定然在七十岁之后。
由此可以推算出,老子至少要比释迦牟尼大十多岁。按庄子之说,孔子拜见老子时已然五十一岁了,说明那时的释迦牟尼已经六十岁了。六十岁的释迦牟尼已经名满天下,弟子遍布印度诸国。说老子点化释迦牟尼成佛,那必然是释迦牟尼三十五岁时发生的事,那时孔子才二十六岁,离拜见老子还有二十五年之久。那时的老子还在做官,离退休也还有至少二十五年。说不定孔子拜见老子时,老子已经七十五岁甚至八十岁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老子去天竺时,释迦牟尼已经七十左右了。
就算我们对那位老是爱虚构的庄子的话不信,那么司马迁的论证至少可以确信。司马迁认为,孔子是三十多岁与鲁人南宫敬叔一起去拜见老子的。即使那次之后老子就离周而去,到达西域时释迦牟尼也早已悟道成佛了。何来老子点化释迦牟尼之说呢?
假如依《开天经》和葛洪所讲,吾辈中人真相信道教之学说,就不应该执念于老子是谁、老子生于何时或死于何时。故而临洮老子飞升之地的传说虽有诸多疑点,甚至有与后世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老子飞升之地其实是后世人猜测的。假如按民间风俗纪念老子逝世,以农历三月廿八日为纪念日的话,就可理解为老子飞身之地正是老子羽化之时。
虽然这些证据还不能满足历史学家们的苛责,但至少可称为一家之说了。
老子的老师是谁
在第一次去临洮的路上,我看着万山重重,顿生忧伤。“道阻且长”“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令人伤感的诗句莫名地跑到嘴边。人心在这苍茫之间太脆弱了,太无力了。人们都说,不必为古人忧。我却偏偏为古人犯愁。据说,那时候要翻过这些山,至少要七天左右。要见一次心上人,多难啊!翻过这重重大山,每一步都渗透着思念和幻想,但也有可能被虎狼吃掉。吃掉就吃掉,也改变不了翻越大山的信念。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来人们就是这样走过的。这么漫长的路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是多大的讽刺!古人为一个信诺,就要翻越这千山万水去兑现,但现在有了手机,大家不需要信诺了。谁曾听说过现在人对天发誓的事?它是好呢,还是不好?我纠结于这些古今的变化,只听老李与姜风在交流。
老李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神秘人物。他是实有。其他很多人都是传说。但是,老子又与那些传说中的人一样最终都成为传说。你不知他的来历,也不知他的去处,只知道他在人世间溜达了一圈,把人世间冷冷地看了一眼就走了。奇人一个。”
“是啊。但如果没有关尹喜的强迫,他也不会写下《道德经》,人世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典,那可如何是好?”姜风说。
“所以说,这些人是应运而生。西方有位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发现,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500年间,在世界各地突然出现了一群先知一样的人物,而且这些地区在那时相对封闭,互不来往。比如,中国与其它地区来往很少,突然间就出现了老子、孔子和孟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龙树等,希腊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很多哲学家。在他们之前,人类处于黑暗时期,漫漫长夜,突然之间,他们神奇般地降临到世界各地,创立了属于他们那个地区的宗教、哲学、伦理,至今,人类还在依赖于他们的思想。”老李继续说。
“但我一直在想,你说这些人突然降临于大地是不是有某种玄妙?”姜风对老李说,“比如孔子,在他之前,很多学说没有人在意,如仁,他忽然提出来了,这世上就有了仁。还比如老子,在他之前,有谁提过道这个概念吗?谁还有他那样的思想吗?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坐在他们的后排,欲说又止。他们的谈话非常有意思。突然,一声冷笑从最后排传过来:“怎么可能没有出处呢?孔子都有自己的老师,说自己向周公学习。老子也一样,怎么可能没有老师和出处呢?”
大家都愣了。冷笑者乃牛爷。半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被他的这几句话打愣了,都在寻找如何对话。大约半分钟后,老李终于红着脸问他:“那么,他的言说出自何师?”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这么一问。因为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便没人回答了,但并不是问题不存在。”
我也终于找到共鸣,便补充道:“还有啊,你们前面说的老子被迫写下《道德经》一事,也就是马司迁那么一说,那也是按照老子《道德经》上的说法推出来的。谁能保证老子不是提前就写好了的呢?今天我们看起来那样有章有节的,如果当时只是随意口述,能有这样优美的文言?那些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的成语,难道就是他脱口而出的口语,而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关尹喜也是道家人物,据说后来跟着老子出关了。连他的行踪都是谜,又怎么能说老子就是被迫而写的呢?谁能作证呢?”
老牛一听,谈话的兴趣上来了,他把身子往前一靠,说:“是这个问题。司马迁写的《史记》,说是历史,其实很多都是传说,比如五帝本纪,都是民间传说,根本没有今天我们的考古证明。你说它是历史呢还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文学创作?老子也一样。再说,如果按照道教的说法,老子是从上天下来的传教者,每一次来到人世间都要传一部经。他是有备而来,或者说必然是要来传道的,而这道便是《道德经》。即使没有关尹喜,也会有朱有道什么的人来将此经传下去。我的意思是,《史记》中的这些说法其实靠不住……”他滔滔不绝地继续讲下去。我原以为很多问题只是我个人的问题,那天我才发现,那些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在思考,只是无力回答而已。
那么,老子的老子又是谁呢?他的学说师出何方?我查阅了相关的典籍后发现,第一个发问的不是我们的牛爷,也不是我,而是那个爱打比方的南方人庄子。他问过自己后又答道:“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也,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他的意思是,老子师承古之道术。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承认:“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和孔子之时的人们也许知道古之道术是什么,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新的问题便来了——何谓古之道术?孔子有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且明确说自己继承周礼,因为它不但有史可查,而且文质彬彬。那么,老子又凭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直在迷惑我。我不停地阅读古人关于老子学说出处的论述,但不知是我查阅的方式有问题,还是认为不必去问,总之少有人述及。有人说,老子思想有可能出自佛教之前印度的婆罗门教或印度史诗的影响。但是,我始终对庄子的说法持肯定态度,即中国古之道术。孔子继承的是周代的东西,老子继承的大概是周代之前的道术。
然而,周代之前的道术有什么呢?我想到文王推演八卦成六十四卦的事,又想起庄子、司马迁以及《太平广记》中老子对孔子的几番话。其实,它们合起来就是一番话,意思是天地本身自有大道存在,现在,你提倡的仁义会扰乱人性,不如舍弃。尤其是《太平广记》提到了《易经》,可摘来一观:
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
曰:“易也。圣人亦读之。”
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子曰:“蚊虻噆肤,通夕不得眠。今仁义惨然而汩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照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
老子问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使道而可进人,则人莫不进之其亲矣;使道可告人,则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传人,则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道不可居也。”
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诵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甚矣人之难说也。”
老子曰:“夫六艺,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陈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陈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岂异哉?”
这个故事有很大的可疑性。如果是真的,那么一定是孔子在七十岁左右见老子有的这番对话,但在司马迁和庄子的记述中,都没有这些言论。庄子认为孔子是五十一岁去见老子的,而按这个年龄说的话,他尚未去列国游说诸王,何来“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所以,此番对话不可信。但是,从道家的编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即老子的学说与庄子的学说之差异重点在于《易经》的不同理解上。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去考察老子的《易经》和孔子的《易经》之区别。显然,孔子遵从的是文王创制的六十四卦,即《周易》。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被崇侯虎陷害而被殷帝纣囚禁在羑里整整七年,狱中正好有时间,便潜心研究易学八卦,通过八卦相叠从而推演出现在《周易》中所记载的乾为天、坤为地等六十四卦。文王从《易经》中既能找到在狱中仍然安身立命的大道,同时,也可以此来预知自己的命运。真乃祸福相倚。反过来说,如果文王没有七年的牢狱生活,又怎么可能有《周易》六十四卦?孔子在陈蔡之间,在各种不快之间,大概都可以拿《周易》和文王之命运来为自己助力。恰恰也是,如果孔子大红大紫,去做大官,没时间搞教育,哪里又会有时间著《春秋》、注《周易》、编《诗经》、正礼乐?一个在官场上失败的孔子,才以另一种沉甸甸的文化集成平衡了他的命运。此乃真正的大命。后世诸多有大成就的文化人不也如此吗?
那么,老子呢?老子显然对孔子的做法甚至文王等圣人之法不大赞同。从他流传后世的《道德经》来看,他认为文王如果懂得天地之大道,就知道自己必须处于水之下游,韬光养晦而不作为,那样就不会去改变世界,也不会有牢狱之灾,至于《周易》,强行加入很多义理,改变大道的方向,更是不应该了。对于孔子要强行为《周易》加入仁义,他更是不赞成。那么,对于孔子之命运,老子认为完全可以避免其流浪之命运。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的那些话:“表现得太聪明,看上去像是洞察一切的智者,反而离死不远了,因为太聪明便喜欢议论他人的不足会招致杀人之祸。广博深厚善于辩论者,反而危及其身,也是因为善于揭发别人丑恶的缘故而会有不测。”
所以,老子一定有孔子所不能理解的另一道术,或者那就是文王之前的世界观,即庄子所说的古之道术。
那么,那时的古之道术《易经》是什么样子呢?
传说中的河图、洛书?抑或从黄河上游飘来的龟甲上的洪范五行?都应当是。它们显然都是古之道术。但我们找的应当是与《周易》最近的易术。
这就不能不谈到《周易》之前的《连山易》和《归藏易》。《三字经》曰:“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但现在《连山易》和《归藏易》已失传,不得而知,只能从古人的一些推测中去理解一二。《连山易》的意思是“如山之出云”,据说此易由炎帝所创,也有他说。《归藏易》一说是黄帝所创,另一说是大向所创。《连山易》是以艮卦为主,说明那个时代被大洪水所扰,山便成了最重要的象征。《归藏易》是大洪水退却、黄河被治理后进入农耕时代的思想,所用的易以坤卦为主,坤是纯阴,一切阳能“归藏”到纯阴的境界里去了。而《周易》面对的主要是人与天地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便以天为主,即以乾卦为主。以此推理,男人便成为社会的主宰。如果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母系氏族社会,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连山易》与《归藏易》所创制的时代还属于母系时代,或者是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的过渡之中。
按照这个推理,孔子所继承的恰恰是以阳性为主的《周易》思想,于是也就有了其积极推进仁义理想的行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便是孔子思想的真实写照。而老子所继承的恰恰可能是《连山易》和《归藏易》的思想,尤其是后者思想,即以阴为主,将阳藏于其中。一部《道德经》不就在阐述这种思想吗?《易经》中云,“一阴一阳为之道”,中国文化中老庄之道代表的是阴性文化,而孔孟之道甚至墨家思想代表的是阳性文化,老子和孔子合起来才是真正的《易经》,所以孔子至死也无法真正通晓《易经》,按道家的说法是在《易经》中强加了仁义思想。然而,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也无法成为十全十美的治世理论,道家的理论往往只能行一时,如文景之治,但马上面临的便是动乱,此时大家需要儒家来出面。对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他们的心中始终端坐着两个人,达则兼济天下时便是孔子,穷则独善其身时便是老子。他们互相依存,互相印证。
为了印证我这样的猜测推理是有道理的,我又在浩瀚的史料中寻找能够证明的材料。终于找到了一位。他与老子一样,也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就是20世纪初的国学大师柳诒征。他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写道:“实则老子之思想,由吾国人种性及事实所发生,非其学能造成后来之种性及事实也……老子之书,专说对待之理,其原盖出于《易》。惟《易》在孔子未系辞之前,仅示阴阳消息、奇偶对待之象,尚未明示二仪之先之太极。老子从对待之象,推究其发生此对待之故,得恍惚之一元,而反复言之。”“老子既知此原理,见此真境,病世人之竞争于外,而不反求于内也,于是教人无为。其教人以无为,非谓绝无所为也,扫除一切人类后起之知识情欲,然后可从根本用功。故曰:‘无为而无不为。”
柳诒征这一论述与古时情状基本吻合。的确,在老子看来,当时流行的知识都与本质相去甚远,所以学得越多,与道之间的距离就越远。他要求人们抛弃这些陃见,去寻找真正的道。
老子之于历史的态度与孔子有大不同。孔子执著于能证明的历史,且是文字等固化的历史,与今天的历史学者有相同的史观。周之历史当然是清楚的了,所以他从周开始。虽然他也常言三代之前的历史,但总觉得渺不可信。老子是一位史官,恰恰越过历史看到的是世界之初和世界之变化,所以老子所言者形而上学。他强调人之本原、人之纯正,万事万物都有明灭之时,因此他以为不可妄为。人所有的问题来自人的聪明。“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但古人治世并非用智,而是用道,“非以明之,将以愚之”。知此两者,就是懂得了玄德,天下也就“大顺”了。
最近我看到一些资料,有学者称在《连山易》与《归藏易》时,还有一种易没被大家认识到,即《水书》。这也是失传的《易经》。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了。不过,老子在《道德经》中恰恰对水有很多的阐释。如“强者示弱,大国必居下游”,“善用人者为下”。老子以为“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众人都讨厌的处境,恰恰是最能保全性命,与智无关,而道共在的状态。同时,“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故能为百谷王”。百川归海,正是因为海是最下游的存在。这些论述正是有关水的理论。
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水书》的哲学呢?
无论如何,我们虽然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老子的师者乃古之道术《连山易》、《归藏易》、《水书》甚至河图、洛书等,但至少可以猜想那个时候影响中国人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些思想。借此,我们也触摸到了古人幽明玄妙的智慧。它恰恰将我们从目前那些呆板的知识中拯救出来,去旷野上重新观察天地之变化、山川河流之走向以及万物的生长。
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就是善的,也不知道大地向哪里延伸便是有利的,我更不知道地底下的幽冥存在。这些我们今天的人都已不关心。但是,每当我在考察古人之道术时,便发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远超过今天。他们既要观察星空之变化,又要以通灵的方式洞悉大地、山川、河流等诸神的意念。我们对天体的认识已然陌生,天体在今天是死亡的星空。他们还在通往幽冥,在认识我们想当然就否定了的多维世界。这世界于他们是活着的天体、大地、山川、河流、万物。他们最初与世界的交流是通过心灵。然后,他们开始有了知识,甚至有了思想和文字,便告别了那个灵的世界。那些原始的巫术告诉了我们这一切。
然而,人类是要完成自己的脱胎换骨,要成为主宰世界的主人,便拥有了后来的一切。这种主宰的意识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意识。世界成了客体,成了他者。从那个时候起,人类就已经告别了世界。天空越来越远,大地越来越陌生。山川、河流不能再对话。
如果说伏羲的先天八卦、河图、洛书包括失传的水书、《连山易》、《归藏易》等,都是人们描绘天地、山川、河流运行变化的智慧之作,那么在那些智慧中,人们往往是顺势而为,将自己藏于自然的变化之中,把自己完全地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是,《周易》改变了中国人智慧的行程。它一方面把家长制思想和男权思想固化在里面,使阴阳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把仁义、君子意识固化在其中,力图使这些思想成为易经中不变的坐标。在老子看来,这些行为可能是不恰当的。
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在那次与老李、姜风以及牛爷讨论过后,虽然我们也时常相见,也为一些事讨论得热火朝天,但竟然谁也没再讨论过那天提出的问题。那些深沉的问题只能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产生,此后,便是像我这样孤独地思考,并以文字见诸世人。它不敢在现实生活中曝光。
中国第一个私人写作者
不知后来那个项目是否结项,总之我和牛爷、老李什么都没做,只是应姜风之邀吃过两次饭。吃饭时姜风听我们谈过一些想法,我还说要多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让全天下的人都来讨论一下这里是不是老子的飞身之地。我不记得牛爷和老李有什么好的想法,但我还记得他们两人的对话。
话题是姜风引起的。姜风在饭局结束时给我们每人给了个信封,说里面有我们的考察费。老李摸了摸厚度说:“姜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做,就是跟着你转了转。下次有什么好处可还是要记得我们啊。”
姜风笑了笑,对老李说:“李老师,这是应该的。下次我们去你们老家凉州吧。对了,也是徐老师的老家。”
是的,老李跟我是凉州人。他们李家在我们凉州可是世家。他们的祖上有好几代人都在外面做大官,晚年时又回到凉州老家,直到老死,再葬到凉州城西边的戈壁上。老李也是书香门第,只可惜不喜欢写文章。
老李笑道:“好啊。下次你们去凉州,我可做一次真正的导游了。兆寿当然也可以,但可能不如我了。是吗,兆寿?”
我笑道:“当然了。”
老李笑道:“我可是从小在文庙里长大的,哪个殿哪块匾我闭着眼睛都能说得上来。武威的文庙可是全国四大文庙之一。八十年代我上大学时,一到暑假我就回家,回家后就被父亲派去给台湾人和日本人当讲解员。那时候台湾人日本人都喜欢敦煌,要去敦煌就要经过凉州,那就要看文庙。”
老李比我大六岁,见过的世面比我大得多。于是,大家便说起了孔子。他对姜风说:“我喜欢孔子的述而不作。你看,孔子多大的学问啊,但他自己只是传承,并不写作。释迦牟尼也一样,苏格拉底也一样。那时候,那些伟大的圣人们都是人世间的教育家。他们自己不著书立说,他们的话被学生记录下来。”
我笑道:“你也是述而不作啊。”
老李大笑道:“啊,啊,啊,我,我是,我是有些述而不作。”
此时,我们就听到牛爷冷笑:“什么述而不作?《春秋》是不是他写的?”
老李说:“只能说编撰。”
“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编著一样,他把很多内容删去,留下与他自己主张一致的内容。这难道就是作吗?”牛爷说。
“这个……这个……”老李笑着。
“我们还要想一想,他还从一千多首诗中挑出来三百零五首成为《诗经》,还和学生们一起对《易经》的《系辞》等进行过编撰。这是不是作?”
“可他没写啊?”老李终于忍不住辩驳。
“是没写,但是述而作,不是不作。还有,既然学生们可以编辑成《论语》一书,后世又有争议,为何不像老子一样干脆自己写一部《论语》,也免得很多问题述而不清?”牛爷生气地说。
“人家是圣人,怎么能像你说的一样功利?”老李也有些生气。
“什么是功利?利于自己是自私,利于他人利于国人是贡献,这也叫功利?那他为何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诸侯?那不是功利?万物生长,要开花要结果,那也是功利。你让它不开花不结果,那就没有功利了。”牛爷瞪着眼睛,拍着桌子说。
他最后的几句话甚是厉害,把我也一样说服了。但老李才要与牛爷争辩,他说:“万物生物,是自然而然的事,不像人心里有功名,所以就有了功利。”
“你不是万物,怎么就知道万物心里没有功名?你看那植物,弯弯曲曲的,无论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不屈不挠地拼命生长,它没有意识?它一定是要活下去,并活出个鲜活来。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众生都有轮回,都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不了解众生,我们只了解自己。人如果没有功利,会怎样?佛教徒的功利先是满足其世俗心,但慢慢地就开始修行,最后是要有所目标的,即下一世要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最终成佛。这是大功利。菩萨的功利就是利益众生,普度众生。道教呢?一样,要成仙,要长生不老。老子和庄子呢?是人修道。各有各的功名,只不过在对待功名与欲望的方法上各有各的修行法则。反过来讲,如果佛教徒不谋成佛,还要修行吗?不会。基督教徒也一样。我们老是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批判佛教和道教,说中国人太功利。基督教徒们的功利就是要进天堂,如果失去了这个上帝的功名,他们还信上帝吗?还要去爱别人吗?”牛爷越讲越激动。
老李说:“你说得太多了。我是说,什么都要顺其自然,不要太强求。这就是不功利。”
牛爷说:“你说的这个,也是有价值观在背后做支撑的。你对一匹狼说,什么都要节制,狼会听明白吗?”
老李只好摇着头,举起空了的酒杯说:“胡说了,胡说了。”
牛爷也举起空着的酒杯,对着我说:“兆寿,你是作家,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看过你写的一篇叫《老子是第一个私人写作者》的文章。你来说说。”
我惊讶而尴尬地笑着说:“你竟然看过我那篇文章?”
牛爷笑道:“我是爱看有些特别的文章。”
我笑道:“好吧,我在你和老李跟前班门弄斧了。我的问题是,老李说的孔子述而不作的观点其实与他一生积极作为的思想是矛盾的,而老子强调的无为和隐士的思想又与他写作《道德经》相矛盾。是吧?既然是无为而治,在他的时代,没有人写过那样的文章,他为什么要写?这不就是有为吗?这不是显示自己吗?虽然司马迁说他要隐去才被关尹喜强迫写下这些文章,但仍然是矛盾的。”
牛爷点着头对老李说:“听听人家,这就是问题意识。不客气地说,你说的那些东西书上多的是,人云亦云。我是直说啊,你不要生气。所以,你懂得很多,但没有过人的思考。你看人家兆寿,就看出了矛盾,这就有意思了。那么,你告诉我们,为什么老子是天下第一个私人写作者?”
我尴尬地看了看老李,见他眼睛都有些红,就又要了一瓶酒,给他们斟满,说:“来,我们边喝边说。老李,我真是班门弄斧,说得不对的地方,你可多批评。牛爷就这德性,喝多了。”
大家便碰杯。我干了这杯酒后,开始讲我的理由。
好几年过去了,我还一直记得那次探讨的热烈场面。很多真诚的探讨就是在饭桌前,在酒后,在不经意间,而课堂上或会议室里的辩论都充满了假相。七八年过去,我离开了原来的单位,而牛爷也早已被儿子接到海南去享受天伦之乐了。老李快退休了,常常来找我聊天,他还是老讲师,临到退休时觉得有些后悔,因为讲师的退休工资太低了。我说,你才牛呢,哪个人看过你那么多书?哪个人甘心讲师退休?他一听,便一定要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他给牛爷打了电话。姜风在我们从临洮回来不久就考上博士去北京了,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她有时候会给我的微博上留言,说在哪里又看见我的书了。
我很后悔那次没有录音,事后整理总是觉得当时的谈吐是那么精彩,而靠回忆整理出来的文章读起来如同嚼蜡。但我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重新回答牛爷的问题了。
首先,我得讲讲老子、孔子生活的背景。这很重要。它是一切知识、话语、行为展开的场域。
我在讲西方文化史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即早期文字的使用情况。世界上所有的地区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文字乃神所传授。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诞生的楔形文字几乎没有个人的色彩,都是国家或皇族记述国家大事及最高事务——祭祀活动。古埃及人认为他们的文字是月神、计算与学问之神图特(Thoth)造的。人们对失去的玛雅文明也不甚了了,对文字更是无法相认,但据极少的研究者称,他们似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说这些文字或符号与祭祀有关。
中国也一样,《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乃史官,黄帝命仓颉造字,也是为记述国家之大事。一旦文字诞生,便为国家所有。所以,知识、教育的拥有者都为国家。国家的拥有者——那些最高阶层的贵族便是最早能接触知识和教育的人。
中国在三代之时,学术、知识、文字都为国家所有,私人基本上不允许独立创作。我们可以从孔子编的《诗经》中看出来,除了一百六十首“国风”是记录十五国民间流传的歌谣外,剩下的便是“雅”和“颂”,都是为国家而书写。即使国风中有文人创作的痕迹,也不会留下作者之名。但是,从国风中的那些讽刺诗可以看出,文人创作已经成为一种潜在写作。这种被压抑的创作情绪一直持续到春秋之时才随着周室的衰微而爆发出来。
司马迁在记述孔子时写得很明确:“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礼乐之废,说明国家伦理混乱,天下人心不稳,而诗书之缺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知识和学说都到哪里去了呢?流落到了民间。学术下移至民间。民间知识分子获得了知识,获得了独立思考和阐述自我主张的可能。这两个条件加起来,便促成了民间学术的兴起。所以孔子才诞生,也才有百家争鸣。庄子也感叹:“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就是说,百家争鸣之时,正是私人写作真正兴起之时。
那么,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这大概来自于他对礼的认识。
因为孔子知道,过去知识和学术都为国家所有,诸侯和个人是不允许写作的,所以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承先王之制和周召之礼。他是顺着前代人的言说,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传承,而不是创新。
然而老子对那个时代的学说是有看法的,甚至持反对态度,所以他要言说,就绝非传承,而是创新。老子与孔子、管子等的不同在于,他超越了所谓的圣人之道这个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站在了更高的价值立场来言说,自然就超越于整个时代之上了。
记得当我说到这里时,牛爷破口而出:“那么,为什么孔子不敢创作,而比孔子还大的老子敢于创作呢?”
这也是矛盾所在。《史记》和《礼记》中都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载。既然他们都是遵守周礼,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原因是对礼的理解不同。这可以从其《道德经》中看出。前面我们对其思想的来源之论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老子之创作确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确是到快隐世之前创作的。事实上,在老子和孔子之时,私人办学已然兴起,私人言说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只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便是诸子之文而已,大多私人创作都已消失了。
其次,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独立创作的形而上学。我们也许会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伏羲是中国第一位知识分子,因为他创造了八卦。我们还可以说,仓颉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创造了文字。但他们都不能算是真正独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创作,而带有浓厚的集体创作的痕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周文王在狱中对《易经》的发挥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创作呢?自然也可勉强来这样说,但他们是帝王,还是代表了国家创作。个体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第一位只能是老子。
如果说《易》乃中国哲学之发端,但《易》之深奥,常人难懂,应该是上古学说。所以,真正的古代哲学应以老子为开端。柳诒征也说:“是则吾国形而上之哲学实自老子开之,亦可曰一元哲学实自老子开之。”在今天我们能读到的人类所有的古代哲学、宗教典籍中,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轮廓:人类早期的思想成果不是对人伦道德和政治的创见,而是对自然观察的总结。这也就是弗雷泽等所说的“古代原型”。人类学家发现,人类最早对大地、天空、太阳、黑暗以及四季的轮回都有一种认识和神化,最后演变为宗教。这就形成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模式。对自然之道的认识与总结也是人类早期的哲学。中国的《易》、八卦思想、洪范五行学说等都是对大自然运行的理解和注释。
海德格尔称,人类早期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为大地和万物命名。那时,人类与大地是浑然一体的。大地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的家园。所以人类不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而是以大地的意志为意志,人类要崇拜山川、河流、大地、太阳。人类的意识是如此之高大,视野是如此之壮阔。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开发,人类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离开了大地。如此,人类与大地之间的冲突也就产生了。现代社会其实也就是人类与大地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人类脱离了生育自己并给予自己诗意和幸福的大地,人类便面临被异化和痛苦的现实。老子的哲学在那个时候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最根本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道术。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老子之学说直接师承上古道术,并开古代形而上哲学之先河。
最后,还有一些小小的障碍。有学者认为,老子之前有管子之学,管子之前有周公,周公之前有大禹,大禹之前还有无数的圣人。然而,周公与管子实际上属于官学。他们的位置大体都差不多,属于相国一职。其所著者自然也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写作,虽说周公所著《周易》爻辞和其它一些篇章以及《管子》中所体现之思想都乃个人之体悟,到底仍然也是个人之立场。但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所处之时代并非私人写作之时。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们在以国家身份写作。当然,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应该说是私人写作之萌芽。真正开一代私人写作之风气者,应该是诸子百家,而在百家之中,则首推老子。老子的写作超越了国家和个体,属于本体性写作。这是那时候其他写作者无以比拟的。
我还记得老牛在听完我的陈述之后,沉默了良久,然后拿起量杯,缓缓给我把酒斟满,又给他自己斟满。大概是他忽然想起旁边还有两人,便给老李和姜风一一斟满,才说:“目前我对你的说法暂时不发表任何评论,但有一点我必须要说,那就是,你的这些想法非常独特,对人有启发。你属于思想型的学者。但如果有一些考证,也许你的学术思想会大放光彩。来,干杯!”
老牛最后的建议我一直记着,但是许多年过去,我依然故我,还是喜欢胡思乱想,对于脚踏实地的考证则有心无力。我有时也会因为如《水书》一类的东西胡乱花上一个月而查阅资料,想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最后也不了了之,未曾为其写过一篇文章。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为写一篇文章而专门去考证。我曾经写过一篇孔子的文章,投给一个刊物后,编辑说我的考证还不足,希望进一步考证。且嘱咐我,把《论语》中引文的注释注清楚,注明白是哪个版本、哪个作者、第几版印刷。我听了她的建议也进行了一番考证,但在最后为《论语》里面的常用证而进行注释时,便突然觉得此文章毫无意义了。我放弃了发表。至今,那篇文章还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
结 语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一行四人去寻找老子的飞身之地,一路上争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结果述而不作的老李似乎早已忘记了那些争论,姜风已然投身于国家旅游局的旅游规划事业,对那些事大概也早已忘记。唯有我,怀着好奇心去看了临洮的岳麓山,并花了七八年时间零零星星地写下如斯之言,也不知是否值得。但我相信很少写文章的牛爷在抱着孙子时,如果看到我的这些文字,或许会给我打个电话。事实上,我倒是非常希望他拿起笔来批评我一番。
当然,我在读《道德经》时也会生出一种力量来,这力量是那样积极,它迫使我压住那些心头的火苗,尽可能看上去是以消极的方式来对待这蠢蠢欲动的世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老子的心是火热的、善的,他不希望我们活在烦恼的中心,不希望我们出事。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安静、长寿,像他那样活到一百六十岁或二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