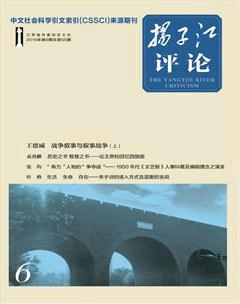现实主义的探索与困境
刘志权
一
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历史命运及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江苏文学创作的传统。坚守这一传承,有时需要付出代价。上世纪50年代江苏的“探索者”群体便是一个例证。而几乎同一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张弦,其努力与命运,与他们可谓殊途而同归。
1956年的张弦,刚完成了从大学生到技术员的转型,几乎还没有摆脱象牙塔的稚气——一种不同流合污的激情、浪漫与理想主义的情怀。这一特点体现在他的处女作、电影文学剧本《锦绣年华》中。剧本既写了爱情方面的矛盾,也写了青年人的创造性与保守主义领导者的矛盾。著名理论家钟惦棐专门在《中国电影》发表了专论《写青年人的和青年人写的——兼评〈锦绣年华〉》,在指出作品生活面不广和“简单化”的同时,高度肯定其真实性:
正因为作者是从生活中获得了这样的主题,而且熟知他所描写的人物,便不是在这些还在成长的青年们中,机械地把他们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作品中所描写到的这些人的缺点,也正是这些人所容易有,所常有的缺点;作品中描写到他们的可爱处,也正是他们实在可爱的地方。
同期创作的小说《上海姑娘》a,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这部小说采用误会法,先是以为白玫只是追求时髦爱玩闹的上海姑娘,却意外地发现是负责自己工地检查的“甲方代表”。她对“我”为赶进度而犯错误的“较真”,形成了小说的另一冲突,最终矛盾解决,“我”也迸出了爱的火花。小说主题算不上深刻,白玫性格的刻画也略显单一;但作者对恋爱的微妙心理刻画细致而含蓄,以及对奉行“人熟为宝”的王技师的塑造和批评,与《锦绣年华》是一致的。
在此后一年内,张弦又发表了《最后的杂志》《羞怯的徒弟》。从内容上看,基本上都是男女因工作相遇,又因为增进了互相了解而逐渐滋生爱情,但又各有不同。《羞怯的徒弟》同样采用了误会法。严厉、喜欢探究的严必胜对羞怯、似乎笨拙而又“软软的顽强”的女徒弟温玉宽一直抱有成见,而直至徒弟不声不响地陪伴他技术攻关并出乎意料地帮他解决了矛盾,他才另眼相看,而几乎是与此同时,“他忽然在胸中激起了一种古怪的、从未产生过的感觉”。这一结尾,与《上海姑娘》的结尾类似,同样体现出浪漫而真诚的双重性。
《最后的杂志》似乎影响不大,情节也并不特别——书店的女营业员喜欢上了每个周末都来看书,并定期买《知识就是力量》的工人。但小说的构思和技巧在50年代却显得比较超前。小说采用双线结构,在波澜不惊的前景,展示了红芬盘点帐目的心不在焉;而背后却隐藏着红芬丰富复杂、充满期待的“意识流”,展现了她爱上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工人的过程——更妙的是,这个工人在整个小说里根本就未登场。这种精巧的“意识流”手法,要在新时期初的一些小说中才能看到,但在50年代,技巧显然并不如主题那样引人关注,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很遗憾地被忽略了。
因此,这一阶段张弦的创作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青春、爱情和理想的关注,而这三者又互相关联:爱情的产生往往源于对主人公优秀品质的体认;着重于爱情产生的过程(与追求理想同步)而非结果。作者很少直接写男女主人公恋爱关系的确立,往往只是留下一个含蓄温情而开放的结尾;二是直面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同时不回避写“有缺点的人物”(如《苦恼的青春》 《上海姑娘》),刻画往往细腻传神,富有生活质感,并不简单脸谱化;三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往往具有一种“较真”的质素。以白玫为例,“较真”貌似个人性格,但其实是技术工作者的工作属性使然。因此也是同为技术员出身的张弦自身所具有的质素。浪漫情怀与白玫式的“较真”的融合与张力,形成了这一时期张弦创作的独特基调;四是注重小说技巧。除了上面介绍过的《最后的杂志》所呈现的技巧之外,他往往能通过多种手段对人物心理尤其是微妙的恋爱心理进行刻画,既质朴简练,又有含蓄委婉的诗意。
当然,衡量现实主义作家是否优秀,更重要的标准在于,作家对社会问题是否有独特的发现和思考。完成于1957年的小说《青春锈》,无疑标志着张弦正在迅速成长和“成熟”。《青春锈》一如继往包含了对青春、爱情甚至婚姻的思考,但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主人公李兰这一人物形象,深入刻画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左倾思想对人性的异化。李兰勤劳朴素,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对组织无限信任和忠诚,但唯独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自我意识,她自觉地在生活、爱情等所有方面,不仅对别人也对自己保持了僵化和刻板的特征。“她的青春却被一层暗淡的阴影笼罩了,失去了应有的光辉,正如闪闪发亮的金属,像上了一层锈”。刘锡诚指出了李兰“左”的幼稚病“这个性格,在五十年代的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作者在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发现。因而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典型。”在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女主人公谢惠敏的身上,有李兰的遗传“基因”。b
因此,《青春锈》的意义还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谢惠敏式的悲剧归咎于“四人帮”,痼疾起码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另一个人物吴慧晴的设置也别具匠心,她一味盲从而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就像李兰放大的影子。“我外婆相信菩萨,碰到什么大小事情,就去城隍庙求签。她根本不懂那纸条上印着些什么,可是她却坚信那上面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同在1957年,茅盾曾给邵荃麟写过一封信,说“一般党员”是“只有两只手,两条腿,两只耳朵,一张嘴巴,而没有脑子”。张弦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切身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并用小说呈现了这一发现。
小说在艺术方面也颇有特色。善于利用场景刻画人物本是张弦的强项,诸如团员们外出郊游,唱歌朗诵的轻松氛围,却每每被注重规矩和主旋律的团支书李兰所破坏,场景之鲜活让人容易想起同时期《春光明媚》等“第四种戏剧”。而值得一提的,还有充分运用了人物的对话乃至(巴赫金理论上的)复调,对立场不同的郭进春还是李兰,作者有意不先下主观判断,而是让双方都有充分的机会陈述、展示自己的观点,人物的行动和思想的变化都遵循着各自的逻辑。
这篇倾注了作者浪漫和真诚思考的作品,本可成为同时期反响颇大的“干涉生活”小说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由于其超越时代的批判,它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发表,张弦也因此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开始了近20年的封笔和颠沛生涯。当这篇小说更名为《苦恼的青春》重见天日时,已经是1980年。由于既错过了“双百”的黄金时期,也错过了“伤痕”的高潮,它并没有给劫后的张弦带来应有声誉。
二
命运的挫折没有让张弦变得消沉。1979年,张弦以电影剧本《心在跳动》、小说《记忆》 《舞台》宣告重归文坛,汇入了当时“伤痕文学”的主潮。他的短篇小说《记忆》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接连获得1979和1980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到1986年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焐雪天》后彻底转向影视,他共创作了21篇小说。c
漫长时期的坎坷经历,洗去了张弦早期“浪漫”中简单化或者耽于唯美幻想的成分。在青春、理想与爱情的三元素中,张弦首先完成了对青春与理想的思考。与当时作品中习见的怨尤不同,他更多选择了宽容和向前看的积极姿态。《记忆》中,宣传部长秦慕平因为自己的主观主义,造成了一个姑娘坎坷的命运,当他劫后想要向这个青春不再的受害者道歉时,对方却已经预先原谅了他。《舞台》中,演员薛兰菲在最富于创造力而艺术上臻于成熟时,却被运动夺走了她最宝贵的青春。等到她重返舞台时,却发现了岁月不再的残酷现实。但是,“难道探索永葆青春的秘密,对于处在人生晚秋时刻的我们,不是个更迫切更有意义的课题吗?”最后她终于解开心结,将机会让给了起飞阶段的徒弟。
而“浪漫”的另外一个内核——爱情,在经历了长期沉淀并融入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之后,成为了张弦创作的核心特色。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当代文学史不能忽略的小说。存妮与同村青年小豹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蒙昧的年代,被青春之火驱使着,做出了“丑事”,酿成悲剧。也因此使妹妹荒妹封闭了少女的内心世界。而等待她的,却是“把女儿当东西卖”的包办婚姻。但时代的契机,终于使荒妹冰结的内心世界开始复苏。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探讨了“极左”的僵化和粗暴,几代妇女的命运悲剧,以及“贫穷”所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蒙昧的现实。多元的主题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张力,在1980年尤其振聋发聩。
之后的张弦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又连续发表了《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小说,“几乎每一篇作品和文学读者见面,总是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耐人寻味的东西”。d有论者认为,“张弦作为一个文学家,如果只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三篇中篇小说,就足以奠定他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不被人替代”。e
据作者自述,小说《未亡人》是被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种无可救药至死不渝的爱所打动,因此起初是想写一篇书信体小说。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习惯性思考,使小说改变了最初的路向:“寡妇”周良蕙,决意放弃一切,与一直关心她的邮递员相爱,但因为她曾经是“书记的女人”,因而遇到的社会性阻力超出了她的想象。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口喊出:“难道要我也关上电灯去摸索那一百个泪血斑斑的‘贞节钱吗?”“为什么共产党员不以破除反而以恪守封建道德为荣?为什么要把我的幸福锁在令人尊敬的骨灰盒里?”这依稀是“五四”时期“我可以爱”的呼声。
《挣不断的红丝线》中,年轻的傅玉洁怀着浪漫的理想,拒绝了齐副师长的示爱,选择了有才气的苏骏。但现实生活却先摧毁了丈夫苏骏的浪漫与才气,继而也就摧毁了她的意志。在与丈夫离婚后,她终于选择了重续能给她带来现实好处的婚姻。整个小说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伤逝》,包括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当时我过得充实,因为我怀着希望。当然,现在想来是虚妄的。但如果他不把严酷的现实带到我生活里来,我并不知道这虚妄,那么我依然可以充实地过下去……”结论其实也是一样的:没有充分准备的反抗很难做到彻底和坚强。
《银杏树》同样耐人寻味。记者下乡时发现了一个现代陈世美的故事,并通过权力帮助被进城丈夫抛弃的农村姑娘孟莲莲实现了其愿望:和负心丈夫结婚。意味深长的是,记者原以为这个强行结合的婚姻不会幸福,但结果却正好相反,孟莲莲却对现状心满意足。孟莲莲并非传统意义上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而是80年代语境下的小学代办教师,但即便对她而言,正当婚姻之必须的意义,也超过了爱情本身。这一现实无疑在提醒我们,封建意识对妇女的禁锢超出了我们的一般估计。
由于对张弦这样的“文学史作家”,已有颇多真知灼见,可以结合已有成果对他这一阶段的小说成就作以下小结:
一是基于现实主义对生活的深度开掘。他的爱情题材小说,续接了五四传统,远离了习见的轻浮甜腻的误区,落脚于一个个沉重的“问题”。首先,张弦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他所致力的,是在人的命运的交织和对比中,从不同侧面探索和揭露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对我国社会生活的侵害。”f其次,他给当代文学史提供了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除了沈荒妹外,无论是周良蕙、傅玉洁还是孟莲莲,都具有各不相同的典型意义。
二是基于爱情婚姻题材的多维度探究。这一题材是张弦小说最为外在的标志,也与作家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他九岁丧父,和母亲、姐姐、祖母生活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自然会更加懂得女性,理解她们的痛苦和愿望,这大概是我偏爱女性题材的重要原因”。g王蒙曾将张弦的小说人物形象越过“女性”而放大到“善良的弱者”,可谓知人之论。究其成功的原因,首先是他往往将爱情置于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以及历史现实之中进行深度思考。翁睦瑞指出,“张弦剧作和他的短篇小说一样,主要描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横断面。但是,他擅长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和表现这些横断面,即把现实与过去、将来联系起来写”。他将之命名为“联纵写横”的手法。h其次,张弦着眼于“爱情”的悲剧。在他笔下形态各异的女性人物身上,体现的不只是女性和历史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张弦的这些小说正是因此呈现出令人注目的多面性和深刻性——这正是鲁迅通过有限的女性小说所开创的小说传统。90年代丁帆等在总结新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时指出:“新时期之初,张弦对存妮、周良蕙、傅玉洁、孟莲莲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创造,鲜明集中地显示出主体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主流文学中形成的妇女解放主题的回归与承继,映现出创作主体的一种拯救的精神姿态。”i这正是张弦的女性小说的文学史价值所在。
三是独特的审美风格及艺术特色。张弦一贯追求精心构思,这也是其作品少而精的重要原因。他的作品呈现出主题的丰富性、多面性、多义性特点,这与他从来不把人物简单化和脸谱化的追求相关;而作为一个双栖作家,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其电影与小说相互借鉴的技术特点。如贺国璋着重指出其小说创作近景远景的场景框架、“戏剧核心”、悬念、突转等手法、螺旋式的回复的内心冲突以及精心设计的“道具”等。j倪震也认为,“张弦在小说创作的结构上,显示出电影般的时空跳跃及段落分切,从而使小说的叙事结构大幅度地省略,简洁化,使得小说非线性状态地发展,使得一篇本来可以很长的中篇小说,在张弦手中恰恰变得很短。……这种省略,我想,得益于电影的营养”。k在总体风格方面,王蒙将其风格总结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平而不淡,深而不艰,情而不滥,思而不玄,秀而不艳,朴而不陋,这就是张弦的风格,这就是张弦的节制,这也恰恰是张弦的局限性”l。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张弦的关注和研究跟进也较为“即时”。早在1981年,日本便转译了关于《记忆》的国内研究m,此后对《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遗愿》 《挣不断的红丝线》等作品都进行了研究n;还出现了系统研究张弦的学者,如岩佐昌暲便发表了张弦的从年谱、传记到专论等许多论文。整体看,相对国内,日本研究更关注新的历史情境中张弦的创作身份与姿态。他们的研究较之国内研究,未必见得更为深入甚至正确,但“细读”向来是日本研究的特点所在,不同文化、政治语境的“他观”,客观上丰富了张弦的研究。
三
创作生涯的高起点和鲜明独特的风格印记,对作家而言向来是一把双刃剑。作家除非躺倒在既定的成功上不思进取,否则,要摆脱既有的“标签”,势必要付出双倍的努力。王蒙在《善良者的命运》一文中,就在高度肯定张弦创作的同时,期望张弦拓展创作新路。正是基于这点,他表达了对张弦《一只苍蝇》(1980)的偏爱和对《春天的雾》(1982)新尝试的关注。前者通过劫后总工程师肖士钧家宴上的一个不速之客,辛辣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者的丑态;后者则是当下的改革题材。
张弦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地应对。其实之前他也偶有其他尝试。如历史小说《最后的恩赐》(1980)写明朝开国功臣徐达背疽未愈,被朱元璋赐蒸鹅吃死,徐达洞晓太祖用意,临死前却遗嘱严令子孙效忠皇上。小说很好地传承了60年代初《陶渊明写“挽歌”》等历史小说以古讽今的传统。但这一尝试并未继续。1984年,他在给鲁枢元的信中曾经说:“《伏尔加》写得匆忙,我自己不大满意,我有个想法,就是尽量写一点‘真实的短篇,改一改自己过去的路子。自去年的《热雨》以来,都在作这方面的尝试,效果如何自己也拿不准。”o“过去的路子”,当然是指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为代表的小说。
“改”的努力,体现在张弦1983年之后的小说创作中。以《热雨》与《伏尔加轿车停在县委大院里》为代表,探索主要分为两个路向:一类是从平淡的日常生活写平凡人的喜怒哀乐,张弦充分发挥了他擅于心理分析、文字含蓄纤秀的特长,同时也包含着对社会现象或某类人群的批判。如《遗愿》 《绿原》 《临街的窗》 《浅浅的游泳池》等。被作家视为新尝试的《热雨》(1983),不再着眼于尖锐的对抗与批判,而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大龄青年。作者用细致绵密的写实手法、丰富传神的心理描写,以及所擅长的清新含蓄的笔触,真切地写出了大龄青年男女所处的社会氛围以及他们的心理,即便在今天依旧没有过时。第二类则是关注“改革”这一时代主题,如《春天的雾》《绿原》《伏尔加轿车停在县委大院里》,以及《焐雪天》(1986)等。《春天的雾》中,一边是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正在走下坡路的、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厂,一边是朝气蓬勃、待遇优厚的新厂和老朋友的盛情邀请,被退休的老印刷专家高松友,最终还是选择了回老厂“尽义务”;《绿原》中,通过女性对年轻的体制内大学生与自食其力的个体经营者之间的爱情选择,鲜明表明了抑前者而扬后者的立场;《焐雪天》则写改革时代,“能人”是怎样凭着手中的金钱的力量为所欲为,并扰乱了平民乃至政府工作人员原有的正义感的。与当时喜欢写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意气风发的时代变迁不同,张弦的这类小说,还是小处入手,贴着人物写出了改革过程中普通人的各种心理变化,保持着他自己的风格特点。
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界的各种新潮已经风起云涌。张弦的知识结构以及生活经历的独特性,使他与各种现代主义思潮、电影领域的写意化散文化等趋势,都保持了距离。如果跟同龄的王蒙比照,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张弦的小说《八庙山上的女人》,写一个刚退居二线的副部长刘刚回他当初打游击的地方看望当初救过他而且与他发生过爱情的女人。这一题材似乎有当时新历史小说的影响,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王蒙的《蝴蝶》。但《蝴蝶》采用了丰富的意识流、复杂的时间穿插技巧,呈现了开阔的历史与人生体验,其题目“蝴蝶”本身也是具有一定哲理内涵的意象;与之相比,《八庙山上的女人》则“朴素”得多,它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线索加上适当的倒叙,穿插了传统的心理描写,通过开端、发展、高潮层层推进,最后,在突转式的结尾(刘刚满足于各方的接待而最终放弃了与当初的腊梅妹子的见面)中,完成了对某种人物类型的批判。
这种对比呈现出张弦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些客观不足。首先,他的小说对社会生活的涉及面不够广——相对于宏观的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他更钟情于生活中的一个个小小的片断。其次,他倾情于社会问题,但他缺少像王蒙或张贤亮那样的思辨力度和文化历史层面反思的自觉。促使他的《在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小说成功的,正在于他把当下的问题楔入到了历史和文化的深层;但当他的探索转向当下时,这种深度和宏阔程度并不能始终保持。
也许张弦1987年之后转向影视部分源于小说创作的困境。当然,他敏锐地意识到,电影作为文化工业产物,正在经历大众化和娱乐化的历史转向。但事实上,张弦在影视方面的成就依旧系于“现实主义”。倪震认为,张弦在文学上属于1957年的一代,属于归来者的一代,如王蒙、从维熙等;而在电影创作上属于第四代,即吴贻弓、黄蜀芹、谢飞、张暖忻等一代。而这一代,是人道主义的一代,感伤的一代,祭奠青春的一代,怀念失去美好的一代。p这种看法是成立的。张弦的真诚、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和探索、对社会问题持久的关注、对人生和人性的思索,既有个人的性格特征,也带着那一代人特有的气质,同时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气质。这是张弦,乃至他们那一代大多数人的“宿命”。
当然,现实主义在80年代后期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其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更何况文学的发展本是一代代作家积累推进、螺旋上升的过程,张弦们探索的意义已经融汇在这一过程之中。在张弦之后,当代江苏男性作家,如苏童、毕飞宇等,在女性写作方面的成就都为文坛公认,即便中间没有直接的影响,也召示着一种值得关注的地域文学现象。
对张弦的关注并没有随时间而消失。新世纪以来,张弦依旧在诸多评论研究以及各种文学史版本中出现,同时不乏从新的视角进行再解读乃至批评之作。如何言宏从知识分子心理结构角度重读《记忆》q;再如葛红兵和吴培显分别从性别政治角度以及“历史发展/历史进步的悖谬”角度解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r等。对张弦而言,其作品能够被几代研究者持续地解读,本身就证明了其所坚守的现实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a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发表时,被改名为《甲方代表》,1957年收入中国作家协会所编的《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重新改名为《上海姑娘》。从小说名字的改变,也能看出时代对浪漫情怀的规训与制约。
b刘锡诚:《独创的艺术——评张弦的小说》,《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2期。
c张弦1987年还有未完成的中篇小说《情网》,去世后由家属整理发表于1998年《中国作家》增刊。
d吴亮:《张弦的圆圈——评〈回黄转绿〉和〈银杏树〉》,《上海文学》1982年第7期。
e倪震:《在张弦电影作品研究会上的发言》,《张弦文集·电影卷》第38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f胡永年:《努力探究生活的底蕴——读张弦的几个短篇小说》,《人民日报》1980年12月3日版。
g张弦:《与意大利学生的通信》,《张弦文集·小说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h翁睦瑞:《凭独创的作品开始他的事业—谈张弦电影剧作的现实主义特色》,《电影文学》1983年第10期。
i丁帆、陈霖:《略论近年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种“他塑”》,《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
j贺国璋:《张弦短篇小说的戏剧性浅释——读小说集〈挣不断的红丝线〉》,《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k倪震:《张弦电影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张弦文集·电影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l王蒙:《善良者的命运——谈张弦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m郑万鹏著,荒冈启子译:《张弦作〈记忆〉赞》,[日]《野草》1981年4月27号;[日]高岛俊男:《文革后文学的新阶段——张弦〈记忆〉提出的问题》,见《于无声处听惊雷——“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文学》,日中出版社1981年版(据称1979年8月开始在《日中友好新闻》上刊登)。
n [日]楠木纪子:《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早稻田文学》1983年7月第86期;[日]井口晃:《张弦的短篇小说〈遗愿〉》,《中国语》1983年11月第886期;[日]千野拓政:《深奥的“爱”的故事——张弦〈挣不断的红丝线〉》,《东方》1984年5月第38期。
o该信收入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心理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304页。
p参见倪震:《张弦电影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张弦文集·电影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q何言宏:《为何要鼓吹遗忘》,《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r葛红兵:《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